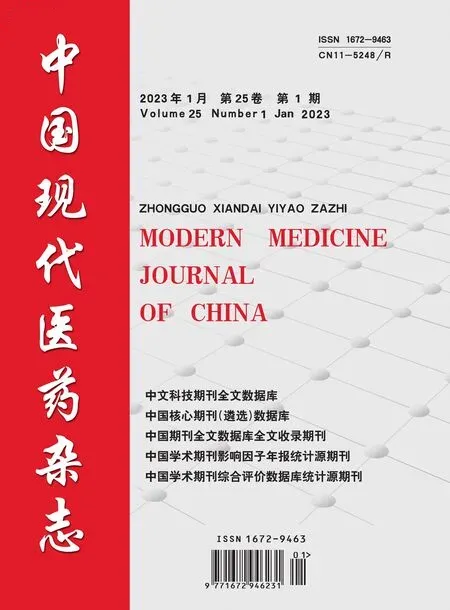藏藥紅景天提取物絡塞維緩解阿爾茨海默癥病變相關研究進展
劉航 馬艷冬 李巖松 張澤宇 李沙弟 石鏡明
阿爾茨海默癥(Alzheimer disease,AD)是老年性癡呆癥中最常見的形式,其嚴重危害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給許多家庭及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和護理負擔[1]。AD 患者腦部主要的病理變化是β-淀粉樣蛋白(Amyloidβ-protein,Aβ)形成神經炎斑在胞外沉積以及tau 蛋白磷酸化引起胞內產生神經纖維纏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2]。AD 的發病機制仍不明確,但在理論和臨床研究中,β-淀粉樣蛋白在腦內異常聚集被認為與AD 的發病具有相關性[3],該蛋白來自其前體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經過β 和γ 分泌酶分別在膜外和膜內水解產生以40 和42 個氨基酸為主要形式的短肽(簡稱Aβ40 和Aβ42),Aβ42 可溶性寡聚體在AD 發病過程中發揮著更關鍵的毒性作用[4,5]。
盡管AD 危害很大,但治療AD 的藥物開發卻較緩慢,一些針對Aβ 的藥物進入臨床Ⅲ期試驗,其中一部分屬于清除中輕度AD 患者腦中Aβ 單體、纖維和可溶性寡聚體的抗體,如Aducanumab、Crenezumab、Bapinezumab、Solane-zumab[6,7],以及抑制β 和γ 分泌酶活性的小分子物質,如CNP520、Atabecestat 和Verubecestat(APECS)等[8,9],然而這些藥物均未能改變患者認知能力或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分析以上致力于減少甚至清除人腦中各種Aβ 形式的臨床試驗不能改變患者癥狀的原因可能為:①大多數失敗的第Ⅲ階段試驗藥物針對臨床中間階段的AD 患者,但在臨床癥狀出現前15~20年Aβ 引發的病理過程已經在AD 患者大腦中積累,此階段實際上是生物疾病的晚期[10]。②Aβ聚集體直接損傷神經元胞體或突觸導致神經元喪失的理論過于簡單,因為Aβ 的積累是開啟病理過程的關鍵,而其引發的下游事件,如神經炎癥、氧化性損傷、神經元線粒體損傷和多種信號傳導途徑等才是神經退行性病變的主要驅動因素[11]。
1 神經退行性病變的主要原因
在AD 患者臨床癥狀出現后再設法減少或消除患者腦中Aβ 的藥物很難改變其認知能力或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因為Aβ 聚集引發后續的神經炎癥、氧化性損傷以及神經元線粒體損傷等多種病理反應是導致神經退行性病變的主要原因,這是一個持續、積累、相互促進的過程。
1.1 神經炎癥中樞神經固有免疫反應引發的神經炎癥在AD 的發病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AD 患者的大腦表現出持續的神經炎癥反應[12],這些神經炎癥在輕度認知障礙者(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早發性AD[13]以及AD 患者腦組織中均可出現。究其原因,在斑塊形成早期,淀粉樣前體蛋白裂解產生的Aβ 形成聚集體,吞噬這些聚集體可導致小膠質細胞被激活從而釋放多種促炎細胞因子和毒性產物增強神經炎癥反應,包括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一氧化氮、白細胞介素-1β(IL-1β)、IL-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等,這些細胞因子將招募更多的小膠質細胞進入淀粉樣神經斑中導致淀粉樣斑增長,再加上AD 發病過程中Aβ 不斷產生引起持續的免疫應答,從而轉變為慢性神經炎癥[14],除小膠質細胞外神經元自身的細胞因子也會發生改變,包括CD22、CD200、TREM2[15]。小膠質細胞產生的IL-6 還可以導致高磷酸化tau 激酶CDK5 的激活,從而促進神經元胞內產生NFT[16,17]。因此神經炎癥反應不僅與神經退行性病變相關,同時也加劇了淀粉樣斑的形成和NFT 病理改變。
1.2 氧化性損傷除神經炎癥外,ROS 和活性氮自由基(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RNS)產生的氧化性損傷也是導致神經退行性病變的重要原因,Aβ42低聚物插入質膜的脂質雙層后,Aβ42 肽的蛋氨酸-35(Met-35)殘基的單電子產生氧化引發脂質的過氧化,促進活性ROS/RNS 的形成,從而放大了Aβ42 引發的毒性,金屬離子在與Aβ 結合時可以催化ROS 的生成,特別是最具反應性的羥基自由基(-OH)的產生[18]。這些自由基將導致MCI 和AD 患者腦內葡萄糖代謝降低、mTOR 激活、蛋白質穩態改變、tau 蛋白質磷酸化改變、細胞核及線粒體內DNA 突變、小膠質蛋白體功能紊亂、星形膠質細胞活化、神經炎癥和細胞死亡[19]。有研究認為Aβ是由氧化應激誘導的產物,氧化應激是先于Aβ 的事件,更多的Aβ 產生后又將引起更劇烈的氧化應激反應,從而形成“氧化應激?Aβ 產生”的惡性循環[20]。總之,氧化應激損傷細胞和線粒體的脂質、蛋白質及核酸,從而導致神經退行性病變,加劇AD 的進展。
1.3 神經元線粒體損傷線粒體功能障礙是導致AD 神經退行性病變的又一重要特征[21]。線粒體通過氧化磷酸化產能以維持機體新陳代謝,Aβ寡聚體產生毒性將導致氧化磷酸化受損并產生ROS,包括O2-、-OH 及H2O2等,過量的ROS 將損傷線粒體DNA 和細胞核DNA,從而影響線粒體通透性轉運孔的激活,導致線粒體功能障礙,如細胞內Ca2+調節紊亂、ROS 的產生、促凋亡因子的釋放和線粒體形態的損傷[22]。此外,Aβ寡聚體進入線粒體內,導致細胞色素C 從線粒體內、外膜之間釋放到細胞質中與Apaf-1 結合[23],激活Caspase 9,活化死亡執行因子Caspase 3,通過蛋白酶水解最終導致細胞凋亡[24]。該途徑可被各種抗凋亡因子包括Bcl-2 蛋白抑制[25]。
神經退行性疾病AD 的發病雖然與Aβ聚集相關,但其病理機制復雜多樣,這些病理變化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關聯,神經炎癥可引發氧化損傷,而氧化損傷與神經元線粒體損傷相互促進,其出現在MCI 及AD 各階段。事實上,抗炎、抗氧化以及阻礙神經元線粒體損傷已成為最新的藥物研發方向[26]。
2 絡塞維防治阿爾茨海默癥的機制
現階段,神經退行性疾病的臨床治療主要以改善神經元生存和維持神經元突觸活性為主,無法從根本上達到預防和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目的[7]。藏醫具有龐大的藥物體系,部分藏藥具備抗氧化、抗炎和線粒體修復等神經元保護功效,篩選并挖掘藏藥可能為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治療提供候選藥物。紅景天是傳統的民間醫藥,研究顯示,紅景天根莖提取物具有抗腫瘤、保護神經和抗缺氧功能[27,28],其活性成分主要包括酚類物質紅景天苷及絡塞維[29,30]。其中,紅景天苷的神經保護、抗氧化、抗炎以及線粒體修復作用得到了較多研究[28,31]。而紅景天另一重要活性成分—絡塞維,分子量僅為428.4,其結構為多羥基酚類物質,具有很強的抗氧化能力。近年來絡塞維提取、純化以及藥理作用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絡塞維具有抗氧化和抗炎能力[27,32],并且可以提升小鼠海馬神經元LTP,在高濃度時其藥效超過紅景天苷[33],絡塞維和鋅的混合性藥物可以增加類風濕性關節炎大鼠抗炎細胞因子的表達[34],在小鼠實驗中采用3%絡塞維與1%紅景天苷的單劑量藥物,具有抗抑郁、提高適應活性、抗焦慮的作用[35]。由此可見,絡塞維作為紅景天提取物中的一種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和改善神經的作用,推測可能在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治療中具有較好的功效,且符合AD 治療藥物篩選的新方向,檢測紅景天提取物絡塞維潛在的抗神經元凋亡、抗氧化、抗炎以及抑制線粒體損傷的能力并探索其具備這些能力的分子機制,從而評估其可能作為AD 治療藥物的潛力。
3 絡塞維防治阿爾茨海默癥的優勢
絡塞維與紅景天苷相比,可能更加適合作為防治AD 藥物,原因為:①紅景天苷的相關功能已研究較多,而絡塞維同樣具備相應的作用,但在神經退行性疾病防治中的研究較少,近幾年得到較多的重視;②研究顯示,絡塞維在大鼠靜脈注射后半衰期為(5.5±1.3)h,灌胃給藥的半衰期為(11.6±2.7)h,在血漿中存在時間較長[36]。而紅景天苷口服吸收差,大鼠口服給藥生物利用度僅為32.1%且半衰期僅為0.74h[37,38]。從藥物代謝方面考慮,絡塞維明顯更具優勢;③有研究顯示絡塞維可以抑制Jurkat 細胞中TNF 相關凋亡誘導配體的表達,而紅景天苷此活性較弱,提示絡塞維抗細胞凋亡活性優于紅景天苷[39]。因此,絡塞維比紅景天苷更加適合作為AD治療藥物。
綜上所述,AD 主要病理變化包括氧化性損傷、炎癥以及線粒體損傷等神經退行性病變,以絡塞維為代表的藏藥單體可以緩解這些癥狀,絡塞維的相關功能可改善AD 的神經退行性病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