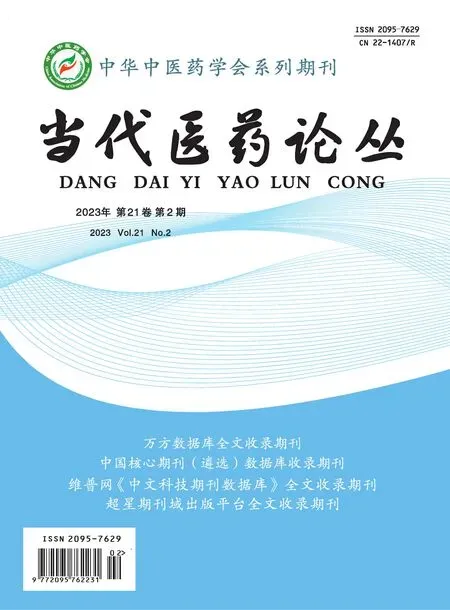肝細胞癌診斷的研究進展
陳 龍,潘光棟
(1. 桂林醫學院,廣西 桂林 541199 ;2. 柳州市人民醫院,柳州市肝癌研究重點實驗室,廣西 柳州 545001)
原 發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PHC)是位居我國惡性腫瘤發病率及致死率前列的一種消化系統惡性腫瘤。PHC 根據病理類型主要分為肝細胞 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 內 膽 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 以 及 肝細胞和膽管的混合細胞癌(HCC-ICC),其中HCC 占PHC 的85% ~90%[1],其與ICC 和HCC-ICC 的治療有所不同。HCC 缺乏早期特異性臨床表現,起病隱匿,惡性程度高,進展快,治療難度大,患者預后差,復發率高,嚴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健康。由于HCC 缺乏特異性臨床表現,腫瘤呈隱匿性發展,因此當患者出現臨床癥狀至醫院檢查時,其病情多已處于中晚期,導致早期診斷率低,治療難度大,預后不佳。而HCC患者盡早診斷及治療是延長其生存時間的關鍵措施。因此,研究HCC 的診斷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對HCC 的診斷方法進行綜述,以期為臨床實踐提供參考依據。
1 HCC 的診斷
HCC 的診斷有病理學診斷及臨床診斷兩種,前者是根據HCC 患者的組織病理學檢查做出的診斷,后者是根據HCC 患者的影像學檢查及血清學分子標志物檢測做出的診斷[1]。
1.1 腫瘤標志物
腫瘤標志物是指由腫瘤組織或細胞產生的一類特異性物質,其在患者血清中超過一定數值時則提示機體內可能存在腫瘤,可用于輔助診斷惡性腫瘤。近年來隨著免疫學、生物分子技術的不斷發展,HCC 腫瘤標志物的診斷技術也在不斷發展,為HCC 的診斷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也成為臨床診斷過程中有參考價值的輔助手段。
1.1.1 基因相關標志物 原癌基因提供的正向調控信號及抑癌基因提供的負向調控信號共同調控正常細胞的增殖和成熟,這兩類信號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互相制約,形成一種動態平衡,當這種動態平衡被破壞時就可能導致腫瘤細胞的產生。有研究顯示,PTEN 基因、p53 基因、IGF-2 基因、c-myc 基因、ras 基因等多種致癌基因參與了HCC 的發生、發展,同時這些基因可作為肝癌診斷的特異性分子標志物[2-3]。DNA甲基化是在DNA 甲基轉移酶的介導下,催化S- 腺苷蛋氨酸為甲基供體,將甲基基團轉移到DNA 某些堿基上的過程。有研究發現,RAS 相關結構域家族1A(RASSFlA)、谷胱甘肽硫轉移酶Pl(GSTPl)、p16、SEPT9 等異常甲基化基因與HCC 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系,或可作為HCC 診斷的標志物[4-5]。研究顯示,長 鏈 非 編 碼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微小RNA(miRNA)等在正常細胞中參與基因轉錄、細胞內轉染等,也與細胞的癌變有著密切關系。近年來的一些研究表明,相較于健康人群,miRNA、lncRNA 在HCC 患者中呈顯著高表達[6-7]。miRNA、lncRNA 或可作為HCC 診斷的標志物,但將其應用于HCC 的臨床診斷中有待于更多大樣本的臨床研究來驗證。
1.1.2 蛋白質標志物 甲胎蛋白(AFP)是一種糖蛋白,屬于白蛋白家族。自1980 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血清AFP 作為診斷HCC 的生化指標以來,其一直是公認的HCC 診斷的特異性標志物。在我國,AFP 是唯一應用于HCC 臨床診斷的血清標志物,因為大約一半的HCC 分泌AFP[8]。AFP 濃度高于400 ng/mL 通常被認為是診斷HCC 的可靠元素[9],但同時需要排除急慢性肝炎、肝硬化、生殖系統的畸胎瘤以及妊娠等情況。但臨床上部分HCC 患者體內的AFP 水平不高,AFP 檢測的靈敏度和準確性均未達到理想水平,因此需要尋找其他的腫瘤標志物來彌補AFP 診斷HCC 的不足。人異常凝血酶原(PIVKA- Ⅱ)是由維生素K 缺乏或拮抗劑Ⅱ誘導產生的蛋白質,其在HCC 患者的血清中有較高的表達水平。自Liebman 等[10]首次發現約90% 的HCC 患者其血清中含有PIVKA- Ⅱ后,PIVKA- Ⅱ就被逐漸應用于HCC 的診斷中,同時還用于評估HCC 患者的治療效果、預后、復發風險等,近年來更被多個國家列入臨床推薦指南[11-12]。Li 等[13]對AFP 及PIVKA- Ⅱ診斷HCC 的相關研究進行meta 分析顯示,PIVKA- Ⅱ診斷HCC 的靈敏度優于AFP。同時Park等[14]研究表明,PIVKA- Ⅱ和AFP 聯合檢測對HCC早期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均優于這兩項指標單獨檢測。AFP 有AFP-L1、AFP-L2 和AFP-L3 等3 種 異質體。但AFP-L3 比較特殊,其僅由HCC 的腫瘤細胞產生,其百分含量越高提示HCC 的惡性程度越嚴重,也是HCC 的特異性標志物之一。AFP-L3 用于診斷HCC 的特異度較高,而在良性的慢性肝臟疾病中,肝細胞不表達AFP-L3,因此該指標還可用于區分HCC與肝炎[15]。其他蛋白質標志物如Wnt 通路抑制因子1(dikkopf-1)、α-L- 巖藻糖苷酶(α-L-fucosidase,AFU)、骨橋蛋白(osteopontin,OPN)、蛋白多糖3(glypican-3,GCP3)、γ- 谷氨酰轉移酶(GGT)等也逐漸應用于HCC 的診斷中。多個蛋白標志物聯合檢測可以彌補單一標志物診斷HCC 靈敏度或特異度不高的缺陷。
1.2 影像學診斷
1.2.1 超聲檢查 超聲檢查因具有無輻射、費用低、可多次重復檢查等優點,常與AFP 檢測聯合應用,作為HCC 初篩及診斷的常用手段。超聲檢查的缺陷是圖像質量易受到肋骨及肺組織偽影的影響,部分位于檢查盲區的病灶難以觀察到,檢查結果的準確性及真實性易受到多種人為因素的影響等。
1.2.2 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成像(CT) CT 檢查不易受骨骼或氣體的影響,圖像較超聲檢查也更為清晰。CT 檢查不僅可以顯示不同期肝臟病灶密度的變化,還可清楚地顯示HCC 病灶的具體大小、數目、腫瘤血供情況等。同時CT 檢查對于門靜脈是否有癌栓、肝周淋巴結是否發生HCC 轉移等都具有重要的診斷價值[16-17]。
1.2.3 磁共振(MRI) 磁共振成像技術因具有可重復操作、無創、無輻射等優點,廣泛應用于HCC 的臨床診斷中。臨床實踐證實,用磁共振成像技術診斷HCC 具有較高的特異性與準確度。
1.3 活檢技術
1.3.1 穿刺細胞學(FNA)診斷技術 當經影像學檢查無法確定肝臟占位病變的性質時,還可通過穿刺活檢獲得明確的病理診斷。肝占位穿刺活檢可明確占位的性質、分子分型等[18]。
1.3.2 液體活檢技術 液體活檢技術具有非侵入性、可重復操作、樣本獲取方便等優點[19]。該技術可用于輔助HCC 的臨床診斷、監測腫瘤發展情況及患者預后等。目前用于診斷肝臟疾病的液體活檢指標主要有血漿細胞外囊泡(EVs)、循環游離DNA(cfDNA)、游離非編碼RNA(Cell-free non-coding RNA)等[20]。但液體活檢技術因其成本較高、缺乏統一標準和操作流程等缺點,在臨床上應用較少,尚需繼續研究和發展。
2 結語
HCC 的惡性程度高、手術切除機會少、致死率高、治療效果差,而盡早明確診斷是提高HCC 患者存活率、降低其死亡率的關鍵措施。目前有多種腫瘤標志物及影像學技術可用于篩查HCC,但單一的腫瘤標志物檢測或影像學檢查其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均較難令人滿意,而聯合應用多個腫瘤標志物及影像學技術可有效提高HCC 診斷的敏感性及特異性。但準確性高、易檢測、費用低廉的HCC 診斷方法尚需不斷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