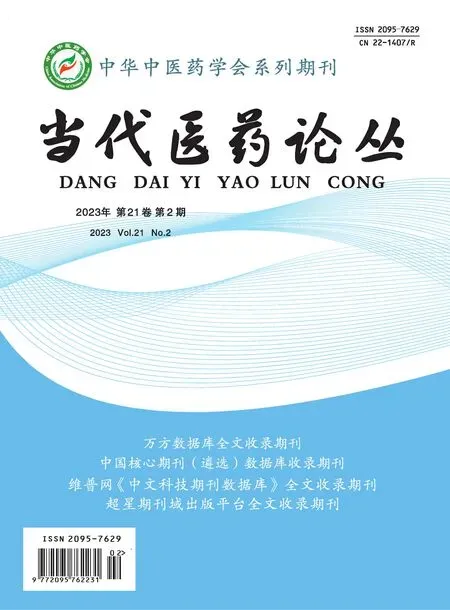從脾論治消瘦型2型糖尿病
祝雯莙,冉穎卓
(1. 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00 ;2.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南京中醫院,江蘇 南京 210000)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中國成年人群中的糖尿病患病率在快速增長,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1]。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在確診時,其胰島β細胞功能已經下降了二分之一[2],與肥胖患者相比,消瘦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細胞功能更差[3]。
消渴是指以多飲、多尿、多食及消瘦、尿甜為典型表現的疾病。《素問·奇病論》中最早出現消渴之名,《金匱要略》首先提出其治法。《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一書中有“肺消癉”醫案記載,可視為本病最早的病案記錄。本病名稱眾多,除“消渴”外,還有“消癉”“肺消”“膈消”“消中”等名稱,這是消渴病根據病位、病機及癥狀不同之稱謂。消渴從脾論治之說始于唐、宋,到了明清之際才逐漸成熟,此后歷代名醫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與分析。此后各大醫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討論分析。當今在臨床上所見到的糖尿病患者普遍肥胖,一般無典型消渴病“三多一少”癥狀,但人們在對肥胖癥與糖尿病患者的關注度相對較高的同時, 也不能忽略消瘦型糖尿病患者。
一般情況下,葡萄糖是人體最重要的能量來源。然而,在胰島素缺乏或胰島素抵抗的糖尿病患者群體中,身體不能吸收和使用足夠的葡萄糖,不得不分解脂肪和蛋白質來獲取能量,導致消耗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質,從而使患者變得更加消瘦。同時,因為患者的血糖隨著尿液流失,導致身體失去了太多的熱量和水分,從而開始日益消瘦,長此以往就有可能導致患者產生身體疲勞無力、營養不良、抵抗力下降等問題。有調查指出, 與BMI 為20 ~24.9kg/m2的人群對比,體重過低人群患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增加了30% ~40%[4]。亦有數據表明,在確診為罹患肺動脈高壓的退伍軍人中,存在糖尿病和較低體重情況的患者其死亡率明顯增加[5]。錢衛沖等[6]的研究表明,體重指數過低是死亡率增長的高危因素之一。
1 從脾論治糖尿病的理論基礎及臨床應用
消渴的典型癥狀為“多飲、多食、多尿、消瘦”,核心病機為 “陰虛燥熱”。隨著現代飲食、生活方式和體質改變的日漸影響,傳統的三消辨證論治已經不能很好地適應糖尿病患者的辨證論治,“脾虛致消”和“肝郁致消”理論近幾年來被人們廣泛接受。
仝小林院士對《內經》中“脾癉”和“消癉”的相關論述進行了深入解讀,從而確定了脾癉或消癉是消渴的前期[7],并將其劃分為肥胖型(脾癉)和消瘦型(消癉)[8]。此二者病因、發病特點和預后有一定差異,但隨病程發展而轉入消渴階段時,其主要病機及其之后的病程發展則歸于一致。消瘦型糖尿病顯著特點為消瘦,此類型患者普遍體質偏虛,整個發病過程不會出現肥胖,按西醫學標準來分,包括1 型糖尿病和部分2 型糖尿病。“消癉”之名,首見于《黃帝內經》。《說文解字》將“消”譯為“盡也,從水”,將“癉”釋為“勞病也,從疒”,意為水液消耗性疾病。消中者,“善食而瘦”。《類經十六卷》中張介賓云:“消癉者,三消之總稱……而肌膚消瘦也。”可見“消癉”的臨床特征是多食、肌膚消瘦等。在糖尿病范圍內來說,消癉與現代臨床的消瘦型糖尿病有很多相似之處,因而也可把消瘦型糖尿病歸屬于消癉一類。
1.1 從“消癉”認識消瘦型2 型糖尿病的病因
1.1.1 稟賦不足 《靈樞·五變》曾云:“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張志聰《靈樞集注》曰:“蓋五臟主藏精者也,五臟皆柔弱,則津液竭而善病消癉矣”。先天氣血虧虛,稟賦不足,致后天失養,而脾之運化,化生氣血,有賴于先天的溫煦。加之內熱傷陰,陰津虧損,臟腑失于濡養,而見形體消瘦。
1.1.2 內熱熾盛 《靈樞·師傳》指出:“胃中熱則消谷,令人懸心善饑”。《素問·氣厥論》中有云:“大腸移熱于胃, 善食而瘦”。胃的受納、腐熟水谷功能,須與脾之運化功能相配合,納運協調才能化水谷為精微,進而營養全身。大腸移熱于胃,胃熱則腐熟功能過亢,則見消谷善饑、形體消瘦。
1.1.3 情志失調 《靈樞·本藏》中說:“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五臟虛,則其外泄也。《靈樞·壽夭剛柔》謂:“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情志受到突然、過度或長時間的持續刺激,會導致人體的氣機紊亂,使得陰陽氣血失衡,臟腑受損,無法化生和儲存精氣。
1.2 消瘦型糖尿病的發病機制與脾相關
近代許多學者認為,糖尿病發生的主要原因為脾虛,根本的病理機制在于脾的運化功能失常,使得水谷精微不能正常化生和輸布,水液轉輸受限。《靈樞·本藏》指出:“……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認為脾虛是消癉發生的根本原因[9]。劉完素有云,“今消渴者,脾胃極虛。”脾胃能運化水谷,化生精微,供養全身,是糖尿病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著名醫家張錫純提及:“消渴有上中下之分……下追至病及于脾……則小便無節,是以渴而多飲多溲也。”《癥因脈治》說:“思慮傷脾,脾陰損傷……此精虛三消之因也。”思則氣結,過度思慮會導致中焦氣滯,氣郁化火,損及脾陰,從而導致消渴的發生。《素問·經脈別論》云:“飲入于胃……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液入胃以后,游溢布散其精氣,上行輸送與脾,經脾對精微的布散轉輸,上歸于肺,肺通調水道,下輸于膀胱。如此則水精四布,外而布散于皮毛,內而灌輸于五臟之經脈。 脾虛則四肢肌肉失于榮養,則見形體消瘦、乏力自汗、四肢麻木等癥狀,水谷精微不能上濟,故見口干、多飲;脾虛不能為胃行其津液,使得胃陰虧虛,陰不制陽。胃火熾盛,而見消谷善饑;水谷精微不能上輸而趨下,隨小便排出體外,故小便量多而味甘;精微物質結聚血中而致血糖升高。
1.3 從脾論治糖尿病的臨床應用
由脾臟著手診斷消渴病是有其現代病理生理基礎的。現代醫學認為,胰島β 細胞的胰島素分泌和(或)胰島素生物學作用的欠缺是糖尿病的根本病理變化。大量資料證實,中醫所說的脾,不僅在解剖學上與西醫所說的脾和胰有很大的相似性,脾臟的運化功能與現代醫學中胰的內分泌功能也有密切聯系。綜上可知,糖尿病的發病關鍵在于胰,因此,中醫治療糖尿病的重點應在脾。清代《侶山堂類辨》有云:“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而為消渴者……以健脾之藥治之,水液上升,即不渴矣。”從脾治療糖尿病應據證立法,或補氣,或養陰,或化濕,或瀉熱,或溫陽,也可與潤肺、益腎等相兼,恢復脾之運化功能,使水谷精微得以正常轉輸。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健脾益氣中藥能促進肝細胞膜分泌更多的胰島素介體,降低腺苷酸環化酶活性,提高胰島素敏感性。有研究[10]已經證實人參、黃芪、茯苓、蒼術、山藥、白術、天花粉等健脾益氣中藥能夠顯著降低血糖。王雪楠等[11]觀察施今墨對藥配方對2 型糖尿病大鼠血糖等指標的影響,結果顯示施今墨之升陽健脾、清肺瀉熱對藥配方可以明顯消除2 型糖尿病大鼠的胰島素抵抗狀態。郭媛[12]運用健脾化濕法治療糖尿病前期,發現健脾化濕方能顯著降低患者的血糖,較好地改善胰島素抵抗,改善患者的預后。周國英[13]認為糖尿病的病機為脾虛失運,故在治療上常選用益氣健脾之黨參、黃芪、茯苓等健脾升陽,并輔芳香化濕藥以清化痰濁、助脾氣散精,效果尤佳。
2 病案舉隅
患者孔某,男,69 歲,身高167cm,體重51kg,BMI:18.28kg/m2。2020 年6 月22 日就診。主訴:發現血糖升高23 年。患者訴近來無明顯誘因下體重減輕8kg,一直服用“拜糖平50mg tid,格華止tid”控制血糖,夜尿3 ~4 次,無尿急尿痛,飲食睡眠尚可。舌淡,苔白膩,脈緩。辨證屬“消癉”之脾虛濕盛證。予檢查腫瘤全套(男10 項):非小細胞肺癌相關抗原:6.08ng/mL ↑; 神經特異性烯醇化酶:30.89ng/mL ↑。1 年間多次于當地醫院復查肺部CT、神經特異性烯醇化及腫瘤全套等,未見明顯異常。二診時,患者體重仍較輕,體重52kg,BMI:18.6kg/m2。當時降糖方案為:拜糖平50mg tid,二甲雙胍0.5g bid,沙格列汀 5mg qd,卡格列凈100mg qd。訴咽干咽癢,夜尿1 ~2 次,小便味重,大便自調。考慮二甲雙胍、卡格列凈有減重作用,遂修改降糖方案為:拜糖平50mg tid,沙格列汀 qd,諾和平14 Uqn。并予中藥治療,患者辨屬脾虛濕熱證,治以益氣健脾、清熱燥濕。予資生丸加減,具體藥物:太子參10 g,麩炒白術10 g,茯苓10 g,炙甘草5 g,炒白扁豆10 g,桔梗6 g,炒薏苡仁10 g,蓮子心5 g,山藥10 g,澤瀉10 g,芡實10 g,麥冬10 g,玄參10 g,豆蔻2 g,木蝴蝶6 g,荊芥6 g。15 劑,每日1 劑,水煎取汁約250 mL,早晚各溫服1 次。三診時患者體重稍有上升,體重53kg,計算BMI :19.00 kg/m2,余癥同前,原方基礎上,加用知母10g,黃柏6g。繼服15d。四診時患者體重為56kg,較前明顯增長,計算BMI 為20.07kg/m2。訴血糖控制良好,無明顯不適,精神狀態佳,繼服原方15 劑以鞏固療效。
按:患者糖尿病病史已有23 年,血糖控制尚可,出現體重無明顯誘因下減輕8kg,細致詢問病史,患者不存在飲食控制過嚴、運動量過大的問題,結合癥狀、實驗室檢查,也排除了糖尿病并發癥或合并癥(如甲亢、胃輕癱、感染等),不排除腫瘤引起體重下降的可能,遂予檢查腫瘤全套,結果示:非小細胞肺癌相關抗原:6.08ng/mL ↑; 神經特異性烯醇化酶:30.89ng/mL ↑。一段時間后復查:非小細胞肺癌相關抗原:5.96ng/mL ↑。查胸部CT 未見明顯異常。1 年來又多次復查相關腫瘤指標及胸部CT,未見明顯腫瘤指征。綜上,考慮為單純糖尿病引起的體重下降。患者年老,加之消渴日久,脾氣漸虛,脾胃運化功能失司,不化水谷,不分清濁,致濕邪伏里,膏脂厚濁蘊積體內。舌淡、苔白膩、脈緩皆為脾虛濕盛的表現。治宜以健脾為主,兼以滲濕。選用以甘淡之品為主要藥物的資生丸加減。太子參甘苦平,既補脾氣,又養胃陰,為清補之品。白術、茯苓合用健脾益氣滲濕。白扁豆、薏苡仁、澤瀉助白術、茯苓以健脾滲濕。山藥、蓮子心健脾益氣,桔梗有載藥上行的功能,與甘草同行,為舟楫之劑,張元素認為諸藥有此一味,即不能下沉。患者消渴日久,恐傷腎氣,芡實即可益氣健脾除濕,又可固腎填精。患者小便味重,考慮為濕熱下注引起,故去砂仁,予溫燥之性較弱之豆蔻化濕行氣。患者熱象不顯,去清熱除濕之黃連,以防損傷陽氣。患者無食積癥狀,去麥芽、神曲、山楂等消食之品。患者咽干咽癢,予玄參、麥冬滋陰生津,木蝴蝶利咽,荊芥祛風。綜觀全方,補其虛,除其濕,行其滯,調其氣,兩和脾胃,濕邪得去,則諸癥自除,使脾胃升降有序,清氣上升,濁陰下降,則營衛化生,氣血有源。三診時體重有所上升,仍咽干,在原方基礎上,加知母10g、黃柏6g,以改善咽干。
3 結語
消瘦型2 型糖尿病的發生與脾緊密相關,人體臟腑百骸皆賴脾以濡養,先天稟賦不足、后天情志失調、加之內熱熾盛等病因, 皆可傷及脾臟。脾主運化,脾虛運化無力、水液則無法正常代謝,在上不能升清,在中則影響胃之腐熟功能,在下會無法固攝精微,以致消渴“多飲、多食、多尿”。同時由于脾虛致運化無力,肢體肌肉失以濡養而出現形體消瘦。另外,臨床對于消瘦型2 型糖尿病的論述較少,中醫治療雖然在從脾論治消瘦型2 型糖尿病方面有辨證論治的優勢,但當前仍缺乏高級別循證研究證據,仍需加強臨床基礎研究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