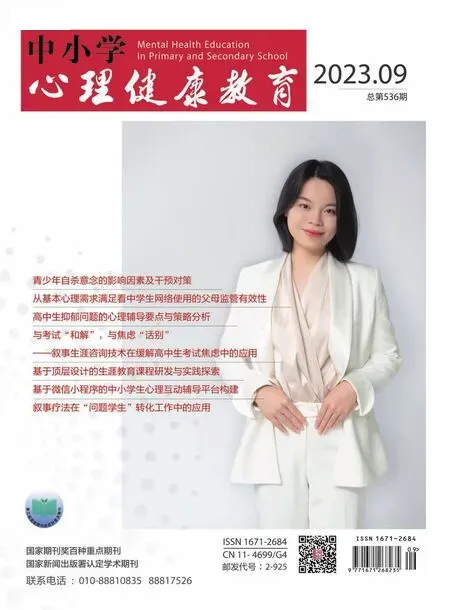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積極心理品質的中介效應分析
◎張瓊芳 余彬楊 向海蓉(湖南省長沙市雅禮實驗中學,長沙 410000)
一、引言
青春期是個人成長與發展的關鍵期,生理成熟與心智發展之間存在的現實差距,使得處在該階段的青少年更容易產生抑郁、焦慮等情緒問題[1]。《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中顯示,2020年,我國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郁檢出率為7.4%[2]。當人們長期處于抑郁狀態時,發展成為抑郁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3]。抑郁不僅影響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形成、社交能力的發展,還與攻擊行為、自殺自傷等危險行為密切相關[4-5]。因此,有必要探討抑郁的影響因素,為預防和干預青少年抑郁提供理論依據。
(一)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抑郁的關系
家庭風險指的是家庭環境中能夠增加青少年不良發展后果概率的相關因素[6]。相對于家庭結構完整的孩子,單親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現行為問題[7]。多項研究表明,家庭的經濟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親密度、親子沖突等因素與青少年的抑郁有著密切關聯[8-14]。
研究顯示,青少年所處環境中的任何一個風險因素的出現都可能增加其抑郁發生的概率,風險的產生以“疊加式”和“累積式”的形式同時出現[15-16]。累積風險假說表明,當風險因素以累積形式出現時,會以更高的不可預測性、破壞性來消耗青少年的認知能力范圍、情緒與行動調控范圍[17-20]。這無疑給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張凡、王佳宇和金童林[21]在2017年的研究中也證明了這一點。家庭作為青少年成長過程中與之聯系最為緊密的微觀系統,家庭維度的風險也是所有風險中最直接和最關鍵的一環,家庭累積風險嚴重影響著青少年的心理健康[24]。研究表明,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內外化問題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隨著家庭累積風險的增加,青少年出現自殺自傷、抑郁、網絡游戲成癮的概率也會隨之上升[25-28]。
以往研究多關注單一風險對于青少年抑郁的影響,缺少關于家庭維度的多重風險與青少年抑郁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本研究重點考察家庭環境中存在的累積風險因素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并探索其內部作用機制。
(二)積極心理品質的中介作用
積極心理學是致力于培養人類積極心理品質的科學,認為積極的體驗與品質是 “抵御心理疾病的最好武器”[22]。這一理念為預防和干預青少年抑郁提供了嶄新的思路——培養積極心理品質或可預防或降低青少年的抑郁癥狀水平。一項針對5~16歲兒童青少年的研究發現,積極心理品質可以降低其未來發生心理行為問題的概率[23],張紅英和周晴等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8,24]。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假設: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抑郁有著重要影響,積極心理品質在兩者之間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以班級為單位,對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岳麓區、天心區、望城區普通初中學校共計1285 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1206 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率為93.85%。其中,男生648 人,占總人數的53.73%;女生558人,占總人數的46.26%。
(二)研究工具
1.家庭累積風險問卷
參照前人累積生態風險研究與家庭累積風險研究,本研究以部分風險因子為連續變量,另一部分風險因子使用單題測量。對家庭結構風險使用家庭結構進行測量;對家庭資源不足風險使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困難、父母長期離家務工導致親子分離進行測量;對家庭氛圍風險使用家庭親密度和家庭沖突進行測量。
(1)家庭類型。參考董奇和林崇德[29]在2011年的研究,采用一個項目測量家庭類型,即“家里哪些人住在一起?”(可多選),選項包括“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兄弟姐妹、繼父、繼母、其他(請寫出)”。風險界定標準:沒有與親生父母共同生活視為有風險,編碼為1(有風險),其余為0(無風險)。
(2)父母受教育程度。參考鮑振宙、李董平和張衛等[30]的研究,采用兩個項目分別測量父母受教育程度。風險界定標準:父母受教育程度均低于“高中”編碼為1(有風險),其余編碼為 0(無風險)。
(3)家庭經濟困難。采用Wadsworth 和Compas[31]于2002年編制,王建平、李董平和張衛[32]于2010年修訂的家庭經濟壓力量表測量家庭經濟困難情況,該量表包括4個項目:“我家沒有足夠的錢買新衣服”、“我家沒有足夠的錢買我喜歡的食物”、“我家沒有足夠的錢買好的住房”及“我家沒有剩余的錢供一家人去娛樂”。采用5 點計分,從“從不”到“總是”分別計1~5 分,計算所有項目的平均分,分數越高表示家庭經濟越困難。風險界定標準:高于第75 百分位數編碼為1(有風險),其余編碼為0(無風險)。
(4)親子分離。使用問卷中的一個項目“在過去的六個月里,因為父母外出工作,我沒有和他們住在一起”測量親子分離狀況。風險界定標準:選擇“是”編碼為 1(有風險),選擇“否”編碼為 0(無風險)。
(5)家庭親密度。采用費立鵬、沈其杰和鄭延平等[33]修訂的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中文版(第2版)中的家庭親密度分量表測量家庭親密度情況。該量表包括16 個條目,采用5點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家庭成員間的情感關系越緊密。風險界定標準:得分低于或等于第25 百分位數編碼為1(有風險),其余編碼為0(無風險)。
(6)家庭沖突。選取費立鵬、沈其杰和鄭延平等[33]修訂的家庭環境量表中的矛盾性因子測量家庭沖突狀況。共9 道題,2 點計分(1=否,2=是)。風險界定標準:得分高于或等于第75 百分位數編碼為1(有風險),其余編碼為0(無風險)。
近年來,構建累積風險模型的方法開始普遍使用。由于每種風險因素的原始測量方式可能存在差異,因此需要對每一種風險因素進行標準化處理,將每個風險因素的得分25 或75 百分位點作為臨界值對每個風險因素進行二分編碼(1=有風險,0=無風險),然后將所有風險指數的得分相加得到總分,再將所有風險因素的分數相加,得到家庭累積風險指數。本研究中,家庭累積風險指數可能范圍是0~6,分布比例分別為26.62%、31.92%、21.56%、13.18%、5.14%、1.4%、0.17%,平均值為2.57(SD=1.24)。
2.抑郁量表
PHQ-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是一個簡明、有效的抑郁自評工具,國內外的研究已證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34]。該量表包括9 個條目,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癥狀越嚴重,總分27 分,總分<5 分為不存在抑郁癥狀,≥5 分為存在抑郁癥狀,其中 5~9 分為輕度抑郁,10~14 分為中度抑郁,15~19 分為中重度抑郁,20~27 分為重度抑郁。
3.積極心理品質問卷
采用官群、孟萬金等[35]編制的中小學生積極心理品質量表,該量表共61 個項目,包括六個維度,分別是智慧和知識維度、勇敢維度、人性維度、公正維度、節制維度和超越維度。采用5 點計分法(5=非常像我,1=非常不像我)。六個分量表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都在0.7 以上。
(三)施測程序及數據處理
本次調查研究采用計算機線上填寫問卷的方式,實施測試前由施測人員(心理教師)主持,以班級為單位,在學校機房進行團體施測。使用SPSS22.0 統計軟件、PROCESS 插件對數據進行統計、檢驗和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收集數據,運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36]。結果顯示,第一個主因子的變異量為30.67%,小于40%,說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嚴重。
(二)家庭累積風險、青少年抑郁和青少年積極心理品質的相關分析
對各變量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抑郁呈現顯著正相關(r=0.29,p<0.001),家庭累積風險中的家庭結構、家庭經濟困難、家庭親密度和家庭沖突四個維度與青少年抑郁呈現顯著正相關(r=0.1~1.29,均p<0.001),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積極心理品質呈現顯著負相關(r=-0.25,p<0.001),家庭累積風險中的家庭結構、家庭經濟困難、家庭親密度和家庭沖突與青少年積極心理品質呈現顯著負相關(r=-0.35 ~-0.1,均p<0.001),積極心理品質與青少年抑郁呈現顯著負相關(r=-0.35,p<0.001)。

表1 各變量描述統計及相關矩陣(N=1206)
(三)積極心理品質的中介效應分析
使用Hayes 編制的PROCESS 插件,將性別、年級等人口學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家庭累積風險為自變量,青少年抑郁為因變量,青少年積極心理品質為中介變量,檢驗積極心理品質在家庭累積風險和青少年抑郁等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數據之前,對各個變量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對模型4 進行多元層次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家庭累積風險可以正向預測青少年抑郁(β=1.33,p<0.001),負向預測青少年積極心理品質(β=-7.87,p<0.001);積極心理品質對青少年抑郁的負向預測達到顯著水平(β=-0.04,p<0.001),說明積極心理品質在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抑郁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具體中介模型見圖1。

表2 中介模型的回歸分析(N=1206)

圖1 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積極心理品質的中介作用
采用Bootstrap 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95%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見表3:間接效應95%置信區間為[0.25,0.46],不包括0,說明間接效應顯著;從家庭累積風險到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應值為0.98,中介效應值為0.35,總效應值為1.33。中介效應分析結果表明,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均顯著,直接效應占總效應值的73.68%,中介效應占總效應值的26.32%。

表3 中介效應顯著性檢驗
四、討論
(一)家庭累積風險、積極心理品質與青少年抑郁的關系
本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累積風險顯著預測青少年的抑郁情況。本研究還考察了家庭累積風險中的各類風險因素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相關分析表明,家庭累積風險中的家庭結構、家庭經濟困難、家庭親密度和家庭沖突風險與青少年抑郁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這些風險因素可以顯著預測青少年的抑郁情況。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37-38]。數據顯示,家庭累積風險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親子分離與青少年抑郁相關性不明顯;父母受教育程度與家庭經濟困難、家庭親密度呈現顯著正相關,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家庭經濟可能越困難,父母疲于工作,家庭親密度也就越低,進而增加了青少年抑郁的風險;長期的親子分離也會導致家庭親密度降低,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風險。
(二)積極心理品質在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抑郁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表明,積極心理品質在家庭累積風險與青少年抑郁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6]。積極心理品質可以緩沖家庭累積風險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不利影響,當青少年處在風險程度較高的家庭環境中,積極心理品質可以緩解青少年抑郁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