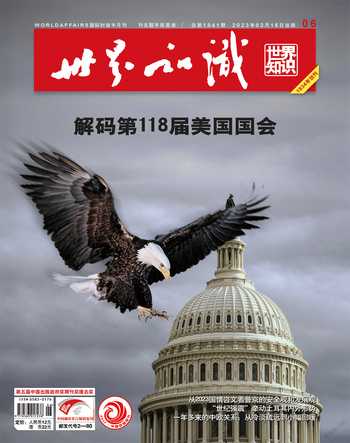印度“世界藥房”兩大短板日益突出
毛克疾
2023年2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下令將一家印度藥廠生產的兩款眼藥水下架,稱其與發生在美國12州的55起細菌感染病例有關聯,感染已造成一人因血液感染喪命,五人失明。此前的2023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出警告,提醒人們不要服用兩種印度止咳糖漿,因這兩種藥物在烏茲別克斯坦導致至少20名兒童死亡;而2022年10月,WHO曾稱,印度梅登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幾種治療咳嗽和感冒的藥物,導致岡比亞至少66名兒童死亡。
長期以來,印度被稱為“世界藥房”,但近年來其制藥產業卻面臨越來越多的爭議。印度先是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時禁止瑞德西韋等抗病毒關鍵藥物出口,而后因出口藥物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導致多國患者用藥后死亡,還在新冠疫情中暴露出其制藥產業自身供應鏈的脆弱性,同時,印度與歐美國家及美國輝瑞公司等國際制藥巨頭間因知識產權糾紛也齟齬不斷。印度制藥產業頻遭非議,其實力究竟如何?
從數量規模上看,2021年印度已成全球排名第三的制藥大國,占據全球60%的疫苗市場和20%的藥品市場。該國也是世界最大仿制藥生產國,占據全球1/5和美國近四成的仿制藥市場,擁有全球除美國外最多符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認證標準的制藥產業線。近年來在新冠疫情蔓延背景下,印度制藥行業快速擴張,在2020年與2021年分別取得13.7%和17.7%的超常增速。制藥行業強勁的發展勢頭刺激了印度政府的發展雄心。2021年該國醫藥總產值為420億美元,印度總理莫迪提出將這一指標推高至2024年的650億美元,并要在2030年達到1200~1300億美元。當前,印度有多達3000家藥企,超過一萬間制藥工廠。
有趣的是,盡管在新冠疫情暴發后美國拜登政府三番五次炒作“藥品對華過度依賴”論,最近美國藥典委員會卻經調研發現,對美國威脅更大的是印度而非中國。美國90%的仿制藥來自印度,而在全美開具的處方中仿制藥占90%,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印度掌握了美國公共衛生的命脈。印度不僅有能力控制對美藥物供給,更展現出使用這種能力的意愿。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各國忙著準備抗疫藥物的關鍵時刻,莫迪政府為優先保障國內用藥供給,毫不猶豫切斷幾種關鍵藥物出口,包括用于制造退燒藥的對乙酰氨基酚等。
不過,若按產值規模計算,印度制藥業當前僅排全球第15位。造成這種反差的原因是產業結構問題。一般來說,制藥產業鏈主要涉及兩個關鍵步驟:一是生產原料藥。按加工深度排序,可分為關鍵起始原料(KSM)、藥物中間體、活性藥物成分(API)等;二是以原料藥為基礎生產制劑。制劑按生產授權情況可分為受專利保護的原研藥和突破專利保護的仿制藥。從總體上看,印度既缺乏以低成本大規模制造原料藥的工業生產能力,又缺乏開發高端原研藥的科技研發能力,這造成印度制藥業當前“大而不強”、缺乏韌性的特點。也因此,印度制藥業主要深耕仿制藥。
在此情況下,較為落后的生產工藝疊加極高的控制成本壓力,導致印度藥品質量問題頻發。一份來自制藥外包行業的報告顯示,全球市場約75%的假藥源自印度,而FDA在 2015~2017年間針對印度醫藥公司曾發布多達31份警告函,大多涉及嚴重數據造假。
在1970年以前,印度85%的藥物市場被跨國企業占據,彼時其本土藥企大多處于邊緣地位。隨著時任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掀起民粹浪潮,特別是其政府在1970年推出《專利法》,以“打破跨國企業壟斷人民健康”為名宣布廢止藥品專利保護后,印度藥企開始借助這一全球罕見的“政策紅利”,通過“逆向工程”“規避流程專利”等方式破解、仿制國外原研藥,生產與其療效相似,但售價大幅降低的“印版藥品”,并以多種途徑向全球市場大量銷售。值得注意的是,無視專利必然導致高烈度競爭,這反過來又刺激印度藥企盡力擴大規模、壓縮成本、提高效率,在客觀上吸引國內外更多資金、技術、人才進入制藥行業,使印度制藥產業競爭力不斷提高,尤其是逐步形成全球領先的行業情報體系、流程控制體系、海外分銷體系。經過幾十年發展,印度太陽制藥、雷迪博士實驗室與阿拉賓度制藥等頭部藥企已建成非常先進的全球仿制藥營銷網絡,其年度海外銷售額達20~30億美元規模。
1994年,包括印度在內的162個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簽署《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盡管這標志著印度時隔多年再次承認并保護藥品專利,但由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獲得十年寬限期,期間印度可以一邊維持原有寬松專利管理,一邊按照TRIPs規定推進調整。因此,直到2005年,印立法機構才推出《專利法》修正案,按照TRIPs要求給予原研藥產品及工藝20年的專利保護期。此后印度不僅需承認2005年后新申請的專利,也必須追認1995年1月1日起申請的專利。

盡管2005年后印度藥企很難再直接無視專利保護,但他們依賴的業務模式卻幾乎沒有改變。據測算,印度憑借在仿制藥領域的路徑依賴、產業聚集、人才隊伍等優勢,能夠把生產成本控制為美國的60%、歐洲的50%,這反過來吸引大量跨國龍頭藥企把包裝、制造等低價值生產環節外包到印度,甚至為利用印本土要素優勢而赴印投資建廠。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雖在2005年按WTO要求推出修訂后的《專利法》,但印度政府仍對制藥產業預留了極大的“灰色空間”。例如,雖然印度政府承認藥品專利,但保留突破專利發放“強制許可”的權力,2012年就曾強制許可印度藥企Natco生產仍在專利保護期內的抗癌藥Nexavar。再如,雖然印度政府在法理上保護生產流程專利,但其在實際上卻難以阻止藥企策略性微調生產流程、制造工藝不同但藥效相似的仿品。
目前,從中國大批進口KSM、API等原料藥,加工成制劑,再向全球分銷,已成為印度藥企運營的典型模式。據印政府2020年6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印進口的原料藥68%來自中國;而印貿易促進委員會估算,印原料藥對華依賴度高達85%;另有研究顯示,印原料藥對華依賴度達70%,其中盤尼西林、頭孢菌素類、阿奇霉素等關鍵品類的對華依賴度更是高達約90%。當前印制藥業高度依賴中國原料藥,這意味著一旦中國斷供,印制藥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將難以為繼。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印度制藥企業曾因對華物流阻斷而陷入整體恐慌,不惜冒著損害國際商譽的風險也要切斷藥物出口,以防國內出現無藥可用的險情。
印對華原料藥依賴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1%陡增至2020年的逾70%,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國工業化生產能力優勢突出,大幅降低原料藥生產成本。中國化工產業依托發達的交通基建網絡、穩定的水電供給、全產業鏈協作,具有全球性價比優勢。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中國原料藥成本比印度低40%,即使近年來生產要素價格全面上漲,總體成本依舊比印度低20%。另一方面,印度國內“藥價天花板”制度迫使企業追求極致成本。印度政府為控制公共衛生支出,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不斷擴大藥物限價范圍,例如被限價的仿制藥從1995年的74種增至2019年的857種,使印藥品市場近18%的藥物都處于限價范圍內。印度仿制藥市場競爭激烈,在政府大規模限價的背景下,考慮到原料藥占藥品總成本的比例高達2/3,印度藥企往往選擇更廉價的進口原料藥增加競爭力。本質上,印度制藥業全球競爭力的重要支柱,就是中國原料藥帶來的成本優勢。
目前,為增強原料藥自主生產能力,降低對外依賴,莫迪政府已推出多項專門政策。一是出臺總額為20.4億美元的生產關聯激勵項目(PLI),在自2020年起的八年內促進53種KSM、API與藥物中間體等關鍵醫藥原料的本土化生產和出口。二是在全印范圍內設置三個醫藥產業園區,計劃五年內投資3.94億美元,專注于大批量生產藥品。三是在2022~2023財年增加一倍預算,劃撥224.4億盧比用于促進醫藥產業發展。四是印度科技產業協會(CSIR)在“印度制造”框架下與本土石化企業合作,點對點生產攻關56種重點API。此外,2019年印制藥行業主管部門為促進本土產業發展,還規定本地銷售的藥品國產API占比至少達到75%,出口藥品也至少要達到10%。
從總體上看,莫迪政府的進口替代政策已取得一定進展,53種關鍵API中的35種已實現本土生產。然而,印制藥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在本質上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成本問題——如果印度不能在根本上優化基礎設施、產業協同、營商環境以降低生產成本,印度藥企很難主動選擇更貴的國產原料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莫迪政府希望不計成本推動API對華進口替代,但是印度藥企和投資人卻更希望政府扶植高端研發,因為大規模進口替代牽涉面極大,而如果政府介入過深很可能會催生效率低下的“騙補貼企業”,因此還不如利用政府補貼攻關高端技術,這樣反而可能更有成效。
毋庸置疑,印度制藥產業為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做出了難以替代的貢獻。然而,在全球醫藥產業競爭激化的背景下,印度制藥業既缺乏美歐的科技研發優勢,又缺乏中國的生產成本優勢的短板日益顯露。在全球制藥產業轉向研發創新藥、生物藥賽道的趨向下,依托歷史慣性和渠道優勢而興盛的印度制藥產業若不能突破這兩大桎梏,在未來或將面臨更大生存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