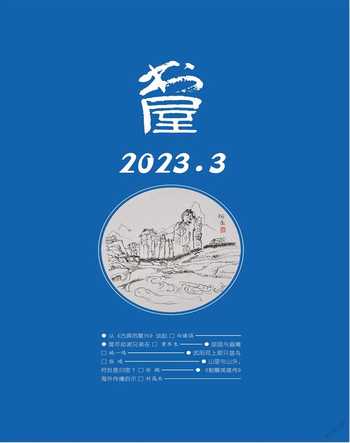張愛玲的“斯黛拉·本森”與“燕歸來”
馬泰祥
香港大學黃心村教授的新著《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簡稱《緣起香港》)令人驚艷。《緣起香港》一書的寫作,緣起于作者在2020年張愛玲誕生一百周年策劃“百年愛玲,人文港大”的紀念活動展覽時的準備工作。黃心村教授通過港大檔案館故紙堆中的新材料,得以發現1939年至1941年間求學港大的張愛玲師友交往、文學閱讀與學術訓練的歷史細節與詳細面目。
書中討論幾位給張愛玲深刻影響的港大師長的章節,尤能顯示出此書爬梳史料、探賾索隱的功底。歷史教授佛朗士在課堂上讓張愛玲形成了“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在現實中他也參與歷史,與宋慶齡、廖夢醒、愛潑斯坦等一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護送中國紅十字會醫療物資北上,在港戰期間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殉職,最后他化形成為張愛玲自傳體小說《小團圓》中的安竹斯先生;中文教授許地山扎根港大,大刀闊斧地改革中文系,他對日常生活史的學術熱情點燃了張愛玲對服飾文化的研究興趣以及對微觀細節的超常規執迷,并且蓄胡須、穿長衫的許地山教授還成了張愛玲小說《茉莉香片》中有著“特殊的蕭條的美”的角色——言子夜的原型。
港大教授佛朗士、許地山與張愛玲有切實的師生接觸,討論他們與張愛玲之間的文化互動問題順理成章,具有理論施力點和史料延展性。相較而言,《緣起香港》中討論張愛玲私淑的一位被遺忘的英文世界文學家斯黛拉·本森的部分,更顯研究者對一則文學史料問題“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求真精神。
1944年4月,將張愛玲奉為上賓的刊物《雜志》上有一篇《女作家聚談會》的訪談錄,這篇文字實錄滬上知名女作家如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汪麗玲等和女性文學研究者、記者等的對談,一直以來也是張愛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篇文獻。其中張愛玲在回應記者吳江楓“對于外國女作家喜讀哪一位”的提問時,迤迤然回應道“外國女作家中我比較歡喜Stella Benson”,但張愛玲未及展開解釋為何欣賞這位女作家,話題便陡然自動切換了。
黃心村教授敏感地捕捉到了這個留存于文字間的尷尬時刻:“她‘比較歡喜’的這位外國女作家似乎是個謎,沒有任何解釋,名字連中文翻譯都沒有。聚談記錄登載在四月的《雜志》月刊上,白底黑字,孤零零的一句話,幾乎能夠想象她說完后全場的靜默無聲,隨后另一位女作家汪麗玲滔滔不絕開始談她的最愛。”《女作家聚談會》一文因記錄了張愛玲講述自己第一篇作品的來歷、對同行女作家作品的點評、對古典文學作品的審美偏好、喜歡讀的外國文學作品等內容,成為學界考察張愛玲文學發生學、解讀張愛玲文學背景資源的重要素材,引用率一直頗高。可是偏偏長久以來,就是無人去深究文中這個張愛玲坦言很“歡喜”的、在當時連中文譯名都沒有的斯黛拉·本森究竟是誰。
《緣起香港》正面迎擊了這個難題。通過細致的史料爬梳,我們才知道這位斯黛拉·本森竟并非無名之輩。她曾靠創作打入以維吉尼亞·伍爾夫為中心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學圈,盡管只能位處編外、不被看好;她曾嫁給一位姓安德森的男人,而這位安德森在她不幸去世之后續娶夫人并育有二子,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與佩里·安德森;她書寫環球旅行的游記《小世界》《世界中的世界》以及以自身經驗為原型的小說,都顯示出一種在當時頗為珍貴的不甚精英化的敘述腔調、平實卻銳利的批評眼光。
張愛玲與斯黛拉·本森是如何發生文學聯系的?《緣起香港》鎖定了當時香港“閱讀文化圈的兩個關鍵人物”,即前后兩任港大校長史樂詩與康寧。康寧在1937年離任后,將個人藏書悉數捐贈給了香港大學,在這些藏書中至少有三本斯黛拉·本森的著作,而1939年入讀港大的張愛玲,完全有機會在圖書館借閱到斯黛拉·本森的作品。通過這樣細致的閱讀史聯系,張愛玲與她“比較歡喜”的斯黛拉·本森之間才有了文學上對話的可能性。
斯黛拉·本森這位作家在張愛玲的文學世界的表層顯像,僅僅只是一句輕飄飄的、無人應和的“外國女作家中我比較歡喜Stella Benson”。而追溯她與張愛玲的文字因緣,我們才能發現,本森以文學創作上介乎“高雅”與“通俗”的“中等趣味”之追求,對張愛玲認同凡俗的小市民審美趣味產生影響、形成呼應;本森的游記和小說,“在寫實架構之外套上一層亦真亦幻的外衣”,張愛玲亦從中發現了“傳奇”再敘述的可操作性。
由此可見,在張愛玲的生命中或許還有許多像斯黛拉·本森的這樣的人物,在文學創作上、在實際生活中或深或淺地對她發生影響。因此,在有關張愛玲的材料中,陌生的名字不宜輕易放過,不可等閑觀之。這種人情的“弱鏈接”(袁一丹語)背后可能隱含著張愛玲文學世界的另一種風情。
2020年出版的張愛玲與終身摯友宋淇、鄺文美的“往來書信集”《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1955—1979)》《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2(1980—1995)》兩冊,不但為張愛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還使得“一切‘作者意圖’都可考本溯源,有力限制了評論者的胡亂猜測”(整理者宋以朗語)。展讀這兩冊“往來書信集”中張愛玲與宋淇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通信,一個陌生的名字——“燕歸來”(Maria Yen)頗為引人注意:
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1978年6月26日
請把我以前信上關于《色戒》的部分影印了寄給我。我還想寫篇短文講《赤地之戀》。因為故事的來源(燕歸來——Maria Yen是姓嚴或顏還是燕,是替友聯還是USIS做編輯工作的,可以問Dick McCarthy——寫的一個極簡單的大綱),我對它一直歧視,直到這次出版被竄改了一個字,十分痛心,才知道已經成了自己的東西。
宋淇致張愛玲,1978年7月19日
燕歸來(Maria)原姓邱或丘,一度去意大利做修女,后來給友聯的同事清算掉,本事極大,到德國讀了一個Ph.D.,研究宋明理學,在德國一大學中教書。
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1978年8月8日
關于《赤地之戀》也不預備寫了,免得又說這書的短處,刺激慧龍。燕歸來我一直覺得漂亮神秘,不怪她在歐洲神通廣大。
這位在“往來書信集”中只匆匆一現的“燕歸來”(Maria Yen),顯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與張愛玲打過交道,張愛玲覺得她“漂亮神秘”;宋淇也明顯知道她的底細,贊嘆其“本事極大”。從簡短的通信中已經能捕捉到這位“燕歸來”傳奇的半生經驗了:原姓邱或丘、在意大利做過修女、主持過出版社、在德國研究宋明理學、在歐洲“神通廣大”……張愛玲、宋淇信中所提到的“友聯”,便是五十年代香港“鼎鼎有名”的友聯出版社(The Union Press)。
友聯出版社因在港發行針對中學生與大學生的報刊《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而名噪一時,其文化影響力遍及東南亞以及歐美的華人社區。余英時就曾在友聯出版社出版的《祖國周刊》上發表不少文章,即使后來赴美求學也未間斷。余還曾協助《中國學生周報》創刊,主持這份刊物,擔任了三個月左右的總編輯。因此,關于這位同為友聯同人的神秘女子“燕歸來”,在余英時的回憶錄中便留下了一段清晰的記錄:
提到友聯的創建,有一個人是絕對不容忽略的,那便是邱然女士。她也是北大西方語文系的學生,大概和徐東濱同班或者低一班。她中、英文都好,風度高雅而富于親和力……這些特質都是和她的身世背景分不開的。她的父親邱椿(字大年)不但在學術界負重名,而且也是與胡適同一代的自由主義先驅。
……
邱然不僅是文化與政治領域中一位有力的活動家,而且也擅長文學創作,她以“燕歸來”的筆名寫了不少散文和詩,頗傳誦一時。(另一筆名是“燕云”。)像她這樣各方面都出色的人才,即在平時也會引起社會上的注目,何況在五〇年代香港那個特殊的文化-政治的社群之中?所以當時友聯的朋友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把她當成了一個核心人物……她在香港時已信了天主教,中年以后(大約在七〇年代末)她到德國去進了修道院,宗教信仰竟成為她的人生歸宿,這是我意想不到的。
原來,“燕歸來”就是教育學家邱椿的女兒邱然。根據她籍貫所在地江西寧都縣史志辦公室所編《寧都便覽》一書,可以看到她更加詳盡的生平描述:“邱燕,女。又名然,海外易名燕云,外文名瑪麗雅·燕,筆名‘燕歸來’。1928年出生。石上鎮蓮塘村人。邱椿之女。縣內首位女博士。亞歐知名學者。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方語音〔言〕文學系。后赴香港,創辦總部設于倫敦的國際作者協會‘國際筆會’香港分會并首任秘書長,曾擔任香港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主席兼研究所所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獲德國漢堡大學博士學位,從此寄居歐洲,在德國及瑞士各大學任教授,講授中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創建‘裴斯泰洛齊項目’,1994年曾在北京舉行裴氏教育思想國際研討會,亞、歐、美三大洲均有代表出席,邱燕為會議主持人之一。”由此看來,燕歸來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遁入修道院后,又在八十年代重返紅塵,繼承父志投身教育界,九十年代還回到祖國參與學術活動。
燕歸來與張愛玲有何關系?首先,“燕歸來”是張愛玲1956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小說Naked Earth(《赤地之戀》)一書導言的作者。導言梳理了小說的生成情況,指出《赤地之戀》是由中文轉譯英文的,“此書原以中文寫成,以英文出版代表著一種實驗”,特別點明小說的特色在于“專注于講故事”。
其次,如果張愛玲的記憶無誤的話,則“燕歸來”不僅僅是給《赤地之戀》寫“導言”這么簡單,整個故事其實都是來自她的設計。張愛玲在信中說這個故事的來源是“燕歸來寫的一個極簡單的大綱”。但仍有不少研究認為這是張愛玲身為作家“自發自主”的創作。比如高全之曾采訪麥卡錫(即張愛玲信中所言的這位Dick McCarthy),麥卡錫否認《赤地之戀》故事大綱是由他人操刀:“ 高:曾有人說《秧歌》與《赤地之戀》皆由美新處授意而寫。《赤地之戀》的故事大綱甚至是別人代擬的。”“ 麥:那不是實情。我們請愛玲翻譯美國文學,她自己提議寫小說。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國北方待過,非常驚訝她比我還了解中國農村的情形,我確知她親擬故事概要。”
張愛玲信中點出“燕歸來”撰寫“極簡單的大綱”,與麥卡錫“確知她(張愛玲)親擬故事概要”的說法迥不相侔。“往來書信集”能夠“有力限制了評論者的胡亂猜測”,并非虛言。張愛玲自始至終都鄙棄自己創作的《赤地之戀》,盡管“被竄改了一個字,十分痛心,才知道已經成了自己的東西”。她在“往來書信集”中坦言對這部作品的感情十分復雜:“故事來自USIS,所以我對它不像對別的作品。”“我始終視為僅次于《連環套》的破爛。”
最后,“燕歸來”在麥卡錫的協助下,于1954年在紐約馬克米蘭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自敘傳小說The Umbrella Garden,以自己在北大求學而后離開赴港的人生經驗作為主要線索。這部小說與《赤地之戀》故事大綱之間,或許還有更深刻的內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