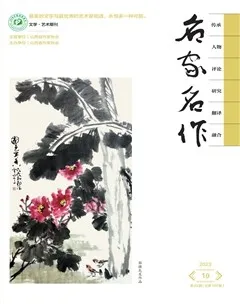天使與魔鬼:電影《流浪地球2》中的“數字人”形象探究
王 越
《流浪地球2》是一部帶有外向型和內向型雙重探索的影片,無論是外向型探索中對外太空的沉思,還是內向型探索中聚焦到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都具有豐富的考究意義,其中“數字人”形象更是代表了科幻電影中對于未來科技的進一步描寫,一方面人工智能通過“人在回路”①“人在回路”指通過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情感分析、環境變化等一系列的學習,此方法是當下科學家認為人工智能獲得更高精度的關鍵。的學習可以和人類的意識相結合,從而使人工智能成為更加接近人類的數字人;另一方面,“數字人”的出現使人類可以拋棄自己的身體與人工智能結合,這使著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在2014 年12月的預言“制造能夠思考的機器無疑會對人類存在巨大威脅,當人工智能發展完全之日,將是人類的世界末日”又一次出現在大眾眼前。“數字人”這一形象的出現究竟是幫助人類的“天使”還是毀滅人類的“惡魔”?可以從情景構建、邏輯生成、審美移情以及表達策略四個方面進行研究。
一、“數字人”概念的情景構建與想象力表達
文學作品和電影中對于人工智能和數字世界的構建由來已久,通過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反復切換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在這些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往往被簡單劃分為兩種類型:破壞者和幫助者。[1]前者始終與人類交好,以保護人類為己任。后者則處于人類的對立面,且通常是由于人工智能具備人類的意識,但是并不具備人類的“道德感”,這種觀念的缺失促使這類人工智能形象往往以毀滅人類為己任。基于此,引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人工智能的出現究竟是一個破壞者還是幫助者?2023 年電影《流浪地球2》中的“數字人”是一種人工智能與人類意識結合的新形象,雖然其初衷是為了延續人類文明,但由于“數字人延續人類的最優選擇就是毀滅人類”這一觀點成為一個變量,由此形成了影片人類與“數字人”二元對立的情景構建,這時的“數字人”變成了一個人為制造的“魔鬼”。與之相對的是,在影片結尾處,“數字人”的出現恰恰幫助影片中的主人公成功化解了危機,促進了人類的團結,這時的“數字人”亦是一種科技發展之下促成的保護人類的“天使”。這種矛盾性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未來人工智能與人類的核心矛盾。
二、“數字人”視覺想象的文化邏輯生成
“數字人”的形象出現“天使”和“魔鬼”這兩種矛盾的概念,其原因在于“數字人”在視覺形象上身體不在場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導致“數字人”對于人類來說是一種存在于暗處的、看不見、摸不到的恐怖意識,且這個意識的主導權可能并不在人類手中,這使“數字人”與人類的關系形成了一種“他者”與“自我”的相對關系,“自我”可以看作是如今的人類,而“他者”就是以“數字人”為代表的人工智能,這里也蘊含著人類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表達。
(一)科幻電影中的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觀念認為,人類是宇宙的中心和萬物的主宰。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對于自我的認識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人類開始認識到自己并不是萬物之靈。宇宙中、另一個空間之中或者在地球上,都有可能存在和人類一樣具有自我意識和高度智能的事物,都可以統稱為——“他者”,科幻電影始終貫徹著以未知力量為“他者”形成與人類“自我”的二元對立。然而,電影《流浪地球2》對“數字人”的視覺想象展現出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表達,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人類對于科幻電影中“他者”的設定更多是基于人類自身的,電影《流浪地球2》中的“數字人”形象與人類并無差異;另一方面“他者”這一概念是基于人類對于“自我”之外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隱含著人類自我欲望的投射。《流浪地球2》中的“數字人”形象使人類千百年來所追求“永生”的欲望得到了宣泄,人類終于可以脫離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在具有和人類一樣的記憶、人格、思維和自主意識的基礎上,在數字世界實現“永生”。由此,《流浪地球2》中作為“他者”的MOSS 和作為“自我”的人類形成了一種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
(二)科幻電影中的“他者”與“自我”
西方的科幻題材作品中對于“他者”的設定往往是一個被拯救者,而“自我”則是一種帶有冒險精神的探險者,影片中產生的矛盾均為文明的現代人和野蠻的土著人之間的二元對立。結合美國好萊塢的科幻電影來看,“好萊塢科幻電影多表現出擴張的、功利的、個人英雄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倫理標準”。[2]《流浪地球2》是一部中國科幻電影,在東方語境中,“他者”這一概念是一個神秘的存在,雖然它們的未知、可怖激發了人類的探索欲望,但同時也帶來了對“他者”的強烈不安感。因此,影片中的矛盾也多表現為地球侵略者和地球保護者之間的二元對立,可以將之稱為中國式科幻的“他者恐懼”。以中國科幻小說家劉慈欣的幾部影視化改編作品為例,在電視劇《三體》中,“他者恐懼”表現為對三體文明和歌者文明隨時會毀滅地球的恐懼。在電影《瘋狂外星人》中表現為對于未知超能力的探索;在電影《流浪地球2》中,這種“他者恐懼”表現為對“數字人”形象深深的憂慮。正是這些對于“他者”的恐懼心態,使中國的科幻題材影視作品形成了屬于自己的中國式想象,從而形成了基于本民族的文化視角下的中國式科幻。
三、美學概念下“數字人”形象的審美移情
《流浪地球2》中的“數字人”將生物智能和數字智能結合在一起,人作為一種數字化的虛擬人,在信息空間中生存。它是虛擬和真實的結合,讓我們主觀認為的“現實”被現實和數字世界中的經驗共同決定。[3]在視覺表達上運用實體化的具象去解釋抽象,將“數字人”形象的真實與虛幻設定在一個與現實世界相似的屏幕中,這可以看作是一個人為設置的鏡像化的空間,是現實世界在虛擬世界的投射,其內涵是“數字人”形象在美學概念下的兩種轉變。
(一)從“理念我”向“鏡像我”的轉變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曾提出著名的“鏡像理論”,從嬰兒照鏡子出發,將一切混淆了現實與想象的情景都稱為鏡像體驗,在這個階段,嬰兒首次充分認識到自我。在鏡像體驗的過程中,嬰兒完成了從“理念我”到“鏡像我”的過渡①拉康認為,嬰兒問世時本來是一個“非主體”的存在物,沒有物我之分、主客之分,只是一種原動力形式的“理念我”。從“理念我”向“鏡像我”的過渡是通過鏡像階段來完成的。。在電影《流浪地球2》中,“數字人”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人類意識在電影這個鏡中世界的延伸,如果把虛擬世界的“數字人”看作人類的縮影,那可以將其看作處于“理念我”的嬰兒狀態。結合影片《流浪地球2》來看,人工智能550W 和劉培強有過兩次不同的對話。第一次對話的550W 是離線版本,僅回答十分機械和程序化的內容,顯然不具備人類的情感。而在第二次對話時,550W 開始給自己取名叫莫斯(MOSS),這表明此時的550W 已經開始擁有了身份認同,進入了拉康所說的“鏡像我”的階段。但是,此時莫斯(MOSS)還沒能進化出“社會我”,即接受了社會文化結構,從而意識到自己、他人和世界之間的關系,形成了一個社會結構中“我”的概念。因此,在“鏡像我”階段,“數字人”很難僅僅通過語言結構體會到屬于人的社會性和文化性,有許多違反人本能和社會規范的危險舉動。
(二)從“玩具”到“鏡子”的轉變
美國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提出的“媒介進化論”認為,媒介進化中存在“玩具”“鏡子”“藝術”三個技術演化階段,不同階段受眾對媒介的感知和使用不同。[4]人工智能在其誕生之初就是作為一種“玩具”的形式出現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1920 年,捷克劇作家Capek 在他的《羅薩姆萬能機器人公司(R.U.R)》劇本中,第一次提出了機器人(robot),它反映著人類希望制造出像人一樣會思考、有勞動力的機器來代替自己工作的愿望。1980 年,卡內基梅隆大學設計出了第一套專家系統——XCON。從這時起,機器學習開始興起。人類開始將機器人看作是映照現實世界的“鏡子”,電影作品中也開始表現機器人的情感交流。“但當玩具演變成為鏡子之后,人類的情感取代了對技術本身的關注。”[5]在電影《流浪地球2》中,“數字人”形象已經模糊了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界限,形成了人工智能從“鏡子”階段之后的發展。但是同時,萊文森認為媒介進化的終極目標都是服務和滿足人類的需求。根據人性化趨勢理論,無論“數字人”的形象如何變化,都是對人的主體地位、主觀能動性的強調,最終目的都是凸顯媒介、滿足人類的能動需求。
四、“數字人”身體形象的視覺表達策略
人類誕生于世界,存在于物質世界中,身體和精神早已成為物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體是人類在物質世界的“自然”生命形式,身體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特有的生命感知方式和意義生產。而日益發達的科學技術卻讓電腦變成了各種不需要身體的“虛擬人”。“身體性”的消逝帶來的是“何以為人類”的身份認同和意義難題。[6]電影《流浪地球2》中對于“數字人”的態度也表現出這樣的二元對立,即人類的精神和身體之間的二元對立,人類拋棄身體在精神世界永生,形成的“數字人”在外在形象和內在精神上有兩種體現。
在外在形象上,電影《流浪地球2》中對于“數字人”有兩種不同的形象設置,一種為機器狗笨笨和MOSS的機械化形象,另一種為小女孩圖丫丫在影像中的虛擬形象,這兩種形象分別對應著兩種不同的“數字人”想象,前者與人類的寵物狗和生活中的攝像頭類似,后者直接與人類無異,這是為了避免“恐怖谷效應”的峰值。“恐怖谷效應”最早是由日本的機器人專家森政弘(MasahiroMori)在1970 年提出的概念。恐怖谷效應認為,機器人的外觀和行為與人類越是接近,人們越容易產生積極的正面情感。但是這種正面的情感到達一個峰值之后,隨著相似度的提高,人們會對機器人產生恐怖的感覺,形成所謂的“恐怖谷”;當相似度持續上升到與人類更為接近的程度時,人們對機器人又會重新產生正面的情感。[7]《流浪地球2》中的兩種形象設置使其恰好避開這種恐怖谷的感受,從而避免對于電影中“數字人”形象的恐懼感,在視覺形象上給予觀眾慰藉。
在內在精神上,電影《流浪地球2》中“數字人”的形象也折射出現代社會人類的身體焦慮。哲學家梅洛-龐蒂指出:“身體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媒介,對一個有生命的存在者來說,有一個身體意味著與一個確定的環境相統一,與某些籌劃相融合,并始終致力于這些籌劃。”[8]機器狗笨笨和MOSS 的機械化形象在物質世界有一個實際的載體,而小女孩圖丫丫在影像中的虛擬形象完全存在于虛擬世界,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在科技文明飛速發展之下,人類對未來身體形態的想象以及對自身身份認同的困境。一方面,人類有保存自己形象的沖動,從歷史上的壁畫、古埃及的木乃伊,到畫像和照相術的誕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所以人類自身抗拒機械化的變化;另一方面,人類又有對于永生的強烈欲望,身體會經歷的生老病死又是無法避免的自然規律。科幻題材影視作品作為一種針對人類想象的虛構類藝術作品,對于身體的塑造也在映射人類,數字生命也將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一種選擇。
五、結語
從整體上看,《流浪地球2》不同于以往的科幻題材影視作品,在對人類未來想象進行視覺化表達的同時,加入了對人類命運發展的探究,并結合拉康的鏡像階段論以及保羅·萊文森的媒介進化論設定“數字人”形象,對人類生命倫理和人類身體認同進行思考。當人類的身體逐漸成為一種媒介,人與媒介的關系逐漸演變成了一種“主客難分”的模糊關系,未來的“數字人”究竟是為人類所用的工具,還是人類生活的巨大威脅,這是“數字人”形象的矛盾所在。基于此,《流浪地球2》中對于“數字人”形象的視覺表達與邏輯架構建立在人類的未來想象基礎上,通過其核心觀念“沒有人的世界毫無意義”,建構出由人類創造產生的科技最終將服務于人類的框架。科技將成為人類主體地位的身體接納者,實現人類自身的精神自由,這即是當下和未來科幻電影的想象力建構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