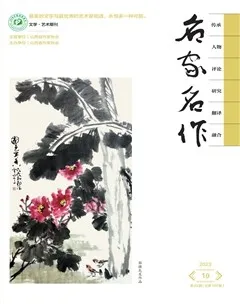論數字技術對紀錄片的影響
——以非遺類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海派百工》為例
徐一諾
數字技術在人類社會的廣泛應用,為社會各方面帶來了創造性的變革。紀錄片作為一種重要的電影電視藝術形式,也隨著數字技術的參與迎來了深刻變革。近年來,非遺紀錄片從小眾題材走入大眾視野,并在數字技術的輔助下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格局。本文圍繞數字技術在非遺類紀錄片中的運用;數字技術推動新媒體發展帶來的非遺類紀錄片樣態的變化;數字技術影響下非遺類微紀錄片的不足及改進三方面展開論述,探討數字技術對非遺類紀錄片的影響。
一、數字技術的運用
數字技術在非遺類紀錄片中的參與從形式與功能上可分為兩大類:數字影像的生成與處理;拍攝技術提升帶來的影片質感的直接上升。
(一)數字影像的生成與處理
數字影像生成技術是一種數字化再生影像手段,在整個過程中不需要使用攝影機,而是運用計算機二維動畫和三維動畫軟件建立數字模型,生成影片所需要的動態畫面,也叫作計算機圖形,簡稱 CGⅠ 技術①張歌東:《數字時代的電影藝術》,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在非遺類紀錄片中,數字影像生成技術往往被用于重現歷史場景或是建構虛擬演示影像,以改變本身的現實性和重構紀錄片時空。2018 年,中宣部、國家文物局、中央電視臺共同實施,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制作的文物類電視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播出,“殷墟嵌綠松石甲骨”一集首先介紹了現存的大量甲骨碎片,及其中已得到專家學者確認的1500 多個漢字。當這些資料交到制作團隊手中后,他們通過數字動畫創作象形文字角色,配以簡單易懂的劇情與畫面,演示了商晚期一位商人的一天和所包含的文字意象,同時展示了其對應的現代文字。如作為能夠擔起家庭證明的束發的發簪配以人的形狀形成了文字“夫”;依據小鹿的形態形成相應的文字“鹿”。諸如此類的創作方式以一種借助數字技術的新思路為非遺類題材紀錄片開拓了新道路,通過激發觀眾的想象力,使觀眾專注于紀錄片的內容并沉浸在紀錄片營造的氛圍中。
數字影像處理是指使用計算機軟件再次加工、處理前期實拍的影像或后期生成的影像,從而產生影片需要的新面面。創作者可以擦除影像中的多余部分,比如去除畫面中穿幫的物體;或者使用軟件在預先拍攝的畫面中增添因條件限制不能實現的拍攝等②黃京京:《數字技術的二次指示對于非遺題材紀錄片的假定性探究》,碩士學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 2022,第22 頁。。數字影像處理在紀錄片中的應用十分廣泛,譬如運用數字克隆技術構建宏大歷史場景;對拍攝的影像調整參數以滿足相應畫面表達的需求等。最簡單及普遍運用的就有對拍攝空鏡的不同處理,以達到不同敘事功能的目的。
(二)前端攝影技術的運用
近年來,上線于交互社區B 站的多款非遺類紀錄片都展現了其迎合當下觀影需求的精心制作的電影質感。而影片質感的直接提升離不開數字技術發展和普遍應用所帶來的紀錄片拍攝技術的提升。譬如由B 站自主出品的從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這一特別群體出發,記錄上海手工藝人的精美作品、獨特匠心和精湛技藝的《海派百工》中,8K 超高清拍攝技術被用于特寫鏡頭語言,細膩準確地展現了非遺藝術作品的精雕細琢。在《海派蛋雕》《微雕微刻》《錢幣生產的手工雕刻技藝》等篇章中,使用了大量微距、特寫鏡頭,幾位匠人的精湛技術在鏡頭前一覽無遺。此類精雕細琢的精美作品體積小,肉眼難以細致觀察,微距鏡頭的采用讓作品的誕生過程得到全方位呈現。此外,非遺類題材紀錄片電影質感的打造離不開聲效質感提升對觀影沉浸感的提升。在《海派百工》第一季的《海派蛋雕》一集中,蛋雕匠人在進行蛋殼殼面雕刻時,聲音中不僅有匠人的畫外音進行主觀經歷的講述,還有雕刻筆撫過蛋殼時摩擦出的細微聲音,與精致的畫面內容共同構成視聽藝術的至臻至美。除此之外,溫婉的背景音樂鋪墊在底層,為藝術的表達做襯托,使紀錄片不再只是紀實紀事,更是藝術的愉悅與追求。由此可見,數字技術的輔助讓影片質感的直接提升成為可能。
如上兩類皆是數字技術在非遺類紀錄片中不同形態與表達方式的運用,從數字影像的生成、合成與處理,到數字技術發展下的拍攝技術的提升,給予非遺類紀錄片無中生有以及錦上添花的可能性。
二、樣態的變化
借助數字技術的發明與運用,各類新媒體得到了不斷發展,紀錄片的樣態也因循而變,表現形式不斷豐富。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從一種過去只在CCTV-9 紀錄頻道播出的帶有官方制作色彩的紀錄片類型逐漸轉變為風格貼近大眾的由獨立制作團隊制作的“網紅”類型紀錄片,在其樣態和表現形式的轉變中,數字技術推動下的新媒體發展功不可沒。
互聯網時代下的娛樂方式從審美鍛煉轉變為“短頻快”的流量模式,以長線戰略為美學特征的紀錄片同樣也將被小而精的短視頻所取代。過去以非遺題材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固定的敘事手法、整體偏長的影片時長的特點使其無法在短視頻浪潮下謀求共生。如此一來,“微紀錄片”的出現成為必然之勢。微紀錄片最大的特征是截取最重要的信息,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傳播。它是快節奏的、碎片化的、十分割裂的,也是易表達的、快速傳播的、最有價值的。《如果國寶會說話》被評為2018年度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紀錄片,這不僅是非遺類紀錄片的突圍,更是紀錄片這一體裁在碎片化表達方式中的求新。以前三季播出的流量為例,該紀錄片在各大平臺上累計播放3449.9 萬次,收獲互動彈幕18.6 萬條,成為名副其實的非遺紀錄片爆款。①魏紅建:《新媒體語境中微紀錄片特征探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9 年第3 期,第68-70 頁。目前已播出的四季《如果國寶會說話》之所以能夠獲得網民的支持,根本原因是其較短的視頻時長適應大多數人的娛樂耐心:每季均有25 期視頻,而該紀錄片會把每期視頻長度控制在5 分鐘之內,完成了紀錄片從長到短、從“遇冷”到“爆款”的轉變與創新。
在極大縮減時長之余,加重故事性、減輕體量也是非遺類紀錄片的新特點。對于傳統的非遺類紀錄片來說,最常用的敘事手法是將故事與鏡頭聚焦在非遺傳承人身上,以人物的經歷、敘述牽引出觀眾對非遺藝術的關注。但這種敘述表達極其容易將觀眾的觀影心理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進而忽視了觀眾的參與,也大大降低了紀錄片的傳播效應。而微紀錄片在敘事手法上向故事化發展,以敘事視角的創新,人物、故事細節的選擇和提煉,以及戲劇性元素的增添,在遵從非遺類紀錄片真實性的基礎上,完善了紀實美學中極為缺乏的故事性與趣味性,調動起觀眾的興趣與參與感。在加重故事性的基礎上,使微紀錄片的時長大幅削減,整體時長把控在4~10 分鐘,形成了輕體量的非遺類紀錄片內容,回應著當下主流的碎片化語言表達。
提高科技比重,美化畫面。對于以非遺題材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歷史上缺少的圖文、影像記錄在數字化時代最好的呈現方式就是借助高科技將片段“演”出來。譬如在《如果國寶會說話》第一季的《錯金銀銅版兆域圖》《后母戊鼎》兩集中,前者采用三維數字動畫技術重現了《錯金銀銅版兆域圖》中戰國時期中山國國王對自己陵園的建筑設計;后者則采用三維數字動畫演示了學者推測的后母戊鼎制作方法的幾種可能性。這種方式既縮短了講解的時長,又代替了枯燥無味的旁白說教,還美化了紀錄片的畫面,大大提升了非遺類題材微紀錄片在各類平臺上吸引相關受眾注意力的能力。
弱化宏大敘事,增加情感表達。傳統以非遺題材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在敘事上比較官方和傳統,多為具有史料價值的有關國家、戰爭的宏大敘事,形式較為嚴肅枯燥。而在新媒體傳播下,受眾更偏向于較為輕松的生活化日常視角敘事,增添具備情感共鳴的表達形式成為非遺類微紀錄片的變化趨勢之一。在《如果國寶會說話》第一季中,央視制作團隊以自身過去未曾使用過的平民網絡化語句風格,例如使用“戰國黑科技”來描述《錯金銀銅版兆域圖》,使用“現在他的頭飾是風”來形容三星堆青銅人像中丟失頭飾的一尊特殊頭像,在網絡上激起極高的話題討論度。而在《海派百工》第一季中,大量設計的海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生活化個人敘述,營造了貼近生活的平民化視角,增加了情感方面人文關懷的表達,符合新媒體受眾用戶的審美傾向。
三、非遺類微紀錄片拍攝的不足及改進
(一)非遺類微紀錄片的不足
由于當代文化是視覺性占據主因地位的文化,圖像的生產、傳播和接受更加普泛化,更具顯赫地位。①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學術研究》2004 年第2 期,第110-115 頁。在各大新流量媒體平臺上播放的紀錄片,為了達到迅速抓住觀眾眼球、獲得播放量的目的,更加重視視覺方面的影響力與沖擊力。紀錄片創作者有時過于追求借助數字技術等方式形成的視覺效果,比如為了追求意境而大量使用慢鏡頭、添加一些與畫面內容有違和感的音樂、后期剪輯痕跡明顯等。過分追求畫面精美和過度的鏡頭語言違背了紀錄片創作的真實性原則,這是非遺類微紀錄片在追隨時代腳步及市場時所體現的不足之處。
另外,在互聯網通信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些非遺類微紀錄片呈現出一種時代裹挾下的娛樂化弊端。觀眾不再有耐心花很長時間觀看一部紀錄片,導致紀錄片創作者做出具有娛樂化傾向的改變。紀錄片創作者會因為設計戲劇性沖突而在創作中引導被攝主體進行表演,這不但與紀實美學的基本特征背道而馳,還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精神大相徑庭,也失去了其本質的魅力。
(二)非遺類微紀錄片的生長空間
未來以非遺題材為主要內容的微紀錄片在創作思維及創作形式上應做出相應的改進
首先,在創作思維上,數字技術促使非遺類紀錄片創作者進行相應思考。譬如在形式與內容的平衡上,長期性的“數字奇觀”會給受眾帶來審美疲勞,人們更需要內在的人文精神與民族文化。②徐濟炳、張名章:《淺析數字技術對歷史文化類紀錄片創作的影響》,《漢字文化》2018 年第9 期,第104-106 頁。作為非遺類紀錄片核心的非遺文化所展示的是民族的智慧和審美、民族獨有的文化烙印,創作者需要在創作前期就把控好“形式”和“內容”的比例,以展現內容為主、形式為輔,從而最終達到最好的呈現效果。
其次,在創作形式上,打造豎屏非遺類微紀錄片是短視頻發展的關鍵。由豎屏呈現紀錄片,其構圖有別于傳統的4 ∶3 或16 ∶9 比例的紀錄片,采用適合通過手機豎屏單手操作觀看的9 ∶16 比例。其在傳播上不僅契合兩微一端發展下新興媒介載體的短視頻平臺——快手、抖音等裂變式傳播和短視頻興起的細分市場③黃京京:《數字技術的二次指示對于非遺題材紀錄片的假定性探究》,碩士學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 2022。,還可以借助抖音等平臺的推送機制吸引到更多原先并非紀錄片受眾的新觀眾。在內容呈現上,采用9 ∶16 畫面比例的豎屏紀錄片能夠凸顯畫面主題,突出畫面細節呈現,與以非遺題材為主要內容的微紀錄片十分契合。而當下也有相應的豎屏非遺類紀錄片案例。如抖音視頻官方曾嘗試過此類創作,其平臺推出的《走丟的神仙們》是史上首部豎屏非遺類紀錄短片,且該紀錄短片的時長僅7 分40秒,以簡單的固定鏡頭作為普遍實用的鏡頭語言,采用了第一人稱的主觀敘述,運用大量的自我陳述、內心獨白和人物之間的對話,直接和鏡頭外的觀眾產生討論與情感勾連,勾勒出豎屏模式的最大特點——面對面交流。由此可見,非遺類微紀錄片不僅突破了體裁本身的限制,更跳出了文化傳播的傳統框架,未來仍有更多的創新模式亟待開發。
四、結語
數字技術在非遺類紀錄片創作的技術、藝術、指向性層面均有一定影響。非遺類紀錄片想要獲得新的機遇與發展,其根本是在遵從人文價值關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精神的同時,摸索一條數字技術和文化內涵契合的可取之道,把握好紀錄片、非遺類紀錄片的本質目的,處理好數字技術帶來的技術與內容層面的平衡問題,如此,非遺類紀錄片既能從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與深厚的歷史語境中汲取養分,也能乘著數字技術發展與變革的新風站上風口,謀求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