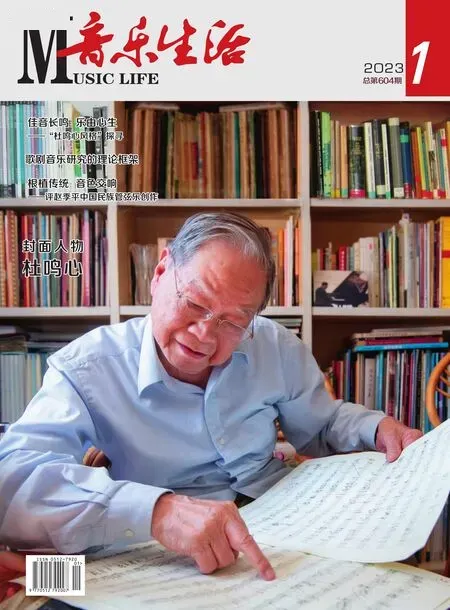中國人的藝術審美旨趣
——論“道”在音樂中的體現
武文華
“道”,是中國人審美旨趣中的最高標準和終極目的,也是人們理解和認識其他相應的中國傳統審美旨趣的一個最根本的前提。“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確如美學家葉朗先生所言——中西方分屬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各自有其巨大的特殊性,而中國論域的審美思維有著自身獨特的體系與范疇[1]。因此,筆者認為,形成“道”的如此格局、如此品位的審美認知觀念,是由中國人自古以來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多元性且包容的民族審美心理基礎以及超越性的思維方式等綜合因素所決定的。
一、作為音樂人,如何認識“道”的表象
對于華夏民族而言,“道”是人們絕對引以為豪的、能夠坦然地論及到的、長闊高深且終極般的宇宙威力,有集結洪荒之能效;“道”是人們若能夠恰當地運用好它,便可讓日常言說具有極強話語威懾力的一種語言修辭魅力。而作為音樂人的思維認知角度,筆者覺得,人們所觸及的“道”之表象,實際上是非常豐富的,因此,在中國話語的詞語現象中,“道”可謂無所不在。
而對于“道”這個概念,古往今來的中國民眾,似乎也并未將其特意地界定在僅為純粹哲思學意之領域才能觸碰的東西。恰恰相反,人們會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地在心目中建立起對“道”的威信感和信任度,對它大談特談并在言行中積極地實踐著對它的理解及運用,因此可以說,中國人是在極為廣泛的領域中,以或深或淺、見仁見智的表達方式,在實現著對“道”的親近;又或者說,人們雖對其有頂禮膜拜之情,但又存有未將其束之高閣之意。
形成這種傳統人文化神奇現象的一個根本原因,其實是不能脫離歷代中國人所喜愛、所敬仰、所推崇的“老子”來孤立看待的。正是由于這位中國先秦時期決絕的、奇異的、隱者型的偉大思想家,在其出關絕筆奇文《道德經》(或稱《老子》)中,為人們展示出了一個曠世奇才心胸內的某種純全至理的存在樣式,他同時又能以極其精辟、精深之言,來啟發和引導人們用超然、恬淡的處世之方,嵌合于這種存在樣式之中,而這所有問題的核心,都指向了“道”這個層面。誠如哲學大儒張岱年先生所說[2],在目前所發現的中文典籍文獻里,最早、最明確、最系統化地言說了“道”的,當屬老子之《老子》。雖然后世的飽學之士們,對老子思想及其“道”的認知上,還有不斷的發展與衍生成果,但達到極致透徹、最具有本質哲思能量的言說,仍要聚焦于老子思想的這個本初的原點之上。
“道”,是老子思想中無論在哲學本體論意義還是在自然生成論意義上,都具有核心地位的終極概念。老子以“道”為中心,建立了系統化的、充斥了方方面面并涉及六合內外的智慧思辨。而這種超越性的主體思維意識,不僅長久地扎根在中國人的頭腦意識中,也深深地震撼了西方近代以來的著名學者們、影響了其哲思理念,他們仰望和熱切關注了這些思維閃光點,在其治學中確實地引用及借鑒了中國古代先哲們這些精神要旨,比如叔本華、比如尼采、比如海德格爾……
二、作為音樂人,如何認識“道”的本質
以“道”為思維核心的老子思想及其表達,在筆者的心目中,是被當做中國先秦以來最為超絕、最為冷靜的詩思一體的“詩學”來看待的。接受主體對其所形成的思維理解,不可能也不應存在一言以蔽之的終結感,或是一家之言的治學話語權。同時,對它們不進行過分解讀、不牽強附會地做以絕對化的主觀理解與闡釋,也是主體在針對性認知思維時需要了然和積極反思的地方。
強調這一點,是由于老子在其思想表述的一開篇,就立論了意識基調——“道,可道,非常道”[3]的認知原則和邏輯起點。因此,作為音樂人,筆者認為對相關內容若帶有主觀性太強的主體思維命定的話,那么所作出的主體思維延續、外化闡釋與傳媒行為的本身,就有可能已走入“過猶不及”的思維謬誤中去了,從而也就會背離《道德經》啟示人們所應避免的思維認知閾限的這一原初本意,繼而更會影響后學后進們對老子思想大道至理的合理接受與傳播。為此,筆者在本段中僅想遵循“老子思想”的開篇規訓,用謹慎和盡量客觀的態度,來表述自我意識中相關“道”的本質認識。
老子思想中所講的“道”,有視之不見其色、聽之不足其聞、觸之不得其形的“夷”“希”“微”的綜合特征[4],它處于“恍惚”“窈冥”“渾成”的難以形容的狀態,它是“玄之又玄”[5]的世界萬事萬物的本源,是效法自然存在法則(也即自然而然地存在著)的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又是讓一切對立之面處于相互變化、相互運轉的和諧統一之境,讓一切有、無、虛、實等的對立傾向性,在“道”中可以各安其分、各司其職并且不斷地變換、往復及更新。
葉朗先生的審美觀念中,有兩處表述特別令人受啟發。其一是中國古典審美之中,“美”并不是中心范疇,也不是最高層次的范疇[6];其二是中國古典審美不像西方那樣重視“美范疇”,而是特別重視“道”“氣”“妙”等范疇[7]。因此,這種對“道”的規定性和對“道”的具體考量,已然體現出的是——作為中國傳統的哲思理念,相對于西方認知層面及其方式而言,具有非凡的思維超越性,因其超越了西方論域中人們僅將“美”的存在和對“美”的追求作為哲思學意終極目的之做法。
除了老子思想之外,在儒家圣賢孔子這里,也有類似的觀念方式[8]。這種不同于西方哲思學意的超越性,為人類的思辨世界提供了如何擺脫、突破純粹理性的物我兩分、主客對立以及生硬分割或認知等的思維局限的可能性,建立出了屬于中國情志的成功的思辨路途,更是在這個以中國為經典代表的東方哲思智慧的路途上,形成著一道道屬于中國傳統審美思維品格的、極為獨特的哲思“風景線”。
在音樂學界中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主要是集中在老子思想的如下相關之處:《德道經》第2 章中的“音聲相和”、《道德經》第12 章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道德經》第35 章中的“樂與餌,過客止”、《道德經》第41 章中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等哲思及審美命題。這些和音樂藝術有密切關系的表述[9],本質上都反映出了“道”的本質在音樂藝術具體存在方式中的細節表現,并且在全文的表述中,老子已經向后世給出了他的具體回答。
如第14 章中明確說了符合“道”的大音,不是完全沒有聲音的那種沉寂,而是聽之卻不足以感受到的樣態,這使得正確理解“希”涵義成為主體合理接受“大音希聲”的命脈之處;也如人應該效仿水的本質,也即“上善若水”[10],還如要以“能如嬰兒乎”[11]“復歸于嬰兒”[12]的純粹、無雜的樣子來融合于天地萬物之中等表述,便使某種不同凡響的領悟充斥進了主體接受過程的心思意念之中。
因此,老子的這些經典觀念在音樂藝術的思想界里,常常被奉為某種圭臬般的思維認知的標準,被加以高頻次引用或細讀化論證,而這種本質認識,不僅承接了源自中國先秦時代的經典的古思古意,同時對當下音樂藝術的實踐方式和實施路徑,也能夠做出方向性的啟示與指引。
三、“道”在音樂藝術中的存在方式
作為筆者所認定的充滿了詩與思之交融辨析、詩學特征極為鮮活和峻拔的老子論道思想,思考其核心的“道”之命題在音樂藝術領域中如何被良好地體用,應是一個非常有學術價值的論題之一。
對于音樂作品而言,“道”在藝術存在方式的意向上,是該作品內在的精神氣的絕對支撐力量,是音樂藝術見仁見智的個性化情感表達以及繁復多樣化之藝術形式的根系土壤,因此,音樂藝術作品中的“道”,是聲音藝術的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絕妙統一。它有源源不絕的、強壯的、堅固的能勢,往往示意或象征了作品音符背后蘊含著的作品的精神性指征,指向著主體藝術創作的本質動力和審美意象,這尤其在中國傳統題材的器樂作品中(如古琴藝術)、古意盎然的聲音作品中(如古詩歌藝術歌曲)等中最為常見,它也或顯或隱地存在于那些意在取趣于華夏文明之古韻悠揚意境的當代音樂創作里。
這首先體現在音樂作品的標題性方面。中國人的音樂創作,往往喜好凸顯作品標題的審美意識,標題文字是理解音樂作品精神品質的最外顯的能指之所指,這既是國人成樂風格的一大重要特征,也是國人藝術審美情趣的語義化的“道”之顯現。往古來今,經典和優秀的音樂作品標題可以說是浩如煙海、繁若星辰,筆者在此并不欲贅述,而筆者意想說明的是,音樂標題集約地表達了中華文字在形、聲、意、趣中種種奇妙的立意與境界,絕大多數的標題還能夠以短小精悍的文字樣式,向人們呈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之貌;其標題的設立范圍也是無所不包的,具體內容的所指可以輻射人世間的千形萬象;其文字攫取往往極盡中文語境的至高修辭藝術,讓人必然感喟于音樂藝術抽象性、特殊性存在價值之一斑;其審美朝向基本上也是在言說主體藝術創作在內心中最深層的關懷之處。因此,這些音樂作品的標題,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人們理解音樂作品本質內涵的秘密通道,仿佛“道”之觸須一樣,沿著它們的內涵與外延,受眾們將通向觀照、解析音樂作品本質內涵的聽樂路途。
其次,“道”體現在音樂作品音響表達的表意性方面。這是“道”在音樂作品音響實現中的重點生成部分,也是中國音樂在生命化存在方式上的某種印跡。對比西方音樂作品構成因素,也除卻部分國內少數民族音樂表達的和聲意識來看,國人成樂的優勢之處和經典所在,主要在于高度發達的、精致唯美的單旋律創作思維與手法,這種音樂性帶有極為強大的東方情懷的藝術表意功能,致力于展現音樂作品中最細膩和最深層次的藝術想象力、詮釋力,其在聲、音、樂的各個具體層次中,盡情地做出生發、生長、極致與消散之勢,同時還具體結合了創作、表演主體對于音響實現過程中的各種聲音技巧的控制與規定性,其存在價值是要全然地將藝術本質中的活態的、屬于人之本性的生命張力和人文脈動勾勒出來,映射于接受者參與下的藝術時空之中。
最后,音樂作品在整體意趣上更加透視出“道”的存在方式。不論是作品標題的具體提立意或設意,還是作品音響實存的生命式的細節展現,都是包納在音樂作品的整體意趣之內的。在華夏樂藝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尋求樂音中最終顯現出來的與自然萬物融合共構的審美意趣,是中國人不同于西方強化理性認知結果的一種本質表達,也是作品藝術本質之“道”在人的藝術經驗之內的外化形式。國人歷來崇尚德行高潔、靈性解悟、旨趣淡遠的存世倫理價值取向,此謂賢良之才、君子之風的陽春白雪之雅趣;但也相應地保留了下里巴人之境,在藝術歷史的演繹中,曾不斷地涌現出豐富多樣的民間音樂藝術,如大量優秀的民間曲藝、地方戲曲等,它們在各自的鄉土地界形成著形形色色的、有著充沛藝術受眾群體的存在方式,其中不乏“大丑中有大美、大俗中有大雅”之象,此種生命本真狀態,亦是中國傳統審美意趣的折射點之一。
注釋:
[1]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2頁。
[2]“最初提出道論的是老子”,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商務印書館,2015年12月版,第79頁。
[3]見《道德經》第1章所記。
[4]見《道德經》第14 章所記——”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
[5]見《道德經》第1章所記——“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6]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3頁。
[7]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3頁。
[8]孔子在其治學中“善重于美,對善與美做了主次、先后之分”。張前:《音樂美學教程》,上海音樂出版社,2022年2月版,第14頁。
[9]蔡仲德在其《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釋》(增訂版)中,對《道德經》的第2章、12章、35章、41章的具體關涉內容,進行過專章的解析與闡釋。
[10]見《道德經》第8章所記。
[11]見《道德經》第10章所記。
[12]見《道德經》第28章所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