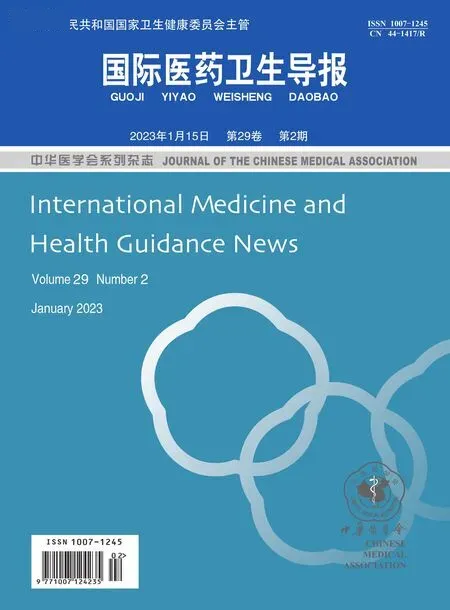神經型布魯菌病的研究進展
林怡如 王波 丁國鋒
1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感染性疾病科,濱州 256600;2 青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青州 262500
布魯菌病(brucellosis)是一種由布魯菌感染所致的人畜共患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列為乙類傳染病。人感染布魯菌后主要臨床表現為發熱、乏力、大汗、關節疼痛等[1]。布魯菌病的誤診誤治增加了相關并發癥的發生概率[2]。布魯菌感染可出現中樞神經系統、骨骼系統、生殖系統、循環系統、呼吸系統等的并發癥[3]。神經型布魯菌病是布魯菌病神經系統的并發癥,出現概率較低但通常比較嚴重[4]。由于該病臨床癥狀多樣且不具有特異性,診斷和治療困難,若患者未得到及時診治,可導致死亡或遺留后遺癥,因此對于神經型布魯菌病應給予高度的重視。本文對神經型布魯菌病的流行病學、發病機制、臨床表現、診斷標準以及治療預防予以綜述,為該病診療提供理論依據。
流行病學
布魯菌病是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人畜共患病之一,每年約有50 萬個新發病例出現,但分布并不規則,其中地中海盆地、沿海地區、南美洲和中美洲是該病的高發區[5]。在我國農牧養殖地區,比如內蒙古、西藏、新疆、寧夏、青海等地發病率較高。近年來非農牧養殖地區也出現散發病例[6]。隨著我國國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飲食結構的變化,布魯菌病發病率呈現逐年上升態勢,進入2000 年后,布魯菌病發病率由1993 年的0.028∕10 萬,上升至2015 年的4.183∕10 萬,2016 年有所下降,2019 年又呈現出回升趨勢,2020 年的發病率為3.370∕10 萬[7]。神經型布魯菌病在布魯菌感染患者中占0.5%~25%,占比差異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布魯菌培養的靈敏度較低以及神經型布魯菌病的診斷標準欠缺[8]。神經型布魯菌病在全球范圍內的布魯菌病流行地區構成威脅,其中年齡的增加以及基礎病的存在是神經型布魯菌病的危險因素[9]。
布魯菌是非運動性革蘭氏陰性桿菌,沒有鞭毛或纖毛,在含有5%~10%二氧化碳的培養基中可以緩慢生長[10]。該菌目前被證實由10 種菌屬組成,其中5 種對人類有致病作用,分別是羊種布魯菌(brucella melitensis)、牛種布魯菌(brucella abortus)、豬種布魯菌(brucella suis)、犬種布魯菌(brucella canis)和海洋布魯菌(brucella marina)[11-12]。布魯菌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傳播給人類,常見的途徑包括病菌污染環境后形成氣溶膠通過呼吸道傳染、攝入未煮熟的牛奶或其他奶制品通過消化道傳染[13]。除此之外,對于已經感染布魯菌的動物進行處理也可以導致感染的發生。人際傳播比較罕見,但有文獻報道人際間可以通過垂直傳播、性傳播、輸血等途徑發生[14-15]。布魯菌病的發生未表現出季節性規律,但我國神經型布魯菌病常在每年4、5、11、12 月發病,這與牲畜的生產及宰殺時間密切相關。導致我國神經型布魯菌病的兩大主要來源分別是羊、牛[16]。
發病機制
神經型布魯菌病的發病機制較為復雜,其中細菌、毒素、變態反應等均不同程度參與疾病的發生、發展,目前具體機制尚不明確。
研究顯示,布魯菌感染網狀結締組織中的巨噬細胞并可在巨噬細胞中存活較長時間,從而導致菌血癥的發生[17]。隨著血液流動布魯菌進入腦膜,當機體免疫力下降時,細菌進一步增殖擴散進入中樞神經系統。布魯菌可通過直接蔓延的方式導致中樞神經系統受損,也可以通過肉毒素、免疫性炎性反應間接使中樞神經系統受損。
Miraglia 等[18]研究發現,采用體外人腦微血管內皮細胞模型研究布魯菌與血管內皮細胞關系時,細菌可以通過感染單核細胞穿過血腦屏障,也可以利用血腦屏障細胞間的非細胞遷移穿過血腦屏障。布魯菌能夠粘附并入侵人腦微血管內皮細胞有賴于真核細胞中微絲、微管、從頭合成蛋白等。血腦屏障的激活與功能障礙也是神經型布魯菌病發病的機制之一。人腦微血管內皮細胞激活需要白細胞介素(IL)-1b 免疫介導,在布魯菌侵入人體后,可使神經膠質細胞分泌IL-1b,最終導致血腦屏障內皮細胞破壞,血管的通透性增加,從而使細菌直接或間接侵入,最終導致中樞神經系統感染[19]。
臨床表現
在神經型布魯菌病中,神經系統可以是多個受累系統之一,在極少數情況下,神經系統的癥狀也可能是布魯菌病的唯一臨床表現[20]。
根據臨床表現的不同,神經型布魯菌病感染者可分為4類:中樞神經系統受累、周圍神經系統受累、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聯合受累、孤立性聽力損害[21]。當布魯菌病累及中樞神經系統的時候最常見的表現為腦膜炎、腦膜腦炎、腦脊髓膜炎、面神經損傷等[22],其中腦膜炎或腦膜腦炎為臨床中最常見的類型,占50%[17]。也可見短暫性腦缺血發作、腦梗死、蛛網膜下腔出血、顱內靜脈血栓等腦血管受損表現[23];單純顱高壓、吉蘭-巴雷綜合征、神經型尿崩癥等為其少見的臨床表現[24-25]。周圍神經系統受累較中樞神經系統受累常見,且感覺神經更易受累,常見的臨床表現有肢端麻木、痛覺過敏、灼燒感、腱反射消失或減退等,周圍神經受累時,電生理改變同時存在軸索損害及脫髓鞘損害[9,26]。Gul等[5]對187 例神經型布魯菌感染的患者進行了分析,發現在布魯菌導致的腦神經損害中,外展神經與聽神經最易受累,其次為面神經。外展神經由于解剖結構的特殊性,容易受到直接或間接的損傷。聽力的喪失考慮是由于聽神經受損導致聽覺通路受損或內毒素痙攣所引起的血管痙攣從而導致神經缺血。神經型布魯菌病還可以導致腦血管受累,主要通過兩種機制發生:一種為細菌性動脈瘤的破裂[27];另一種則為血管的炎性反應[28]。
神經型布魯菌病由于沒有特殊的臨床癥狀,因此在農牧養殖地區,當患者出現神經系統癥狀并伴隨發熱時,需要與布魯菌病進行鑒別診斷[17]。
診斷標準
對于神經型布魯菌病的診斷標準,目前尚無專家共識。當患者臨床表現符合神經型布魯菌病且有以下標準者,可以診斷為神經型布魯菌病[20]:⑴流行病學密切接觸史;⑵腦脊液中分離出布魯菌或檢測出布魯菌抗體(任何滴度);⑶經過治療后,臨床癥狀得到改善;⑷除外其他類似疾病。
根據研究,45%的神經型布魯菌病例會出現影像學改變,包括腦膜炎癥表現、顱神經受累、腦膿腫、蛛網膜炎、肉芽腫及血管變化等[29-30]。神經型布魯菌病患者可根據頭顱MRI表現的不同分為4類:正常表現、炎癥改變(異常的增強信號)、白質改變、血管改變[31]。因此,中樞神經系統影像學的改變在神經型布魯菌病的診斷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于中樞神經系統彌漫性受累的患者而言,預后較差,雖病死率較低(<5%),但20%~30%的患者會出現后遺癥[10]。早診斷早治療可改善患者預后。
由于虎紅平板凝集試驗、標準試管凝集試驗等傳統的輔助檢查方法靈敏度、特異度較低,且存在實驗室污染風險,同時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具有特異性強、靈敏度高、操作簡單等優勢,可作為血清學檢測陰性患者的補充試驗[32]。Kattar 等[33]對收集的354 份樣本進行了PCR 檢測,結果證明16S-23S 為引物和探針的實時PCR 靈敏度最高,且內部轉錄間隔區(ITS)PCR 是可以增強人感染布魯菌病診斷的檢測方法。除此之外,馬匯豐和張哲林[34]研究表明炎性因子IL-1β、IL-6 對神經型布魯菌病有重要指導意義,上述兩種炎性因子在神經型布魯菌病患者的血清及腦脊液中高表達,檢測靈敏度高,可為早期神經型布魯菌病診斷提供依據。
治療及預防
早期正確的治療對于神經型布魯菌病患者而言十分重要。藥物治療是其主要方法,由于布魯菌主要在細胞內生存,普通藥物很難進入細胞徹底殺滅細菌,因此人感染布魯菌后較難根治且易復發[27]。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對急性期布魯菌病治療選擇多西環素(100 mg bid)聯合利福平(600~900 mg qd),治療時間為6 周[35];目前,國內多選擇利福平、多西環素為基礎藥物,同時聯合奎諾酮類或氨基糖苷類或頭孢三嗪進行治療,一般可達到較為理想的效果,但還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個體化方案的制定[36]。對于慢性期布魯菌病則傾向使用中西或中西蒙結合的方法進行治療[3]。N 等[37]研究發現,蒙藥聯合抗生素治療可降低抗生素的毒性,避免耐藥性的發生,同時還可以起到預防布魯菌感染的作用。
總體上對于布魯菌病的治療應遵循以下原則[38]:⑴抗菌藥物需在酸性介質以及細胞內發揮作用;⑵聯合治療;⑶根據感染系統的不同,適當延長藥物使用時間。針對神經型布魯菌病患者藥物的選擇不僅需要遵循上述原則,還應在此基礎上聯合使用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具有滲透作用的抗生素。頭孢曲松因其可以穿越血腦屏障并與神經系統中的目標受體相結合,在治療中應作為首選藥[39]。選擇以長療程或多療程進行治療,治療持續時間的判定以患者臨床表現好轉以及腦脊液檢查恢復正常為準。除此之外,對于出現神經系統癥狀的患者建議加用改善循環及營養神經的藥物對癥治療[27]。
布魯菌病的慢性損傷影響患者的日常活動,且該病反復發作難治愈,消耗醫療資源,對個體、家庭、社會都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對于布魯菌病的預防也同樣重要。由于布魯菌為胞內寄生菌,疫苗免疫被認為是最有效的預防措施[40]。有研究記錄,滅活的布魯菌疫苗曾被用作進行人群免疫,但效果并不顯著。另外,用于動物進行免疫接種的相關疫苗,對于人類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應[41]。因此,至今為止還沒有可用于人類預防布魯菌感染的疫苗[42]。
除疫苗接種外,對于從事畜牧業人群進行疾病預防等方面相關的健康宣教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對奶制品進行有效的巴氏消毒。另外,由于該病為人畜共患病,當動物感染布魯菌后,妥善處理血清反應陽性的動物,以減少健康動物的感染率,同時對動物進行疫苗接種可以減少布魯菌病給在流行地區的傳播,也是防治布魯菌病在人群中傳播的重要方法[43]。
總結與展望
布魯菌病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國內外關于神經型布魯菌病的報道相比于其他疾病較為少見。該病危害較大,但由于該病臨床表現不具有特異性且缺乏可靠的診斷標準及治療方法,容易出現漏診、誤診,從而錯失最佳治療機會,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神經型布魯菌病的發病機制,為制定明確的診斷標準及治療方案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