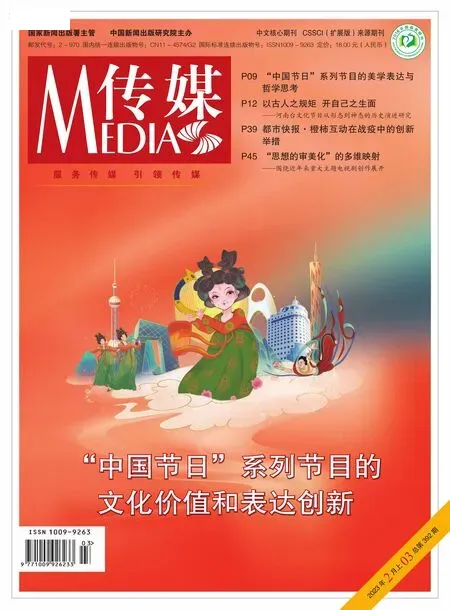社會化媒體對使用主體的監視與規訓
——基于“空間”視角
文/卜祥維
隨著媒介技術的更迭、社交媒體的發展,以微信、微博、抖音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早已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不僅打開了認識新世界的大門,還為人們提供了傳播和分享觀點的入口。在大家歡呼雀躍,積極擁抱新媒體技術帶來的諸多便利的同時,我們也應警惕伴隨其而來的諸多問題。前人早已發出諸如“娛樂至死”“消費社會”的警示,而如今對社會化媒體時代而言,這些問題似乎并沒有減輕,反而又增添了許多新的問題。文章基于“空間與規訓”的視角,分析社會化媒體之下隱藏的“控制”問題,以期為沉浸在這場狂歡中的人們提供一些警醒。
一、物理空間:從“空間規訓”到“空間生產”
權力主體通過對“空間”的設計來滿足其“監視”的要求,從而達到“規訓”的目的。我們如果從“空間”生產本身的角度出發,也可以將這個過程理解為是對空間的透明化處理,從而讓個體處于被看見的狀態。因此“空間規訓”也可以說是一種對空間可見性的生產。
1.福柯的“空間規訓”。在1975年出版的《規訓與懲罰》中,福柯對他的“空間規訓”思想做了系統的闡述。“在福柯看來,空間的規訓本質上就是一種對空間的監視”,他從懲罰形式的歷史轉變分析,認為懲罰形式從對肉體的毀滅到對精神懲罰的轉變,其目的之一在于培養“溫馴的人”。比如,使農民成為一名優秀的工人和士兵,使兒童變成一名合格學生等。福柯稱之為對人的“規訓”,而精神懲罰的手段是通過“監視”來完成。
對于監視,福柯借助于圓形監獄空間的設計——認為這種前后透光,圍繞中心監視塔鱗次櫛比環形排列的牢房設計——是權力形式表征性運用的典型。在這種監獄空間中,被囚禁者能清楚地目睹監獄中心監視塔的高大輪廓,卻不知道自己此時是否被監視。借此福柯認為,現代社會管理的基本空間構型就是這種“全景監獄”的模式,它的功能是對權利空間化的處理,比如“學校的考場、購物中心鏡頭、各行各業的保安和警察,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在起著某種類似的監視或注視作用”。總之,在福柯這里,他關注的是權力對于空間的設計與利用,從而對人進行監視和管理。
2.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與福柯相比,“列斐伏爾更關注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從關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出發,強調“空間”在整個生產中的決定意義。他認為對資本的生產首先體現在對“空間”本身的生產過程,因為物質的生產離不開空間意義上搭建的生產關系。比如,由資本家和工人的生產關系構成的“工廠空間”的生產成為產品生產的起點,由賣家和消費者關系構成的“商業街空間”的生產成為商品與消費的起點。因而工廠、商業街、購物中心這些空間本身就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物質生產資料。
伴隨著作為“物質生產資料”的空間生產而來的是社會關系的加固和生產,如地產商對某個區域的開發,不僅是生產出幾座高樓和幾個商業空間,更是生產出某種隱秘的經濟關系。而商業街、購物中心等配套設施的投入使用,帶動了地方的經濟布局,更帶來了一種消費關系、一種消費生活方式,這必將影響生活在此空間內人的關系、思想和行為。
二、從“物理性”走向“虛擬性”的空間
在前面的介紹中,無論是福柯還是列斐伏爾,其都是在物理空間的層面討論各自的問題。如今,世界早已進入互聯網時代,上網或者數字化成為人們生存的一種常態,空間理論的發展也從單一的物理空間走向了物理和網絡空間共存研究,比如,紐曼爾·卡斯特的“流動空間”思想,齊格蒙特·鮑曼的“液態現代性”、戴維·哈維的“空間壓縮”等都是對傳統空間理論的擴展。其中又以卡斯特的“空間流動”思想傳播最廣,因此下面就對其進行簡單介紹。
1.卡斯特的“流動空間”。相較于福柯和列斐伏爾關注固定的物理空間,卡斯特敏銳的發現網絡空間中“流”的特征。何為“流”?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卡斯特對社會的流動性解釋為“社會行動者所占有的物理上分離的位置之間那些有所企圖的、重復的、可程式化的交換與互動序列”。得益于互聯網和傳播技術的進步,卡斯特認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在資本流動、信息流動、組織流動、技術流動、符號流動等各種‘流’的作用下,一種以流動為主要特性的新空間形態產生了”。與傳統的有固定生活地點,受法律法規制約,生活與行動往往受到當地文化背景、政治生活、經濟水平等的影響的傳統地方空間不同,流動空間更側重變化的、流動的結構關系,這種流動性打破了原有地方空間所強調的邊界,打破了原有行政區劃的限制。因此在網絡中,過去、現在、未來被壓縮和被拼貼在一起,在對速度和流動性的追逐中,空間被壓縮,原本互不相通的空間也被鏈接起來。
卡斯特進一步指出這種流動空間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電子交換技術構成的信息回路;二是由節點和核心構成的信息網絡;三是由管理精英掌控的空間組織。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以及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到來,流動空間的技術支持變得更加完善。首先,基于地理位置的信息技術的應用,使得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產生了實際的連接,虛擬和現實的切換變得更加容易。其次,5G、大數據、人工智能、VR、AR等技術的應用,使得數據的生產、傳輸、利用越來越方便,空間的打造越來越趨向于虛擬和真實的融合,甚至是完全的虛擬化,因此對應的社會實踐也必然更多地走向這種新的網絡社會之中。除此之外,社會化媒體之下,不得不提的一大特點就是“碎片化”。
2.社會化媒體下的“碎片化”。隨著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微信、微博、抖音等社會化媒體逐步融入我們的生活,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碎片化”,直接體現是日常生活的碎片化閱讀、碎片化交流,或者概括來說,體現在我們碎片化的實踐當中。碎片化似乎已經成為我們的一種生存狀態。就空間層面而言,一方面,碎片化傳播入侵了傳統的大空間,使之分散、瓦解,使得空間的整體性被割斷、被撕裂。比如教室在傳統媒體時代對于學生和老師來說是一個整體性的存在,而智能手機的入侵,導致學生和老師的生存早已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的教室,而走向了更大的社會網絡空間之中。另一方面,這種碎片化傳播激活了被遺忘的邊緣空間。在人類的實踐空間中,除了學校,工廠,商場等這類整體的空間之外,還有諸如分布于這些空間之間的縫隙空間,如上班路上,電梯內,課間休息等。這些被列斐伏爾看作垃圾的空間,如今統統被激活。究其原因,這依賴于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使得人人隨時隨地都能鏈接到網絡之中;同時社會化媒體之下,生產出的大量的碎片化的微文本,如簡短的微博信息,實時更新的朋友圈,大量生產的幾十秒一段的短視頻等等,而這些微文本就成為點亮這些黑暗的碎片化空間的最理想燃料。正如等車、等電梯以及課間休息,在一切可以利用的碎片化間隙中,你總會發現人們迫不及待地刷微博、刷短視頻的身影。因此,原本被遺忘的這些邊緣空間,在社會化媒體背景下,就成為連接網絡世界的中介。
三、社會化媒體背景下的碎片化空間生產、監視與規訓
基于前文對空間的理解,我們可以分別從“空間生產”“監視”“規訓”的批判視角來分析社會化媒體背景下發生的一系列變化。
1.從“碎片化空間”的可見性生產到“流動空間”的可見性生產。社會化媒體的背景之下,人人都能接入到互聯網,社會媒體軟件的使用,使得人們處于“數字化”生存當中。新媒介技術使用,成為如電一樣不可或缺的背景性存在,早晨醒來的第一件事是打開手機翻看動態,出行路上依賴“百度地圖”等軟件的導航,工作中更是離不開各類軟件的使用,甚至吃飯、睡覺都需要相關APP“協助”,電子設備早已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但從空間生產的角度,資本在推動這些媒體技術走向大眾化的過程也是對“碎片空間”的開發與利用的過程。它使原本被人們遺忘的,黑暗的角落成為資本生產的空間。如對車體空間、地鐵空間、電梯空間等的利用,成了車體廣告,地鐵廣告和電梯廣告。如果說早期資本對空間的開發還比較機械、單一與不完全,那么如今的微信、微博、抖音等具有社交屬性APP的出現則直接宣告了碎片空間的“不可見性”“私密性”的全面死亡,它使得人們走向了一種幾乎“全透明”的狀態。
不僅如此,資本對空間的追逐還在不斷延伸。網絡時代,人們的生活空間從具體固定的分裂的物質性空間走向了卡斯特所說的“流動空間”,這種空間與空間之間“流”的過程,以及對應人際關系的流動化聚合與再造狀態,構成了網絡時代個人生存的基本特征,而資本對空間可見性的追逐也進一步關注了“流動空間”的整體可見性,已達到資本對整個空間的跟蹤利用。比如,微信的附近好友功能,百度地圖會隨時顯示你周邊的各類場地信息功能,KEEP運動APP的運動軌跡全記錄功能等等,這些基于LBS技術和圍繞社交屬性打造的APP正在記錄我們的生活“流”,更有像智能手表等穿戴設備的全天候跟蹤與記錄。當然,我們不要忘了對空間的生產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過程”,社交媒體的出現重構了新的社會關系,無論是隨意加入的豆瓣小組,拉取的微信群還是以維基百科構建為代表的“自組織”,都無不在告知我們的社會開始從“熟關系”走向一種“弱關系”,而這個過程正是通過碎片化空間的社會化途徑得以實現。
2.從“全景監獄”到“多數人看多數人”,從他人監視到自我監視。從“監視”的角度看,現代社會已不僅僅是“全景監獄”的“少人看多數人”的狀態,而成了一種“多數人圍觀少數人”與“多數人看多數人”的新“監視”形式。社會化媒體背景下,技術的賦權使得人人都能輕而易舉接入互聯網并參與圍觀和信息的生產,同時人們也更愿意分享自己的信息。比如,人們會在微信、微博進行動態發布以及對事件進行評價和分享,會在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隨時隨地拍攝分享自己的現實狀態。正如某APP的口號所說的那樣“隨時隨地發現新鮮事,隨時隨地分享新生活”。而這些分享與發現的背后其實可以理解成是一種“看”與“被看”的狀態。典型的如微博熱點,它會使某個事件,某個人物瞬間成為人們圍觀、談論的對象。再比如,抖音短視頻的上傳與分享實際是一種“多數人看多數人”的行為,你在看其他人表演的同時,他人也能看到你的表演。
更進一步,福柯則從這種“看”的行為中看到了一種新的監視方式——“自我監視”,“人們開始把單純是別人對自己的監視或注視轉變為自己看待自己行為的一種方式,也即由注視或關注別人轉變為注視或關注自己”。比如,現在的人拍照一般都會開美顏,朋友圈分享動態甚至會強迫性地處理每一張照片并且將九宮格填滿,對應的文案更是字字斟酌。再如,人們總是喜歡第一時間分享最新流行的熱點信息,怕自己沒能趕上時代的潮流等等,這些行為的背后是現代人越來越重視網絡中自我的“印象管理”,同時也是人們開始漸漸走向“自我規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性、多樣化逐漸被單一、流行所取代。
3.從強制鎮壓到消費塑造,從精英制定標準到共同定義標準。在福柯看來“監視”的目的是“規訓”,權力主體通過對空間的規訓從而培養出“溫順的人”。社會化媒體下,監視形式的變化也帶來了“規訓”樣式的變化。具體而言,一方面,“消費主義”如今早已成為社會的典型特征,一切的行為主體都可被稱為“消費者”;一切的事物都可能變為商品;一切經歷皆可成為消費選擇的經歷。人們在不斷被創造出的需求中迷失了自己。不僅如此,在廣告和營銷的作用下,物質消費走向符號消費,符號消費成為身份、品味、個性的象征。也正是在消費實踐過程中,一種隱含的新規訓形式誕生了,這就是消費塑造的統治模式——“它以誘惑取代鎮壓,以公共關系取代警察,以廣告取代權威性,以創造出來的需求取代了強制性規范”。仿佛一切的問題都能歸因于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時一切的問題都能通過消費得到解決。在對消費需求的追逐過程中,人們被馴化成一種溫順的消費物種。
另一方面,標準的制定也從精英制定走向共同定義。早期標準的制定,它更多來自精英階層以及歷史文化當中,人們對權威的重視讓他們所發表的言論成為普通大眾行為的準則。我們知道,官方媒體曾是權威的象征,因此傳播效果非常好,但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人們開始對權威產生懷疑,諸如官方媒體的傳播效果也越來越小,隨之而來的“標準”來自于大眾自身。社會化媒體時代下,人們開始越發關注自己,越發地重視別人對自身的關注,關注自己是否符合社會的審美標準,是否符合特定圈層的文化規則等等,但要知道,這些標準,這些規則卻又是通過無數個像自己一般的個人在背后通過點贊、分享而形成的。用福柯的話說這是一種“自我監視”,一種“自我規訓”,“其后果之一將形成一種新的‘正常和正當’的標準,也即一種普遍的社會標準,一種帶有強制性的道德體系和價值標準”。只不過這種“標準”的制定來自人們相互“監視”的結果。再比如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對價值的定義同樣發生了變化,流量成為一切的衡量標準,短視頻點贊量多的,評論多的會優先被看見,公眾號文章的好壞直接的評判標準也成了閱讀量和點贊量。可以說我們正經歷一種用時間篩選經典到流量定義價值的過程,符號的無限堆積帶來巨大傳播力量的同時其背后是對文化多樣性、價值多樣性的壓迫,是對“價值標準 ”的一種重新定義。
四、結語
社會化媒體之下,資本全面入侵了碎片化的空間,使得我們走向透明化的存在。其結果是,在看與被看之中形成對他人甚至對自我的監視;在分享和點贊中形成新的社會標準;在無限的欲望和符號消費中成為溫馴的消費物種。總之,社會化媒體之下,這種控制不知不覺,悄無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