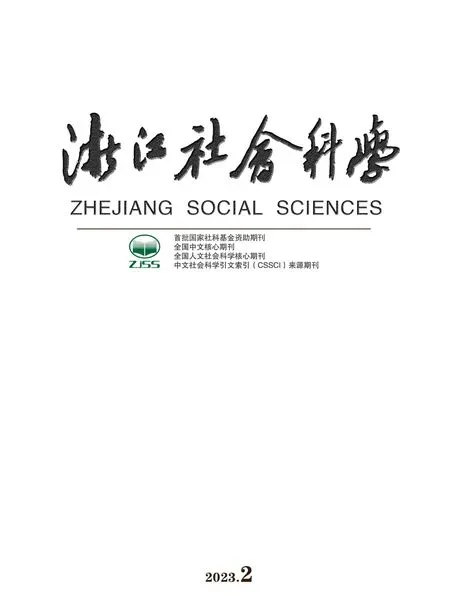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的面前?何種平等?
□ 駱意中
內容提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視為法律的一項基本原則,但是該原則的適用范圍,以及具備何種效力卻是不清楚的, 并且將其具體化為同案同判原則仍然將面臨冗余的懷疑。 內在于法律本身的平等在概念上依賴于規則的一般性,這是因為法律中的平等原則范圍只能是在適用法律中的平等, 而無法完全保證法律內容中的平等, 并且也不能等同于完全正當的判決。 但是,平等原則在法律制度中通過抽象化的方式予以實現,并且該形式性的平等原則仍然具有實質平等無法替代的規范重要性。
引 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下簡稱“平等原則”)作為基本原則的地位, 被所有秉持現代法治理念的法律體系所確認。僅以中國現行法為例,該原則在我國的根本法與部門法中反復被強調:比如《憲法》 第三十三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除了該一般性條款之外,《憲法》第四條和第四十八條還分別強調,公民的平等權利不受民族與性別的影響。 而民法作為調整平等主體間法律關系的部門法, 該原則在本質上必然就成為了其根本性的法律原則之一。《民法典》總則部分第四條規定:“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并且第十四條還專門規定了自然人享有平等的民事權利能力。然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 一方面平等原則被視為法律常識與基本原則, 但與該原則不可撼動的地位相反,學界對于該原則究竟意味著什么,是否真的具有任何的實質內容等等問題卻一直存在爭議,甚至有學者認為,該原則不僅是“空洞的”,更是道德上“扭曲的”。①
眾所周知, 平等原則作為現代國家的標志之一,彰顯的是封建法律體系,或者等級制法律體系的消解, 但除卻這一帶有宣言性質的歷史內涵之外, 平等原則在當代的法律體系中是否還有其他實際的內容,是否能夠承擔額外的公共倫理價值,就成為了一個具有重要意義, 但卻很難回答的問題。之所以難以回答,在我看來大概包括了這兩方面的原因,分別對應該原則中的“面前”以及“平等”這兩個模糊的表達。
首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能指代:在民主立法的過程中, 每個人對于法律的內容是什么可以產生平等的影響;②或者法律的具體內容中實質平等地對待所有主體;或者是無論法律內容如何,法律適用的過程中平等地對待所有公民。 本文將主要在后兩種對于“面前”的解釋中做出判斷,也即該原則究竟指代的是法律內容中的平等, 還是法律適用中的平等。
平等原則中另外一個模糊之處來自于“平等”這個價值本身。 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非常準確地描述了這種令人困擾的局面:“平等是一個爭議中的概念: 贊揚或者貶低平等的人們對于他們在贊揚或貶低什么也存在分歧。”③簡言之,平等之所以很難處理是因為, 脫離平等價值所處的具體實踐來單獨討論平等應該是實質平等或形式平等、機會平等或結果平等都是沒有意義的。比如在分配正義的討論中,最初有不少觀點認為,社會資源的有限性使得結果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只能保障某種形式的機會平等。但羅爾斯與德沃金讓我們注意到,僅僅機會平等(或者伊麗莎白·安德森所說的“起點平等”)仍然是不正義的,因為社會與自然的偶然性使得表面上的機會平等仍然不平等, 有些人因為其出生就注定無法過上體面的生活, 而另外一些人因出生這一偶然事件所帶來的財富與社會地位讓其一生無憂, 因此正義原則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在于如何控制偶然性對于個人生活的不正當影響。④相反,在百米賽跑中的平等要求的僅僅是選手處于同一起跑線上,而不應當去限制天賦、人種等等偶然因素所帶來的不平等, 因為這是競技體育本身的性質與目的所決定的。 所以,何種平等的觀念是正確的,必然需要放在平等出現的具體實踐的目的和意義之中來討論, 而這也是為何當代平等理論往往在分配正義的框架之下進行。同樣,法律中的平等原則究竟預設了何種平等觀也需要我們首先澄清上一段中的問題, 也即我們討論的平等出現在與法律相關的什么問題之中, 而這一前序問題的答案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法律面前的平等應該采納何種平等觀。
結合上述平等原則中“面前”與“平等”所帶來的兩方面的困難, 本文嘗試論證的將是相關聯的兩個命題:其一,法律的平等原則僅指法律適用面前的人人平等,而非法律內容中的平等;其二,平等原則通過抽象化的方式來確保形式平等, 并且這種平等最終來自于形式法治的要求。
一、冗余命題
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 正義的要求就與平等關聯在一起,因為正義要求平等地對待平等的人,不平等地對待不平等的人, 并且不正義往往就來自于不平等地對待了平等的人, 或者平等地對待了不平等的人。⑤這一要求也被總結為一個根本的平等原則,即“同等情況同等對待(treat like cases alike)”,那么,只要我們將該原則中的“情況”限縮在法律案件的情況中, 似乎平等原則在法律中的具體化順理成章地就成為了“同案同判”原則。⑥但是,即使我們在寬松的意義上來理解這個原則,將“同等情況”僅僅理解為依據法律規定具有相同性質,而非完全一模一樣的情況,并且將“同等對待”理解為“將人們作為平等的主體來對待”,而非“相同地對待不同的人”,⑦同案同判原則仍然無法必然滿足平等原則的要求。 這是因為在完全不考慮同案同判這個要求的情況下,法院基于獨立、正確的裁判,能夠最終形成同案同判的情況。 或者說,同案同判對于平等的貢獻依托于依法裁判所形成的狀況, 同案達成同判只是依法裁判的附帶現象(epiphenomenon)。 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在對平等主義的理論進行批評時認為, 如果一個原則能夠被認定為平等原則, 那么,“在所有該原則出現的情況下, 它必須展現出平等不僅僅是該原則所產生的結果,而同時也是它們的目的。 ”⑧據此,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平等價值在同案同判原則中所處的位置:
作為結果的平等: 所有類似的案件在事實上得到了同等的對待;
作為目的的平等: 所有類似的案件為了得到同等的對待, 而在事實上得到了同等的對待。
而同案同判之所以不是平等原則的必要條件是因為, 同案同判無法證明其實現的必然是作為目的的平等, 而不僅僅是作為附帶產物而出現的結果的平等。 但是,平等原則中,“人人平等”本身就是作為法律對待不同主體的目的所在, 因而必然要求的是作為目的的平等。 并且對于保障作為結果的平等而言, 同案同判原則相較于其他授予權利的原則也并沒有額外的優勢, 因為誠如拉茲所言:“所有授權的原則都會產生 (某方面的)平等,而這種平等是偶然產生的副產品,因為所有擁有平等資格的人們,在這些原則面前都擁有平等的權利。”⑨但是,這個結論不僅僅說明了同案同判無法必然滿足平等原則的要求,更暴露了平等原則本身的一個困難:法律中的平等,甚至一般意義上的平等都是冗余的,只能依附于其他的原則作為副產品出現。并且可能會讓我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除了拉茲之外, 許多對于法律的本質有著深刻理解的學者們, 卻對于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平等原則不以為然。 以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為例,他就認為平等原則在法律中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
所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條特殊的原則又如何呢? 它的全部含義不過是這樣一種機制, 如果將要被適用的法律中沒有做出區分,那么法律不應當區別對待。如果法律僅僅授予男性政治權利,而沒有授予女性;只授予公民,而沒有授予外人;只授予特定種族或者宗教的成員, 而沒有授予其他種族或者宗教的成員,那么如果在具體的案件中,司法機關判決一位女性、外國人或者某一宗教或種族的成員不享有政治權利, 但是這一判決卻完全遵守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該原則幾乎與平等不再有任何關系。 它所陳述的僅僅是, 法律應該按照其本應該被適用的方式來適用。這是合法性或者正當性的原則,而它本質上內在于所有的法律秩序, 而無論這種秩序是否正義。⑩
凱爾森的這段論述事實上包含了兩種批評:首先,平等原則在概念上等同于對于法律的正確適用,或者合法性(legality)原則。 這一批評類似于上文提到的對于同案同判的批評,也即當法律內容本身是平等的, 那么正確的適用會形成作為結果的平等,但是,這是因為平等原則被合法性原則所取代。其次,如果法律在內容上沒有保證平等,那么平等原則在適用法律中也無法保證平等, 因為平等原則要求適用那些本身對于不同人群予以區別對待的法律,因而與某種法律秩序是否正義沒有關聯。據此,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形式的平等冗余論?。
一是概念冗余論: 平等在概念上依附于規則的本質屬性, 等同于規則的一般性以及對于規則的正確適用。
對于拉茲而言, 法律面前的平等之所以冗余正是因為平等這個概念本身是空洞的, 因為所有的原則都是對于一般性理由的陳述,如此一來“對于滿足適用條件的人們而言, 這些原則便平等地適用于他們。 一般性暗含了對于特定人群的平等適用。 在一項原則的條件或者后果陳述中增加上‘平等地’并不必然使得該原則與平等產生更多的關聯”。?換言之,在拉茲看來,法律中的平等事實上指代的是法律規則本質在適用中的一般性,而并非真正指代某種平等的概念。例如,法律規定十八歲以上的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權利,那么,平等對待所有十八歲以上的公民, 以及區別對待十八歲以上與十八歲以下的公民, 這并非來自于平等的要求, 而是因為存在著客觀的標準來規定什么是“相同情況”,以及需要何種方式來“相同對待”。也正是出于類似的考慮,有學者認為,法律中的人人平等需要的是規則來界定人們應該在什么問題上被認定為“平等的”,并且何種方式才是“相同對待”,所以,平等原則的表象之下是由權利分配的實質原則構成的,因而,平等原則不僅僅在概念上依賴于權利的陳述,從而是空洞的,并且平等的陳述還會帶來掩蓋真正重要的權利陳述, 從而帶來混亂。?
二是規范冗余論: 平等僅僅指代平等適用規則,因此,如果規則內容本身不平等,那么,平等的適用規則并不能促進正義的要求。
這種對于平等原則的批評則有些不同, 并且同樣在凱爾森的論述中能夠找到證據。
假設在一個存在種姓制度的國家中, 法律將人分為三六九等, 并且賦予高種姓的公民各種特權,那么,正確或者平等地適用這種本身不平等或者不正義的法律,并不能更好地促進平等和正義,甚至通過立法將不平等固化, 將會使得該社會的不正義更加惡化。 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自然是納粹時期的德國, 正確適用仇視猶太人的法律促使了極端不正義的情況出現。 正如杰拉德·高斯(Gerald Gaus)的陳述: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之中,官員僅僅考慮的是個人的法律權利, 而不考慮超越法律的其他因素,例如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等等。不同的人們擁有不同的權利, 但正是法律將人們進行區分,形成了不同人群,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僅僅是法律在對待人們的時候, 其待遇完全由他/她的法律地位決定, 而與其社會地位無關。該原則本身與給予特定的人群法律特權是相容的。 ”?簡單來說,規范冗余論認為,法律對待公民的方式是否正義或平等是由法律本身的內容來決定的,而平等原則并不能額外地促進正義與平等。
在正式開始回應冗余命題之前, 我們首先需要反思這兩種冗余論斷是否會對平等原則的重要性產生實質的影響: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規范冗余論成立的話, 也即平等地對待相同狀況的人們并非法律本身應該追求的目的,那么,平等原則將無法對于法官或者其他官員的行為產生任何規范上的約束,從而指引他們的行為。 因此,如果我們需要辯護平等原則仍然是有意義的法律基本原則,那么,我們不得不對此加以回應。而概念冗余論則是認為, 法律面前的平等被還原為規則的正確適用與規則的一般性,但是如果在規則的本質中以及規則的正確適用中包含了對于某種形式的平等的追求與保障,那么,即使平等原則在概念上被還原,但是平等的價值仍然具有規范上的分量, 得以影響法律對待人們的方式。?或者說雖然平等在概念上被規則本身的性質所吸收, 但是這仍然有可能是因為規則必然包含了某種程度上對于平等價值的追求, 因此即使平等原則在概念上不獨立于規則本質, 但是該原則的目的仍然是促進平等價值所具有的道德重要性。出于這個考慮,本文將重點回應規范冗余論,并且對于概念冗余論做出讓步。
二、法律內容中的平等與適用中的平等
在論證平等原則的道德重要性之前, 首先需要論證為何平等原則只可能指代法律適用中的平等,而非內容中的平等。?這當然不是說在制定法律的時候,立法者不需要對公民予以平等的對待,而是只有將人們進行區分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時,這樣做才是道德上能夠被允許的。但是,我們認定為基本常識的法律平等原則卻不可能對于法律內容上的平等施加約束。一個直覺性的觀點似乎是,圍繞法律內容中的平等觀的爭議, 與不同法律體系在法律平等原則上的共識, 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對等之處。 誠如布萊恩·巴里(Brian Barry)所說, 即使存在道德共識的立法也會對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影響: 比如禁止傷害的刑法條款顯然對于情緒管理能力薄弱的人群更可能適用, 而對能時刻保持理性的群體不會有任何影響。?那么,法律內容中需要保障的平等觀是什么, 這似乎是一個必然會引起爭議的問題。 好在我們不需要過多地卷入到何種具體的平等觀是正確的這一爭議中去, 而可以通過兩個情境來論證為何平等原則指涉的是適用中的平等。
首先,假設國家A 認為,政治與法律的安排應該最大可能地保障個人自由, 而平等必然會限制個人自由,從而不應該被視為政治價值,那么,我們可以將A 看作一個“諾齊克式的國家”;而國家B 認為, 政治與法律的安排應當最大可能地保障人們平等的基本自由, 并且經濟與社會的不平等只有在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情況下才是可以被允許的,我們可以將B 看成“羅爾斯式的國家”。 雖然,A 和B 在法律內容中是否應當首要保證平等的價值存在激烈的沖突,但是兩個國家卻仍然同意,法律應當平等對待所有人。
其次,假設國家C 認為,雖然政治與法律的安排中,平等是首要價值,但是平等是指給予每個人基本生活能力所必需的條件保障, 而并非只在對所有人有利的情況下才允許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這是“森式的國家”。 那么,雖然B 和C 都認為平等是政治需要保障的價值, 并且應該在法律的內容中存在相應的制度安排,但是B 和C 卻對何種平等應該體現在制度安排中存在分歧, 不過這兩個國家仍然同意,法律應當平等對待所有人。
從A 和B、B 和C 之間的分歧與共識中我們可以總結認為, 無論法律內容中是否應當保證平等,以及應當保證何種形式的平等,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在于所有合理正當的國家都認為, 法律應當平等對待所有人,也即我們所說的“平等原則”。需要說明的是該論證預設了這樣一個事實, 在合理正當的國家中都認為法律的平等原則是應該被保證的。 依據這兩步論證,我們似乎可以確認:被認定為基本原則的平等原則指代的是法律適用中的平等,而非內容中的平等。為了進一步穩固這一結論,需要補充的另一個論證是,這兩種平等本身是相互獨立的。
兩種平等之所以相互獨立其原因在于, 在法律的安排中兌現這兩種平等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假設張三是一名高校藝術史的任教老師,她的課程以論文的方式對學生給出評價, 并且論文的評價標準包括選題、文獻選取、論證深度等等明確規定的方面。 李四與王五是該門課程中最努力的學生, 且選擇了同一名藝術家為題材進行論文寫作,然而兩人的區別在于該藝術家是李四的至親,因而獲得了大量其他人無法獲取的文獻與材料,而王五卻出生貧寒, 除了公共圖書館之外沒有其他渠道獲取資料。自然而然,李四的論文在各方面都要勝過王五一籌,從而獲得了課程的最優,王五屈居其次。 這個場景中存在兩種不同形式的平等可以分別對應法律內容與適用中的平等:其一,張三依據論文評價的標準本身對于兩位學生的文章進行評價,平等地適用事先制定的標準;其二,我們可以認為, 論文評價標準本身并沒有平等對待李四與王五,這兩位學生因為偶然性的因素,而非自己的選擇而導致背景性的不平等,因此,真正平等地對待他們,需要考慮偶然性給予李四不應得的優勢地位,并且通過補償弱者或其他方式來消除優勢地位的影響。第一種平等中要求的是,學生的任何信息對于張三的判斷都不能產生影響,或者說張三除了提交論文的質量與論文評價的標準之外,不應該知曉其他任何信息, 所以匿名制往往是保證這種平等的制度設計。 但是第二種平等則截然相反, 張三必須了解學生所有可能會對論文質量產生影響的偶然性因素, 并且通過對處于劣勢的學生予以正當的偏袒性待遇,從而達到這種平等。
我們可以用一種更理論化的方式來表明兌現兩種平等時的迥異。要實現法律內容中的平等,需要立法者掌握社會中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的各種不平等,例如因為階層、性別、民族等等因素而產生的不平等, 并且對處于法律權限范圍之內的不平等進行調整。因此,實現內容中平等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立法者面對的是具有詳細信息的不同個人,而不能僅僅是抽象的法律主體。 以德沃金的資源平等觀為例, 他明確地闡述這種平等觀的目標是“描述每個人(person by person)的資源平等”,因此需要考慮每個人的個人歷史中會在平等原則中影響其應得的各種因素。 并且德沃金強調資源平等觀考慮的基本單位并非某種社會或者經濟階層構成的群體,而是每個人的個體權利,因而更凸顯了平等原則對于個體歷史信息的要求。?安德森的平等觀則更強調公民之間不存在壓迫性的關系,每個公民最終需要對其他人保證的是一些自由的社會性條件, 而這些自由是人們作為平等公民發揮功能所必需的。然而,因為人們內在能力與社會狀況中存在著區別, 所以在將資源轉化為參與到社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的過程中, 他們并非是平等的, 因此為了讓他們能夠擁有作為平等公民的自由, 每個人有權獲得分配的資源在數量上將會是不同的。?換言之,為了保證法律內容中的平等,要求立法者在考慮公民“個人歷史” 或者不同的“內在能力與社會狀況”之后,再做出相應的立法決定, 而這種決定往往是賦予特定的人們以優先待遇,從而來滿足平等的要求。 與此相反,法律適用中的平等要求法官排除一切與法律規定本身無關的當事人信息,盡可能地保證不偏不倚的審判,或者用某種極端的方式來表述: 當事人在法律適用面前,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抽象主體,而不是具有個人歷史、不同能力、不同社會狀況的個人。
至此, 我們區分了法律內容中與適用中的平等, 并且由于不同法律體系對于平等原則所持有的共識, 以及不同的平等觀在法律內容中所存在的廣泛分歧,基于這兩者間的不對等,我們可以確定平等原則中的法律“面前”所指代的是法律適用過程中的平等。而接下來需要處理的問題是,法律適用中的平等是何種平等, 以及如果這種平等并不能保證人們得到實質的平等對待, 那么為何平等原則仍然具有道德重要性?
三、平等與抽象化
威廉·露西(William Lucy)認為,司法平等必然包含了三個組成部分:第一,推定性身份,也即法律將其主體視為相同的抽象存在(identical abstract beings),而并非具有特性的個體。 這其中包含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法律推定人們在認知與身體的能力上是完全相同的, 因而他們具有相同服從于法律的能力; 另一方面則是人們擁有完全相同的“形式上的”法律權利與能力的資格。 第二是一致性,這意味著法律在對人們做出評價的時候,依據的是同等適用于所有人的一般、客觀的標準。第三,有限的例外情況,該條件與一致性相關,即法律在適用這些具有一致性的標準時, 僅僅在限定的情況與范圍之內, 才能通過免責條款來放松一致性的要求。?前兩個部分正好對應法律適用中的平等,因而我們對此進一步展開論證。
通常似乎沒有一種關于實質平等的理論會認為,平等對待意味著將人們視為相同(identical)的主體,并得到相同的分配份額。從德沃金和安德森的論述中我們發現, 實質平等恰好要求法律將人們視為不一樣的個體, 并且通過不同的分配來矯正社會結構中已經存在的不平等, 從而滿足平等的要求。但是,法律適用中的平等卻又正好要求在通常情況下,法律將人們視為相同的主體,因此法律規則對他們相同地適用。 而這種相同要求的滿足是通過抽象化的方式來完成的,或者說,對于法律適用中的平等而言, 人人平等是因為從法律的視角出發, 每個個體擁有的都是法律規則抽象化而形成的相同的法律身份。因此,在法律面前的人們既非原告亦非被告, 不是受害者也不是犯罪嫌疑人,并且法律對于人們的社會、文化、經濟、種族等等差異“顯然是無視的(ostensibly blind)”。?抽象化的法律身份廣泛出現在各部門法之中, 其中最明顯的制度當然是責任能力的劃分。例如,在民法中, 只要年滿十八周歲的自然人就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地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假設某人A 雖然年過十八歲, 但是其認知能力仍然稍弱于通常十八歲的自然人, 卻又不足以被認定為限制或者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那么,A 與所有其他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民事行為能力; 而相反B 雖然年齡不滿十八歲(且尚未獨立生活),但卻有超乎常人的認知與意志能力, 遠超大多數成年人。 那么,當A 和B 因為相同的行為,分別侵犯了C 和D 相同的權利,但是,從法律的視角看待當事人與其行為,A 與B 在認知能力的真實狀況完全被法律排出,A 以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抽象法律身份出現,而B 僅僅具有限制行為能力。并且法律在評價A、B 的侵權責任時,不考慮任何與他們個人身份相關的信息,僅僅考慮在侵權事件中,是否出現了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必要因素,以及A 與B 的法律身份是什么。因此,在民法規定自然人具有一律平等的民事權利能力時, 正是通過抽象化的方式來完成的。而在公法中,通過抽象化來滿足平等原則的制度同樣常見,例如在刑法中,除了同樣通過抽象化的方式來認定刑事責任能力之外, 在過失犯罪的認定中, 無論是當事人應當預見的危害結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抑或是因為輕信能夠避免而導致結果發生, 這其中都預設了當事人能夠滿足的注意義務或者應該具有的認知能力,而預設的認知能力標準正是通過抽象化的客觀標準來設定, 也即正常理性的人應該具備的認知能力。 因而,刑法在確定過失刑事責任的過程中,不考慮不同犯罪嫌疑人具體的認知能力,正是刑法中對于平等原則的遵守。?所以,無論是在公法還是私法領域, 法律都通過抽象化的法律身份來進行評價,從而排除人們與評價無關的所有其他信息。
但是,這里會引起的一個懷疑是,前文提到過法律內容中的平等不僅無法通過抽象化的方式來實現, 反而需要盡可能知道每個個體在社會關系結構中所處的地位, 以及因為這些地位而存在的不平等,那么,這似乎至少說明抽象化并非是平等的必要條件,對此我們可以通過下述論證來回應。
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試圖澄清平等的理念時提供了一個論證, 我們可以簡短地復述為:平等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道德價值,在根源上是因為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道德地位, 因此值得被平等地對待, 予以平等的尊重。而尊重之所以能夠負擔平等的道德意義,這是因為尊重意味著我們在判斷一個人的時候, 依據的并非是某種能夠適用于這個人的標簽, 而應該從他或她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 而這進一步要求我們忽視掉人們的成就、社會地位等等頭銜(titles),因為它們顯然是社會、政治以及職業不平等的載體,所以,“尊重”要求我們“對待人們的根本態度不應該被職業上的成功或者社會地位來左右……每個人都有資格要求其他人盡力地去理解他們,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每個人都應該從顯著的特定不平等的結構中抽象(abstracted)出來”。?人們都擁有潛在的能力來實現 “反思性的自覺(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從自己的角色和身份中脫離出來,因而,只有當我們從“人類的觀點”來看待每個人的時候, 這種觀點才將人們從不平等的結構中抽象了出來,所以,抽象化或者人類的觀點就成為了平等的必要條件。?
依據上述論證, 一般意義上的平等都需要某種形式的抽象化來保證,所以,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無論是法律內容中的平等,還是法律適用中的平等必然都包含了抽象化的要求。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如何還能像第二部分的結論那樣,將兩種平等區分開? 威廉姆斯的論述中仍然為我們提供了可靠的理論資源: 例如在高等教育資源如何分配的政治決定中,應該將學生的性別、種族、社會地位等等身份都排除在外, 找到與該分配具有相關性(relevance)的理由。 假設與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相關的理由僅僅是學生的學術能力,那么,抽象化意味著備選的學生除了學術能力的面向外,不再是具有具體信息的個體。但是,在實踐中情況往往并非完全由理由來決定, 因為學術能力的抽象化仍有可能制度性地將一部分人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 假設學術能力強的學生都來自于社會地位較高且父母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那么,最終獲得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學生僅僅限于這個群體。因此,在高等教育權利的社會可操作性(operativeness)層面,抽象化還有另外一層含義,也即家庭出身對于學生學術能力的影響本身是發生在學生身上的事件,而非這些學生本身,因此需要將待分配的學生從這些本身不平等的 “環境中抽象出來”。?因此,當立法者決定一種平等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方式時, 那么這種法律內容中的平等同樣需要通過抽象化的方式來保證。
不過, 法律內容與適用中的平等在抽象化上仍然存在重要的區別: 我們可以將內容中的平等理解為某種道德爭議, 那么對于諸如決定高等教育資源的相關理由以及社會可操作性的諸多因素,這種公共討論仍然是開放的,或者借用威廉姆斯的話來說, 當公民在爭議中討論是何種理由具有相關性,以及某項制度需要具有可操作性,那么這種觀點“的確是言之有物的”。?相反,在法律適用中, 法律的權威性特征已經確定了何種理由與可操作性對于特定的分配制度具有相關性,因此,法律的規定確定具有何種特質的學生有資格享受高等教育, 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考量和爭議都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換言之,法律適用中的平等依據的是抽象化的法律身份,實現這種平等的方式是將這種抽象化之后的標準平等地適用于所有學生,并且排除其他的信息。因此,這一論證推導出了兩個結論:其一,一般意義上的平等都依賴于某種形式的抽象化,但是在法律內容中與適用中實現平等所采取的抽象化的方式仍然是能夠區分開的;其二,法律適用中的平等依賴于形式平等,將抽象化的標準平等地適用于法律主體,而如果這些標準本身并非完全實質平等,那么,這種形式性的平等將無法保證實質平等的實現。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何法律的形式平等仍然是重要的?如果平等原則無法防止實質不平等或者不正義的發生,為什么人們還會認為該原則具有規范上的分量?
四、形式平等的重要性
拉茲在辯護形式法治時的一個論斷對辯護平等原則也具有啟發性,他認為“法治”并不等同于“善法之治”,如果兩者等同的話,那么弄清楚法治則需要一整套社會哲學來澄清何為“善法”,這樣會使得法治的理念沒有了任何作用。因此,法治是法本身的內在品質,而非法的內在道德品質,其最重要的價值體現在防止法律本身可能帶來的危險,而并非其他更積極的道德作用。 拉茲認為,法治就在于法能夠引導其主體的行為,因此,法治僅僅是法的諸多理想中的一種,而“善法之治”則需要補充其他實質的道德價值。?該論證給予我們的啟發在于:“法律面前的平等”可能也不要求“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因為澄清法律內容中的平等同樣也需要一整套的社會哲學, 這將使得法律平等的理念被架空。所以,本文在前幾部分嘗試澄清的平等原則同樣也是一種內在于法律本身的平等原則,或者說法律本身蘊含的平等。?那么,在探討平等原則的重要性時, 我們同樣不應該指望滿足該原則的法律決定一定是在全盤考慮下 (all things considered)道德上完全正當的決定。 借用哈特的表述,正義僅僅是道德的一個切面,而法律平等又僅僅只是正義的一個切面。?但是當法律適用中的平等得以實現,所適用法律的內容卻并不平等,那么,平等原則還有何種重要性呢?規范冗余論的挑戰正在于,平等地適用內容不平等的法律,例如包含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那么法律平等不僅不能促進正義, 反而會將這種不正義與不平等制度化。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平等原則反而是損害正義的。
一個顯而易見的回應是, 即使在法律不正義的情況下, 平等地適用這些法律也要勝過反復無常、恣意擅斷的情況。因為至少受制于這種法律的主體能夠知道和預期他們的行為將會引起何種后果,所以可以嘗試保護自己。反而如果法律本身已經不正義,而法律主體還要遭受到肆意的處置,那么這將造成更大的不正義。?換言之,比起無法預期的不正義, 可預期性本身就是法律平等能夠帶來的價值。不過這種回應可能無法說服所有人,例如假設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黑人, 知道自己如果申請高等教育的資格必定會因為自己的種族而被拒絕, 那么這種確定性究竟給他或者她帶來了什么善呢? 或者平等適用這種歧視性的法律又在什么地方促進了正義呢?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在法律整體結構中包含了類似極端不正義的情況下,平等原則對于促進正義或者防止更大的不正義出現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因為平等地適用法律,顯然無法對于整體政治制度中的不正義做出修正,這也是為何羅爾斯承認:“形式正義……所宣稱的力量,顯然依賴于這些制度的實質正義,以及改造這些制度的可能性。”?不過,這也不代表平等原則不具備重要性,相反即使內容完全正當的法律,仍然需要平等原則促進實體正義的實現: 假設高等教育的資格設定中沒有包含歧視性的規定, 僅以學生的學術能力與潛力(符合抽象化要求)作為標準,張三與李四都滿足了該評價標準,但是高校最終以張三是本地人,或者是男生,或者是校友后代等等隨意的理由錄取了他,而拒絕了李四。在這個案例中,雖然法律的內容符合正義的要求,但如果李四以沒有得到法律平等的對待為理由進行申訴,她的申訴顯然是有效的,因為張三確實得到了不正當的優先待遇。因此,雖然平等原則確實對于極端不正義的情況無法產生太大的作用, 但是這不代表該原則完全喪失了重要性, 并且一方面平等原則無法保證完全正當的法律判決, 而另一方面平等原則仍然具備內容平等所無法代替的重要性,該原則的重要性正應該處于這兩極之間。平等原則之所以在效力上受到限制, 其原因在于涉及法律適用的平等時,往往存在“一個非比較性的正義原則確定了在適用形式性的比較正義原則時其相關性的標準是什么”。?
在理想的情況下, 一條法律規則要能完全滿足平等的要求必然包含三個部分的考慮?: 第一,如果法律規則需要規定某種制度, 而這種制度必然會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對待方式,那么,該制度的證成需要符合平等的要求。 通常這種會在事實上產生不平等的制度其證成是通過前文提到的抽象化來完成的,例如在就業的選拔中,競爭必然會帶來篩選, 有人能獲得工作機會, 有人不能獲得,那么,這種制度本身必然需要被證成。 而抽象化則意味著找到就業選拔的依據, 并且該依據僅僅考慮的是就業這項制度的本質或目的, 所以就業機會的分配通常只應該考慮工作能力, 而不應該考慮年齡、性別、學歷等等與工作能力并非必然相關的其他因素。 抽象化的標準與將會產生不平等的制度的本質是“理性相關的”,因而如果我們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中考慮了病人的經濟狀況,而并非僅僅是病人的病痛情況,那么這將是一種“不理性的狀況”。?滿足制度證成的法律規則也就避免了特定人群被制度性地認定為在法律或道德上低人一等的情形出現, 也即抽象化的標準使得前文提到的諸如種族、性別歧視、污名化(stigmatization)等等嚴重不平等的情形出現。
第二, 抽象化的標準在形式上不針對任何特定人群,但是結合特定國家的實際狀況,卻無法保證在事實上不會制度性地將一些人群排除在法律受益者的范圍之外,因此第二部分需要保證的是,人們在滿足抽象化標準時都擁有“實質機會”。 在前文提到的教育資源的分配中,如果抽象化標準以學術水平為依據,那么實質機會需要保證來自貧困家庭,或者少數族裔的考生也能有同樣的機會達到與其他學生相同的學術水平,否則他們將在事實上被抽象化的標準排除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之外。因而,諸多平等理論以及國內外的許多平權法案都可以被視為在嘗試滿足實質機會的要求。
第三, 在理性相關的抽象化標準以及實質機會的保障之外, 一項法律規則想要完全符合平等的要求還需要滿足程序公正的要求, 也即法定的利益是通過公平的程序分配給了一部分人群,用哈特的話來說也就是:“執法者不因為偏見或者利益的原因而違背‘平等’對待當事人的要求。 與此相符的一些程序標準例如‘聽取雙方之詞’‘人和人不應該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 都被認為是正義的要求,并且在英美時常被表述為‘自然正義’的原則。 這是因為這些原則是不偏不倚或者客觀性的保障, 用來保證法律適用于所有并且僅僅適用于那些在法律本身規定的相關方面上相同的人們。 ”?程序公正的目的是保證抽象化的標準能夠平等地適用于不同的人們, 并且除了這些標準本身,當事人的所有其他信息都被排除在外,從而保證法律適用中僅僅依賴抽象化的標準。
制度證成與實質機會顯然是對于法律內容的要求,而法律平等原則僅僅對應程序公平的要求,但是我們也能看到, 只有當一個法律決定滿足全部三個要求時,該決定才是完全平等的,這也就意味著對于一個最終正當的法律決定而言, 法律適用的平等同樣有著內容平等所無法替代的規范重要性。一個滿足實質正義的判決是制度依賴的,這卻并不代表法律適用的平等本身是無法與制度本身是否平等相分離的, 或者說我們所辯護的平等原則所能夠阻止的一些道德上壞的情形, 這是制度證成和實質機會所不能做到的。一方面,平等原則保障抽象化的標準在最終的適用中仍然能保證抽象化, 不因為與法律無關的因素而使得法律的適用變得偏倚, 這是任何一種法治觀中都需要確保的形式正義, 或者對于人們可預期性保障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即使滿足制度證成和實質機會的法律規則, 仍然可能會出現違反平等要求的情形,例如在公共職位的選拔中,如果選拔的標準本身符合前兩項要求, 而此時仍然有多名候選人滿足這一標準,那么,公正的程序能夠防止諸如“裙帶關系、任人唯親或者純粹惰政”?的情形出現,并且任何一名候選人以官方沒有平等地適用選拔標準為理由進行申訴, 她申訴的根據顯然并不是要否定標準的內容中存在歧視, 而是在適用標準的過程中給予了其他人不正當的優待。 或者例如前文中,張三和李四具有相同的學術能力,都配得上最后一個高校錄取資格, 如果此時學校錄取張三的理由超出抽象化的標準之外, 或者通過某種恣意的方式做出了最后的決定, 那么李四根據該判決違反平等原則進行申訴則完全是合理的。所以,這三部分所構成的實質正義防止的是“彼此能夠區分開的錯誤, 這些錯誤可以在彼此獨立的情況下發生, 并且它們之所以構成錯誤是因為不同的理由”。?
據此,我們就回應了規范冗余論:雖然在極端不正義的情況之下, 平等原則能發揮的規范作用十分有限, 但這并不意味著該原則對于完全符合正義的政治決定而言沒有任何貢獻。事實上,在適用法律中的平等所能防止的道德錯誤正好與法律內容中可能出現的道德錯誤是相互獨立的, 并且平等原則的考慮更多地出現在合理正當的現代法律體系之內,因此,法律適用中如何保證平等比起法律內容的證成如何更切合制度的理性, 前者甚至要出現得更為頻繁。
結 語
在漫長的分析之后, 我們得出了一個與人們的直覺存在落差的結論,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最為人所熟識的法律原則在概念上不具有完全的獨立性, 其涵蓋的范圍僅僅包括法律適用之中的平等, 并且其規范效力也無法保證實質正義的最終實現。然而當分析與直覺產生落差時,出現問題的并非必然是分析一端。 如果本文的分析是正確的, 那么顯然我們模糊的直覺中對于平等原則的效力賦予了過多的重要性, 甚至將其等同于實質正義的全部主張。 在支持平等原則冗余論的文獻中, 時常會看到學者引用威廉姆斯的一句話來表達平等價值的無趣:“當平等的陳述不再言過其實,它竟然相當迅速地變得不再有趣。”?但是用這句話將威廉姆斯認定為冗余論的支持者顯然是忽視了他在整篇文章中對于平等理念的分析。 對他而言, 平等的理念之下諸如機會平等或者平等尊重在政治領域中同時存在, 想要用其中一個來吸收所有其他平等理念都將是錯誤的, 即使它們彼此之間可能會導向完全相反的政治決定,“雖然這是個令人不悅的情況, 但是這種令人不悅之處正是真正的政治思想。 平等帶來的不悅并不會超過自由,或者其他任何高貴與實質的政治理想。”?我們將法律中的平等區分為了內容與適用中的平等, 后者才是法律所特有的平等原則并且無法被實質平等所吸收;更甚者,該原則也可能與實質正義中的平等相左,但是,這種令人不悅的情況也許才是對于平等原則準確的分析。
注釋:
①例 如Peter Westen, The Empty Idea of Equality,Harvard Law Review, 95 (1982), pp.537-596.
②Charles Beitz, Political 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3.
③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
④例如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4-15.
⑥關于同案同判義務的效力以及該原則的范圍討論,參考Andrei Marmor, Should Like Cases Be Treated Alike?,Legal Theory 11(2005), p.27; 陳景輝:《同案同判: 法律義務還是道德要求》,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3 期;雷磊: 《如何理解“同案同判”?》,載《政法論叢》2020年第5 期;孫海波:《“同案同判”: 并非虛構的法治神話》,載《法學家》2019年第5 期;泮偉江:《論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質》,載《法學》2021年第12 期;王凌暤:《“同案同判”蘊含著“遵循先例”嗎? ——一對易于混淆的概念及其澄清》,載《浙江社會科學》2022年第4 期。
⑦該區分來自于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73.
⑧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5.
⑨Ibid., p.228.
⑩Hans Kelsen, What is Justice? in his Essays in Legal and Moral Philosophy, trans.Peter Heath,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p.15.
?類似的區分參見Alfonso Ruiz Miguel,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Precedent, Ratio Juris, 10 (1997), p.374.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0.
運用該模型將各個坡面采樣點的 7Be含量轉化為表層土壤的侵蝕或沉積量可以說明坡面土壤侵蝕的空間分布特征。
?例 如Peter Westen, The Empty Idea of Equality,Harvard Law Review, 95 (1982), p.542, 547.
?Gerald Gaus, Politic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Theories, Westview Press, 2000, p.151.
?對于概念冗余論的回應參見Alfonso Ruiz Miguel,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Precedent, Ratio Juris, 10(1997), pp.377-8.
?類似的區分參見FrejKlem Thomsen, Concept, Principle, and Norm-Equality Before the Law Reconsidered,Legal Theory,24 (2018),p.105.Alfonso Ruiz Miguel,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Precedent,Ratio Juris,10(1997),p.377.
?Brain Barry, Culture and Equality: An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 Polity, 2001, p.34.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4.
?Elizabeth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Ethics 109 (1999), p.320.
?William Lucy, Equality Under and Before the Law,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61 (2011), pp.413-4.
?Ibid., p.415.
?眾所周知, 在注意義務以及認知能力的認定上,刑法學界存在諸如客觀說與主觀說的爭論,而本段的論述中并不必然采取客觀說,因為本文并沒有證明平等原則是絕對的(absolute),因此,當采取客觀說會明顯違反正義的要求時,平等原則同樣可能讓位于其他更重要的價值考量。
?Bernard Williams,The Idea of Equality, in his Problems of the Sel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37.
?Ibid., pp.235-9.
?Ibid., pp.241-6.
?Ibid., p.241.
?Joseph Raz,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Virtue, in his The Authorit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11.
?[英]亨利·西季威克,《倫理學方法》,廖申白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313~315 頁。
?后半句并非哈特的原話, 但是他認為正義在結構上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是法律適用時的平等;其二是平等適用所依賴的標準本身是正義的。 參見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pp.157-161.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給出了這樣的回應,參見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p.58-9.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9.
?Joel Feinberg, Noncomparative Justi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 (1974), p.313.
?這三部分的平等觀來源于托馬斯·斯坎倫(Thomas Scanlon), 他將三個部分分別稱為 “制度化證成”“實質機會”以及“程序公平”。 參見T.M.Scanlon, 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4 & 5.
?這是威廉姆斯的表述,他與斯坎倫都認為,類似需要得到證成的制度,只有在考慮與制度本質理性相關的根據時,才是滿足平等要求的,因而斯坎倫也將這種證成稱為 “制度化的平等觀”。 Bernard Williams,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his Problems of the Sel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240-1; T.M.Scanlon, 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42-5.
?H.L.A.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60.
?T.M.Scanlon, 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3.
?T.M.Scanlon, 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4。 除此之外,程序性的平等原則還具有其他類型的實用價值, 參見FrejKlem Thomsen,Concept, Principle, and Norm-Equality Before the Law Reconsidered, Legal Theory, 24(2018), pp.131-133.
?Bernard Williams,The Idea of Equality, in his Problems of the Sel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31.例 如Peter Westen, The Empty Idea of Equality, Harvard Law Review, 95 (1982), p.547.
?Bernard Williams,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his Problems of the Self,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