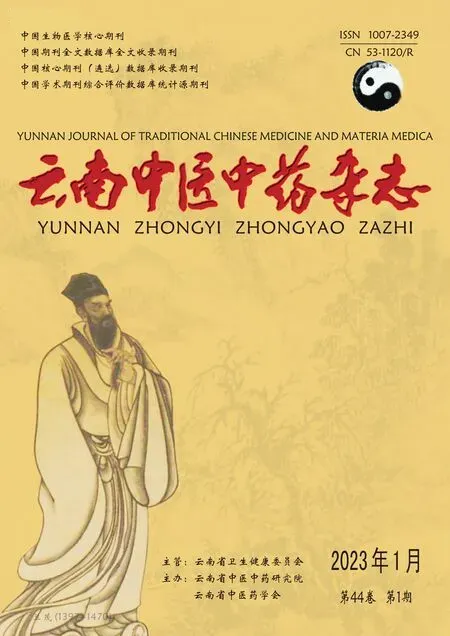陳楓教授針刺治療痿證經驗
李梓婷,班林強,陳 楓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北京 100102)
陳楓教授為“首都名中醫”“首都群眾喜愛的中青年名醫”、“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青年名中醫”。從事針灸臨床、科研、教學工作 30余年,在臨床常見病的治療方面已形成完整治療體系。筆者有幸跟隨導師學習,受益匪淺。
“痿”的甲骨文由疒(形象是一張豎放的床鋪,表疾病)和委(形象是一個人手里拿著枯萎的禾苗,表示枯萎無力)組成,表示人因為疾病而肌肉萎縮,癱瘓在床。中醫的“痿證”是指肢體經脈弛緩,軟弱無力,不能隨意運動或伴有肌肉萎縮的一種病證[1]。《素問·痿論》中最早論及痿證,其中定義的痿證是廣義的,可以包括人體內在臟腑及外在五體、五竅、五華的形態萎縮、功能痿廢;而本文的痿證主要針對狹義而言,任何肢體或局部肌肉的痿廢不用都隸屬其范疇,臨床上脊髓或腦部病變導致肌肉無力,運動神經元病變,乃至一側面肌癱瘓無力的面神經炎皆屬痿證[2]。
現檢索臨床文獻上針灸治療痿證多從“治痿獨取陽明”中著手,或只取足陽明胃經穴位;或取多經多穴,選少陽經、太陽經以及手、足三陰經的腧穴施治;也有醫家是主取足陽明胃經穴位,配合辨證取穴,其中雖不乏有選取肝經穴位者,但乃是出于痿證遷延不愈,損及肝腎而選取肝腎經穴位的考慮[3]。陳楓教授認為“治痿獨取陽明”非僅取胃經腧穴,因此語出于《素問·痿論》,而本篇最后中有“各補其滎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順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說明可針對性選取他經穴位。陳楓教授從肝本身的特性“肝為罷極之本”考慮,且與“治痿獨取陽明”有機融合,首創“肝胃組穴”聯合足陽明胃經經筋排刺法治療痿證。
陳楓教授在臨床治療痿證諸如脊髓炎、格林-巴利綜合征等多用此法,結合患者病情變化辨證選取少許配穴,收效甚佳,現將導師臨床經驗分享如下,以饗同道。
1 痿證病因病機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痿躄屬內臟氣不足之所為也”,痿證病因主要是因為臟腑有所不足[4]。陳楓教授認為針灸治療痿證主要責之于肝、胃不足,分析如下。
1.1 肝臟罷弱,不堪小勞 肝為罷極之本,“罷”通“疲”,可分為形罷、神罷兩方面,形罷與筋相關,而神罷則與魂有關,筋與魂又依賴于血的潤養[5]。肝藏血又主疏泄,“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素問·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胃運化水谷精微得到精血,肝藏精血然后疏泄,將精血疏泄至人體四肢百骸而能動,“故人臥血歸于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素問·五臟生成篇第十》),因此肝是人體中掌管物資輸出的系統。陳楓教授認為肝能輸出一定物資為人所用,才能耐受疲勞,這就是“肝為罷極之本”的原因[6]。而當肝經所能承擔的耐力閾值變低,肢體不能耐受正常勞動,肌力達不到正常肌力,就形成痿證。
形罷這方面與筋相關,肝主筋,《類經·藏象》曰:“人之運動,由乎筋力”,可見四肢的靈活運動除了與肌肉有關,亦與筋正常作用的發揮密不可分。《臨證指南·痿》:“蓋肝主筋,肝傷則四肢不為人用,而筋骨拘攣”,痿證在臨床上除肌肉痿軟表現外,常伴有肌肉瞤動、肢體攣縮、舌顫、走路搖擺等筋罷特點[7]。“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為拘,弛長為痿。”(《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篇第三》),說明患者筋罷而成痿,而肝其充在筋,故陳楓教授強調治肝以治筋。
神罷這方面,臨床上痿證患者多伴頭昏、失眠、神疲乏力等神氣不足的癥狀[8-9],“肝藏魂,人臥則血歸于肝。陽氣者,煩勞則張。罷極必傷肝,煩勞則精絕。肝傷精絕,則虛勞虛煩不得臥明矣。”(《醫宗金鑒》),陳楓教授認為以上神罷的伴隨癥狀為肝經罷弱,魂不守舍之象,再次驗證患者痿證亦責之于肝。
1.2 胃腑虛弱,生化乏源 胃屬中焦消化系統,與肝主疏泄相對,這個系統是人體中掌管物資輸入的系統之一。“水谷皆入于胃,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靈樞·五味第五十六》),從外界進來的食飲進入胃中,然后經過胃的運化成為身體可吸收的精微物質,再輸布至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素問·陽明脈解》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可見肌肉功能正常的發揮、形態的飽滿與否與足陽明胃經是否血氣充盛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4]。胃受納水谷,匯成多氣多血之經,為五臟六腑之海,再滲灌肌肉百骸,故陳楓教授認為痿證患者往往胃腑虛弱,使肌肉筋骨氣血供應受限而成痿[10]。
臨床相關文獻中近四成痿證患者多見肢體瘦削,納差,便秘,面色不華,神疲乏力,脈細弱等胃腑虛弱之象[11],生化乏源而致氣血虧虛,肌肉失于充養。“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素問·痿論篇第四十四》)、“陽明為闔,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靈樞·根結第五》)再次闡明患者痿證與胃腑虛弱關系密切。
1.3 肝胃相互影響 綜上,陳楓教授認為患者痿證主要責之于胃、肝,而胃、肝之病機又互相影響。
其中,胃影響肝而成痿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方面,“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靈樞·決氣第三十》),水谷入胃變化而赤生血。胃腑虛弱則精血必虛,精血虛則肝失所養,不能行罷極之本而肌肉痿廢不用。另一方面,“虛勞損血,不能榮養于筋”(《諸病源候論》),胃弱血虛后,筋枯不榮,而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且陽明主肉,陽明虛弱則肉亦孱弱,筋馳肉弱而成痿。另外,胃屬中焦,是人體氣機樞紐,統率各臟腑的氣機并制約其失衡[12-14],當胃出現問題,肝的正常升降就失去了樞紐的統率,肝疏泄精血不足而成痿。
相應的,肝也會影響胃而成痿。肝疲弱不堪,則疏泄給胃的所藏之血不足,影響胃的進一步運化生血,于是成為肝愈虛,胃愈虛,肝益虛的惡性循環。另外,《黃帝內經》中載肝所生病者,會出現嘔逆,飧泄等胃的癥狀,影響胃的消化吸收,四肢百骸得不到營養而成痿。
2 針灸治療
陳楓教授基于以上對痿證的認識,以“養肝益胃”為法,針刺治療痿證,改善四肢痿弱,活動不利的癥狀。
2.1 取穴 (1)主穴:雙側陷谷、足三里、下巨虛、曲泉、太沖共10穴。為尊重原創且概括其治療痿證主要理論,現將導師陳楓教授針刺治療痿證的這組穴位命名為“肝胃組穴”。(2)配穴:頭昏明顯加雙側風池、完骨、懸顱、陽白;失眠明顯加神門;排尿障礙明顯加太淵、中封;下肢麻木明顯加雙側三陰交、陽陵泉、至陰;納差明顯加中脘、陰陵泉;上肢麻木明顯加內關、極泉、青靈。
2.2 選穴分析
2.2.1 足陽明胃經 內經中多篇中有治痿取陽明之說,“帝曰: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素問·痿論篇第四十四》),“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余不足,無所止息者,真氣稽留,邪氣居之也”(《靈樞·根結第五》),陽明為多氣多血之經,針對痿證導師往往選取足陽明胃經經筋排刺法,此特殊刺法于后文“操作方法”處詳述,可針刺雙側足三里、上巨虛、下巨虛。且上述三穴分別為胃經、大腸經、小腸經下合穴,可以調理中焦消化系統,改善患者納差癥狀,使生化得源,如魚得水,四肢得養。陷谷是五腧穴中輸穴,“俞主體重節痛”,故可治痿。陽明主肉,痿證患者肌肉瘦削無力,補法針刺陽明經可以使肌肉強健有力。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束骨則人能立,利機關則人能動,痿證難立難動,故針刺足陽明經穴位對癥治療。
2.2.2 足厥陰肝經 曲泉、太沖為肝經穴位,肝為罷極之本,針刺此二穴可刺激激發肝罷極之能,使人所能承擔的耐力閾值由低逐漸恢復。
曲泉為肝經合水穴,《針灸大成》中記載曲泉可治四肢不舉,肝屬木,水能生木,根據“虛則補其母”的原則,肝之虛癥,可用曲泉補之,既養四肢,又定肝魂而助眠;另外肝主筋,膝為筋之府,曲泉位于膝關節部位,“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筋將憊矣”(《素問·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故痿證下肢不能站立屈伸可刺曲泉。
太沖為肝經輸穴、原穴,“俞主體重節痛”(《難經·六十八難》),而痿證表現為肢體不能支撐自身重力,患者直觀感受就是“體重”,故選取作為罷極之本的肝之俞穴;原穴是臟腑的原氣經過和留止的部位,“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難經·六十六難》)、“五臟有疾也,應出十二原”(《靈樞·九針十二原》),而痿證患者肝不能行罷極之能,就選取肝經原穴太沖來鼓動肝之原氣治療;《指要賦》曰:“且如行步難移,太沖最奇”、《馬丹陽十二穴歌》也記載了太沖能醫“兩足不能行”,故可知太沖有讓人棄杖重行之效。
2.3 操作方法 陳楓教授臨床針灸時亦重視刺法,治療痿證時善用足陽明胃經經筋排刺法。排刺是確定某一治療部位,確定兩個穴位作為端點,將兩點之間的距離等分,針刺端點及其等分點,使之整齊排列成行的刺法。排刺根據深淺及部位不同,可分為皮部、經筋、經脈排刺。痿證為宗筋不能束骨、利機關,宗筋主要指十二經筋,是十二正經連屬于筋骨的部分,多結、聚、散、絡于骨骼和關節附近,所謂“諸筋者皆屬于節”(《素問·五臟生成論篇》),故常用經筋排刺。經筋在皮部之下,故經筋排刺時,應使針尖達到肌肉、肌腱的深度[15]。陳楓教授的足陽明胃經經筋排刺法,以足三里、下巨虛為兩個端點,中間可取1個等分點,即上巨虛,痿證重者中間可取2個等分點,不再拘泥于具體穴位。
“肝胃組穴”均采用解剖定位。選取漢醫牌0.25 mm×40 mm一次性無菌針灸針,對穴位進行常規消毒。其中足三里至下巨虛行胃足陽明經排刺法,直刺1.2 寸,曲泉直刺1.2 寸,均以每分鐘 120 次的頻率捻轉補法30 s。太沖、陷谷直刺 0.3 寸,不使用手法。以上穴位操作后均留針 30 min,每周一、四上午門診治療,每次針灸治療主穴同前,配穴根據伴隨癥狀較明顯者加減。
3 典型病案
孟某,男,57歲,2021年1月18日初診。主訴:四肢無力,行動不便漸進加重一個月。現病史:患者無明顯誘因于1月前出現四肢無力,行動不便并漸進加重,伴頭昏,失眠,四肢麻木,排尿障礙,便秘,17天前開始不能行走,需借助輪椅。發病后曾就診于協和醫院,診斷為脊髓炎,未予系統治療,等待協和醫院安排床位住院。因病情漸重,患者欲在住院前針灸治療減輕癥狀,遂來我處門診就診。刻下癥見:形體羸瘦,面色不華,神疲乏力,四肢麻木,步履全廢,四肢瘦削,頭昏,失眠,納差,尿儲留,便秘,舌淡苔白膩,脈細弱。查體:神清,顱神經(-),四肢深淺感覺減弱,四肢肌力2級,肌張力正常,腱反射對稱,病理征(-)。西醫診斷:脊髓炎。中醫診斷:痿證,證屬氣血虛弱證。對癥予針灸治療,主穴:雙側足三里、上巨虛、下巨虛、陷谷、曲泉、太沖,配穴:頭昏加雙側風池、完骨、懸顱、陽白;失眠加雙側神門;排尿障礙加雙側太淵、中封;下肢麻木加雙側三陰交、陽陵泉、至陰;納差加中脘、雙側陰陵泉;上肢麻木加雙側內關、極泉、青靈。操作方法同上文。患者2021年1月18日初診后入協和醫院神經內科住院。2021年2月20日出院復診,患者述四肢無力麻木癥狀較以前加重,仍不能自己行走,因協和未有明確的治療方案,故出院復來我處針灸。2021年2月22日三診時,患者述癥狀減輕,雙下肢肌力由二級恢復三級,雙上肢肌力由二級恢復到四級減,排尿正常。對癥繼予針灸治療同上,鞏固治療。2021年2月25日四診時,患者能擺脫輪椅,獨立行走來診,頭昏癥狀消失,四肢肌力恢復。至2021年5月24日患者述每日已能鍛煉行走2千余步。目前仍堅持門診,欲繼續減輕雙上肢麻木的癥狀。
按:患者中年男性,四肢無力,行動不便,辨為痿證之氣血虛弱證。肢體瘦削,納差,便秘,面色不華,神疲乏力,舌淡,脈細弱皆是胃腑虛弱之象,生化乏源而致氣血虧虛而成痿;頭昏、失眠、神疲乏力皆是肝血不養,神不守舍之魂罷表現;四肢痿廢不用為筋不任身,排尿障礙為宗筋無力,總為筋罷之表現。故選取“肝胃組穴”聯合足陽明胃經經筋排刺法使兩經氣血運化起來,從根本上使肉壯筋強而治療痿證。脊髓炎在西醫病因尚無定論,無特效藥物[14-15],但從中醫痿證論治而獲奇效。陳楓教授尊內經之旨,將痿證主要責之于肝胃二經,補其榮,通其俞,待以時日,雖難愈之癥而向愈。
4 小結
神經根脊髓炎指各種感染后引起自身免疫反應所致的橫慣性脊髓、脊神經根炎性病變,以病損平面以下運動障礙,感覺障礙和自主神經功能障礙為特征。若無嚴重并發癥,1/3的患者僅遺留有輕微感覺運動障礙;1/3的患者能夠行走,但步態異常,遺留有便秘、尿頻,1/3的患者將持續癱瘓,伴二便失禁。西醫治療主要以激素抗炎和減輕神經水腫,康復療法進行功能鍛煉;但激素有一定副作用,遠期療效不佳,治療具有一定局限性;康復療法多側重于運動功能,對感覺和二便障礙療效不足[16]。針灸簡便驗廉,無毒副作用,且研究表明針灸不僅能改善運動和感覺功能,對膀胱直腸功能障礙也有療效。陳楓教授運用“肝胃組穴”聯合足陽明胃經經筋排刺法治療痿證,亦重辨證,針刺時根據每次患者具體病情選取少許配穴,臨床上為大量患者緩解了病痛。此法治療痿證亦可推廣到任何局部肢體或肌肉的痿軟無力,如頑固性面癱、中風后遺癥等,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