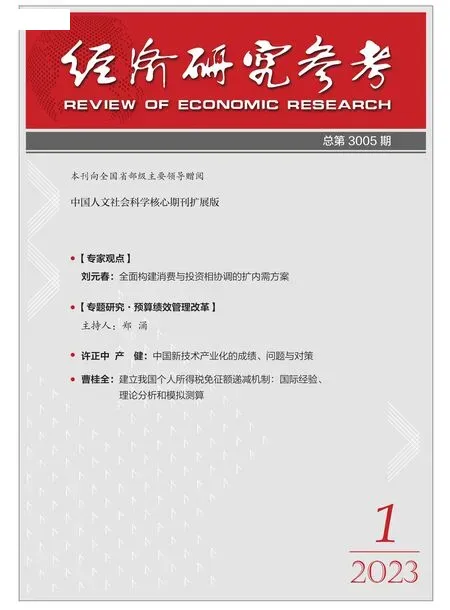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社會流動研究新進展:縱向流動、橫向流動及二者關系
蘇京春 張 荀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完善分配制度方面明確提出,要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我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總體思路中,“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1)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J].2021(20).被置于重要位置。鑒于達成橄欖型分配結構是邁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那么關于推動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的“社會流動”研究便凸顯出其重要性,這為進一步研究如何增強社會流動奠定基礎。
實際上,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Sorokin)早在其1927年出版的著作《社會流動》(SocialMobility)中,就已首次對社會流動開展過系統研究,并于1959年改寫為《社會與文化流動》(SocialandCulturalMobility)出版。他將社會流動定義為社會個體、價值或一切能被人類活動創造與修改的事物從一個社會位置向另一個社會位置的轉變,并認為社會流動有縱向流動與橫向流動兩種形態。所謂縱向流動,是指造成社會階層上升或下降的流動,包括經濟(如收入)分層、職業分層、政治分層等方面流動;所謂橫向流動,是指未造成社會階層上升或下降的流動,包括空間流動、宗教信仰轉移、家庭重組、職業變化等。
21世紀以來,社會流動日益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布的《2020年全球社會流動性報告:平等、機遇和新的經濟要務》指出,第四次科技革命為人類社會帶來了機遇與挑戰,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收入不平等問題日漸凸顯,現有的社會流動狀況不容樂觀且不可持續。報告統計數據顯示,平均而言,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與發展經濟體中,收入位于前10%者的收入水平是后40%者收入水平的3.5倍。報告測算的全球社會流動指數顯示,極少經濟體具備提升社會流動性的適當條件,在當今絕大部分社會經濟系統下,人們的出身背景往往決定了其受教育水平、職業方向、收入水平,產生了“鎖定效應”,這使收入分配不均衡愈加嚴重。(2)The Global Social Mobility Report 2020: Equality, Opportunity and a New Economic Imperative[EB/OL].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social-mobility-index-2020-why-economies-benefit-from-fixing-inequality, January, 2020.鑒于此,為了解決收入分配不均衡問題,世界范圍內需要將如何打破階層固化、激發社會流動活力提上議程并重點關注。否則,低社會流動將降低公眾經濟生活參與度,使收入分配不公根深蒂固,甚至阻礙全球經濟增長。
基于如上分析回觀我國,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產階層比重有所上升,但大部分中產階層位于邊緣,受外部沖擊后可能加劇回落低收入群體的風險,且中下層群體占比仍相對較大,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群體間收入差距問題仍較突出(李強,2021)。社會流動則是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之一。如果社會流動不暢,社會階層出現固化,那么縮小收入差距的努力也勢必受到明顯約束和阻滯。根據學者測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代際流動率明顯上升,尤其是步入21世紀以來,我國總體代際流動率在世界范圍內處于較領先位置(李強,2021)。反觀我國社會流動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城鄉之間的橫向流動在轉換為縱向流動時遇到阻礙(3)擴大社會性流動 促進共同富裕[N].光明日報,2021-09-14.、城鄉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規則有待健全、仍需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提供社會流動的基本保障(4)為什么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EB/OL].http://china.chinadaily.com.cn/ 2018-01/17/content_35525105.htm, 2018-01-17.等。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但是,在社會流動這一議題日漸矚目的當下,目前較少文獻基于社會流動具體表現以及影響因素進行綜述研究,進而探討如何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將相關前沿研究進展基于縱向流動、橫向流動,以及二者關系三個視角進行了梳理、歸納、總結與評述,并淺談了對我國現實問題的啟示,這是對現有研究視角的有益補充,以期引發新思考、提供新思路。
二、縱向流動:現狀與影響因素
縱向流動是激發社會活力、優化收入分配不均衡格局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將著眼于經濟分層等方面的縱向流動,對探討縱向流動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
(一)各國縱向流動狀況
索羅金(1959)認為,在較長的歷史階段中,包括縱向流動在內的社會流動程度并不可能呈現持續提升趨勢,如果流動程度在某一時期有所提升,那么該時期過后將有所下降,長期來看呈現出“無趨勢波動”狀態。基于此,本文將基于現有研究梳理我國與部分歐美國家一定時期的縱向流動狀況。
1.我國縱向流動狀況
依照以收入水平劃分階層構建的社會流動分析框架與衡量指標,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CHNS)基礎上,Liu等(2020)一文從總體縱向流動狀況、分時期流動狀況、縱向流動貢獻率三個視角展現了我國1989~2011年在經濟分層方面的縱向流動全貌,為分析2011年以來我國的流動狀況提供了可參考的分析框架。基于文章分析,本文得到的啟示在于,一方面,我國的縱向流動具有向好的一面:1989年以來,人們的實際收入水平持續提升;20世紀90年代,我國階層流動程度不斷提升;進入21世紀,處于最低收入階層的家庭擁有更多機會躍升至最高階層,且變動數量為4的家庭對縱向流動的貢獻率顯著增加。另一方面,我國的縱向流動亦存在許多需要關注與完善的方面:20年間,很大比重家庭并未實現階層躍升,在改變階層的家庭中,向上或向下流動1個階層者占比較大,流動4個階層者占比極少;最低階層家庭對向上流動的貢獻最大,但效應呈下降趨勢;進入21世紀后,總體的流動程度出現波動。
結合以上分析與現實困境,我國出現縱向流動活力不足、社會階層相對固化現象的潛在原因包括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教育資源不均衡等。在以市場回報為導向的當下,社會階層固化會引發“馬太效應”,身處高階層者有能力和動機將自身擁有的經濟優勢傳遞給其后代,若教育不均衡等問題未得到改善,將進一步阻斷弱勢家庭后代的向上流動通道,使收入分配不均衡加劇(Zhou & Xie, 2019)。因此,如何破解以上現實困境,進一步激發縱向流動活力,拓寬流動渠道,應成為當下需要聚焦的重點。
2.歐美國家縱向流動狀況
從歐美國家20世紀縱向流動總體狀況看,由于工業化帶來的社會階層結構變動,歐美國家出生在20世紀前50年的人們獲得了更多向上流動空間(more room at the top),向上階層流動程度平穩上升,向下階層流動程度有所下降,這一時期被稱為“黃金時代”;但隨著后工業時代的來臨,歐美國家出生在20世紀后50年的人們向上流動空間有所縮減,向下流動程度提升(Bukodi & Goldthorpe, 2022)。
相應地,在1950~1980年的美國(對應出生年份約為20世紀前50年),經濟層面代際縱向流動程度呈上升趨勢,1980~2000年(對應出生年份約為20世紀后50年)則不斷下降(Aaronson & Mazumder, 2008),但也有文獻認為該時間段內流動程度變化不大(Lee & Solon, 2009),而對于教育代際縱向流動程度,1940~1980年先顯著提升后逐步平穩,1980~2000年則不斷下降(Hilger, 2015)。在英國,20世紀70年代出生者與50年代出生者相比,經濟層面代際縱向流動程度有所下降(Blanden et al., 2005),但社會階層的縱向流動沒有顯著變化(Erikson & Goldthorpe, 2010)。在法國,1950~1986年也經歷了社會流動率的提升(Van et al., 2016)。
除以上視角外,也有文獻以姓氏分布這一全新的視角對社會縱向流動問題進行研究。Clark等(2015)基于歷史上英國和智利不同姓氏對應的教育或收入均值相關數據,發現英國在19世紀、20世紀表現出較高程度的教育階層繼承,智利在20世紀表現出較高程度的經濟階層繼承。也就是說,從這一視角,兩國縱向流動程度在相應歷史階段均呈現相對較弱水平。
在以時間維度梳理過歷史上部分歐美國家縱向流動趨勢后,本文還將整理展示國家之間近幾十年流動程度比較的相關研究。在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典五國之中,Alesina等(2018)將收入水平劃分五檔,分別為收入最低的20% (Q1)、20%~40% (Q2)、40%~60% (Q3)、60%~80% (Q4)、80%~100% (Q5),以父親一輩作為觀察對象,位于Q1收入水平的群體,觀察他們子女一輩的收入分別位于Q1、Q2、Q3、Q4、Q5各個不同水平的概率,以此來衡量縱向流動程度。經過統計后發現,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前十年,平均來看,美國的縱向流動程度在五國中處于最低水平,其子代收入水平位于Q1、Q2的概率在五國中最高,達到Q3、Q4、Q5的概率最低,瑞典和意大利縱向流動程度較高,英國和法國處于中間水平。
在加拿大、瑞典、美國,Corak等(2014)從社會階層的向上與向下流動兩個視角,基于父子兩代的收入比較進行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前十年,從階層流動概率看,三國向下流動程度的差異比向上流動更明顯,加拿大向下流動的程度最高;從向下流動者與父代的收入差異期望值來看,美國的向下流動程度最高;比較向上與向下流動者與其父代的收入期望值差異水平,美國和加拿大后者絕對值顯著更大,瑞典二者基本持平。
綜上,在一國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縱向流動狀況差異明顯。21世紀以來,我國縱向流動活力相對不足,而歐美部分國家則面臨著一定程度向下流動壓力。對比中美兩國,根據《2020年全球社會流動性報告:平等、機遇和新的經濟要務》,兩國社會流動指數分別排在82個經濟體中的第45位、第27位。報告顯示,我國在城鄉教育公平、勞動收入公平方面表現有待提升,而美國勞動收入公平程度排在82個經濟體末位。鑒于此,由于縱向流動狀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分配水平(Beenstock, 2004),并且部分歐美國家的社會流動發展階段可能領先于我國,存在某些值得學習借鑒的經驗。因此,為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我國需要重點關注縱向流動面臨的阻礙與現實困境,并結合他國經驗與本國實踐,拓寬流動渠道,持續激發流動活力。
(二)影響縱向流動的因素
索羅金(1959)認為,教育機構越來越成為檢驗、遴選、分配人才進入對應階層的主要機構,可以將其形象地比喻為“篩子”,在這個過程中,流動性可能被抑制或是提升。如今,除了教育,創新、公共評價、戶籍制度等也逐漸成為影響縱向流動的重要因素。
1.教育對縱向流動的影響
教育在人們從初始社會階層到最終社會階層的縱向流動中發揮著中介作用(Kuha et al., 2021; Erikson & Goldthorpe, 2009)。對英國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出生者數據的研究顯示教育對于多階層縱向流動的效應更為明顯(Kuha et al., 2021),且影響效應具有一定相當的穩定性。
進一步來看,對于教育對縱向流動的作用機制,有研究進行了基于模型的探討(Cremer & Pestieau, 2010)。首先引入三個概念:一是“平等主義”教育,即主要關注學生在受教育后是否能夠達到一定的基本讀寫能力水平;二是“精英主義”教育,即主要關注學生是否擁有最優秀的能力;三是經濟分層方面的縱向流動水平,即父母與子女處于不同收入階層的穩態比重。依據數理模型推導和數值模擬結果,研究發現,當社會只提供公共教育,并且公共教育完全奉行“平等主義”時,縱向流動程度可以達到最高值;當社會允許私人教育(主要形式為課外補習)與公共教育同時存在時,縱向流動程度較之前有所下降,其最高值將出現在公共教育背離“平等主義”、偏向“精英主義”的某一點。這是因為,如果此時公共教育仍然完全奉行“平等主義”,那么高收入父母會投資更多在私人教育上,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使其后代技能水平得到提升,從而有更多機會在未來繼續成為高收入者(父母收入越高,該效應越明顯),而主要依靠公共教育的低收入者后代更難實現向上流動,最終社會縱向流動活力下降;但如果公共教育一定程度上背離“平等主義”、偏向“精英主義”,高收入父母會更少投資在私人教育,不公平程度反而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縱向流動活力。
基于以上分析,對我國而言,為了激發縱向流動活力,需要首先從提升城鄉教育均等化程度(Marginson, 2017)、地區教育均等化程度等方面著手著力推進教育均等化,深化校外培訓治理以促進教育公平,改進中學教師指導模式(Richards, 2020)、提升高等教育整體水平(Marginson, 2017)、加大技能培訓的支持力度以提升人們向上流動能力,助力共同富裕。
2.創新對縱向流動的影響
有研究基于美國州級數據發現(Akcigit et al., 2017),當以專利數量衡量創新活力、以低技能父輩的后代獲取高技能職業的比重衡量縱向流動水平時,創新越強的州,往往更具有縱向流動活力;也有研究基于個人視角發現(Toivanen & V??n?nen , 2012),創新能力能夠顯著提升個人收入水平,尤其是對于高水平創新成果的創造者。
進一步來看,對于創新對縱向流動的作用機制,有研究進行了深入分析(Philippe et al., 2018)。基于熊彼特增長模型以及實證回歸,發現創新能夠提升縱向流動水平,這是由于普通勞動者與企業家之間存在收入不平等,勞動者有動機也有能力通過自身的創新成果,實現從普通工作者向企業家的縱向流動。
由此本文獲得的啟示在于,創新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其在激發縱向流動活力從而緩解收入不公問題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拓展縱向流動通道。因此,我國可以通過鼓勵萬眾創新、加大對其財政支持力度、完善創新創業相關投融資機制、優化創新創業環境等方式進一步促使縱向流動活力迸發。
3.公眾評價對縱向流動的影響
Piketty(1998)基于數理推導,發現人們在能力等方面獲得的公眾評價對其縱向流動會產生重要影響。具體來說,在多個假設下(如高努力者在公眾眼中具有更高能力),當個體對公眾評價的關注度不高,則存在一個縱向流動方面的低努力程度均衡;當個體非常關注公眾評價,那么存在兩個均衡,分別是低努力程度與高努力程度,前者帕累托占優于后者。但當社會地位出身比個人努力與能力的回報更顯著時,縱向流動會被削弱,原因在于低階層缺少動力投入較大程度的努力,而高階層為了保持自己現有的社會地位、避免失去現有的一切,會投入較大的努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雖然文章中的部分假設與現實并非完全適配(如現實中公眾更偏向于結果導向的“以成敗論英雄”,很少以努力的過程評價個人能力等),也沒有結合現實數據驗證該模型的可靠性,但也獲得許多啟示:一方面,為了激發縱向流動活力,我國可以考慮大力宣傳奮斗者的榜樣故事,以堅定大眾“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的信心與信念,激勵人們為夢想而奮斗;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引導公眾輿論更加關注個人的努力過程,鼓勵大眾投入更多努力以實現自我價值。
4.戶籍制度對縱向流動的影響
戶籍制度于1958年建立,在二元戶籍制度存續期間,如農村戶籍人口與城市戶籍人口相比,面臨著更明顯的向上流動阻力(Zhao & Li, 2019);外地居民在本地無法享受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務(Huang, 2020)等。基于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Huang(2020)研究發現,從農村戶籍轉變為城市戶籍者具有更高可能性實現向上流動,但對未來向上流動預期沒有顯著高于其他人,而從外地轉為本地戶口者對未來向上流動預期持悲觀態度。
但不能忽視的是,近年來,我國正不斷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包括2022年發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強調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落戶限制、完善城鎮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完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等。隨著各項改革不斷深化,這將有助于拓寬社會流動渠道、優化人們向上流動預期、激發社會流動活力。
綜上可見,影響縱向流動的因素多種多樣,縱向流動可能受到教育、創新、公眾評價、戶籍制度等影響。因此,我國可以考慮通過推進教育均等化、鼓勵創新、激勵人們通過努力與奮斗實現個人夢想、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等激發縱向流動活力,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三、橫向流動:現狀與影響因素
索羅金(1959)認為,橫向流動包括空間流動、職業變化、宗教信仰轉移等。本文將主要梳理空間流動與職業變化的相關文獻,內容包括相關流動狀況以及影響流動的因素。
(一)橫向流動相關狀況
首先,本文將回顧我國以及部分國家的空間流動與職業變化視角下的橫向流動狀況。
1.橫向流動狀況:空間流動視角
在我國,空間流動的表現形式包括因就業等形成的長期或短期居住地轉移,主要有城鄉流動、城市間流動,以及因旅游、探親、通勤等產生的流動行為等。本文在此部分將主要梳理我國、英國、美國城鄉流動與人才流動的相關狀況。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定義,近年來我國“人戶分離人口”規模(5)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定義,人戶分離人口即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持續上升:2010年人戶分離人口約為2.61億,較2000年增長81.03%,(6)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EB/OL].國家統計局官網,2011-04-28.2020年人戶分離人口約為4.93億,較2010年增長88.52%。(7)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EB/OL].國家統計局官網,2021-05-11.其中,城鄉流動,尤其是鄉村流出人口規模也呈大幅度增長趨勢。根據學者的測算,基于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國鄉村流出人口規模約為1.34億,2020年則達到2.72億,增長了一倍以上。(8)2.7億農村流動人口,歸宿是就地城鎮化嗎?[J].財經,2022(5).隨著城鄉流動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城鄉人口比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2010年居住在城鎮、鄉村的人口占比約為49.68%、50.32%,城鎮人口比重較2000年上升13.46個百分點;2020年居住在城鎮、鄉村的人口占比約為63.89%、36.1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今城鄉人口比例的倒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國的城鄉流動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流動就成為我國人口流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推行、民營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流動限制的逐步放開,我國農村地區出現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就已經開始向城市流動以尋求工作機會(Hao & Liang, 2016)。基于2012年中山大學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CLDS),Hao和Liang(2016)研究發現在出生年份為1948~1996年的城鄉戶籍人口中,鄉村戶籍人口進行了相對更多的空間流動,并且實現了更多職業方面的向上流動,其中鄉村戶籍人口中受教育水平較高、相對年輕的男性勞動力更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
除城鄉流動外,人才城市間流動也是各界的關注重點之一。2016~2019年,我國一線城市的人口凈流入占比分別為0.8%、-0.5%、-0.9%、-2.7%,(9)2020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報告[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40134,2021-02-25.呈現下降趨勢,而二三線城市的人口凈流入比重呈現一定上升趨勢(Jin et al., 2022)。根據《2021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2015年26%的本科畢業生選擇在一線城市工作,但2020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7%,相關研究認為,這與生活成本、家庭因素、戶籍制度等有關(Jin et al., 2022; Hu et al., 2022)。
綜上,我國城鄉流動與人才城市間流動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除此之外,隨著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因旅游、探親、通勤等產生的流動活力也在不斷增強,本文將在影響空間流動因素、空間流動對縱向流動的影響部分對其進行簡要探討。
在歐美國家,國內的人口流動特征各不相同。Lomax等(2013)研究發現,在21世紀前十年的英國,各地都有相當比例的國內各區域間的人口流動,其中英格蘭地區占比最大。而從總體來看,2007年與2002年相比國內人口流動呈上升趨勢,2011年與2007年相比則呈下降趨勢,這與英國人均GDP(2007年高于2002年與2011年)、失業率(2011年高于2007年)變化趨勢相關性較高。從城鄉流動看,英國持續著從20世紀70年開始受到廣泛關注的逆城市化趨勢,城市呈人口凈流出,鄉村地區則人口凈流入。另外,英國東南部地區呈現出國外移民凈流入、國內各區域間人口凈流出的特征,這表明該區域進入21世紀后仍然呈現出相關研究(Fielding , 1992)所歸納的“階梯轉移地區”(escalator region)特征,即國外移民來到東南區域后很快便流動至英國其他地區,后文將對此進行簡要介紹。
在美國,國內呈現出了高度的人口流動(Cooke, 2011)。從城鄉流動來看,其從鄉村向城市的流動開始于19世紀早期,但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郊區化使人們開始從城市向鄉村流動,其中向非大都市的遷移率在70年代左右大幅增長,80年代出現鄉村向城市回流趨勢之后,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人從城市流動至非城市區,2000年開始,雖然從城區外流的人數有所減少,但以上趨勢并沒有改變(Ambinakudige & Parisi, 2017)。從州縣際流動狀況看,21世紀頭十年,該流動率有下降趨勢,這可能與經濟危機、人口特征的變化有關(Cooke, 2011)。
綜上,本文梳理了中國、英國、美國近年來人口空間流動的大致狀況,發現在流動程度、城鄉流動、城市間流動等方面,我國與歐美國家的特征差異較為明顯,這可能與短期經濟狀況以及各國發展階段不同有關。對我國而言,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可以關注歐美各國的相關歷史經驗,緩和與解決我國在空間流動中產生的新問題,助力共同富裕。
2.橫向流動相關狀況:職業變化視角
沒有階層改變的職業變化是橫向流動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Sorokin, 1959),但現有文獻較少對其進行探討。Xiong (2008)基于美國人口普查局1988~2003年數據,發現20世紀90年代早期到晚期,職業流動率有所上升,20世紀90年代晚期到21世紀,職業流動率有所下降,其中橫向流動始終比縱向流動顯著更活躍,年長者流動率始終相對較小。Maren (2018)基于出生在1955~1975年的全體挪威人口在2003~2012年時的職業相關數據,以縱向與橫向兩個方向劃分社會階層進行研究,發現相對于高階層文化類工作者(如教授、藝術家、建筑師等)與經濟類工作者(高收入商界人士)而言,高階層平衡類工作者(如醫生、法官、工程師等)穩定性較高,即隨著時間的推移,轉變階層(縱向流動)或工作類型(橫向流動)的人數比例相對更少,但總體而言,各工作類型的工作者均較少轉換工作類型(橫向流動)。對于不同出生年份群體而言,更多相對年輕者進行了縱向或橫向流動,年長者則大多保持穩定。
但是,對于我國而言,目前較少研究關注職業變化的橫向流動,因此可以基于相關調查數據嘗試進行探討,以豐富與深化對我國社會流動總體情況的認識與理解。
(二)影響空間流動的因素
接下來,由于現有文獻較多關注于空間流動,本文將梳理探討影響空間流動因素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就業與收入、社會資本(社交)以及思想理論與政策背景。
1.就業和收入與空間流動
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以及更高收入是人口空間流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據統計,在25個OECD國家中,平均有約10%的人口流動與就業相關因素有關,其中美國、英國等國該比例相對更高(Sánchez & Andrews, 2011)。在英國,根據相關研究,基于就業因素產生的搬家想法對區域間流動概率貢獻最高(B?heim & Taylor, 2002)。而在英國、澳大利亞、瑞典三國之中,無論是短距離還是長距離流動,就業因素始終與其他因素(如家庭、住房等)相比處于相對重要的位置(Thomas & Gillespie, 2019)。進一步來看,對于高技能工作者而言,基于理論分析,Borjas等(1992)研究發現,高技能收入回報越高的地區,會有更多高技能工作者來此謀生。以美國為例,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其各州之間的技能回報差異是國內人口流動的最重要驅動因素(Borjas et al., 1992)。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就業與收入也成為人們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的主要因素(Morrison & Clark,2011)。
基于以上分析,對我國而言,目前也普遍存在由于就業與收入原因而進行的人口空間流動,如城鄉流動、人才城市間流動等,但對于其中凸顯出的一些問題,需要持續關注與完善,如提升鄉村進城務工人員社會公共服務水平,打破人才流動壁壘等,以此為人口流動創造良好空間、進一步激發人口流動活力,助力實現共同富裕愿景。
2.社會資本(社交)與空間流動
除了就業因素外,社會資本(社交狀況)也會影響空間流動。Wasmer (2010)基于數理理論模型,使用1994~2001年15個歐洲國家的社區家庭戶面板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研究發現,如果社會資本偏向“本地化”,即與朋友、家人、鄰居的聯系更密切時,社會資本增加會降低空間流動的可能性,而若社會資本偏向“專業化”,即與同事等群體聯系更密切時,社會資本增加會增加空間流動的可能性。Büchel等(2020)使用瑞士匿名電話數據與兩階段估計方法,探討社交網絡如何影響人們更換居住地的選擇,研究發現,當越多聯系密切的朋友居住在自己住址附近,人們搬家的可能性越低;如果人們決定搬家,那么搬至聯系較多、距離不遠的朋友所在住址附近的概率更高;通過與朋友聯系,人們能夠獲取更多該朋友以及該朋友的朋友所在住址區域的內部消息,可以作為前述影響的作用機制之一。Büchel等(2020)的主要結論與Wasmer (2010)具有一致性,均認為與鄰近朋友、家人的密切聯系會減少人們的空間流動,這在我國也是較為常見的現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后文所述,較少的空間流動可能相應會減少向上的縱向流動機會,因此很有必要做出權衡。除此之外,由于空間流動深受個人社交網絡的影響,對我國而言,應關注其中引發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著力破除信息壁壘,創造公平的空間流動機會。
在社交狀況影響空間流動的同時,空間流動也會對社交狀況產生反作用,進而還可能影響縱向流動。Weijs-Perree等(2015)基于通徑分析模型,探討了空間流動相關因素如何影響人們主觀意義上的社交網絡狀況,研究發現,由于汽車為人們去更遠的地方與朋友團聚提供了便利,擁有汽車的人群孤獨感更少,而騎行外出頻率越高者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步行外出頻率越高者社會滿意度更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啟示在于,我國可以更多考慮鼓勵大眾做空間流動,如看望家人朋友、旅行等,以提升人們的精神幸福感,使人們有更好的狀態投入工作與生活,進而有助于實現向上的縱向流動。
除此之外,對于空間流動與社會資本的相互作用,Wasmer (2010)還發現更少的空間流動會使人們對本地社會資本進行更多的投資,這進一步減少其空間流動,可能會提升其失業概率。因此本文認為,為了促進就業,我國可以適當鼓勵人們進行空間流動,以尋求更多就業機會、積累專業社會資本、進行更好的個人職業規劃,最終實現向上的縱向流動。
綜上可見,社會資本(社交)是影響空間流動的重要因素之一,空間流動也對社會資本(社交)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二者相互作用之下,還可能會對人們的就業狀況、幸福感等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對我國而言,可以考慮鼓勵人們進行多種形式的空間流動,如外出探親旅行、更換工作地點等,并著力創造公平的流動機會,激發橫向與縱向流動活力,最終直接或間接優化收入分配格局。
3.經濟思想理論、政策背景與空間流動
接下來,本文將介紹結合思想理論與政策背景對空間流動展開分析。Bill(2008)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以來三個時期與空間流動相關的經濟學等領域相關理論以及歐美國家的政策措施。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住在貧民區的人們一旦有能力就尋求空間流動,即搬家至其他居住區,因此以凱恩斯理論為指導的歐美國家在房屋供給方面進行干預,在貧困地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以提供福利。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政府不再在貧困地區進行基建投資,而是促使人們自己從貧民區離開,并將住房工程私有化。但弱勢群體如患有疾病者、無技能者等由于缺乏自主流動的能力,境況惡化。隨后歐美實行的第三條道路相關舉措減緩了美國大部分地區的貧民區聚集速度,但歐洲相關地區境況并未改善。21世紀以來,產生了全新視角的討論,如“幸福理論”(Layard, 2005)認為,為了減少犯罪、避免弱化與家庭和社區的聯結關系、提升幸福感,應當減少空間流動。
綜上可見,在不同時期,影響空間流動的思想理論基礎與政策背景各不相同。對我國而言,應根據我國的新時代新特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思考如何將思想理論與政策措施相結合,以空間流動作為著力點保障與改善民生,優化收入分配結構。
四、縱向流動與橫向流動關系:機制分析
縱向流動與橫向流動二者之間存在密切聯系。本文將探討以空間流動為主的橫向流動與縱向流動關系的相關研究,包括空間流動如何影響經濟、教育、職業分層方面的縱向流動,以及公眾對縱向流動評價如何影響空間流動兩方面內容,以期為緩解收入分配不均問題提供新思路。
(一)空間流動對縱向流動的機制影響
在英國,基于英國普查和健康相關數據,Fielding(1992)的研究發現,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英國的東南區域可以被稱為“階梯轉移地區”,即該區域能夠吸引國內(至少在21世紀以來也包括國外,Lomax et al., 2013)別處的年輕人流動至此,助力其實現階層的躍升,但最終這些移民又會流動至別處。“階梯轉移地區”的存在證實了空間流動對縱向流動的顯著影響。除此之外,以姓氏分布視角進行的研究發現,以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為例,選擇性的空間流動是造成高校錄取率(即教育分層方面的縱向流動)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Clark et al., 2015)。
視線轉向美國,基于歷史上空間流動的準自然實驗,即部分公共住房住戶搬遷至環境更好居住區產生的外生沖擊,Chetty等(2016)研究發現,長期來看,從高貧困率居住區搬家至低貧困率居住區的孩童在大學入學狀況、收入水平等方面表現顯著提升,即對于教育和經濟方面的縱向流動具有積極效應,其中對于搬家時年齡越小的孩童,該效應越明顯。
以上文獻主要關注空間流動對經濟、教育分層等方面縱向流動的影響,而從職業(技能)分層視角,也有研究(Borck & Wrede, 2018)深入探討了空間流動對其產生的影響。該文章建立“兩技能類型”空間均衡模型,推導后進行數值模擬,最終得出結論,職業(技能)分層方面的縱向流動與各地區高低技能者分布的分化程度、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呈負相關;低技能者的通勤成本會相對降低縱向流動程度;一定范圍內,空間流動程度越高時,縱向流動程度也越高。
綜上所述,適當的空間流動能夠對縱向流動產生積極影響。這對我國的啟示在于,一方面,各地應出臺并完善符合本地實際的人才引進政策,吸引各類技能人才,利用空間流動激發縱向流動活力;另一方面,對于工作地與居住地不在同一區域的群體,即想通過空間流動換取縱向流動者,如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無法負擔工作地附近高房價而選擇通勤時間較長住址的勞動者群體等,其面臨著收入水平低于期望、通勤成本高等問題,我國可以考慮通過對前者大力支持技能培訓、對后者政策補貼等方式改善其境況,使空間流動與縱向流動順利實現轉化。
(二)公眾對縱向流動狀況的評價對空間流動的機制影響
從各國縱向流動狀況的評價看,基于調查數據,在中國,平均而言,人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國內縱向流動狀況樂觀程度有所上升(Du et al., 2021)。在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典五國之中,美國公眾對本國縱向流動狀況最為樂觀,即實際向上流動程度低于公眾眼中的向上流動程度,歐洲四國公眾則相對悲觀(Alesina et al., 2018)。
而在主要的OECD移民國家中,基于各國數據和實證回歸研究發現,高技能者會有更高的可能性移民至公眾評價(即對于“通過努力能夠提升自身所處的社會階層、以獲得更好的生活”的看法)較為積極的國家,且移民成本較低;分年度回歸結果顯示,1990年與2010年的公眾評價對高技能移民有顯著影響(Lumpe, 2019)。這為我國提供了研究縱向流動如何影響空間流動的分析視角,可以嘗試使用相關調查數據或開展調查,以展示目前大眾如何評價我國各地的縱向流動狀況、該評價是否影響各地的空間流動狀況等,以豐富對我國社會流動現狀的認識與理解。
綜上,空間流動與縱向流動具有重要的相互作用關系,適當的空間流動對激發縱向流動活力具有積極效應,而公眾對縱向流動的積極評價能夠相應提升空間流動程度。結合我國空間流動與縱向流動現狀,我們需要更加關注并逐步完善在人才的空間流動以及空間流動與縱向流動相互轉化等方面出現的問題,進而提升縱向流動水平,最終在縱向流動與橫向流動的共同作用下實現收入分配格局的進一步優化。
五、總結與啟示
隨著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進一步優化收入分配格局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的焦點議題,而社會流動可以作為其中的有效路徑之一。基于索羅金(1959)對社會流動的界定,本文以縱向流動、橫向流動以及二者關系三個視角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主要得出以下結論與啟示。
從縱向流動來看,各國呈現的流動趨勢與索羅金(1959)觀點較為一致,即并沒有國家表現出流動程度持續上升或下降的趨勢。根據相關研究,我國20世紀90年代縱向流動程度持續提升,但21世紀前十年出現波動,縱向活力需要進一步激發,而歐美國家也面臨著活力不足,甚至存在向下流動壓力的狀況。根據相關研究,教育、創新、公眾評價、戶籍制度是影響縱向流動的重要因素。因此為了提升縱向流動水平,我國可以通過推進教育均等化、深化校外培訓治理、加大對創新的支持力度、激勵人們通過努力與奮斗實現個人夢想、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等方式,激發流動活力,優化收入分配格局。
從橫向流動來看,本文主要梳理了目前現有研究較多關注的空間流動相關文獻,發現近些年來,我國人口空間流動程度不斷增強,其中鄉村向城市流動、人才城市間流動較為活躍,而歐美國家21世紀以來流動水平出現波動,且持續著城市向鄉村的流動趨勢,以上差異可能與各國發展階段、經濟短期狀況有關。根據相關研究,就業與收入、社會資本(社交)、經濟思想理論和政策背景與空間流動息息相關。其中,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以及更高收入是人口空間流動的重要動機之一,而這一動機有助于優化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因此,我國需要著解決其中凸顯的問題,如鄉村進城務工人員公共服務水平不足、人才流動仍然存在壁壘等,為人口流動創造良好空間,進一步激發人口流動活力,助力實現共同富裕。除此之外,社會資本(社交)與空間流動之間也存在相互作用關系,因此對我國而言,一方面,應當關注其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創造公平的空間流動機會;另一方面,可以鼓勵人們多進行空間流動,包括更換工作地點、外出探親旅行等,激發橫向與縱向流動活力,最終直接或間接優化收入分配格局。最后,本文還發現思想理論、政策背景與空間流動具有密切聯系,因此在新時期,我國應結合新時代新特征,思考如何將思想理論與政策措施相結合,以空間流動作為著力點保障與改善民生。
從縱向流動與橫向流動關系來看,根據相關研究,二者具有重要的相互作用關系,適當的空間流動能夠對縱向流動產生積極影響,而公眾對縱向流動的積極評價能夠相應提升空間流動程度。因此對我國而言,需要關注并逐步完善在人才的空間流動以及空間流動與縱向流動相互轉化等方面出現的問題,進一步激發縱向流動與橫向流動活力,最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助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