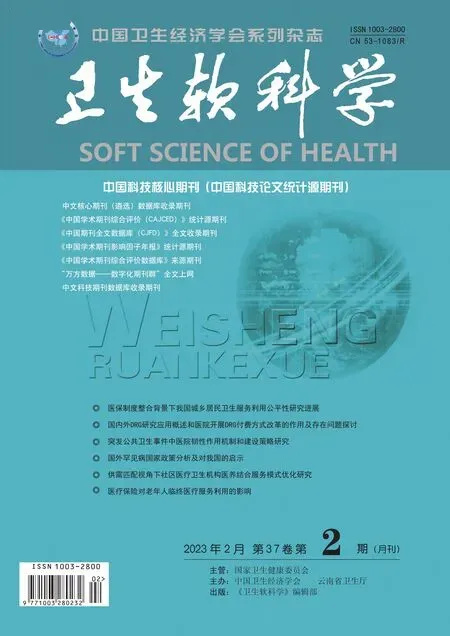國內外衛生系統脆弱性研究進展與思考
王羽璠,萬建成,劉 遠,孫麗麗,鄒冠煬
(1.廣州中醫藥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2.廣州市荔灣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廣東 廣州 510000;3.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廣東 廣州 510440)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將全球公共衛生系統的脆弱程度充分暴露,同時為提升系統韌性敲響警鐘。學界尚未對衛生系統脆弱性明確定義,國內也缺少對衛生系統脆弱性的直接研究。本文從脆弱性概念著手,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和總結,并為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加強衛生系統建設提出建議,以期為今后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1 相關概念
1.1 脆弱性
脆弱,漢語釋義為“易折易碎”,描述物體時為不堅強、不穩固的意思[1]。脆弱性意為“容易受傷”[2],對應英文“vulnerable”和“fragile”。二詞源自拉丁語“vulnus”和“fragilis”,分別是“傷口”和“易碎的”意思,前者用來比喻對非物理攻擊的無防御能力;后者起源于“frag”(打破,粉碎)和 “-ilis”(服從,易受)2個詞[3,4]。在最初應用的領域,即流行病學領域,脆弱性用于描述更易發生或感染流行病的地區[2];在應急管理領域,H’horges[5]將脆弱性定義為導致系統性失敗和崩潰的級聯效應的品質;在生命倫理學領域,Carmo等人[6]認為,脆弱性是由于個人固有的脆弱而處于危險或暴露于潛在傷害的狀態。
對脆弱性一詞的理解和使用隨著二十世紀80年代處理艾滋病流行的新方法而演變[6]。因為人們逐漸認識到傳染病的易感更多是由于一系列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而非個人行為[6]。二十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脆弱性概念研究從自然災害拓展到生態學、地理科學等領域;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更多關注,相關研究已廣泛分布于金融學、災害學、社會學等領域,與資源環境、政策指標、社會經濟等緊密相關,用以評價地區發展狀況以及衡量未來發展規劃[2,7,8]。
1.2 衛生系統脆弱性
脆弱性是健康領域常用的術語,但它仍然是一個有多種定義的概念[9]。衛生系統是指所有致力于衛生行動的組織、機構和資源[10],是衛生機構和衛生從業人員按一定秩序和內部聯系組成的功能整體[11]。脆弱性(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和安全等)與衛生系統以及健康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互聯系[12],因為醫療系統對不確定性的反應方式可能會使患者保持無知,從而為他們帶來進一步的脆弱性[13]。WHO指出,衛生系統對國家健康狀況和衛生規劃的運作至關重要。而逆向來看,衛生規劃不僅幫助實現衛生系統的目標,而且有助于減輕總體脆弱性[12]。
2 研究現狀
2.1 國內研究現狀
在社會科學領域,國內文章對“脆弱性”的研究多著眼于以“金融脆弱性”“銀行脆弱性”等為主題的金融學、以“城市脆弱性”“貧困脆弱性”為主題的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學和農業經濟學。衛生健康領域中許多文獻使用脆弱性的概念來表示患某些疾病或遭受環境危害的潛在風險[14]。
國內現有衛生系統脆弱性研究較少,且主要集中在衛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脆弱性和農村基層公共衛生應急系統脆弱性兩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學界對衛生系統脆弱性的內涵因學科差異尚未有統一標準。仇蕾潔等[15]在討論農村基層公共衛生應急系統脆弱性時,認為應急系統脆弱性是公共衛生應急系統及特定范圍內人群健康水平因內部的不穩定性,易受到某種外部因素的干擾,缺乏抗拒干擾,恢復初始狀態的能力;而應急能力是整個脆弱性研究的中心環節,農村滯后的預防和監測機制以及專業應急能力不足等是農村基層衛生應急系統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武春燕等[16]認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系統的脆弱性主要是指公共衛生應急系統的某些構成部分易受干擾和影響,存在薄弱點,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適應性不強,應對乏力。該團隊同時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中,農村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系統在制度體系、組織保障、人力資源、資金物資儲備、居民意識5個方面的脆弱性表現尤為突出。薛喬丹等[17]對我國省際衛生資源系統脆弱性進行了綜合評價,將衛生資源脆弱性界定為在健康風險或損害的壓力下,國家、社會、個人所表現出的衛生資源供給、利用現狀及能力,并得到我國衛生資源系統脆弱性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壓力主導型,且省際間存在差異性。
在研究衛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脆弱性方面,古德彬等[18]評估了氣候變化背景下基層衛生系統的脆弱性和適應能力。其團隊通過收集廣東省3市25名基層衛生機構管理人員對基層衛生系統氣候變化脆弱性和適應能力的主觀認識和評價,得出基層衛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為嚴重脆弱,未來脆弱性處于嚴重和一般之間。結合蘭莉等[18,19]對哈爾濱市衛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 VRA 的調查結果,提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管理人員認為目前基層衛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脆弱性會更加嚴重,適應氣候變化、保護公眾健康措施的可持續性一般,但仍對未來風險的應對抱有信心。
2.2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的脆弱性研究主體多集中于“脆弱”和受沖突影響的國家[20]、社區、臨床科室、特定人群、氣候變化等。Diaconu等[21]將脆弱國家視為政府不愿意或無法為其人民提供核心職能和基本安全的國家。Macharia等[22]通過為肯尼亞的子縣編制和計算社會脆弱性指數(SVI)、流行病學脆弱性指數(EVI)和社會流行病學脆弱性指數(SEVI),量化和反映出該國最脆弱的人群及其地理位置。Kim等[23]在研究芝加哥COVID-19死亡中的社會脆弱性和種族不平等時,指出該市COVID-19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非裔美國人社區的原因是貧困、種族歧視和空間排斥等結構性脆弱性已經摧毀了社區能力,加之疫情大流行之前,這類社區受多種慢性病干擾的情況已尤為嚴重,繼而得出社會脆弱性和健康風險共同導致了COVID-19死亡中的種族不平等。Wardrop等[24]在研究脆弱性在急診科的應用時,認為脆弱性是一個過程,在急診科患者的脆弱性的過程性體現尤為明顯;內在和外在因素共同導致了它的風險狀態。同時強調脆弱性是可習得的經驗,其積極性在于可以從脆弱經歷中吸取教訓,增強應對機制的能力。Shin Oejin等[25]根據生命經驗和文獻研究,將退休人員生活領域的老齡化脆弱性進行分類,使用物質、身體健康、社會和心理脆弱性的多維方法檢查了退休人員的脆弱性概況,并確定了脆弱性和幸福感之間的關聯,表明退休后脆弱性反映了多種不利因素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Mekuyie M[26]在一項定量研究中,通過應用戶主脆弱性指數,確定女、男戶主家庭對與氣候有關的沖擊和壓力的脆弱性。結果表明公共保健服務是增強其家庭對氣候適應能力的關鍵一環。而農民卻很難獲得。更好的保健可及性能夠增加家庭對氣候相關風險的脆弱性。
雖然該術語適用于國家特定情況,主要用于指脆弱的國家或環境,但脆弱性也用于指有缺陷或資源不足或表現不佳的衛生系統。Diaconu等[21]對全球衛生領域“脆弱性”相關文獻進行范圍審查,指出這一概念越來越傾向于在描述衛生系統與社區資源的相互作用時使用,長期處于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壓力因素影響的地區或社區,其衛生系統脆弱性主要是指有缺陷、資源不足或表現不佳的,且信任對于尋求健康服務利用以及衛生系統和社區復原力具有重要意義。
在Rae Dong等[27]對肯尼亞農村地區焦點小組進行討論時,發現對衛生系統的懷疑態度是實施非傳染性疾病計劃的潛在障礙,不僅患者因就醫過程中缺乏尊重、沒有得到充分服務而對臨床提供者缺乏信任,臨床醫生也因藥物供應不足和醫院人員不足對衛生系統表示懷疑,這進一步影響其照顧患者的能力。隨著COVID-19在全球傳播,生活在衛生系統薄弱的沖突地區的人們受到最嚴重的打擊[28]。在巴勒斯坦,衛生系統缺乏有效的治理、循證政策、資金、知識和信息共享、資源和技術以及衛生行動者之間的協調,阻礙了國家實施有效的衛生應急計劃和應對COVID-19[29]。在印度,各邦擁有管理衛生系統的主要權力,因此各邦之間以及內部城鄉一級均存在著巨大的醫療資源差距,第二波COVID-19中,缺乏可及性、覆蓋面和供應的印度衛生系統在龐大的醫療服務需求下遭受了系統性的崩潰[30]。南非豪登省建立了創新、多部門和全面的省級COVID-19應對措施,包括數字創新、尋找合作伙伴和為抗疫提供專用資源,但個人防護裝備腐敗、衛生機構封鎖、信息系統脫節、政府間關系不佳等脆弱性問題也被充分暴露[31]。
2.3 總結
強健的衛生系統支持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預防、應對及預后各環節工作科學開展,而不會陷入混亂局面。衛生系統脆弱性是入境問俗的,因此大部分研究是從某地區或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區展開。國外關于衛生系統脆弱性的研究較早,其中定量研究大都通過構建評價指數以量化系統脆弱性程度,實證研究主要基于問卷和訪談的統計分析揭示系統脆弱性原因,也有少部分論文總結了相關地區為增強衛生系統作出的有成效的努力。在國內,公共衛生領域的脆弱性研究寥寥無幾,且發表時間在近8年之內,集中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可見研究深度廣度和理論發展仍處于初步上升時期。同時,國內目前缺少對城市、國家衛生系統脆弱性的系統性的研究,而是集中于應急、衛生資源等方面的評價;其次,總結國內外系統脆弱性的文章甚少。本文通過文獻梳理,總結了衛生系統韌性的國際經驗,對減少我國衛生系統的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3 脆弱性研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加強我國衛生系統的啟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衛生系統的沖擊巨大。在我國,衛生系統脆弱性也表現在醫院停診、非新冠患者就診延誤以及醫院感染事件上。醫院停診使得腫瘤患者早期診斷、孕產婦定期檢查、慢性病患者的常規診療、購藥等的求醫空間受到了擠壓。在一項針對國內慢性病患者的網絡調查中,近4成患者表示出現了就醫延遲,其中近7成的延遲行為發生于本省市三甲醫院[32]。疫情爆發以來,湖北、黑龍江、山東、河北等多家醫院都報告了院內感染事件[33-35]。這些問題均反映了我國衛生系統的脆弱性:系統外部資源未能得到重視和有效整合,削弱了聯合全社會抵御風險的能力;系統框架內各部分本身具有高依存性的特點,但在實際運行中缺乏互動,配合松散,信息遲滯;在職人員數量不足且應急能力僵化……脆弱的衛生系統不僅無法應對突發且巨大的公共衛生需求,也會使政府、衛生系統和社區之間出現信任危機。基于國內外文獻的分析,提出降低衛生系統脆弱性的策略如下。
3.1 提升基層社區衛生治理能力,引導多元主體參與韌性建設
基層衛生設施、人員保障及服務質量未能得到有效的資金支持是衛生系統脆弱的原因之一。社區是基本衛生服務的首要提供者。初級衛生保健是實現衛生安全的途徑[36],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取得良好成效,社區作為最基礎的治理單位作用不可小覷。疫情常態化的背景下,一方面,政府應該提高對衛生系統特別是社區衛生服務的重視,包括增加財政支持以保障和完善必要的基礎設施、提高基層衛生保健在整體衛生規劃的比重,以及規范正式的系統治理結構;另一方面,動員社區各方力量,發揮非營利組織、民營單位等關鍵群體優勢,建立“平時-戰時”轉換機制,確保社區衛生服務平時準備到位,戰時儲備充足;再者,引導非正式的社會規范[5],以強化社區韌性建設,減少衛生系統脆弱性因素。
3.2 支持系統動態協作,提升應急響應能力
系統性風險源于風險之間的聯系,具有多個互連的系統中不僅具有獨立故障,而且相互依賴或“級聯”故障的風險[37]。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境下,衛生系統外部環境是高度變化和無序的,因而系統內部的穩定和快速運作是對抗風險逐級傳播的關鍵因素。此外,化解動態風險依靠社會多個政治部門的有效協調和通力配合,特別是利用現代通訊技術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的信息監測、預警系統。建議針對突發衛生事件制定靈活可變的管理流程網絡,用以支持衛生系統內部應急響應;完善全部門聯合應急機制,以容納橫向和縱向層級的快速聯動,避免各組織僵化行動而造成危機擴散。
3.3 保障衛生人力數量質量,增強系統可信任度
面對復雜的公共衛生環境,降低衛生系統脆弱性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提高其勞動力水平。醫療保健質量和可及性會受到衛生人力的制約,從而降低衛生服務雙方的信任感。有效的衛生工作者必須掌握提供高質量護理所需的技術知識和技能,也必須具備人際交往能力,才能從事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38]。不僅需要專業知識和人員齊全[39],也需要在動態響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和挑戰的過程中探索更具前瞻性和包容性的衛生技術[40]。對于政府而言,衛生人員的分布與充足性[40]、工作量與安全性[40]、薪酬福利和包容性的工作環境[41]、支持性監督[42]、賦權[42]和決策回歸[43]等都需要科學和創新的管理。最后,也要加強學術界與公共衛生部門之間的伙伴合作關系[44],以確保充分的教育培訓和連貫的人才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