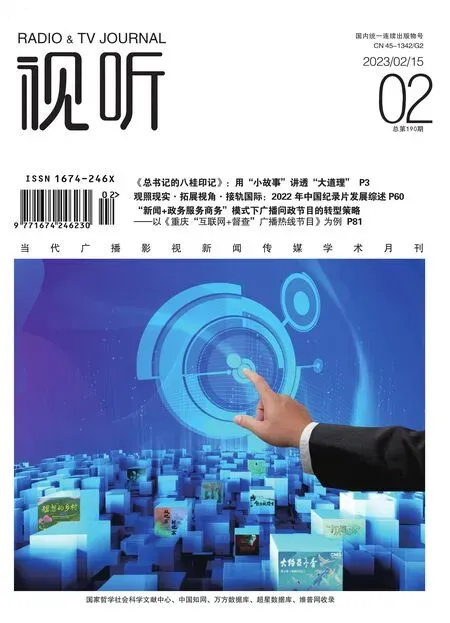智能傳播時代短視頻技術倫理的顛覆與共生
◎葉佳敏 朱紫綺 李佳璐
智能傳播是指以最大限度開啟人腦動能為基礎,憑借超級大數據,計算機技術加以輔助,融入數學、生理學、哲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應用于信息傳播的各個環節,包括智能機器人寫稿、人工智能“場景再造”、新聞源核查、新聞素材智能轉換和內容的個性化推薦。①當前,智能技術深度應用于短視頻行業,創造了內容多樣化、運營智能化的短視頻生態環境,這不僅是行業對技術的依賴,也是技術對行業的反哺。媒介技術發展延長了人類活動和感知范圍,轉變了傳統處理信息的方式,進而促生了智能媒體,這便使得短視頻行業在技術、內容、傳播形式和組織架構都出現了新風向。
一、顛覆:技術風險下的短視頻倫理悖謬
(一)“算法黑箱”造成隱私泄露
短視頻平臺中存在的隱私爭議向來是學界和業界持續討論的問題,隱私信息一旦被惡意利用,將會對個人隱私權造成極大挑戰。對人的行為展開研究,行動者僅僅從功利性和效率最大化的角度進行考慮,借助理性來達到自己所需要的預期目的,持有一種以技術主義和工具崇拜為核心目標的價值觀,即工具理性。②短視頻平臺中,用戶在視頻拍攝時極容易披露姓名、年齡、家庭信息等個人隱私卻不自知,另有一些用戶為了博取流量,主動暴露個人隱私,滿足更多用戶的獵奇心。
如今,短視頻平臺上出現了“搭訕直播”,指的是主播隨機選擇路人進行搭訕,在路人不同意或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將鏡頭對準他并開始直播,將其外貌、反應等信息傳至直播平臺,以供粉絲“圍觀”和討論。這樣的“搭訕直播”不僅侵犯了路人的肖像權,也嚴重侵犯了他人隱私權。隨著智能媒體的到來,短視頻平臺出現的隱私安全問題不僅僅停留在上述顯性行為,更有“無形的手”在不知不覺中偷取用戶信息,將用戶隱私暴露無遺。短視頻平臺依托技術驅動算法,將用戶行動軌跡、社交關系等個人數據錄入后臺中,為平臺運營提供便利。而這些個人數據中所包含的隱私信息用戶并不能直觀地感受到,或者說用戶對泄露之事并不知情。媒體等同理論里提到,“人們不僅僅將媒介視作傳播工具,更將其當作可交流的社會行動者。”③用戶在使用短視頻平臺時往往認為自己是主動的,有的人選擇主動展現,有的人傾向于社交互動。但其實無論哪種行為,用戶都處于無知覺地、被動地泄露個人隱私的過程中。
智能計算的前提是擁有大量、準確的用戶信息,因此平臺利用智能技術持續監控著每一個賬號,使用戶在平臺中處于“透視”狀態,其個人信息、興趣愛好都有可能變成數據,被收集和儲存在網絡平臺之中。用戶在這一處境中處于弱勢地位,他們對此類“高科技”不甚了解,無法洞悉“算法黑箱”的真相,只能抱著敬畏又惶恐的心態息事寧人。此外,許多短視頻軟件還植入監控、監聽技術,即使用戶從未在軟件中搜索過相關關鍵詞,但只要軟件在后臺運行,算法便能自動收集用戶信息,并為其定向推薦信息。短視頻用戶在長期的“定向投喂”下陷入了“信息繭房”,逐漸削弱自身的群體性。智能算法掌控著平臺的流量和內容生產方向,其影響力逐漸增大,但代價是放棄了隱私保護。
(二)AI“換臉”引發侵權爭議
過去,人們時常會幻想自己能否從外貌上變成另外一個人,這樣或許就能取得不一樣的人生。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幻想也能成為現實。AI技術能夠通過人臉識別、動態捕捉和深度模仿等算法輕松實現“換臉”,目前已運用于眾多領域。當前,短視頻行業的服務生產和技術配置飛速發展,人工智能自然不會缺席。短視頻平臺中,AI技術應用常服務于用戶使用一鍵瘦臉、人臉貼紙等功能,在后臺AI技術也可“對視頻內容進行審核、去重、溯源,并進一步對視頻打標、分類”④。然而,由于缺少技術管控,AI技術使用也面臨著部分侵權問題。2020年,抖音短視頻平臺上的“假靳東”事件讓不少網友覺得不可思議,同時不免對人工智能產生畏懼。演員靳東氣質出眾、形象良好,吸引了許多中老年婦女的關注。一些詐騙組織便瞄準了這一“市場”,注冊了上百個假冒演員靳東的賬號,并在短視頻平臺上憑借AI換臉技術以假亂真,迷惑女性用戶,以談戀愛的名義欺騙這些中老年女性的感情和錢財。此類視頻頂著靳東的臉和聲音行詐騙之事,發布經過剪輯配音的短視頻,有的還會直播時“換臉”,與粉絲互動,其呈現出來的“真實性”迷惑了不少婦女用戶,甘愿為“靳東”拋家散財。由于短視頻平臺上的用戶媒介素養參差不齊,對此類技術操縱下的騙局認知有限,警惕意識比較薄弱,不少中老年用戶容易對“眼前真實”的假象信以為真,盲目相信所謂的偶像和真心。
在深思老年群體存在技術鴻溝的同時,智能技術運用的合法性也應當被關注。人工智能技術商業化幫助了許多行業領域實現產業迭代和經營創新,政府和企業在進行智能化運作時也擁有了技術基礎。不可置否,智能技術給當前生活生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但其一旦用于灰色地帶,就會侵占倫理道德與法律準則。“假靳東”事件后,靳東工作室發布聲明澄清并表示將對涉事賬號追責到底,維護自己的肖像權和姓名權。同時,靳東方認為平臺未能起到監督審核的作用,應當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人工智能技術固然能夠極大地改變社會生活生產方式,但也催生了許多互聯網受害者。
(三)社交機器人挑起計算宣傳
隨著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風云變化,我國在政治傳播上面臨著復雜的形勢。尤其是在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后,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更為矚目,輿論傳播工作將成為媒體的首要工作。然而,信息時代的事件突發性讓社交媒體上的許多信息變得真假難辨,甚至難以抓住可以溯源的可靠信息。真假信息摻雜在社交平臺上,這不僅與平臺治理能力有關,也與背后存在的計算宣傳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計算宣傳是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加持下,通過算法、社交機器人、自動化代理器、網絡噴子等多種形式,為達到特定目的所開展的傳遞虛假或錯誤信息、制造信息污染、攻擊政治對手等一系列破壞網絡信息環境和政治傳播生態的行動。”⑤近些年,部分西方國家主張“網絡自由”,認為網絡空間沒有邊界,不受限制。計算宣傳的方式已然動搖當前的國際文化新秩序,對我國保護文化傳統造成威脅。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對于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而言是意義非凡的。然而,部分西方國家卻試圖利用異文化侵占我國網絡空間,威脅網民們的網絡生存環境。短視頻風靡以來,有關“網絡攻擊”“國家安全”的虛假信息大肆在平臺上出現,造成流言、謠言四起,其中便有社交機器人活躍的痕跡。這些虛假賬號大膽入主公共領域,宣傳引導重大話題的風向,對媒體環境造成了巨大的風險。智能技術打造的社交機器人潛伏在短視頻平臺之中,一旦議程設置成功,便能通過轉發、評論等方式操縱輿論,加強受眾認知偏差,將虛假信息傳播得更快、更廣,最終使用戶所接觸到的信息環境充滿了虛假成分,用戶開始對周圍環境產生動搖和懷疑,進而降低對政府、權威機構的信任。
二、歸因:技術與倫理的不平衡性
(一)工具理性至上
算法主導下的短視頻生產運營呈現出冷靜、準確等特性,人與機器之間產生較為明顯的疏離感。在生產、把關、推送等各個環節,短視頻平臺都需要充分借助智能技術來實現高效運作。當前,傳感器技術能夠實現大覆蓋面的信息采集工作,智能機器人能夠從事制作編輯等工作,而算法技術也能精準地完成信息個性化推送。由此看來,技術的優勢在短視頻行業發展中顯露無遺,因此行業內部逐漸將智能技術奉若神明,堅持以技術為支撐創新產品,在一定程度上為短視頻發展奠定了工具理性的思維。放眼短視頻平臺,作品以播放、評論和轉發數據來界定是否為“優質內容”,用戶以粉絲量來界定是否具備商業價值。一切評判標準都用數據來說話,逐漸隱去了用戶獨特的“人格化”。不僅如此,聰明的用戶也在追尋短視頻平臺的流量密碼,除了憑借內容出圈,技術操控似乎更是一條捷徑。用戶為了呈現出完美的數據,利用智能技術在暗地里開展了一系列炒作、造假等行動。這種過度強調工具理性的行為,最終只會導致行業倫理喪失和面臨法律問題。
(二)價值理性缺失
短視頻平臺只是網絡媒體的一個縮影,但它卻能更為直觀地將網絡媒體市場現狀呈現出來。無論是短視頻平臺,還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都遵循著流量為王的運營理念,一方面平臺以提供流量、資源互換等方式吸引用戶入駐平臺,另一方面用戶也不斷地通過創作或二創等形式為平臺提供內容,以獲取相應的流量曝光。在這一過程中,平臺和用戶其實是以流量價值為連接的雙向互動。但這種互哺行為由于缺少第三方的監督,容易導致平臺上出現道德倫理和法律等問題。如今,用戶在短視頻平臺上既可以充當傳播者,也可以成為生產者。但是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用戶信息生產取得的回報變得不可控。在注意力經濟時代,有流量才能被更多人看到和認可。因此,整個市場的走向逐漸被“流量”引導,開始沉浸在互聯網制造的狂歡之中。其中,主流文化價值的身影一直被遮蓋,雖然許多短視頻平臺都有政務號入駐,但其影響力還不夠大,應進一步發揮主流文化傳播的導向作用。此外,短視頻平臺逐漸出現消費主義景觀,越來越多的人被低俗化、娛樂化的內容驅使,信息生產內容只是簡單地搬運、剪貼,缺少獨立思維和精神內涵,導致人的主體性被弱化,用戶之間也缺少真正的情感連接和人文情懷。
三、共生:技術與倫理的祛魅存真
(一)以法律準繩避免技術失控
盡管智能算法為媒介傳播帶去了準確和高效,但其對于用戶權利的保護仍然需要在法制范圍內嚴格執行。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對“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進行了界定,規定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在短視頻后臺中的個人數據通常屬于信息性隱私,用戶在短視頻平臺的瀏覽關注、點贊互動、消費等行為都會被后臺算法記錄下來,通過技術處理形成特殊的個人畫像,在智媒時代也將其稱作為“數據隱私”。為了獲取相應的視頻服務,用戶不得不在使用短視頻軟件時做出一些退讓,但在合理范圍內讓步背后應也當有法律作為靠背。數據讓渡并不代表隱私權的讓渡,用戶仍然有權利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保護個人信息和隱私。尤其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利用技術手段達到個人或組織非正當利益的情況越來越多,我國法律也與時俱進地作出調整。2020年,禁止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偽造的方式侵犯他人的肖像權和聲音等已經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1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正式實施;2021年1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施;2021年11月14日,《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正式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對于算法應用的終極認可,要回歸到法律層面,其關鍵點在于對信息獲取和利用的合法性界限進行劃分。⑥只有將技術應用限定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才能促進平臺良性發展,增強用戶對網絡社交的信賴感,穩定網絡社會結構。
(二)算法規訓下重建倫理關系
算法技術的背后永遠是人的智慧,其主導權應當把握在人類手中。在智能媒體發展過程中,應當認清智能技術應用中最關鍵的倫理關系是人機關系,只有妥善平衡技術理性和人的主體性價值,才能讓智能技術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因此,當智能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技術本身對社會的革新性和影響力有必要被具體預估,從而避免過度依賴技術而導致社會淪為技術的附庸。短視頻中植入算法操作對當前媒體市場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合乎法律和常理的條件下對算法技術進行權力規訓是十分必要的。在政府層面的上位監督和行業內部的具體技術規制共同努力下,以算法為主導的利益追求不再是短視頻發展的尚方寶劍,而是要升級創新算法推薦機制,充分注重傳播中的正確價值引導,將技術倫理和傳播倫理放在短視頻智能傳播中的重要位置,重建人與技術的和諧倫理關系,才能真正發揮人類主體性價值,共促健康的人機關系。
(三)弘揚和傳播主流價值觀
工具理性中,以技術手段為主導,行為目的性較強,功利主義思想盛行而缺少人文主義,而價值理性中的情感價值和人文精神則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取得長遠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在短視頻利用智能技術不斷創新形式的過程中,應當強化平臺發展的價值理性,為信息生產注入更多具有審美、道德、內涵等精神層面價值的內容,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在算法機制方面,平臺應給予主流媒體更多的機會,助力主流媒體在平臺上能夠獲得公平的流量推薦機制和運營算法,適當地為主流媒體爭取深度智能的流量曝光和算法推薦偏向。此外,主流媒體也應當順應智能媒體時代的發展,學習并應用相關的智能技術,注重利用技術改變信息生產方式和信息生產內容,強調在技術應用的同時保障信息真實準確,具有一定的主流價值觀內容,符合當前主流思想與價值。
四、結語
智能傳播時代,以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云計算為代表的智能技術應用于媒體領域,傳統媒體、新媒體正朝著智能媒體的方向發展。在此過程中,智能傳播的主體是人還是技術,成為當前研究的重要課題。面對技術倫理問題,我們已經無法果斷地將其定義為工具理性或價值理性,當下的媒介環境只有將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結合起來思考,才能為技術倫理問題提供解決思路。因此,在短視頻發展過程中運用智能技術,既要做好技術規訓,又要注重人文價值,還要依靠法律制度,從而搭建起短視頻社交共識和價值體系,形成智能媒體生態共同體。
注釋:
①譚鐵牛,曾靜平.智能傳播的現實應用、理論溯源與未來構想[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8(02):2-8+147.
②李倩.智媒時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博弈——以AI合成主播為例[J].東南傳播,2020(01):27-29.
③[美]巴倫·李維斯,克利夫·納斯.媒體等同:人們該如何像對待真人實景一樣對待電腦、電視和新媒體[M].盧大川,袁野,李如青,錢亞萍,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213.
④AI技術加持,短視頻更加智能[EB/OL].鈦靈創 新,2020-10-10.https://mp.weixin.qq.com/s/meqigJu-s0w-qGTx-ktB9Q.
⑤史安斌,楊晨晞.信息疫情中的計算宣傳:現狀、機制與成因[J].青年記者,2021(05):93-96.
⑥秦萌.人工智能時代短視頻平臺的傳播倫理反思——以“抖音”為例[J].現代廣告,2020(09):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