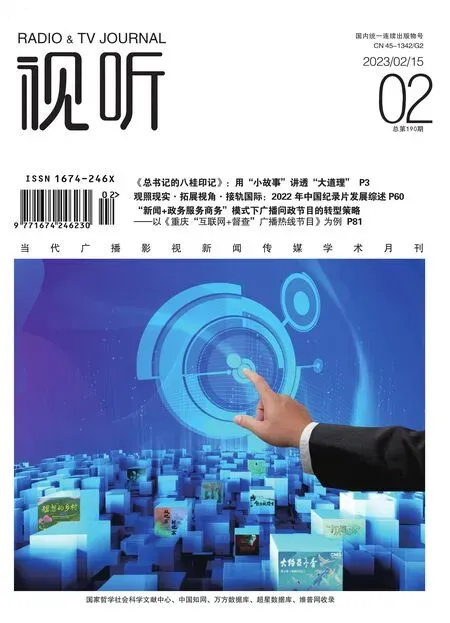從林明美、初音未來到A-SOUL:虛擬偶像的代際流變及本土化發展
◎楊雨萱
偶像是指吸引個人主觀對客體產生認同心理,并為人所崇拜模仿的對象。從蒙昧時期的宗教偶像演化到世俗時代的觀念偶像,是否崇拜偶像成為一件個人化的事情,“粉”偶像的過程也開始偏向于個人情感的表達和日常生活的調節。到了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娛樂偶像占據主流,追星成為一種繁盛的文化景觀。由追星引發的一系列風潮,也構成了現代社會審美文化的獨特現象。
麥克盧漢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喊出“媒介即訊息”的口號:“因為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媒介正是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人在新技術形態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進入的催眠狀態和自戀情緒。”①正如希臘神話美少年納西索斯因沉湎水中自身嬌美容顏的倒影,溺亡后化身水仙的故事,偶像是其粉絲內心期待的投射,是一場成功的美夢。埃里希·弗洛姆在《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中提出:“偶像崇拜的實質在于,偶像是人自己的雙手做成的東西,它們是物,而人卻向物跪拜,對物尊敬,崇拜他自己創造的東西。”②在消費主義的語系下,偶像是一種可盈利的商品,“造星”的根本目的也在于銷售。隨著造星工業的日漸成熟,一種更具可控性和再生性的消費產品誕生,那就是虛擬偶像。“虛擬偶像”一詞最早產生于日本。廣義上,它一般被認為是依靠數字技術手段制作,借助互聯網等虛擬場域參與活動,基于生產端在消費層面的需要進行塑造包裝的虛擬圖繪形象。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指出:“一旦技術使用了某種特殊的象征符號,在某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經濟和政治領域中,它就會變成媒介。”③虛擬偶像是一種新型傳播媒介,是人的延伸。它的興起與發展得益于現代科技的發展以及泛娛樂業態的體系化。
一、虛擬偶像的迭代與類型
現代技術及媒介以人的感官生理需要,構建擬真的環境,進化方向呈現出人性化趨勢,更加強調與滿足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一種“補償性”媒介,虛擬偶像沿著人性化趨勢的軌跡進化。根據其發展階段,虛擬偶像可以分為“有形無魂型”虛擬偶像(具有動畫設計的外形但缺乏肉身的現實性)、“形神分離型”虛擬偶像(有肉身聲音、動作等作為設計依據的虛擬外形)、“形神合一型”(直接捕捉肉身聲音、動作的虛擬外形)虛擬偶像這三大類型。
(一)“有形無魂型”虛擬偶像——以林明美為例
日本動畫人物林明美作為第一個以虛擬偶像身份誕生的虛擬人物,是虛擬偶像的元祖。她來源于1982年日本TV動畫《超時空要塞》,人設為藍發綠瞳的星際偶像歌手。從設計之初,林明美就是按照包裝真人偶像的思路為青少年動畫粉絲量身打造的虛擬偶像,所以一經推出便收獲大量粉絲,其發布的單曲《可曾記得愛》曾榮登日本音樂公信榜。林明美的外在形象與所呈現的內在性格由公司負責策劃與運營,是屬于“林明美”這一文化符號的,而聲優與作畫只是生成林明美這一虛擬偶像中的一環,并不賦予它自身的人格。其粉絲與偶像的關系是一種單向鏈條的聯系,粉絲對林明美的喜愛基于動畫作品與視覺形象,未產生深刻的交互性。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普及,虛擬偶像這一概念在20世紀末逐漸走俏,其后“有形無魂型”虛擬偶像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出來。但在虛擬偶像發展的初期階段,單一平面化的虛擬偶像只是市面中已存在的娛樂產品的補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受眾的視野,但因聯系范圍僅存在于“二次元”空間,缺乏粘連性,粉絲與虛擬偶像之間存在巨大隔膜,其變現能力也更多是建立在作為載體的電子產品銷售上。
(二)“形神分離型”虛擬偶像——以初音未來與偶像大師為例
“有形無魂型”的虛擬偶像以內容作為自身發展動力,是新興科技產品在泛娛樂業界的成功試水,為后世虛擬偶像行業的形成奠定基石。在新舊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跨媒介傳播成為資本競相角逐的新趨勢。21世紀初,虛擬偶像行業因此獲利,迎來了新的發展。虛擬偶像自此從第一階段的“有形無魂型”虛擬偶像走向了第二階段——“形神分離型”虛擬偶像。
“形神分離型”虛擬偶像形象專屬于虛擬偶像本身,內核基于人工創造,虛擬偶像與產生它的“中之人”(虛擬偶像背后的聲音動作等捕捉的肉身原型)存在彼此互異的發展路徑。舉世矚目的虛擬歌姬初音未來,是“形神分離型”虛擬偶像的代表。初音未來本質上是2007年8月31日雅馬哈公司與CRYPTON FUTURE MEDIA發布的VOCALOID2.0版本的音源庫。初音未來清亮甜美、帶有電子音感的音源數據取自著名聲優藤田咲,蔥綠色雙馬尾的少女歌姬形象則取材于插畫家KEI。初音未來憑借世界級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已然成為ACGN(Animation即動畫、Comic即漫畫、Game即游戲、Novel即小說)文化的象征。
與前輩相比,初音未來被賦予人格化,具有角色性,用戶體驗感得到增強。粉絲在使用VOCALOID2.0時,可自主編曲作詞,可以盡情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因版權開放,粉絲掌握了更多自主權,他們通過自定義編輯獲得滿足感,并聚集形成以同好為基礎的粉絲圈層。公司遂順應市場要求推出周邊活動,形成一條雙向良性反應鏈,使初音未來商業價值與文化價值不斷擴大化。以初音未來為代表的VOCALOID系列的虛擬偶像,是以真人聲源為基點,由公司打造的二次元形象。公司以它作為對象展開營銷活動。“中之人”只作為音源提供者,并不參與后續活動。而制作公司僅為虛擬偶像設置基本信息,并始終以“一款能歌唱的機器”來定位VOCALOID系列產品。
初音未來作為虛擬偶像,僅在特定的場合與話語體系下具有偶像性,與她同年“出道”的《偶像大師》是“形神分離型”虛擬偶像的另一個典型代表。2007年7月26日,由日本游戲公司南夢宮集團推出的養成游戲《偶像大師》誕生。《偶像大師》運營團隊深度借鑒日本偶像團體AKB48的制作模式,以選拔機制為基礎,賦予玩家對偶像高度的決定權,通過購買道具包裝偶像,使其出道,公司也通過展開多方合作來延長其紅利周期。《偶像大師》系列的“中之人”被視為二維空間的虛擬偶像在現實世界的投射,其演唱會也是由“中之人”代虛擬偶像出鏡參與其中的。“中之人”可以是一個扮演虛擬偶像人設的素人,也可以是已成名的現實偶像,她們在工作之余仍作為自身而存在。因“中之人”需大量曝光于臺前,培養“中之人”被納入《偶像大師》的運營體系中。粉絲可以關注虛擬偶像,也可以僅關注“中之人”,從而有了更多元的選擇。“中之人”與虛擬偶像存在差異性,若“中之人”個人活動出現問題,并不會波及虛擬偶像的人設,解約更換也屢見不鮮。
“形神分離型”虛擬偶像與前代相比已有巨大的進步。虛擬偶像與粉絲之間的互動聯系增強,把粉絲從消費方的被動狀態中釋放出來,促使他們在創造性的過程中成為積極的參與者。而虛擬偶像與扮演者“中之人”的分離,則意味著一種適合于成熟資本消費市場的、具有穩定產出能力、不易受現實干擾,同時具有現實粉絲基礎的一種幻覺式偶像的誕生。
(三)“形神合一型”虛擬偶像——以絆愛為例
隨著速率高、延遲低的新型移動通信技術的普及,設備具有的便攜性與私人性,以及媒體信息傳播與服務的流動性,操作系統日益朝著開放式方向發展,人機物互聯日益緊密。在虛擬偶像3.0階段,各種類型的KOL百花齊放般地涌現,虛擬偶像發展呈現多元化趨勢。但在2016年絆愛誕生并將“Virtual YouTuber”的概念引入大眾視野之前,虛擬偶像并未獲得極大關注。
絆愛以人工智能的概念出道,引發社會廣泛討論,被視為虛擬智能人般的存在,似乎賽博人的時代近在眼前。但事實上,絆愛是動作捕捉技術與虛擬現實技術發展結合的產物。通過在“中之人”的身體各部位設置傳感器,經過信號捕捉設備與數據傳輸設備對物理方位空間及身體尺寸動作的實時跟蹤測量,并由計算機分析數據建模成像,絆愛才能出現在直播間里。
絆愛是“形神合一型”虛擬偶像的代表性人物,其虛擬偶像的人物設定更依賴“中之人”的演繹。“中之人”雖依照虛擬偶像的設定框架為其填充內容,但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個人色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之人”為虛擬偶像賦予人格。“形神合一型”的虛擬偶像,其形象設定與內在詮釋的聯系更加密切,但并不意味著“中之人”是在簡單地扮演虛擬偶像,更貼切的理解是,“中之人”為虛擬偶像的身份認同問題提供了更好的解決思路,與此同時,“中之人”的業務能力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虛擬偶像的受歡迎程度。如果“中之人”有多方面的才藝展示,與粉絲建立的黏性就更強,能提高變現能力。
“形神合一型”虛擬偶像拓寬了與粉絲交互的渠道,粉絲觀看虛擬偶像的直播視頻采用的是非敘事的觀賞方式,即獲取虛擬偶像的動態更加自主和便捷,不受時空限制。粉絲與虛擬偶像的距離變得更近,粉絲可以通過彈幕或留言與虛擬偶像實時聊天互動,在“賽博”空間里實現親密接觸。
二、虛擬偶像與傳統偶像的異同——以樂華娛樂為例
“追星”已然成為現代人的心靈安慰劑。作為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工業產品,虛擬偶像與傳統娛樂偶像之間存在共相與殊相,具體從生產與消費兩個方面來進行區分。樂華娛樂作為中國知名的經紀公司和最大的藝人管理公司,其商業運作模式具有典型性。
(一)偶像的生產機制
約翰·費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中將大眾的快感分為兩類:“一種是躲避式的快感,它們圍繞著身體;另一種是生產諸種意義時所帶來的快感,它們圍繞的是社會認同與社會關系。”④大眾在消費偶像與體味生活間構建起兩者的聯系,產生娛樂意義,而大眾快感伴隨著人利用資源創造意義的生產過程。因此,一個偶像要想被大眾接受,就要符合大眾趣味,并在此基礎上留白,給受眾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間及自主創造空間。
娛樂偶像的“造星”方式大多依托于經紀公司。據2022年3月8日樂華娛樂向港交所提交的《樂華娛樂招股說明書》披露,其藝人從海選到成為偶像的培養周期共有四大階段,從素人選拔到偶像包裝,皆由公司一手打造。公司根據市場的期待,為偶像塑造不同的人設。人設是偶像的華麗光環,是商品類型的標識,以此為賣點精確捕捉受眾。但偶像的神話如同他們濃妝與濾鏡之下無暇的臉頰,只是一個美麗的泡泡,輕戳即破。偶像的名字被藝名或是人工設立的昵稱替代,淪為一種符號化的存在。經紀公司刻意制造偶像與粉絲之間的距離,呵護偶像被賦予的完美熒屏形象。粉絲面對偶像如同拜神教一般,只能在其后追隨與仰望人造的美麗皮囊和天然優秀的幻象。資本的篩選建立于商業邏輯而非道德范式,偶像“塌房”事件屢見不鮮。在工業化“造星”的模式下,更多的是產出優質包裝,而非優質偶像。
隨著技術的成熟,經紀公司推出“不老、不死、不塌房”的虛擬偶像成為有別于傳統偶像的另一條變現路徑,虛擬偶像的發展業態勢頭良好。虛擬偶像產業已形成覆蓋上中下游的規模化產業鏈。樂華娛樂憑借其龐大專精的偶像培養體系和字節跳動有力的技術支持,在2020年11月推出旗下首個虛擬偶像團體——A-SOUL,正式把虛擬偶像納入泛娛樂業務,進一步擴大了其商業版圖。《樂華娛樂招股說明書》顯示,管理虛擬藝人涉及的風險與挑戰較少,公司對虛擬偶像具有全方位管控權,易打造虛擬偶像零負面形象,并可以通過技術方法及時調整虛擬偶像的運營方向,以把握實時變動的公眾品位及市場偏好,維持其知名度。虛擬偶像可根據品牌或受眾的需求進行量身定制,又因虛擬偶像能突破時空界限,全天開展業務,所以越來越多的品牌方愿意與虛擬藝人展開業務合作。
2021年,樂華娛樂總收入約為12.90億元,其中藝人管理收入為11.74億元,占比達91.0%。雖然虛擬藝人所屬的泛娛樂業務板塊年收入只有3741萬元,僅占總體營收的2.9%,但對比所屬板塊的營業成本就會有極大的反差。2021年,樂華藝人管理成本占總營業成本的92.1%,傳統偶像的一年運營成本超6億元,而泛娛樂業務一年的總成本僅1.2%,毛利率高達77.7%。由此可見,虛擬偶像雖然在收入方面與傳統偶像相差懸殊,但由于易管理、投資風險低、營收毛利率高、發展前景廣等優勢,虛擬偶像在生產端極受青睞,是一片市場廣闊的紅海。
約翰·費斯克提出:“在一個復雜且高度精密的社會結構中,與日常生活的問題相協商的必要性,已經造就了‘游牧式的主體性’。”⑤當下人們獲取物質資料與信息資源的途徑十分便利,社會生活呈現出快節奏的特點,日常消費習慣也趨向“快餐式”。為防止對一個事物缺乏長久關注度,變得麻木,需要新生事物帶來的感官刺激。讓·鮑德里亞對消費生產力做出如下定義:“消費者與現實世界、政治、歷史、文化的關系并不是利益、投資、責任的關系——也非根本無所謂的關系:是好奇心的關系。”⑥偶像更新迭代速度越來越快,他們從工業鏈條上源源不斷地被輸送到市場,大多聲名鵲起后迅速“貶值”過氣,缺乏持久的吸引力。對生產端而言,虛擬偶像同樣面臨著如何長足發展的眾多問題。
(二)偶像的消費機制
偶像是大眾期待在具象化的人或物上的集中反映,粉絲將他們的個人情感投射在偶像身上,用他們完美的形象反映自身的審美價值取向。追星文化是大眾文化的分支,所謂粉絲可以界定為是一種大眾文化迷。約翰·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迷是過度的讀者:這些狂熱愛好者的文本是極度流行的,作為一個‘迷’,就意味著對文本的投入是主動的、熱烈的、狂熱的、參與式的。”⑦在傳統偶像的商業模式下,經紀公司推出各式各樣的偶像,通過營銷使偶像得以曝光,粉絲因對其產生認同而投入情感和消費。而偶像因積攢大量的粉絲走紅,產出符合粉絲預期的文化產品使事業得以延續,從而形成完整的商業閉環。粉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出發就是受眾中心論,即粉絲力量作為偶像價值的評估標準,深度參與偶像的生產與運營,通過粉絲行為進行反饋。
愛奇藝全國創意策劃中心在2019年發布的《虛擬偶像觀察報告》顯示,ACGN文化在Z世代的用戶中滲透率高達64%,有3.9億的年輕消費者正投身于虛擬偶像市場。在以新媒體為主流媒介環境的后追星文化下,粉絲得到更多的技術賦權,虛擬偶像與粉絲之間的關系也更近乎是共動的鏈式反映,而粉絲與偶像之間的不對等關系被完全打破。與傳統偶像相比,虛擬偶像有更多的“召喚結構”,即由未定義性和空白意義構成的基礎結構,所以虛擬偶像的粉絲生態更具再創造與生成性。⑧
虛擬偶像產業作為一種體驗經濟,最看重用戶的體驗感,而體驗感主要來源于偶像為粉絲提供的情緒價值和粉絲在人際交流中獲得的社會歸屬感。虛擬偶像本身的硬實力和人設特性是與粉絲建立牢靠關系的基礎,而粉絲社群是虛擬偶像文化得以生成與傳播的重要土壤,也是粉絲自我價值實現的場所。粉絲為了守護虛擬偶像這一共同目標,在持續的交流互動中投入社會資源,通力協作打造社群文化。這種交流雖然發生在虛擬空間,但人的感受卻是真實的,這是一種自帶濾鏡的情感假象。正如讓·鮑德里亞所說:“形象、符號、信息,我們所‘消費’的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心中的寧靜,與外界產生的距離則鞏固了這份寧靜。”⑨在虛擬社群中,盡管表現形式存在差異,但因成員間依靠分享共同的語言進行交流,某種程度上“圈地自萌”造成一個信息繭房,使粉絲產生一種虛擬烏托邦的幻覺。德·穆爾做出暢想:“電子顯現和虛擬現實似乎給古老的柏拉圖式和笛卡爾式的逃逸出身體囚牢之夢重新注入了活力。”⑩粉絲在現實中被抑制的自我得到釋放,愿意投入更多的情感與金錢,自此完成從虛擬偶像生產到消費的閉環。
三、虛擬偶像的本土化發展
虛擬偶像作為一個舶來品,在中國經歷了從無到有的本土化的發展過程,取得不錯的成績。艾媒咨詢數據中心發布的《2021中國虛擬偶像行業發展及網民調查研究報告》顯示,虛擬偶像行業發展至2020年,中國虛擬偶像的核心產業規模已擴展到34.6億元,與2019年的20.5億元相比,增長率達到70.3%,預計2023年將增至205.2億元。在調查的樣本中,有超過80%的網絡用戶存在崇拜偶像的行為,其中63.6%的用戶關注虛擬偶像的相關事件。虛擬偶像具有可塑性和延續性,其本土化的進程也是科技不斷下沉的過程。
虛擬偶像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而中國虛擬偶像行業在新千年才開始起步。誕生于2001年的青娜是中國公司自主研發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個可以被定義的虛擬偶像。她作為中國首部全數字電影短片《青娜》的女主角,成為當年中華世紀壇展映會上的璀璨新星。青娜的名字源于英語中“中國”的音譯,墨色秀發搭配一襲白衣的人物設計體現出中式審美,輕盈舞動的身姿展現出古典舞的韻味。短片《青娜》雖然只有5分鐘時長,但填補了中國數字電影領域的空白,青娜也成為中國虛擬偶像的開山之祖。令人遺憾的是,當時國內虛擬偶像領域并未形成完整的商業閉環,一切皆在發展初期。青娜作為中國第一位虛擬偶像,盡管當時媒體對其大力宣傳,但收效甚微,又因制作方的合約矛盾,導致青娜的后續運營化為泡影,成了一個歷史遺跡。
2004年,E欣欣成為中國首位虛擬形象與真人原型相結合的虛擬偶像。她以藝人李欣欣為真人原型,頂著“八位一體”超人氣虛擬偶像的名號出道,通過大量熱點事件博得關注,開啟一代炒作營銷虛擬偶像之先河。此后,中國內地仿佛成為虛擬偶像的試驗場,群魔亂舞,商家通過構建一個與市場貼合的虛擬形象為噱頭,販賣概念。生產端的粗制濫造無法吸引積極消費,虛擬市場存在虛擬偶像變現難、過氣快的問題。真正將中國虛擬偶像的概念引入大眾視野的是八年后出現的洛天依。
2012年7月12日,雅馬哈公司在第八屆中國國際動漫游戲博覽會正式推出第三代音源——VOCALOID3,它是全球首個以中國元素打底制作的虛擬形象,擁有中國發音聲線的VOCALOID音源庫。作為一款面向中國市場的音源庫,洛天依從設計之初就被確定走“國風”路線。洛天依定位為靈秀天然的15歲中國少女,梳灰色古典發髻,佩以中國結腰墜及碧玉發飾,夏風華韻,極具古典美。洛天依初創前三年,因雅馬哈公司缺乏對中國市場調性的把握,其運營一度陷入停擺,直到上海禾念公司全面接管洛天依這一項目的官方運營,組建新團隊專理洛天依IP拓展事務,洛天依才開啟全方位本土化運營階段。通過后續良好的運營,洛天依從一個小眾圈層的虛擬偶像成長為一個能代表國內頂尖水平的跨媒介IP,成為中國虛擬偶像日漸崛起的證明。
在洛天依誕生之前,中國就已經有了虛擬歌姬的概念。與洛天依相比,中國的第一位虛擬歌姬東方梔子的命運就更顯坎坷了。2011年12月27日,在天津電視臺承辦的中國文化藝術獎首屆動漫獎頒獎典禮上,東方梔子作為晚會的特殊嘉賓,演唱了一首同名歌曲,正式開啟了虛擬偶像之途。但因與初音未來極其相似的外形以及粗劣的制作,網民對東方梔子的謾罵嘲諷不絕于耳。2012年5月15日,制作者劉冰決定放棄對東方梔子的運營。雖然隨著版權的開放,一些有能力的粉絲對“棄養”的東方梔子進行了重新開發,使她迎來短暫新生,但僅靠情懷支持根本無力回天。東方梔子雖然開一代虛擬偶像之先河,但其結果卻難逃隕落。
從2015年起,中國虛擬偶像迎來了蓬勃發展的階段。2015年2月1日,由華夏動漫設計的虛擬偶像紫嫣在深圳灣體育中心成功舉辦名為“記憶碎片”的全息三維演唱會,開創中國該領域之先河。2015年10月26日,在湖南衛視舉辦的選秀節目《一唱成名》中,作為虛擬族群代表的零登場演唱原創曲《真實世界》,成為中國第一個參加選秀節目的虛擬偶像。2018年1月28日,安菟女團中“時尚擔當”夏行美在國內互動直播平臺虎牙成功實現了全世界第一場由虛擬偶像作為電競主播進行的游戲直播。這一舉動進一步拓寬了虛擬偶像的發展道路。
技術升級推動虛擬偶像對真人的仿真程度逐步提高,從外形寫實程度和智能程度兩個角度提升,虛擬偶像也越過恐怖谷效應,朝真人形象發展,并越來越打破互動方式的符號化,虛擬偶像與粉絲也從隔空對話走向零距離對話。2017年8月12日,虛研社旗下的小希在嗶哩嗶哩彈幕視頻網站開播,成為中國首個虛擬主播。2019年,百威投資集團制作的哈醬作為哈爾濱啤酒的代言人,成為中國首個超寫實虛擬偶像。隨后產生了以翎Ling、Qeelia、AYAYI、柳夜熙、蘇小妹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形神俱佳的超寫實虛擬偶像,獲得資本的極力追捧和消費者的喜愛。
2022年1月1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十四五”時期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總體要求和發展目標。虛擬偶像產業方興未艾,是數字經濟的行為主體,符合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也是時下熱門的“元宇宙”概念在現實領域投入應用的雛形。虛擬偶像產業發展勢頭良好,具有極大的潛力,受到生產端與消費端的廣泛追捧。發展虛擬偶像產業不僅利好整個上中下游產業鏈,還能成為向世界展示中國智能化的一面亮眼旗幟。
四、結語
約翰·費斯克認為,“一種商品要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須包含大眾利益,大眾文化不是消費,而是文化——是在社會體制內部,創造并流通意義與快感的積極過程:一種文化無論怎樣工業化,都不能僅僅根據商品買賣來進行差強人意的描述。”?虛擬偶像作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在帶給用戶愉悅的同時應關注其獨創性,在提升虛擬偶像商業價值的同時應考量其是否有恒久的存世價值。當前,我國虛擬偶像行業還在初始階段,雖然未來前途光明,但目前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需提升技術能力,提高工藝水平,兼顧其審美屬性,謹防早期虛擬偶像過度追求商業回報,造成藝術性和文化性缺失,墮落為以獵奇為偏好的亞文化群體的囊中物,進而產生負面社會影響。
注釋:
①[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4-44.
②陳學明.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西方馬克思主義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348.
③[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0.
④⑤⑦?[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玨,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28-173.
⑥⑨[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12-13.
⑧陳云昊.魯迅的神思與《新生》的神思——以魯迅、許壽裳、周作人為中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04):194-210.
⑩[荷蘭]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M].麥永雄,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