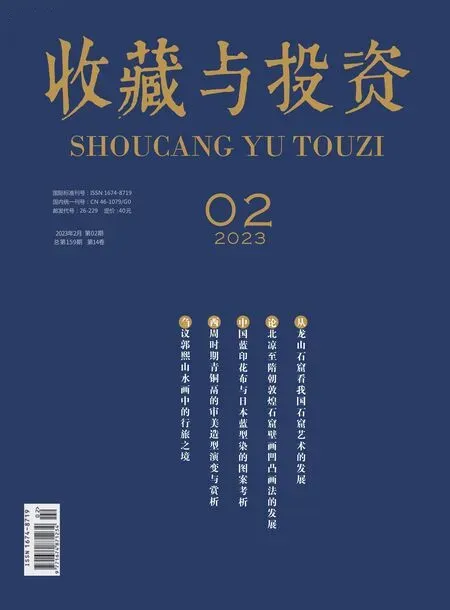長沙出土多子漆奩的情感化設計分析
陸雨龍,高帆(.天津美術學院,天津 30043;. 中國地質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0)
一、漆奩概述
在古代中國,漆奩是常用生活用器,最早出現于戰國楚地,妝奩是其常見的用途。在漢代經過發展演變出了多種形制[2]。在多個長沙出土的漢墓中,多子漆奩是極具地方特色與高超造物水平的文物,真實地反映了漢代漆器設計之高超、工藝之精美、巧思之豐富,是研究秦漢工藝美術的重要資料。對其進行研究,可以發現其設計理念以及文化符號與美國心理學家唐納德·諾曼在其著作《情感化設計》中的解釋有諸多相通之處。其將設計分為3個層次:本能層次、行為層次和反思層次。每個層次在多子漆奩的設計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本文挑選長沙漢墓出土的多子漆奩來進行情感化設計內涵分析,探究其與現代設計的共通之處,從而尋求中國傳統設計思想對現代設計進行啟發的可能性。
二、長沙出土多子漆奩的情感化設計分析
(一)經濟發展、更高的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工藝進步(本能層次)
諾曼對于本能層次設計的描述是這樣的:“人類的進化結果使我們對來自外界環境的強烈情感信號非常敏感,這自然形成了本能層次的反應。人們對于某樣器物最直觀的感受,我們稱之為本能層次的反應,最直觀的就是對于一件器物是否‘漂亮’的判斷,即來源于本能層次。”反映到設計中就是器物外觀以及裝飾是否能夠吸引人去使用,體現到具體的器物上就是物體的形狀、色彩等等要素給人的直觀感受。
長沙出土的漆奩在視覺上給人一種精致、華麗的感覺,并且隨時代進步,其精美程度越來越突出。長沙出土的漆奩形狀以圓形和方形為主,頂蓋為平面或者微微隆起,裝飾多為帶狀環繞于器物周身。漢初時期的漆奩裝飾多采用錐畫或錐畫與彩繪結合的方式。1971年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錐畫狩獵紋漆奩(圖1),其奩蓋、奩身均為錐畫紋飾,蓋身外壁上刻畫有長達101.4厘米,高4.4厘米的畫卷,其中人物刻畫細致(圖2),故事銜接巧妙,整個器物盡顯華美,是西漢早期的漆奩佳品。

圖1 錐畫狩獵紋漆奩 長沙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出土

圖2 錐畫狩獵紋漆奩上刻畫的裝飾
漢初文景時期的漁陽墓中出土了一件銀扣六子漆奩[3]。其在錐畫技法之外還加飾了數周銀扣,使得工藝更加精美,是長沙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采用金屬鑲嵌工藝的漆奩。金屬扣具的使用代表這一時期金屬鑲嵌技法開始與漆器工藝相結合,此后金屬鑲嵌工藝的使用更加頻繁,紋飾更加精美繁復。到了西漢中晚期,金銀貼花逐漸替代了錐畫工藝,成為漆器裝飾的主要手法。1958年在長沙五里牌公路的西漢中期墓出土了一套多子漆奩鑲嵌葉形金屬裝飾[2]。從以上出土的漆器所在的時代來看,可以看出每一個時期的器物都代表著當時工藝水平和裝飾技法的最高水平,也直觀地表現了當時精美華麗的外觀設計更能夠刺激感官,使產品更受歡迎。
裝飾技法的發展直觀地體現了情感化設計中本能層次的審美進步與工藝進步,究其原因應是與漢代的經濟進步有關。從漢代開始,漆器生產發展得更為成熟,經濟繁榮使得物質資源更加豐富,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夾貯、木片卷貼等胎體工藝的成熟使用,使得漆器的造型可以更加精美,漆器工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這樣的設計也體現了漢代貴族的審美高度。
(二)“應物賦形”的先進收納設計(行為層次)
南唐謝赫在其著作《畫品》中提出畫有“六法”,其中有“應物象形”“隨類賦彩”這兩個概念。所謂“應物象形”,即要求畫家描繪的事物要與描繪對象形似,而“隨類賦彩”即要求畫家在繪畫中將畫中物象分類賦色。多子奩盒為了充分利用邊角空間以及適應其內盛放物品的具體形狀而設計了各種不同的器型,可將其歸類為“應物賦形”。如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繪雙層九子奩,其9個子奩分別采用圓形、橢圓形、馬蹄形、長方形等(圖3)[2],均是為了盛放形狀不同的生活用品而單獨設計:圓形和方形的奩盒多用于存放胭脂、鉛粉等油狀、粉狀化妝品;馬蹄形子奩用于存放梳篦;長條形子奩用于存放發簪等長條狀物品。并且采用了斫木胎制作,用了一整塊厚木板削出凹槽,使得子奩在其中更加穩固。以上這些都體現了“應物賦形”的人性化設計理念,經過量身設計的子奩和母奩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盒內空間,子奩和其內容物同樣是嚴絲合縫,精致又美觀,使得空間能夠物盡其用。

圖3 漆繪雙層九子奩的各子奩形狀
這樣的設計理念充分體現了本能層次的設計,提升了便利性,是人性化的設計理念。這種設計使人們可以更安全高效地收納,使金屬類裝飾品、木制用具、脂粉類、銅鏡等都可以安全地放在同一器皿內而互不影響,收納的保護性做得很好。
事實上現代的運輸包裝也與其理念有同工之處,在現代物流運輸中,普遍認為方形外包裝是最便于運輸空間的規劃,為了保護包裝內各種形狀的物品,廠家一般會將產品嵌進切削好的泡沫中,如此在運輸中就不會因為晃動而導致物品損壞。這一方式還在不斷地發展,設計師也在將更安全的運輸方式與環保概念相互結合,如今各類電子產品的包裝盒多使用紙板切割來固定產品,使各類部件能夠嚴絲合縫地“鑲嵌”進包裝盒,同時也方便折疊和回收。在保護產品之余,也使包裝本身充滿人性化的設計巧思。
(三)飽含人文情懷的裝飾設計(反思層次)
1.多子奩盒的文化底蘊
在漆器發展史中,多子奩盒這一特殊形式中蘊含的傳統文化與人文氣息都在裝飾的運用中得以體現。它承載著時代的記憶,也是時代精神的產物,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同時也隨著朝代的更迭不斷注入新的精神力量。器物精神的本質就是人文精神,《易經》中提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之理念,器物之道不僅包含了使用目的,也傳承了文化內涵。人對于器物的態度和見解會對工藝設計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一理念反映了人類造物中物質與精神的統一。
漢代漆器的裝飾紋樣多受先秦時期的影響,并且有所繼承,中國的傳統造物理念中也蘊含著“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理念,所以在漢代漆器中也蘊含著古代先民的美好生活愿景,同時漢代漆器也受到了道教“道法自然”、楚騷美學以及封建禮教等多種文化的影響[4]。例如漆器中的云氣紋是受到商周時期的云雷紋的影響發展而來,漢代漆器的云氣紋則多是為了表達漢人羽化登仙的精神需要和浪漫的時代追求,即是受到了楚文化的影響,為云氣紋轉向精神意義為主與更多對于哲學上的思考發展做了一定的鋪墊。可見在當時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大背景下,當時的工匠已經能夠從不同角度去挖掘器物深層次的文化底蘊,從而滿足使用者的情感需求。
反觀當下,社會正處于高速發展的狀態,原本是可以使器物被賦予更多的文化底蘊,但是受到現代主義設計浪潮的影響,器物設計中更多地考慮了使用功能而忽視了文化表達,其設計中精神方面的匱乏也使其多了一種“冷漠感”,當代的器物設計仍應秉持物以載道的準則,實現在機器大生產的社會背景下的現代傳承與發展,從而使器物設計重新煥發活力并蘊含更多文化底蘊,這也是多子奩盒情感化設計在反思層面中值得探討的部分。
2.多子奩盒的交互體驗
器物設計的目的在于人而不是器物本身,因此器物設計必須要從多個維度去提升使用者的體驗舒適度,器物與使用者的交流互動也是需要被考慮在內,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多子奩盒都能給使用者帶來不同的體驗。
在生理上,觸覺與視覺是使用者與多子奩盒主要的交互形式。從視覺的角度來看,多子盒是一個大的圓盒,容納多種不同形式的小盒,相比于傳統的漆器形式會帶來更大的視覺沖擊力,多子盒內形狀各不相同,曲直結合產生一種富有變化的韻律美,是節拍的象征化。紋樣豐富多樣,多為植物紋、云紋、動物紋等形式,并且一般是主紋與地紋結合,疏密有致,突出主體。
在心理上,漆器在使用過程中,受到使用者的觸摸等多種行為的影響后,自身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其表面會更加圓潤、光亮。這個過程中,使用者與漆器之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也會令使用者對漆器的喜愛加深,而且器物因為受使用者的影響變得更加具有美感,能夠進一步地提升使用的滿足感,打破了器物主要以觀賞為主的傳統,增加了使用者對器物的依賴感。使用者使用漆器的過程不僅對漆器帶來了外觀上的改變,同時也會改變自己對它的評價。
另一方面,多子奩盒這一特殊形式是將不同形態的子奩組合在一起,既有實用性,又帶給人們一種和諧的美感,彰顯著獨特的形式美法則和“以人為本”的設計思想,而且增加更多的是趣味性,增加了不同子奩組合的可能性,將原本的被動選擇改為根據所使用的物品選擇其內部的組合形式,并且漆奩內部的自由組合拼裝拉近了使用者與器物的關系,并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使用者“求新”的心理。
三、結語
由于漆器制作的復雜性,其自古以來多是權貴一族玩賞和使用的器物,多子漆奩也常見于漆器盛行的荊楚、秦漢時期。在長沙漢墓出土的多子漆奩,使我們能夠一瞥那個時代工藝美術的最高水平,隨著時間的推進,漆奩的工藝也在逐漸進步,其本身就可以體現那一時期的漆器發展史。而對于其情感化設計的研究,是我們基于現代設計思想對漆器的出現、發展的一次重新解構,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功能、工藝發展中對人文的關懷。如今精美的工藝品早已進入普通人的生活,人性化、充滿情感關懷的設計也在逐漸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期待在未來我們能夠看到傳統工藝發展出更加具有情感表達的創新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