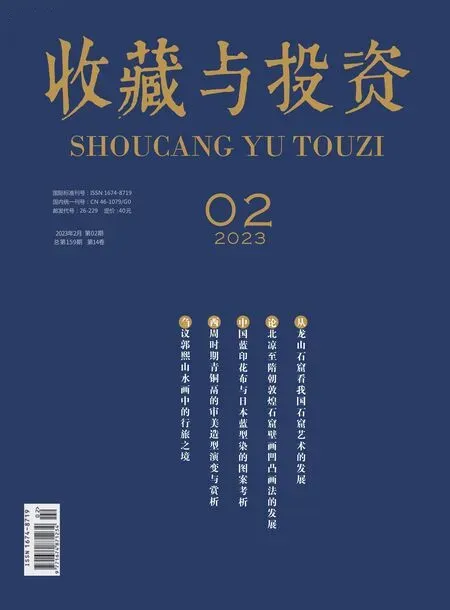婺州窯堆塑藝術研究
黃信遠(東陽市文物保護所,浙江 東陽 322100)
我國陶瓷考古界將散落在金華(婺州)、衢州和浙江西南部等地的古代窯場叫作婺州窯,其在唐朝之前的整個瓷器行業中位居第二,僅次于越窯。婺州窯所生產的瓷器主要為青瓷,同時還燒制彩繪瓷、褐瓷、黑瓷以及花釉瓷等多種瓷器,為我國陶瓷歷史的發展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堆塑是一種特殊的陶瓷裝飾技法,能夠在器物坯體上粘貼立體形式的動物、植物或人物等密集但有規律的裝飾品。其中,婺州窯堆塑藝術就通過不斷探索、創新和發展,打造出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展現了地方特色,具有較高的美學境界和藝術賞析價值。
一、婺州窯發展源流
有“千古風流”之稱的婺州窯有一千八百多年的發展歷史,遺址數量多達600處,分布非常廣泛。其瓷器產地主要位于東陽、武義和金華等地。婺州窯的發展最初始于商周原始窯,發展到東漢晚期才燒制出褐釉瓷、青釉瓷,在明代成功生產出青花瓷。婺州窯堆塑工藝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呈現了獨特的藝術韻味和魅力。婺州窯于東漢三國時期已經做到了熟練應用各種陶瓷裝飾技藝,包括鏤空、雕刻、捏塑和粘貼等,能夠將不同造型的裝飾物生動地呈現在器物上,使陶瓷更加精美和華麗。在不斷發展和經驗積累的過程中,婺州窯在宋代創新生產了高浮雕,其最知名的堆塑工藝品是乳濁釉雙龍梅瓶,直觀地反映了該時期人民各方面的生活形態,揭示了雜技藝術、建筑服飾以及宗教民俗等狀況[1]。婺州窯在陶瓷史上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其堆塑工藝是我國一項珍貴、燦爛的藝術文化遺產。
縱觀歷史發展進程,婺州窯堆塑工藝呈現了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婺州窯的窯工在生產實踐過程中積累了充足的堆塑藝術經驗,經過不斷完善、創新,才形成了特色化、完整化的婺州窯系。在西晉時期,婺州窯對化妝土這一裝飾性原料進行了巧妙的運用,結合材料的特性,不僅覆蓋了原坯質的顏色,還使坯體表面更加平整、光潔,生產出的瓷器釉面滋潤、飽滿、光滑,更具藝術美感。唐代婺州窯可以燒制出藍白色乳濁釉,瓷器呈現了玉石般的質感,美觀程度大大提升,創新了瓷器美化方式,甚至到元代也依然備受推崇。相關歷史資料記載,婺州窯生產的瓷器甚至銷售到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其中婺州窯在唐宋元時期燒制的乳濁釉器物出口量最大,促進了各國經濟貿易的發展,也加快了國際文化的交流。
二、婺州窯堆塑藝術作品類型劃分
婺州窯堆塑藝術產品的造型、種類同甌窯、越窯存在很多的相同點,但在胎色上有所不同。唐代中晚期之后,婺州窯產品逐漸生活化,器物傾向于民用瓷器,所以裝飾也會隨著人民生活、社會習俗有所改變。婺州窯產品的品種雖然具有時代共性,但也獨具自身的特征。根據婺州窯堆塑藝術作品在功能、造型上的差異,能夠將其劃分成堆塑瓶、堆塑罐、瓷俑、仿生藝術作品以及實物模型五大類。
(一)婺州窯堆塑瓶、罐及瓷俑
從本質上看,婺州窯堆塑瓶屬于南方魂瓶,通常采用動植物圖騰、世俗生活、仙境等圖案,打造相應的氛圍空間,發揮引魂升天的作用,因此喪葬文化中應用最多。窯工會對堆塑瓶器身進行空間劃分,參考中國畫的卷軸構圖法,將復雜人物空間勾勒出來,展現了繁復的民俗活動或仙境的神秘之感;婺州窯堆塑罐工藝非常復雜,應用泥條盤筑輪制拉坯,成型后管同鼓腹體以分段的方式進行粘接[2]。在造型方面,堆塑罐的制作主要采用了模印、劃刻、堆貼以及拍印、鏤雕等工藝技巧,通常會運用捏塑或模印的方式將動物、人物等造型裝飾在坯體,而婺州窯瓷俑的單獨作品數量不多。
(二)仿生藝術作品
婺州窯仿生藝術作品主要有燈盞、壺、硯、水盂、鼎、杯子、燭臺、熏爐、碗、盤、鐘、尊等,會模仿動物、植物的形態,以此為造型對瓷器進行裝飾。動植物仿生對象包括鳥、羊、雞、獅子、熊、老虎、麒麟、鳳凰、狗、蛇、老鼠、蓮蓬、蓮花及荷葉等,體現了動物、植物的不同形態及神韻。仿生藝術作品造型非常豐富,活靈活現的動植物造型呼之欲出,彰顯了婺州窯的鮮明個性,極具藝術感染力。
(三)實物模型
婺州窯實物模型藝術作品多種多樣,且造型題材非常豐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實物模型堆塑作品是結合窯工所處時代的生活狀況而生產出來的,包括狗圈、豬欄、房舍、雞籠、谷倉、水井、火盆、羊舍等生活設施,這些題材注重造型的寫實,盡顯生活氣象,揭示了人們內心的信仰,充分記錄了該時期的歷史環境,為深入研究時人的民間信仰風俗及經濟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三、婺州窯堆塑藝術風格特征研究
婺州窯之所以聞名于世,在于其堆塑與器型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婺州窯藝術。因此在對婺州窯堆塑藝術風格特征進行分析時,必須要基于整體角度,將裝飾與婺州窯器整合起來,挖掘藝術深層的氣韻、物象,了解其背后的時代背景,進而有效傳承和弘揚這一鮮活的藝術文化,彰顯傳統民族文化內涵及智慧。
(一)寫實藝術,融入日常之美
婺州窯堆塑藝術作品追求寫實藝術,即記錄和體現真實的題材內容。窯工會根據當時的建筑風貌、建筑形制或出殯送葬的場景來設計堆塑藝術作品的造型,講究真實體現當下的殿宇樓閣、社會環境及民俗活動,重現人們吹拉彈唱的活動場景,例如義烏博物館藏西晉青瓷堆塑罐、北宋婺州窯堆塑人獸紋蓋瓶和三國青瓷谷倉罐等[3]。雖然婺州窯堆塑藝術作品由于時代的變化會出現形式的差異,然而基于整體角度看,其會將鮮活的動物形象、喜聞樂見的事物裝飾在器物上,依然彰顯了民族精神,反映了生活情趣。
人物、動植物及日常生活用具等堆塑藝術模型的寫實藝術風格非常鮮明,簡單的器物在物象堆塑的裝飾下,形體表達更加豐富,能夠使人們感受藝術品的精神氣質、美感。無論是磨、爐、豬欄,或是蛙、鱉、爬蟲、蟾蜍,還是青龍、鳳凰、麒麟或白虎等,這些堆塑模具的內容和題材都貼合人們的實際生活,都是鮮活的紀實載體,充分體現了當時人們的民間信仰、風俗習慣及經濟發展水平。婺州窯窯工所創作的堆塑藝術作品體現了對生活理解、概括,蘊含著生活之美,具有藝術的真實感。
(二)造像簡練,突出意象神態
婺州窯的窯工匠大多來自民間,所設計的堆塑藝術作品本質上透露著簡練、質樸和淳厚的藝術氣息,所以堆塑造型具有天然化的神韻。工匠憑借其高超的堆塑技藝,打造出簡約的堆塑造型,不會過分追求造型栩栩如生,但非常關注生活意趣的體現,使堆塑藝術品的意象更加靈動,可以生動地將動植物的神韻體現出來[4]。有時,窯工會特意在堆塑作品中留下手工之痕,以實現生動而后氣韻生的目的。
婺州窯堆塑藝術作品中有仰天長嘯的老虎(東晉時期的婺州窯青釉虎子一對),有四人恭候且左肩馱有幼兒的男性(三國堆塑人物塔式五聯罐)和圈內覓食的塑豬(西晉青瓷豬圈),這些人物、動物的形象和體態雖然簡練,但只要認真欣賞和觀察,就能夠感受到簡約造型下的逼真意象。在窯工高超技巧的加持下,造像擁有了傳神的意象神態,體現了婺州窯堆塑藝術的魅力。其將寫意和寫實進行整合,同時具有現實和浪漫的藝術氣息,形成了視覺美感,所以感染力極強。
(三)對稱平衡,強調整體布局
婺州窯堆塑藝術也非常重視對稱平衡,通過堆塑造型可以展現穩重、大方的美感,提高堆塑藝術品的視覺沖擊力,增強作品印象。因為器物本身質地光滑,輪廓曲線明顯,在單調中卻具有統一性的美感,而要想添加煩瑣復雜的堆塑裝飾,很可能會將統一性打破,使美感下降[5]。窯工在追求對稱美的過程中,會基于整體角度進行構思、設計,使各部分都能夠協調統一、完整勻稱,優化堆塑裝飾的布局,在呈現堆塑造型多樣變化的同時,重新找到統一美感的實現路徑,由此將器物、堆塑裝飾進行完美地整合。
東陽市博物館藏西晉青瓷堆塑罐、東晉青瓷辟邪燭臺、西晉青瓷堆塑罐、宋蓮瓣紋青瓷蓋罐和北宋婺州窯堆塑“抬轎”蓋罐等婺州窯堆塑藝術作品構成了藝術中的對稱與平衡美,注重空間統一。以宋蓮瓣紋青瓷蓋罐為例,宋蓮瓣紋青瓷蓋罐圓口、弧肩、鼓腹,腹下漸,近足處微外撇,圈足。蓋面裝飾有5瓣復線蓮瓣紋,伴有彎曲花蒂紐,而罐身通體滿飾復線蓮瓣紋,且呈上下兩層重疊分布,釉色精美,色澤清脆,光澤感較強。蓋面和罐體的蓮瓣紋分布非常對稱,疏密程度相對一致,秩序感較強,有一種韻律性和節奏性的變化,充分地體現了蓋罐輪廓曲線。青瓷蓋罐蓮瓣紋層次不多、內容質樸,彰顯了潔凈高雅、清新脫俗、文雅大方的品格,突出其實用功能,同時以平衡的堆塑裝飾、流暢的線條表達原始美,使婺州窯堆塑藝術品的美感境界大大提升,讓人們能夠感受到宋代人的生活氣息,具體詳見圖1—3。

圖1 宋 蓮瓣紋青瓷蓋罐(整體) 東陽市博物館藏

圖2 宋 蓮瓣紋青瓷蓋罐(側面) 東陽市博物館藏

圖3 宋 蓮瓣紋青瓷蓋罐(底部) 東陽市博物館藏
四、結語
婺州窯作為我國古陶瓷研究的重點對象,其在堆塑藝術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極具文化研究價值,屬于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婺州窯堆塑藝術不斷積累經驗、開拓創新,堆塑技藝逐漸純熟,造型日益多樣化,構建了追求寫實藝術、造像簡練、對稱平衡、剛柔并濟的藝術風格,極具美學意蘊及文化內涵。當下非常有必要加大對婺州窯堆塑藝術的系統性研究力度,保護、弘揚和傳承婺州窯堆塑藝術,發揮婺州窯堆塑藝術的時代價值,才能促進我國陶瓷藝術創作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