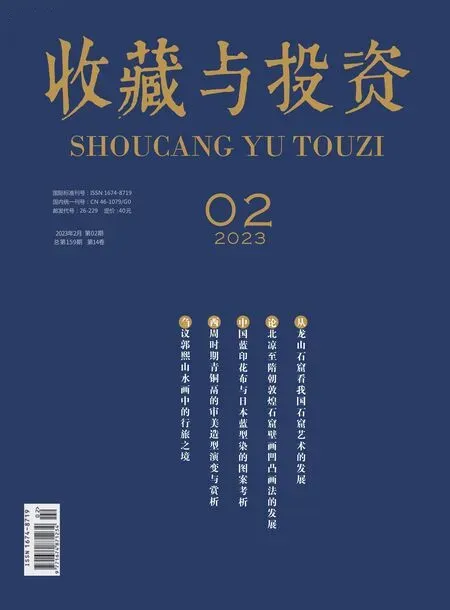方力鈞繪畫作品中的審美觀念
彭春霞,羅 莉(華南農業大學 藝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653)
自20世紀初觀念藝術出現,藝術作品從表現到觀念表達不斷在發展和演變。雖然觀念繪畫的概念來源于西方,但它卻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1]。克萊夫·貝爾曾說“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指向創作者傳達觀念,“形式”是指藝術語言,即創作的形式表現。在繪畫藝術中,觀念的傳達離不開物質載體。不同于傳統繪畫大多停留在記錄寫實和繪畫技法表現上,觀念繪畫更注重對觀念的傳達。觀念征服物質,其主觀性不在于對形式的把握,而在于創作者個人精神和思考在對象中的表達。
一、關于中國觀念繪畫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85新潮美術”為代表,隨著改革開放,經歷過“文革”時期的藝術家們不滿傳統文化里的一些價值觀,嘗試從西方觀念藝術中尋求新活力,強調人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復出。當代藝術中的觀念繪畫單純強調以何種觀念進入繪畫當中,卻忽視了繪畫本身的形式語言[2],繪畫本身的審美性缺乏,讓繪畫中的觀念與審美表現產生脫離,這使得觀念繪畫處于瀕臨脫離藝術本體的尷尬境地。觀念繪畫是從觀念到形式的統一體,其離不開自身特有的藝術形式語言的修飾點綴,這樣能使觀念的輸出更為立體飽滿。用審美觀修飾觀念繪畫作品的藝術形式,是為了更好地呈現以觀念為主的繪畫作品,目的是使觀眾得到更好的審美體驗。
中國觀念繪畫作品蘊含著豐富的內在力量,其匯聚著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特征。中國觀念繪畫包括五個流派,它們存在相似的創作動機和藝術表達,藝術家們為表達自身觀念想法而進行藝術創作,堅持“觀念為主、藝術為輔”的創作原則。“玩世現實主義”流派以方力鈞作品為代表,其作品是現實主義與觀念主義的混合體,將方力鈞自身的形象進行符號化和模式化,通過夸張的手法描述與傳達藝術家的精神狀態和理念,呈現在觀眾們眼前的是方力鈞的觀念內容而不是藝術形式。方力鈞的觀念繪畫作品主要以人物內心情感為批判與思考的對象。
二、以光頭人物為主的審美觀念
(一)審美對象:光頭人物
方力鈞的觀念繪畫作品是以光頭人物為主的創作,表情大多夸張荒誕。光頭的視覺寓意,一般表征著叛逆,不同于常人。在現實生活中,光頭造型是具有獨特個性或特有表意的外在形象,如不涉世俗紅塵的出家和尚是光頭,處于醫學化療階段的患者是光頭,這使得光頭的概念十分模糊,沒有明確的語義傾向或定位。方力鈞模糊了觀念中光頭的個性差異,體現了光頭在語義中的不確定性。光頭人物既是方力鈞的視覺美學符號,也是其觀念表達符號,更是其觀念的審美對象。
方力鈞的觀念是因人而起,他將觀念的抒發本體轉移到人身上,由人去傳達、表述他對當下社會與人的聯系的思考。光頭的形象看似滑稽,但卻能準確抓住其觀念傳達的核心內容,能很犀利地將觀念進行視覺剖解并結合藝術語言實現視覺展示,被觀眾所感知與領悟。
(二)審美態度:虛無與反叛
方力鈞生于1963年,他的童年時期正處于“文革”從發展到高潮再到末期的階段,文革成為其童年深刻的記憶,之后他又在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中成長,這造就了他的繪畫觀念。他曾表示:改革開放前大家生活在仇恨與爭斗中,因身份地位、教育觀念與自身想法產生分歧導致他從小學會偽裝自我,促而形成“兩面派”。自我不能得到釋放,導致方力鈞主要以玩世不恭、特立獨行的態度進行藝術創作。他在作品中尋求解放,作品反映了他不羈與反叛的強硬態度。
方力鈞的作品《系列二(之二)》(圖1)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用為其中一期的封面,作品注釋為“不是在打哈欠而是在吶喊”。該作品以成年光頭在打哈欠的形象為近鏡頭特寫,數個光頭面無表情、目光呆滯地佇立其后,與常規概念的人物形象相悖,這表露出人內心的無聊、木訥,毫無世俗之欲及生活之所望。《系列二(之三)》(圖2)通過重復多個相同的光頭人物進行畫面布局,畫面十分怪誕,人物的面部充滿笑意,而該笑意卻與常人不同,這彰顯了方力鈞本人的觀念意向,揭露了20世紀90年代初很多人的生存狀態。社會的變動讓人不知所措,從前的觀念及抱負等隨之消散,人們處于迷茫狀態,不知何去何從,陷入虛無狀態,內心空洞無力。方力鈞此時的繪畫作品正是用繪畫語言對現狀進行觀念性的表達,通過人物五官的夸張化,將人們內心的虛無空洞展露得淋漓盡致,引導觀眾以第三視角去審視自身。

圖1 《系列二(之二)》

圖2 《系列二(之三)》
(三)審美判斷:靈暈的籠罩
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指出“震驚”是機械復制時代藝術的總體美學特征。方力鈞的繪畫作品體現了文藝思想中的“震驚”概念,人物夸張的五官造型超過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體驗范圍。方力鈞將其觀念融入以光頭為主的人物形象,為人們提供了釋放心理困惑的一個通道,作品流露出他潛意識中的叛逆與戲謔,這讓觀眾從經驗感受轉為體驗感受,充實了作品帶給人的觀念審美體驗。
本雅明提出“靈暈”的靈感來自照相技術,讓觀者在凝視照片中人物眼神的過程中回憶人物。本雅明將具有獨一無二性的傳統藝術定義為有“靈暈”的藝術,其“靈暈”籠罩著人們,并與其投下的陰影融為一體。方力鈞觀念作品中的光頭人物凝聚了他對世俗的不滿與反叛以及對中國當代的社會狀況進行的思考與批判,并將其凝練成繪畫語言對自身的觀念進行闡述,這就是“靈暈”的藝術。它能較好地使人籠罩于作品的“靈暈”中,體驗“靈暈”帶來的觸動并引起心理共鳴。
(四)審美體驗:欣賞與感知
方力鈞觀念繪畫作品的重點不在于繪畫語言與形式的突出,而在于繪畫形式蘊含著他特有的觀念。觀眾在欣賞作品的藝術與觀念價值的過程中,與藝術家進行觀念性對話。這種審美體驗是觀念繪畫區別于傳統繪畫的一大特色,凸顯觀念為主、藝術為輔的創作理念。
審美體驗亦可理解為對審美的解釋,匯聚著現象學和認知觀念的相關內容。審美體驗的發展具有連續性,向高潮發展即為觀眾體驗的審美對象,從而實現一個審美觀念的良性循環。同理,方力鈞的觀念作品便是進行了該循環,從連貫性的光頭人物審美對象到對光頭的審美體驗,是方力鈞個人觀念在觀眾心中的完整呈現。
三、與傳統色彩相悖的色彩觀念
方力鈞作品的色彩具有艷俗傾向。畫面多以藍天、白云、大海為背景,主角光頭在被賦予生動戲謔的表情之余,配以絢麗的色彩,使人覺得夸張而不失親切感,咧嘴笑或是怪異的表情無形中都拉近了與觀眾溝通的距離。這種夸張的色彩處理方式奪人眼球,視覺上有著很強的沖擊感。從方力鈞《1993.2》(圖3)和《1993.3》(圖4)的作品看都是以藍天白云為背景,人物色彩以飽和度較高的暖色系上色繪制,畫面給人帶來視覺“震驚”,達到視覺享受與體驗的效果。這種獨特色彩也是方力鈞觀念繪畫里的重要美學要素和審美觀念。他的作品突破了中國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的色彩美學樣式,大色塊顯現強烈對比,如大量用紅藍等飽和度較高的色相、缺乏環境色等內容的匯入,而不對這些顏色畫面進行協調處理,僅保留了物體本身的固有色相。

圖3 《1993.2》

圖4 《1993.3》
審美觀念包含審美對象、審美判斷、審美態度和審美體驗[6]。光頭人物造型的創作與艷麗色彩的使用作為觀眾的審美對象,其屬性為能被觀眾所理解的視覺特性。觀眾通過該藝術形式對方力鈞的觀念進行審美判斷,在感受中尋求觀念的共性與個性,在作品中將光頭的個性抹除,把共性展現出來,即同為方力鈞個性的展露,共性與個性來回切換的過程即為闡釋共性與個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的體會就是自身審美態度的表達,該立場是無利害性、自由無私的。
方力鈞的觀念繪畫構建了人們溝通的藝術場所。這與法國評論家尼古拉斯·伯瑞奧德提出的“關系美學”概念貼近,他將關系美學定義為評判以表現、制作或推動人的關系為基礎的藝術作品美學理論。方力鈞在觀念繪畫作品中進行觀念的傳播,在審美過程中融入了互動的過程,互動的對象彼此之間產生關系,構成了點與點之間相互聯結的幾何場所。這幾何場所就是由作品中的觀念作為起始點,激發觀眾審美意識的各個端點聯結匯聚而成的觀念場所。
四、結語
從審美觀念中的審美對象、審美判斷、審美態度和審美體驗中體會并理解方力鈞繪畫中的觀念,該過程具備完整統一性。中國觀念繪畫仍在不斷調整并發展著,從審美觀的角度解讀中國觀念繪畫的創作能更易于藝術家觀念的傳達,擴展著觀念在藝術表達的邊界,以便促進觀念繪畫的多元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