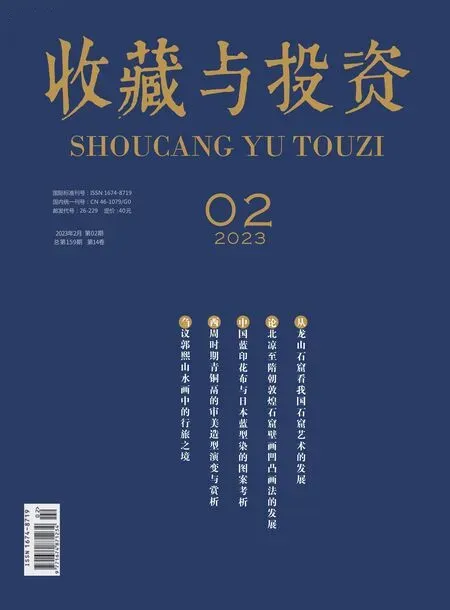從圖像學角度分析莫迪里阿尼的人物畫
梁婷儀(湖南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翻開西方藝術史的書籍,我們的腦海中便會出現許多耳熟能詳的藝術家名字,譬如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倫勃朗、塞尚、馬蒂斯、畢加索、杜尚、達利……他們都曾是其所在時代的開拓者或引領者。提及莫迪里阿尼,大家對他的印象可能極其模糊,甚至不認識他,但他的藝術精神和藝術成就卻給了后世畫家一條有跡可循的道路。莫迪里阿尼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巴黎畫派的代表人物,他主觀表現性和原始主義的繪畫風格以及作品中意象的象征意蘊對20世紀初象征主義和表現主義畫風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莫迪里阿尼的一生渺小卻偉大,平凡又傳奇。他的人物畫風格標新立異,優秀的畫作會“奪走人的靈魂”,他筆下的很多人物看起來像是失去了靈魂,有種神秘、憂郁之感。
一、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概述
圖像學是藝術研究的方法之一,旨在通過對圖像形式的研究以及作者想要表達的意義來探尋作品的主旨和其中蘊含的價值。“圖像學”最早的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圖像志,由希臘語“εικωυ”(圖像)演變而來,當時主要研究的是繪畫的圖像與文化發展的聯系[1]。潘諾夫斯基的理論內涵是要通過對圖像的解讀來尋找其中的歷史人文價值,他關注圖像與觀念之間的關系,將藝術作品與具體的文化背景相聯系,尋求外部世界與內在精神的統一。即在探究藝術作品背后的本質時,通過對表層圖像形式語言到內部精神層面的分析來挖掘深層價值。正如塞尚所說:“真正的本質隱藏在其中。”[2]圖像學研究方法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前圖像志描述、圖像志分析和圖像學解釋。第一個層次前圖像志描述,即通過對作品的形式語言如構圖、造型、色彩等描述,描述作品的基本信息;第二層次圖像志分析即在第一層次的基礎上分析所傳達的傳統意義,發掘藝術品背后所潛藏的某種意義或者某種主題以及內涵;第三層次圖像學解釋即是把作品放在大文化背景下來探討,涉及所處的國家、時代以及當時的宗教和哲學思想,從其中可以尋找到作品更深層次的內涵和價值,透過現象看本質。
二、從圖像學角度分析莫迪里阿尼的人物畫
(一)莫迪里阿尼簡介
莫迪里阿尼(1884—1920年)出生并成長于意大利,由于從小受意大利強烈藝術氣氛的熏陶,加上家庭氛圍的影響,他沉迷于文學和藝術,于是便開始了他偉大又絢爛的繪畫生涯?莫迪里阿尼雖藝術生涯短暫,卻依然留下了許多作品,有雕塑?風景畫?靜物畫,但大多為人物畫?其畫中的人物造型有著變形拉長的特點,如修長的脖子、杏仁眼,作品也因此被貼上了“莫迪里阿尼式”的標簽?莫迪里阿尼的人物畫關注人物的內在精神,他拒絕“所見即所畫”的表達方式,而是從人物的神態?性格?情感方面入手,他“有眼無珠”的表現方式讓觀者萬般疑惑?耐人尋味?
(二)前圖像志描述
前圖像志描述即是對圖像作品的視覺形式作基本的概述,也就是對作品的題材、基本形式內容進行描述,這個階段是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的第一階段。突出“所見即所得”,即作品通過什么樣的圖像呈現了何種視覺效果,通過什么樣的線條、構成、色彩呈現于外,給觀者帶來了何種直觀感受。前圖像志的描述應當源于人的實際經驗和主觀的直覺感受。
莫迪里阿尼的人物畫多為單人女性題材,且較多為半身像或者胸像。就直觀視覺體驗而言,其所畫的對象雖不同,但卻都有著相似的造型和情緒。
《戴項鏈的珍妮·赫布特尼》(圖1)給我們呈現了一位優雅又憂郁的女性形象,眉眼的高低、頭發的錯落、肩膀的低聳給這幅安靜的作品增添了一絲跳動的旋律。畫面的憂郁氣氛從有眼卻無瞳的位置逐一散發到整個畫面。當人們注視畫面時,好似在與珍妮進行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憂郁深沉的氣氛還來自畫面中大面積的深色使用,就連模特的衣服都是低明度、低純度的藍色。

圖1 莫迪里阿尼《戴項鏈的珍妮·赫布特尼》
放眼望去,《讓娜·埃布特納》(圖2)映入眼簾的是讓娜那嬌柔的身姿,人物的姿態像是正在思考。莫迪里阿尼的作品總能調動人的情思,他更關注人物內心的變化,把筆墨重點放在人物情緒狀態上。讓娜的形象有種中國唐朝女性的豐腴之美,這得益于畫家在概括形象過程中使用了弧線。畫中沒有明顯可見的生硬的長直線,就連人物右手所靠著的墊子都是用弧線概括的。雖然兩幅作品都帶有鮮明的莫迪里阿尼式的標簽,但兩個人物所傳達的感受又稍有不同,珍妮的憂郁、讓娜的深思,耐人尋味。莫迪里阿尼的作品雖形成了強烈的符號,但卻能在大同的基底下尋得小異,同而不同。

圖2 莫迪里阿尼《讓娜·埃布特納》
(三)圖像志分析
進入圖像學的第二階段—圖像志分析就不再是“所見即所得”這般直白。藝術家在創作時皆是有感而發,畫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它獨特的意義,是藝術家向觀者傳遞信息的語言。圖像志分析階段正是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研究的關鍵點,通過相關的專業、文化的知識對圖像進行分析,即對藝術家放在作品中的圖像符號、圖像特征進行解讀分析,加深人們對于畫面的理解,從而實現圖像學理論分析的意義。
潘諾夫斯基認為,圖像學闡釋是不局限于與作品本身打交道,將繪畫作品當作其他某種東西的征兆,這些征兆往往是藝術家們的無意識在作品中的表露[3]。縱觀莫迪里阿尼的作品,可知女性人物畫是莫迪里阿尼抒發情感的載體,畫中的女性多為他的情人、妻子。在美術史上有數不勝數的女性題材作品,作品真正的意義與精神、藝術價值往往隱藏在背后,而這需要圖像學的方法去探索。自古以來便有托物寄情這一說法,如倪瓚以“一江兩岸”式的景致表達心中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的淡然心態;朱耷以“翻白眼”的魚、鴨、鳥等動物去抒發憤世嫉俗之感。莫迪里阿尼則用變形的女性人物畫去表達內心的孤寂、不被認可和理解的傷感。其所畫的女性恰巧都與他人生觀、世界觀相同,甚至都對他有著崇拜迷戀之情,而這份支持的力量正是孤獨地走著藝術之路,甚至繪畫風格不被當時的藝術社會所理解的莫迪里阿尼強烈需要的。他把內心的傷感、憂郁通過所畫的形象傳遞出來。值得讓人深思的是畫中人“有眼無珠”的表達方式。寓言故事中的畫龍點睛、顧愷之所言的“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的理念,無不說明眼睛的重要性。大家都盡可能地把所謂的神與情從人物的眼睛中表達出來,而莫迪里阿尼卻反其道而行之,去掉眼珠,眼睛部分作簡單地平涂,與中國畫中的“空”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正是“空”,給觀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四)圖像學解釋
潘諾夫斯基[4]說過:“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階級、一個宗教和一種哲學學說,會不知不覺地體現于一個人的個性之中,并凝結于一件藝術品里。”藝術家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員,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各種社會觀念、思想的影響進而在個人的藝術創作中有所表現。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的第三個階段—圖像學解釋,這一階段的主旨是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把作品放到大環境中去分析,尋找其中所蘊含的深層意義。
莫迪里阿尼是矛盾綜合體,他的身上既有古典藝術的烙印又有當代藝術的前衛與不羈,同時也帶著非洲藝術的“怪”與“拙”。莫迪里阿尼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雖生于古典藝術時期,但卻有著突破古典藝術界限沖勁和藝術精神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凝結著他所生活的時代里諸多藝術大家的精華。20世紀,在意大利和佛羅倫薩求學之旅結束之后,莫迪里阿尼只身一人來到了巴黎,這是一個前衛藝術和先鋒派藝術占據主流地位,兼容其他傳統藝術流派的時期,加之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影響,不管是藝術、哲學,還是文學,都有著多元化的特征。莫迪里阿尼也深受這種多元化藝術氛圍的影響,取其精華凝練于畫中。“藝術精神是哲學精神的折射投影,藝術與哲學的滲透融合”[5]。莫迪里阿尼的藝術不僅僅是個人的藝術也是時代的藝術,其藝術背后與所處時代的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作品中強烈的憂郁、悲傷的感情色彩,除了與他悲慘的人生經歷有關之外,也受到了西方現代美學先驅尼采悲劇美學思想中所主張的酒神精神的影響。酒神精神是相對于日神精神所提出的,代表著迷醉的世界。酒神精神讓人在放縱的過程中釋放壓抑的激情,暫時忘卻痛苦,使人從郁悶中解脫出來[6]。莫迪里阿尼吸毒和嗜酒,過著紙醉金迷的放蕩生活,被酒精麻木之后的意識使他把憂郁情感放大,創作出了眾多動人的作品。他的藝術作品是他在困苦的環境和哀婉的情緒下努力開出的雅致藝術奇葩。
三、結語
以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的研究方法對莫迪里阿尼的人物畫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剖析,從圖像學的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層層深入,讓我們對莫迪里阿尼的創作有了深刻的理解。基于莫迪里阿尼圖像作品的視覺元素加之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歷史資料對其進行分析與解讀,透過現象尋找本質,可以達到內在精神和外部世界的統一。莫迪里阿尼用憂郁的變形人物畫述說著他豐富的內心情感,其獨特的“有眼無珠”的處理手法在作品和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莫迪里阿尼的創作致力于探索主觀世界與客觀現實的平衡,他的作品不僅是他內心精神世界的映射,更是那個戰火不斷的動蕩年代下,于精神和社會危機紛擾中,人們內心不安和混亂狀態的映射,是時代的產物。房龍在《人類的藝術》中指出,“一切的藝術,應該只有一個目的,即克盡厥職,為最高的藝術—生活的藝術,作出自身的貢獻。”[7]莫迪里阿尼的圖像作品不僅是一種視覺的享受,更是一種精神的財富,具有很強的自省性。他獨特的人物形象和直擊內心的人物內在精神是后世藝術家創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