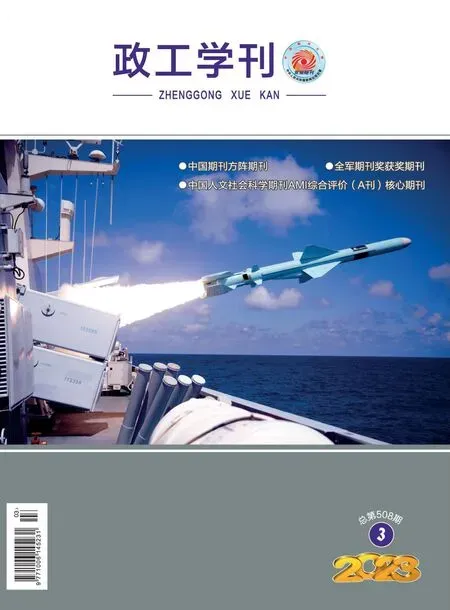變化的故鄉
☉張十味

今年是我三年來第一次回老家過年,而我也像一個異鄉人回到了故鄉。之所以說異鄉人,是因為父母前兩年搬家了,搬到了城市的新區,這也是我第一次在這個新家過年。
父母買的這個新房子遠離我以前生活的老城區,連路名都是我從來沒聽過的。我現在出個門要導航,要在點評平臺上找飯店,動輒還要坐地鐵——在我近20年前離開老家的時候,我對故鄉的印象就是連打車都不用,我的生活圈幾乎就是步行可達。
這也導致我春節期間都不太愛出門了。回家的一大樂趣其實就是看看故鄉風物,但因為搬家搬得太遠,這地方對于我來說和陌生城市差不了太多了。當然,到陌生城市也是快樂的,至少很新奇,但因為是春節,新家旁邊的商店都關了不少,也少了好些出門的樂趣。
或許這也不是我家的個例,而是這些年城市變化得太快了。我記得上高中的時候,公交車剛剛裝上了空調,要貴一塊錢,我和同學只有在熱得受不了的時候才坐;而現在,我拎著大包小包的行李,等著地鐵到來。這一刻,我真的有點恍惚,我到底在哪呢?
故鄉總被稱為“鄉梓之地”,對故鄉的審美是靜態的,是用來憶往追懷的,人們希望家鄉保持穩定,以便自己在多年歸來后還能找到熟悉的事物,用來喚起陳年往事。就像那句“何事吟余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家鄉要保持和記憶里的相似,仿佛才是她最大的價值。
但這樣,對家鄉和家鄉里的人其實都是不太公平的。他們當然沒有必要為了情懷,為了自己小城市、小縣城、小鄉村的身份而保持靜止。父老鄉親當然也需要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也想有變化,一如要出去闖蕩的游子一樣。
就像我父母的這次搬家,遠離了我的成長環境,但我依然認為是十分必要且成功的。現在他們每天都會到家對面的一個大公園遛狗。這個公園規劃得很晚,整體的審美風格都是現代的,又因為在新區,占地面積也很大。他們每天很享受在這個公園里散步,拍的照片里,藍天白云之下,是一望無際的草坪,這個環境確實令我羨慕。
而更重要的,則是新房子有電梯,這是他們第一次住上有電梯的住宅。上一個房子樓層也不高,也并不覺得電梯有什么必要。但當他們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老去的時候,他們走路的速度開始變慢,也越來越習慣勾著我的胳膊,我才發覺電梯是多么重要。他們和每一個即將、終將老去的人,都必須考慮養老的問題。
所以,即便我的新家不再像“故鄉”了,但我依然十分慶幸他們換了房子,過上了更舒適的生活。其實這個新區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城市景觀,都比老城區要好很多。城市的宣傳片,也常會用無人機在這一帶取景。我想,父母即便老了,或許他們也更喜歡這種流光溢彩、活力洋溢的感覺,這和年輕人沒什么不一樣。
在返程的時候,我又發現了新家的一個好處。以往返程,印象里總是忙忙叨叨的,火車站有點遠,路上還很堵,總要提早很長時間出門。但新家離新修的高鐵站很近,還通了地鐵,提前45 分鐘出門就能趕上。
所以這次返程,我睡到了自然醒,從容不迫地吃了午飯,看了會兒電視劇,才晃晃悠悠地出門。而父母也沒有給我塞滿行李箱,他們覺得沒必要——小區門口就有個快遞驛站,需要什么給我寄過去就是。
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思考家鄉的意義。鄉愁是個很美好的事物,人們多么企盼故鄉“春草年年綠”,總是和記憶里的一樣。就好像劉邦的父親,在長安住得不習慣,天天想念家鄉豐邑,劉邦只好在長安邊上修了一個“新豐”(今西安市臨潼區新豐街道),把故舊都請過來,硬是克隆了一個故鄉讓父親高興。
但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不妨有更通達的“故鄉觀”。故鄉未必會一成不變,我們的記憶也不會消失,重要的不是永遠有一個靜態的老家供我們返鄉,而是我們和家鄉以及家鄉的人,一起經歷著歲月變遷,一起奔向遠方。
所以,家鄉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張網,是人們認識的親朋故舊、山川風物,在這張網格里連結在了一起。網格就如同坐標,不會一成不變,彼此的距離也可能會被拉長,但中間那條來自血緣或是生活的線條,卻始終會把人們拴在一起。無論人們走到了多遠的地方,家鄉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只要順著這些線條,人們都能找到此心安處,找到情感寄托,找到可以歸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