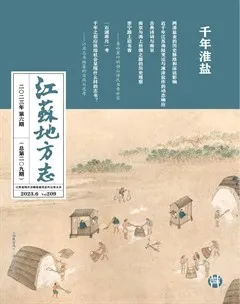漕運時代的淮鹽與運河
◎李德楠
(淮陰師范學院,江蘇淮安 223300)
漕運是借助江、河、湖、海等水路調運糧食等物資的活動,其中運河漕運是最重要的水運類型。今大運河江蘇段溝通了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8市,然而江蘇13個設區市全被列為運河城市,原因在于除運河主河道外,與之相連的“鹽河”也被作為運河的一部分,從而確立了江蘇運河的網狀結構。本文擬從鹽政、鹽運、鹽署、鹽商、鹽官、鹽城鎮等方面梳理漕運時代淮鹽與運河的關系,以期有助于講述生動的運河及鹽業故事。
一、“東南三大政”中的河工、鹽務與漕運
兩淮是古代最重要的海鹽產區,兩淮鹽稅在全國稅收中占有重要份額。晚清重臣曾國藩的幕僚金安清在《東南三大政議》中提到:“本朝列圣切切以南顧為根本……而其大政不出三事:曰河,曰鹽,曰漕而已。”表明江浙地區的河工治理、兩淮鹽務、運河漕運為三大國家事務,事關國計民生。河工、漕運兩大系統與運河的關系最為明顯,所以運河之都淮安曾駐扎河道總督府、漕運總督府兩大管理機構。不僅如此,鹽務與河工、漕運的關系也非常密切。
其一,鹽務、河工均涉及巨額的銀兩收支。河工治理是個燒錢的窟窿,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古人稱之為“金穴”。據《水窗春囈》記載,嘉道間管理江南水利的河道衙門,每年河工經費400萬-500萬兩,“其中浮冒冗濫不可勝計”。與耗費財富的河工不同,鹽務既創造財富又耗費財富,道光十五年(1835)皇帝下旨稱河工人員的奢靡之風受鹽務影響,“近皆移害于河工”[1]。
其二,鹽是借助運河輸送的重要物資之一。開挖運河的主要目的是運糧,此外還運鹽、鐵、銅、鉛、竹、木、磚、瓦、瓷器、茶葉、棉花、煙草等物資,以及搭載官員、士兵、商人、士子等人員。唐代首創鹽船綱運法,十船編為一組,據前來中國的日本和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當時“鹽官船積鹽,或三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不絕數十里”。《宋會要輯稿》載曰,宋代每年春夏之際,將長江潮水“放至運河,鹽綱往來,無淺涸之患”。明清時期是運河漕運的繁忙期,文獻中多見運河鹽運的例子,例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南京鎮監覃力朋到北京進貢后,沿運河返回南京,以百艘船只搭載私鹽,沿途騷擾州縣。康熙四十二年(1703),廢閉淮安清口的仲莊閘,將中運河口從仲莊移到楊莊,“由是漕、鹽兩利”[2]。雍正間漕運總督張大有建議回空糧船每艘夾帶食鹽40 斤,多帶者按運輸私鹽治罪。乾隆六年(1741),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稱,江都三汊河乃瓜、儀二河口門及“漕鹽船只必由之要津”[3]。
二、鹽稅、鹽官與運河
鹽為財賦利藪,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提出了“官山海”的食鹽專賣政策。漢代始見“鹽稅”一詞,唐代隨著第五琦、劉晏的鹽政改革以及北方地區池鹽的衰落,兩淮鹽業地位凸顯,出現了專職的鹽商。宋代以后,“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中淮鹽占有相當比例。明清時有“兩淮鹽賦實居天下諸司之半”的說法。歷史上的鹽稅使用以及鹽官設置往往涉及運河。
其一,鹽稅常用作治理運河的經費。兩淮鹽課是明清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其中相當部分被用作河工治理,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十八年(1539)大水災,朝廷下撥兩淮運司余鹽銀50000 兩予以賑濟;嘉靖三十二年(1553),徐邳等十七州縣連遭水患,朝廷下撥運司余鹽銀50000 兩,派刑部右侍郎吳鵬前往賑災;又據潘季馴《河防一覽》記載,萬歷初年修筑高家堰所用30000 銀兩,相當部分來自“運司挑河鹽銀,或淮徐各處鈔稅,或撫按贓罰”。
其二,鹽官有時兼管運河。鹽官的設置由來已久,《周禮》中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的記載。齊國管仲推行食鹽官營,漢代始置鹽官。唐代設江淮轉運使管理鹽運,明代設長蘆、山東、兩浙、兩淮、福建、河東六個都轉運鹽使司。明景泰間以巡鹽御史兼管運河,“以巡鹽監河道,而鹽法之任益專”[4]。成化八年(1472)規定:濟寧州至南京一帶河道,由兩淮巡鹽御史帶管;通州至濟寧州一帶河道,由長蘆巡鹽御史帶管。嘉靖二十年(1541),朝廷命監察御史胡植巡理鹽法,兼管濟寧至南京段河道。嘉靖四十五年(1566),參政凌云翼奏請專設御史監督蘇松兩地水利,朝廷下詔由巡鹽御史兼任。隆慶二年(1568)十月,根據總理鹽屯都御史龐尚鵬的奏請,下詔撥兩淮運司挑河銀3000兩作為徐呂二洪協濟河夫之費。隆慶六年(1572)六月,差江西道御史周于徳督理兩淮鹽課,兼理河道。萬歷二十年(1592)漕撫陳于陛提出開周橋閘泄水時,巡鹽兩淮兼有河漕地方職責的御史王明提出反對意見,理由就是有損運道、鹽場和民生。
清代在運河管理中注意做到“鹽漕并重”,改巡鹽御史為兩淮鹽政,其職責涉及鹽場管理、轉運管理、食鹽銷售等。雍正七年(1729),命兩淮鹽政高斌就習河務。雍正八年(1730),根據奉差辦理江南水利郎中鄂禮的奏請,添設江南揚州府水利同知一員,駐扎泰州東臺場。嘉慶十三年(1808),淮揚運河淤塞300 余里,兩淮鹽政阿克當阿建議漕船全部過完后,堵閉淮安清江三壩,筑壩斷流,自清江至瓜洲分段挑浚。道光十一年(1831),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
三、鹽商、鹽販子與運河
鹽商即從事食鹽銷售的商人,相傳商周時的膠鬲為鹽商始祖。明代實施開中制,促進了徽商、晉商等地域鹽商的興起,清代“總商”的設置,標志著鹽商地位的顯要。據研究,清代兩淮鹽業興盛時,鹽商資本積累達七八千萬兩,兩淮鹽商集團成為我國古代最大的商業資本集團[5]。鹽商因鹽致富,發家后常參與運河治理,而鹽販子為販運私鹽方便,往往私自開挖運河,其與運河的關系表現為破壞性活動。
其一,鹽商承擔一定的治河款項。鹽商常為治河捐款捐物,乃至直接參與治河,元代《鹽商行》詩有“司綱改法開新河,鹽商添力莫誰何”的描寫。《明神宗實錄》中有“鹽商修河銀”的說法,顧名思義為鹽商承擔的款項。萬歷四十五年(1617),鹽商集資挑浚淮安府安東縣以北至海州的官河。〔光緒〕《安東縣志》記載,康熙四年(1665),黃河決安東縣茆良口,漂沒廬舍,鹽商程朝宣踴躍捐資堵口,當地百姓非常感激,允許程氏一族“占籍安東”。康熙四十四年(1705),淮安河下鹽商程增出資修治運河險工,恰逢皇帝南巡,御書“旌勞”二字賜予他。鹽商除挑挖疏浚運河主河道外,還挑浚與運河相通的鹽河,例如溝通兩淮鹽場的串場河,向來由“鹽商挑浚”[6]。
其二,鹽商為皇帝南巡河工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巡視河工是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南巡的重要內容。南巡過程中,富可敵國的鹽商提供了大量錢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途經揚州,都由大鹽商江春出資操辦。《清史稿·高恒傳》載曰:“兩淮鹽商迎蹕,治行宮揚州……諸鹽商具言,頻歲上貢及備南巡差,共用銀四百六十七萬余。”[7]。
其三,鹽商的慈善活動為運河城鎮發展做出了貢獻。鹽商在運河沿線城鎮進行的修橋筑路、筑城興學、救災賑濟等慈善活動,發展了運河城市,方便了百姓生活。例如天啟初改建安東縣磚城,鹽商出資一半。乾隆六年至七年(1741—1742)兩淮地區連遭水災,波及淮河中下游地區48個州縣衛,災后“疫癘盛行,流民病斃者,累累于道”,徽州籍鹽商程鍾、程涵學捐資賑災。乾隆《淮安府志·公署》記載,鹽商出身的候補知縣程鍾捐銀3000 兩,購買了淮安府城西門外南四鋪的民房,然后由山陽知縣金秉祚委托縣丞徐斌負責建造普濟堂,共計大小堂房128間,以收容流民。
其四,鹽販子常破壞運河堤壩。鹽販子為了避開稽查,想方設法避開正常的運道,其盜掘堤壩、開辟私道往往給運河修守帶來危害。《北河紀》中有“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的記載。《行水金鑒》引《禹貢錐指》稱,洪澤湖“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為盜決計”。
四、鹽河與運河
淮鹽主要銷往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六省,其中運鹽河是食鹽運輸的重要通道。京杭運河沿線大大小小的運鹽河很多,有東西向的山東大清河,也有南北向的江蘇串場河,其中以東西向的居多,他們是運河的分支和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江蘇地區河湖水系眾多,檢索《清史稿·地理志》中“鹽河”一詞,共有20條記錄,全部位于江蘇條下(包括今上海地區的記載4條)。
其一,通揚運河。貫穿今揚州、泰州、南通三地的通揚運河,其前身為吳王劉濞所開的茱萸溝。西漢時劉濞煮海為鹽,為運鹽方便而開挖了茱萸溝,西起茱萸灣與邗溝相連處,東通海陵倉。清宣統元年(1909)改稱通揚運河,1958年開挖了新通揚運河,形成了泰州市南北各有一條通揚運河的景觀。
其二,串場河。又名運鹽河,其前身是唐代修筑捍海堤時挖土形成的復堆河,宋代范仲淹進一步修筑捍海堤(范公堤)并拓寬復堆河。南宋咸淳年間以及明隆慶年間,又重加疏浚。因該河貫串了沿線的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十大鹽場,故稱串場河,全長170公里,是重要的水上運鹽通道。
其三,蚌蜒河。又名蚌麓河、蚌沿河、駁鹽河、運鹽河,傳說因巨蚌爬行成河,或曰因開河時發現大量蚌殼而得名。蚌蜒河是淮南各鹽場駁運食鹽的水上要道,自淮南鹽場運出的食鹽,沿串場河北行至東臺附近,經蚌蜒河至陵亭鎮食鹽檢驗處,檢驗后分三路外運:一路至高郵入運河,一路至揚州入運河,一路入長江。
其四,鹽河。西起今淮安境內的雙金閘,東至連云港玉帶河,全長145 公里,其前身是唐武則天垂拱四年(688)開挖的官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靳輔開挖中運河時,在官河基礎上開挖了一條東西向的泄水河道,〔乾隆〕《淮安府志》記載:“鹽河自楊家莊分中河之水,由王家營北穿大路達安東,入海州之五丈河下海,以泄運河異漲及王營減壩之水,兼濟鹽、柴重運。”[8]
江蘇境內鹽河眾多,除上述通揚運河、串場河、蚌蜒河外,還要很多已廢棄的或更小的鹽河。例如,淮安境內還有古黃河與運河間的小鹽河,連接了缽池山、淮安城和河下鎮,〔乾隆〕《淮安府志》載曰:“小河一道,今名鹽河,即古黃河遺跡也。”還有萬歷九年(1581)總漕尚書凌云翼所開的永濟河,一度作為清江浦河的備用河道,乾隆以后改稱鹽河。
五、食鹽轉運與運河城鎮
大運河堪稱古代的水上高速公路,在長期的物資、人員等運輸過程中,帶動了沿線城鎮的崛起與發展,促進了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兩淮地區城鎮因坐擁鹽場之利和運河交通之便,吸引大批商人前來定居,鹽商聚居與食鹽轉運集散促進了揚州河下街、東關街、儀征十二圩以及淮安河下鎮、西壩鎮的發展。
其一,揚州運河城鎮的繁榮。隋唐大運河的開鑿促進了揚州的發展,成為當時重要的海鹽集散中心。明代時揚州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駐地,兩淮食鹽由鹽商經運河運到揚州,沿運河的河下街、東關街一帶集中了大量鹽商,會館住宅密集排列。清代兩淮鹽政駐扎揚州,負責巡視兩淮鹽課,督察鹽務,乾嘉時揚州鹽業達到鼎盛。儀征在明代時為淮南掣驗鹽引所駐地,清同治間建兩淮鹽務總棧于儀征十二圩,一躍成為晚清民國時期的鹽運樞紐,號稱“東南利浦”。
其二,淮安運河城鎮的繁榮。明代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下設三個分司,淮安分司為其中之一。兩淮巡鹽御史下轄淮南、淮北兩個掣驗鹽引所,其中淮北鹽引所駐扎淮安。位于淮安府城西北的河下鎮,是淮鹽轉運樞紐,明中葉開中法的實施,吸引“鹽策富商挾資而來,家于河下,河下乃稱極盛”。淮安西壩鎮因黃河大壩而得名,道光間兩江總督陶澍實行鹽政改革,打破了官商對食鹽的壟斷,將淮北掣驗鹽引所由河下鎮遷至西壩,西壩成為淮北食鹽集散中心,一時間商鋪林立,一派繁榮景象。
歷史上淮鹽與運河的關系密切,涉及鹽政、鹽河、鹽運、鹽商、鹽徒、鹽署、鹽官、鹽城鎮等方面,挖運河需要鹽,管鹽的人也兼管運河,運河不僅運糧也運鹽,運鹽河是運河的分支,鹽業促進了運河城鎮的發展,鹽場和鹽販子也與運河有關。淮鹽與運河的關系主要體現為財富與交通的關系,在淮鹽的生產運銷過程中,運河發揮了重要的交通運輸作用,淮鹽憑借運河而行銷各地;運河依賴鹽業而得以維持發展,在運河修治和管理的過程中,淮鹽發揮了重要的經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