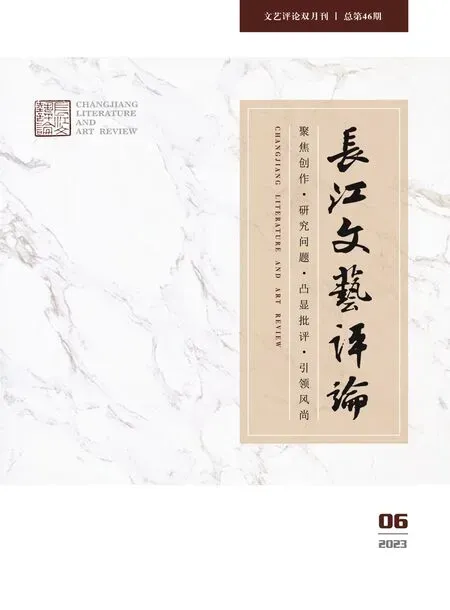地方性意義如何可能?
——“意義—地方”學術研討會綜述
◆范生彪
自從人文主義地理學提出文化文本的意義地方性問題,地方和地方性就逐漸發展成為現代人文學術的重要概念。由文化文本的意義生成機制觀之,地理學家段義孚的“戀地情結”(topophlia)概念彰顯出地方性在現代審美文化的意義生產實踐中的重要功能。鑒于此,由湖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牽頭,聯合諸所科研院校,于2023 年10 月27 至29 日在湖北恩施舉辦了“意義—地方”學術研討會。會議以現代審美文化的意義地方性為研討主題,從地方與地方性概念、地方性在文化實踐中的呈現以及人文學科知識生產中的地方性機制等角度,深入探討了現代審美文化中的意義地方性問題。
一、地方與地方性概念
何為地方?何為地方性?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按常規把地方理解為區域,地方性即為區域性;現象學生存論哲學意義上的“地方”乃是個人生存最為具體、最為穩定的“生活世界”,地方性即返回存在之家,孕育生存意義的生活世界的建構性;人文主義地理學領域里“地方”,就是這經驗的生發之處,生命真實感誕生之所,人類不自覺的意向性(unself- conscious intentionality)所指的地方;地方性則為一個已然與人建構了文化認同,是其安全感的來源,能產生存在意義和歸屬感的地方所具有的全部屬性;知識學意義上的“地方”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吉爾茲從闡釋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相應的地方性則為基于特定“地方性”人群生存經驗的“地方性知識”,另一種科學哲學的“地方”指的是實驗室這樣一個“情境化”的地方,相應的地方性無非實驗室這樣一個“情境化”的地方歸納出的經驗性結論,言下之意是不具備“對于普遍規律的概括”的權威性……對此,各位專家有精彩闡釋。
“我居”故我在,湖北民族大學特聘教授馮黎明分析了作為意義生成機制的地方。他認為現象學的存在論影響下,人文地理學和闡釋人類學將地方和地方性概念提升成為現代人文學科知識活動的重要論題。地方性是一個意義論概念,它在知識論和真理論范疇里的闡釋有效度并不高,而在以意義論為闡釋軸心的文學研究領域中,地方和地方性可以發揮重要的釋義作用。地方是一個介于“情境”和“空間”之間的概念,它兼有情境的個別性和空間的普遍性。地方性指向文學文本意義生成機制的闡述,其要旨在于從主體與其居所的交互關系的歷史中辨析文本意義的生成。他強調當代中國的人文社科領域中,“地方性”概念基本上都是用以指涉“區域”而非現象學意義上所謂存在的“居所”(Live Emplacement)或者“處境”(situation)的特性;人的處境乃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之源始,這是在直面當代生存的根本問題并設想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情境、地方、空間等概念的核心內涵恰恰就是我們在“居所”或者“駐地”之中的意義經驗,可以說“我居”故我在;文學研究的終極任務是對于文學性的闡釋,而文學性中顯現的地方性意義經驗同樣也是一種獨異性的個別經驗。只能采用發生學意義上的地方性研究才能奏效。在藝術的地方性意義生成機制的分析方面,薩特對于文藝復興時代威尼斯藝術家丁托列托的敘述很有典范效應。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王慶衛指出“地方”內涵豐富,亟待厘清。該概念進入文學社科研究領域已久,但是國內學界存在混用定義的情況,而在人文地理學的“地方”與闡釋人類學、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地方其實是有區別的。在西方學術語境中,“place”意義上的地方屬于人文地理學的“地方感”,指地方自身的固有屬性以及人們對地方的依附感。而“local knowlege”所表述的地方屬于闡釋人類學或科學實踐哲學的“地方性知識”。王慶衛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地方”這一概念對應著“中央”“核心”“主流”“總體”,它是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平衡的產物。在異質性和普遍性的權利關系中,地方是身不由己的,它有待主流的接納、認可與定位,從而進入一個被收編、被設置甚至自我消泯的過程——要么作為主流文化的裝飾,要么被抽空內容成為空洞的符號。“地方”概念錨定著多元的價值取向:堅持地方文化自信——這是一種古典主義的態度;堅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是近代啟蒙主義的態度或者說主體性的態度;主張地方文化之間的協商交流和融合——這是現代主義的態度;把地方看作中心的天賦力量——是后現代的態度。“地方性知識”概念的啟示意義人類學家克里福德·吉爾茲總結得很到位,人類關于世界的已有認知無非是基于特定“地方性”人群生存經驗的“地方性知識”而已,并無神圣性可言。這對于遏制任何知識的普遍化沖動和針對知識權利系統之間的收編或被收編的合法性都是不無裨益的。
四川大學教授閻嘉從地方性與全球性的互動中,分析了地方的獨特作用。閻教授指出物質層面全球趨同的癥候,這很容易讓人們忽視了地方所承載的文化獨特性。按照逆全球化的思路來看,資本的運作一旦到了地方,大概會很難消滅那種基于日常生活經驗的對于故土的心理依賴,即段義孚所說的戀地性,一種基于鄉土的生存意義歸宿感。藝術創作即便是要傳達世界意義,也是需要借助一定的地方體驗。文學研究需要擴展到文化研究,需要建構一種本鄉本土的生活方式,留住民族文化之根。閻嘉還在分論壇發言中,詳細論述了關于“農家樂”這一獨特的審美文化符號的生成淵源與文化審美意義。他認為農家樂作為一種獨特的,間隔于城市與鄉村的休閑審美意識形態與獨特的審美文化符號,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了一個詩意的棲息地。“農家樂”所帶來的中國式的消費文化,正在形成一種特殊的“休閑審美意識形態”,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公共消費空間。
湖北大學副教授吳天天回溯了現象學和后結構主義共同影響下的意義理論建構的歷史過程。隨著形而上學的衰落,出現了意義危機。在20 世紀,現象學致力于在尼采之后繼續推進形而上學批判,在現象學之后興起的后結構主義在借鑒現象學的同時,致力于清除現象學中殘留的形而上學因素。后結構主義意義觀主要呈現出三重面貌:第一重面貌的主要代表是德里達,用能指游戲說解構了符號所傳達的終極意義;第二重面貌的主要代表是福柯,福柯“看”與“說”、“詞”與“物”的斷裂說將穩固的意義轉化為不同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第三重面貌概括可為“重釋sense”,代表性的思想家有德勒茲、南希和薩利斯。德勒茲將意義視為事件,強調意義在命題和事物之間的邊界上生成。他強調意義的悖論性,強調無意義有助于我們思考意義的生成,強調意義總是伴隨著無意。南希也致力于彰顯意義的生成性與差異性,強調存在是朝向他者的存在,是共同顯現。薩利斯認為藝術的真正意義在于意義的雙重變容(transfigurements),向上的維度通向認識和思想,向下的維度通向感知和感性。吳天天認為遭遇意義危機時,不是主體將意義賦予事物,而是與事物一起生成意義。
二、地方性在文化實踐中的呈現
地方性作為意義生成的重要機制之一,那么,它如何體現在文化文本的創制活動以及文本之中?與會代表們就地方性的呈現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河南大學教授張清民認為地方對文學意義的影響現實地體現為文化區位對審美精神取向及題材的選擇。具體而言,文化區位影響審美選擇的因素有兩類:一是影響文化類型的自然空間因素,二是影響文化類型的社會制度因素。自然空間因素影響人們的生活狀態、日常習俗、精神信仰與心理性格。制度因素人為塑造著人們的審美旨趣和藝術的生產方向。不同文化區位所形成的文化類型各有其特色并為其所在區域的民眾所適用,不存在高低之別,亦不必相互競爭,亦各行其是為宜。蘇州科技大學博士李桂全從藝術自律論的角度考察了地方對文學意義生成的影響。李桂全認為藝術自律論本質上是發源于西方的藝術理論,當這一理論遭遇中國問題的時候需要重新認識。原因在于藝術自律論的生成、發展、演變等深深植根于現代性語境之中,相比西方,中國作為后發現代性國家,現代性具有獨特性。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李俊國則從“地方”所包含的異質性與邊緣性出發,總結了地方對文學意義生成的影響。李俊國重新梳理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從“中心”向邊緣回退的發展歷史。發現“邊緣敘事”已然成為了當代文學發展的動力。文學“邊緣化”之后,作家們分別從不同路徑趨向文學的頹廢審美,讓當代中國文學獲得了區別于社會學歷史學新聞學中國的表達方式與意義呈現。中國文學也在“邊緣敘事與頹廢審美”的狀態里,一是得以自律性的存在,從而回到文學原點,落實對每一個人的關心;其二,文學中國得以更好地參與當代中國精神公共空間與審美世界;其三,它們又反過來推動社會公共空間的建設與拓展,促進某些公共空間的“重新洗牌”;第四,為社會當代讀者提供了別一樣的精神視閾和閱讀審美空間。
南京大學教授汪正龍認為地方對文學意義生成的影響直接體現在文學的地理想象上。他在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學地理空間建構的三個層面,或者說三重境界:地方志、文化志、精神原鄉。“地方志”不同于地方史,指的是一種富有地域性,富于地方的原生力量及其獨特氣息的書寫。譬如賈平凹80 年代對商州的書寫。地方志對應了吉爾茲所說的人類學研究的“深描”,即從一種“內部眼界”去把握“文化的內在生活形式”。地方志的美中不足,在于太局限于地方性的書寫;文化志指的是超越了單一地域的文化視野的狹隘,能以他者眼光對于地域文化特點進行反思性的想象虛構,以向他人表現自己的地域書寫。這種書寫,隱含著地方與他鄉、地方與中央、地方與世界的潛在對話關系,達到了一種文化互鑒的馬賽克書寫的思想高度,具有地理虛構的特點。賈平凹從西安的視角看商州,莫言筆下具有文化隱喻功能的高密東北鄉,都具有福克納“約克帕斯塔法縣”式的地理虛構。精神原鄉,指根據對歷史和當地的某種認識,作家超越現實地域,虛構出來的精神空間書寫。精神原鄉是作家藝術虛構,偽托的可以撫慰精神、安放靈魂,讓生命覺醒的地方。這樣的寫作對作家而言,不啻為一次精神還鄉,這是文學創作所需要的。湖北民族大學副教授范生彪認為地方性的強弱,影響作家文學地理想象的呈現方式。具體而言作家與筆下生活的情感距離,決定了文學地理想象具有地方、景觀和空間三種不同面相。“地方”指作家與生活情感距離很近,藝術構思偏重于感性,能傳達出自己獨特人生體悟,描繪出地域文化特質的文學地理想象。阿來《云中記》中的云中村便可稱為地方。“景觀”指作家與生活保持很遠的情感距離,藝術構思偏重于理性,生成的觀念化、奇觀化的文學地理想象。魯迅筆下的故鄉便可稱之為景觀。“空間”指由于作家生活保持恰當的情感距離,情理皆備狀態下,虛構的象征隱喻的文學地理想象。例如作家蘇童筆下的“楓楊樹故鄉”。其實文學地理想象的不同面相,與作品質量的優劣并無必然的聯系。武漢大學副教授袁勁考辨了沈約的《郊居賦》的寫作時間、創作情境、歷史書寫,得出了沈約所謂郊居,實乃虛擬精神家園,表達向往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而已,本在虛實之間耳。可視為一樁地方意義生產的文學事件。思想史研究需要注重從空間的視角研究文學史,進行文學批評史中的“地標”研究。
浙江師范大學教授陳國恩認為地方對文學實踐的影響體現為文學的地方性。文學的地方性在文學創作中依靠想象、建構與超越這三種文學地理的建構方式來實現。目前日益盛行的逆全球轉向,導致了文學的地方性越來越受到重視。文學與地方的關系中,文學的重心在人,不在地方。地方性的重要性,要通過人的重要性顯現出來。只有當地方性有助于強調人的生動性和豐富性時,地方性才有審美價值。重視文學的地方性要警惕矯枉過正,把文學的地方性誤以為地方文學,甚至用文學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去否定文學的世界性和人類性,造成文學中人與地方的關系的撕裂,損害文學審美的人性基礎。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段吉方以法國文論史家孔帕尼翁為例分析了文論生產的地方性與意義生成。孔帕尼翁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自成體系、自有法國文學理論研究獨特性的地方。他對文學的生產與認知充滿了“本國情懷”,習慣于通過對本土文化和理論家的鉤沉和深描,展現出一種遠離普遍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文學觀念和高度的文化自信,這點是值得國人學習的。陜西師范大學教授陳守湖認為文學是人學,人類的生存都是在特定的空間中展開的,從本體論意義上講,文學是一門空間的藝術,因此,地方對于文學創作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作家創作過程中,空間意識的自覺是把雙刃劍。畢竟,文學創作最重要的價值并不在于展現風貌或呈現某種異質文化,而是要通過文學去狀寫人類心靈的宏闊景象。因此文學地理建構需要同時處理好在地與超越的關系,這考驗著作家的才情與見識。湖北大學教授劉川鄂先做了概念辨析,后反思了文學的地方性。劉川鄂認為地域文學概念更著眼于文化、更注重傳統;地域特色是地域長期發展形成的并且往往跨行政區域;區域文學概念就更行政化;“地方”則是地域或區域更為口語化的表達。“國家藝術”是一種制造“同意”的藝術,其根本目的在于營造“想象的共同體”。這必然要求全國文學具有一體化的顯著特征,共性大于個性,全國性統領地方性。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絕大數時間都遵此原則行事,因此地方、地域、區域性的文學書寫,都共同參與著這種營造,不過是國家文學大樹上的枝葉,其獨立價值不可夸大。文學研究包括文學史的編寫的意義,在于通過對前人創作經驗的總結推動文學更好地發展,自然區域文學史的編纂其實必要性并不大,倒是地域文學的研究很有必要。愛德華·雷爾夫的觀點很有見地,“太強烈的地方性可能會導致狹隘的鄉土觀念;太突出的無地方則會導致因看起來相似而產生的混淆與沮喪。”地域性只是文學風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決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備要素。另外,只用“地域的”而不是“時代的”“文化的”視角觀照和描繪地域的文學現象,只寫出地域特點而忽視文學的審美共性和人類的共通性是不夠的。作家通過對某一地域特性的描寫,要為歷史,為人類提供價值參照和評判。還有,文學的人性探尋和審美創造比地方風習展覽和方言比拼更重要。雖然“匆匆忙忙說小地方,有時候也可能是對大地方的一種回避”,但太局限于當下性、地方性、民族性或者說“中國經驗”等,是值得檢討的。湖北民族大學教授李莉則從文學接受的角度,強調了文學地方性的重要性。李莉認為文學意義的地方性是指文學作品包含的思想、內容、意義所具有的地域性特性。這是由作家的成長經歷、反映的社會生活、使用的語言的在地性決定的。若不考慮文學作品的地方性,文學意義便很難被把握,鄉土文學尤其如此。
三、人文學科知識生產中的地方性機制
人文學科關于為了更好理解世界與自身的知識生產有三種形態,即:意義、知識和真理。其中意義是我們對世界感知的源始,意義的形式化類型化邏輯化則形成了知識,知識的普適化抽象化精確化再形成了真理。地方作為主體的居所乃是生成意義的重要機制,因此很有必要考察其具體運作。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趙勇做了題為《周揚請黃藥眠審閱文代會報告考》的主題報告,展示了文藝理論決策時“地方”與中央的互動。趙勇講述了周揚和黃藥眠的交往史,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所處的境地和黃藥眠的批注、修改建議,以及周揚對建議的采納程度。通過扎實的歷史考古和文本細讀,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場,以及中央對于文藝的指導思想的知識生產也是通過至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中完成的。下午分論壇趙勇分析了毛澤東《講話》對趙樹理文學創作的影響,從歷史的褶皺處再現了文學創作實踐中“地方”在知識生產中的張力作用。中南民族大學龔舉善在分析新中國民族詩學共同體的生成、語域及功能的過程中解析了地方在知識生產中的作用。龔教授認為新中國民族詩學共同體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民族共同創造、分享和發展的文學理論批評集合體。詩學共同體的歷史生成受多種要素的合力推進:首先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現實情境的規定,其次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指導,再次是民族文學學科建設的基礎性鋪墊;詩學共同體主要有多元一體與多元共生、民族性與現代性、單邊敘事與多邊敘事等三大核心語域;詩學共同體及其研究具有強大的文化建構功能,彰顯了中華民族詩學融創新形象,拓展了中國民族詩學闡釋新視野、開創了中國民族詩學體系的新格局。武漢大學副教授李佳奇從延續與對話的角度,探討了王國維“南北文學觀”的生成問題,彰顯了地方對于文藝理論建構的巨大影響。武漢大學教授李松關注文學史意義上的“地方”與“國際”的互動。李松通過考察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后現代立場,得出了地方開辟了國際文學史著述話語博弈的場域,應該避免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直線思維的結論。因為現代性的本質主義一元論、決定論經過現代主義解構之后,呈現了現代社會知識學的張力形態,不如把后現代主義視為———它之于現代性是一種反駁、互補的建設性立場。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吳子林對于“地方”的張力思考深入到了文化傳統和語言文體的層面。吳子林認為述學文體的創構與學術思想的創造是同步展開的。當代人文學者中國悠久的“尊體”傳統與以“魯迅風”為傳統的五四文脈,迷信于邏輯的、科學的方法論,述學文體“新變”之“訛勢”造成諸多理論、思想的“失語”。作為未來述學文體之預流,面對全球化語境下的時代問題,“畢達哥拉斯文體”的創構充分吸取了劉勰《文心雕龍》以“通變”“定勢”為代表的文體思想之精髓,力圖通過融合會通古今中西的述學傳統,“重寫中文”以激活中國文化基因,實現思想與語言的戛戛獨造,“畢達哥拉斯文體”的創構是對當代述學文體的一次“定勢”,他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傳統即創造。
地方對審美領域知識生產的制約體現在審美地方感的生成過程之中。河南大學副教授裴萱分析了“地方感”與空間美學的意義結構表達的關系。裴萱認為現代性工程建構了時間與空間的新秩序,推動了空間整體知識場域的形成。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正是現代性的產物,并在與空間的對應關系中得到凸顯。地方感的生成維系了主體與地方、地方與空間以及主體日常生活結構之間的詩性情感話語,通過“主體”“社會”“生活”三個維度凸顯空間美學的意義結構。貴州師范大學教授劉海從論述現代都市審美感的角度,論述了地方對于現代人審美感知的重要性。劉海對于都市審美感知的認知深受本雅明和波德萊爾的影響,其核心觀點是現代性美學圖景由三個核心因素組成:第一個是觀視;第二個是空間;第三個是驚顫。現代性美學圖景離不開這三個要素的語境。換言之,現代性的都市體驗改變著人們的認知方式與生活經驗,也影響著人們的審美認知與藝術表達,藝術的轉型和變革都與都市生活的現代性體驗密不可分。四川大學副教授趙良杰則關注了“地方”在后現代藝術的解放功能。趙良杰以博伊斯的“7000 棵橡樹”為切入點,探討這個項目如何與人類集體自治的規范理想相互關聯,認為后現代藝術是人類自由價值的推進和深化,其深層目標是人類集體自主和自治。湖北民族大學博士吳飛分析了“地方性知識”與西方現代藝術的形成。闡釋人類學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識”概念對于知識的普遍性提出了質疑。借助這一概念,我們可以對西方現代藝術的發展歷程進行“深描”。從現成品對審美的排斥、極簡藝術對物性的張揚、觀念藝術對藝術的語言化,再到波普藝術對圖像的重復化,西方現代藝術以“地方性”的姿態不斷挑戰著業已成為“普遍知識”的傳統藝術觀念。通過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地方性知識”進行探討,我們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藝術觀念的多元發展與個體表達的重要性。湖北民族大學博士崔凱華做了“樂舞、氣與天道:以簡帛《五行》為中心”的報告。湖北民族大學博士林靜闡發了自己對中國當代電影中奮進的三重演繹的看法。湖北民族大學文藝學研究生鄭雪禮分享了自己對審美遺忘與現代性危機的思考。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朱國華在會議開幕致辭中指出,本次會議的研討論題即審美文化文本意義的地方性,應該得到中國人文學界的高度重視,將其視作一種新型的意義闡釋的知識學路徑。出席本次會議的代表們共同認為,意義生產和傳播實踐中的地方性問題關涉著現代審美文化的諸多方面,對此論題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工作;此論題的研究可能生發出諸多新的學術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