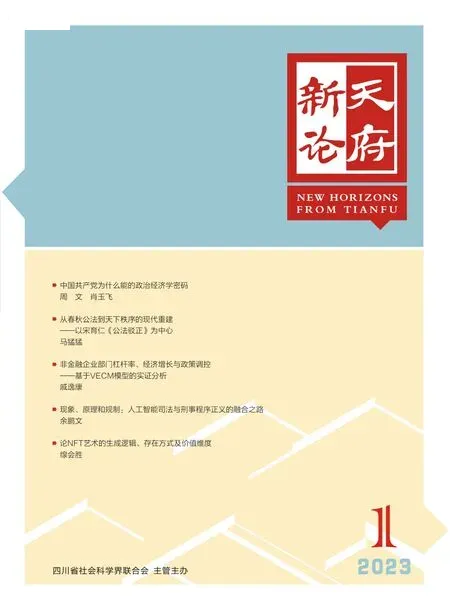數字社會下的審美泛化危機
危昊凌
新世紀以降,一場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與“審美日常生活化”的美學討論點燃了學術界對藝術與日常生活關系的探討熱情。數字媒介護航下的大眾文化一路凱歌,被納入市場化進程之中的藝術與審美卻叫人憂心忡忡。美在今日已降格至粉飾現實的胭脂粉黛,對美的追求亦不再是對精神超越與心靈自由的向往,而是跌落為一種提高生活品質的合理訴求為消費活動提供話語修飾,難怪有學者直言:“‘審美化’已經成為當代西方社會理論家把握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大命題。”(1)金惠敏:《圖像—審美化與美學資本主義:試論費瑟斯通“日常生活審美化”思想及其寓意》,《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在數字社會被韓炳哲指認為同質化社會的當下,審美泛化所牽扯的諸多問題浮出歷史地表,資本、技術、大眾文化等因素經由數字媒介的組織整合在經驗與感受層面侵蝕了當代人的精神世界。“泛審美化”的討論并未因時間的消逝而喪失理論張力,與此相反,數字生存困境與同質化社會的發展為這個問題的思考注入了動能。
一、純審美的淡出與泛審美的打造
隨著技術理性的高揚與資本市場的介入,固守“審美本質主義”的精神意愿在大眾文化場域中顯得孤立無援。數字時代迎來了快感中心主義的思想宰制,消費主義將一切視作可消費商品的同時也對藝術采取了降解式處理,超越性與先鋒性必須以商業化妥協的代價換取進入文化消費市場的門票。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相持勾勒出當今時代的文化圖景:形而上的追思與典雅的審美趣味成為少數文化精英的特權,對物質享受與感官愉悅的渴求則構建起蕓蕓眾生的文化趣味,傳統美學中對于審美超越與精神空間開拓的向往讓位于泛審美化的快感體驗,數字媒介的興起點燃普羅大眾文化熱情的同時也為社會話語改寫藝術提供了某種可能。當淺層次的物質文化與消費者的宣泄欲求出雙入對,審美活動便在更多時候以消費性享受的形式出現,文化工業被確立為以機械生產方式來創造“詩意”表現的消費話語體系。
人們目睹審美消費化的轉向后耽于狂歡也好,陷于漠然也罷,關于藝術與日常生活的追問不會因大眾文化的虛假繁榮而終止。自費瑟斯通在《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中提出“日常生活審美化”以來,關于日常生活與審美的討論就捕獲了無數學者的視線,在其思想被引入國內后,更是出現了論爭日常生活審美化與審美日常生活化的美學熱潮。在國內學界向西方世界尋求智識來源的過程中,詹姆遜與韋爾施的思想大放異彩。詹姆遜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誕生的后現代主義,其主要表現特征就是商品化。在商品化的力量逐步滲透個人的日常領域及文化生活的過程中,藝術與生活間的隔閡被刻意抹除,文化工業開足馬力的后果就是主體迷失在形象井噴的視覺文化之中,如他所說:“現代性的巨變把傳統的結構和生活方式打成了碎片,掃除了神圣,破壞了古老的習慣和繼承下來的語言,使世界變成了一系列原始的物質材料,必須理性地對它們加以重構并使之服務于商業利益,以工業資本主義的形式對它們加以控制和利用。”(2)弗雷德里克·詹姆遜: 《時間的種子》,王逢振譯,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68頁。詹姆遜將日常生活視作無聲的戰場,現代主義對本質、意義的追問在后現代主義這里消失殆盡,喪失深度的快餐文化將認知主體懸置于能指符號的汪洋之中。與詹姆遜對后現代主義的揭露批判不同,韋爾施更加突出了當下社會的“美學轉向”,生活的美學化意味著“用審美眼光來給現實裹上一層糖衣”(3)沃爾夫岡·韋爾施: 《重構美學》,陸揚、張巖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5頁。。時尚潮流對社會現實的粉飾催生出一種“美學經濟”,被商業竊取的“美”為消費披上一層合法性的外衣。對美的追求并非過錯所在,意圖美化任何事物的時髦潮流才是“平庸之美”的幕后元兇。這種機械復制的美化行為消解了崇高和優美的可能,流于爛俗的精致走向了平庸和淺薄。韋爾施對淺層審美化所作的診斷指出泛審美化的導向必然以服務消費主義為目標,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審美麻木”的現象。流俗于精致與平滑的藝術品喪失了顛覆觀者的沖擊力,可消費的藝術品溫馴地迎合觀者,通過將每一個自在主體轉化為消費者,消費主義以物欲的饜足防范著反思出現的可能。
以上兩種理論范式都透露出對審美泛化的隱憂,藝術的平庸性與消費性上升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先鋒性的消解。在如今的“消費社會”中,人們對物的購買選擇不再出于使用價值,而是更多帶有符號價值的考量,消費作為當代人的生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化藝術活動的創作與傳播。商業文化對藝術審美的規訓似乎已成定局,但美與藝術不應滿足于扮演一位商品推銷員的角色,極盡迎合之能事,抑或親自入場,將自身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求博得顧客青睞。誠然,在燈紅酒綠的消費漩渦中保持自律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移動媒介的興起讓藝術“飛入尋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則是文化大眾對“美的占有”早已迫不及待。當大眾作為新的文化階級高調崛起之時,占有美便成為他們確立話語權威合法性的文化象征。對此大眾文化的擁躉者可能會提出疑義:為傳統美學搖旗吶喊,究其本質不也是文化貴族維護自身趣味話語的一次努力嗎?
這樣的說法確有一定道理。布爾迪厄對“趣味區隔”的闡釋揭露出趣味作為一種文化區隔的同時,也為社會等級制度的維系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男用小便池似乎難逃被搬進路旁一個無名公廁的命運,但藝術家與社會話語的保駕護航卻能使它搖身一變,堂而皇之地高居于藝術殿堂之上。這一切都取決于精英階層的謀略,通過將自己的審美趣味合法化與正當化,傳統審美發揮起維護社會區隔和社會等級秩序的功能。這樣的說辭賦予了大眾文化打破文化等級制的解放功能,卻夸大了大眾文化自身的獨立性。當泛審美化的滲透撬動了藝術現實存在的常數,當流行音樂與短視頻軟件俘獲了我們的視聽體驗,當《羊了個羊》 《合成大西瓜》等魔性小游戲的沉浮起落正批量式收割我們的休閑時間,當高雅藝術被大眾文化放逐出境,我們是該將大眾文化視作打破枷鎖的解放者,還是被技術與資本操縱的提線木偶?虛擬現實從不吝嗇于為我們提供感官刺激,可商業化藝術卻無力為個體的完滿指示精神路徑,娛樂藝術只是借助藝術的“審美”形式來填充當代人貧瘠的精神荒原。意義消逝時代的精神困境為審美泛化的假象所掩蓋,與數字媒介的合謀更是締造出“泛審美化”的現代神話,對格調與品味的夸耀正在制造新的“趣味間隔”。我們不由發問:當美學遭遇數字社會,是急不可耐地投身于文化狂歡中邀寵,自甘成為消費的修辭藝術?還是高揚美的內核與超越性,自愿與膚淺的現實保持距離?
二、關鍵詞的轉變:從“麻木”到“平滑”
技術以及文化產業的裹挾幾乎是將藝術強制架離了熟悉的無功利場域,對漂亮外表的重視制造出審美與消費間的化學反應,美學不再是對技術進步的反思,而是在技術的依托下追名逐利。為美明碼標價的舉動彰顯出消費主體的精神空虛,附庸風雅或是文化作秀都為審美泛化貼上文化貧血癥的標簽,審美在追求形式的過程中花樣頻出,結局就是在現實中愈發乏力。如何理解泛審美時代下的藝術與審美?不觸及問題本質的批判與反思無異于隔靴搔癢,理解審美泛化之下的這場精神危機需要我們對幾個關鍵詞進行梳理。
首先是“麻木”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形成要歸功于本雅明與阿多諾的敏銳洞見。本雅明直言今日我們正駛向“靈光消逝的年代”,隨著機械復制時代的興起,藝術原作與摹本之間的鴻溝被人為抹去,崇拜價值讓位于展覽價值。本雅明在論述“靈光”這一概念時展現出他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本雅明嘆惋于機械復制對“靈光”的戕害,但另一方面本雅明始終秉持著對科技進步的樂觀立場。雖然機械復制的廣泛應用威脅著藝術品的獨一無二性,但本雅明依舊強調“去靈光化”的進步作用。在本雅明看來,“靈光”的消失固然將藝術品變成了大眾消費品,但恰恰是復制技術的興盛拉近了人們與藝術的間距,這也使得“人群”在作為文化工業消費者基礎的同時也孕育著革命的潛在力量。如果說本雅明還對大眾文化抱有希望的話,同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就是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最嚴厲的批判者。在其與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中,阿多諾指出文化工業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地控制著文化與藝術的生產,當商品的等價交換機制滲入藝術創作過程中,一種受啟蒙的“快樂”取代了傳統的審美愉悅。對大眾文化與科技的態度不同造就了阿多諾同本雅明之間的理論分野。在阿多諾眼中,本雅明高估了機械復制藝術以及文化工業的進步意義。對電影的過分期待讓本雅明忽略了電影革命性與娛樂性之間的齟齬,熒幕上轉瞬即逝的電影圖像“綁架”了觀眾的注意力,而悄然滲透的意識形態更是杜絕了觀眾做出批判性反應的可能。阿多諾進一步指出,文化工業“啟蒙”了娛樂,通過將娛樂需求轉化為商品,缺乏思想深度的“庸俗藝術”成為大眾逃避現實的麻醉方式:庸俗藝術“縮短了人類與藝術之間的距離,并且一味地迎合人類的欲念。庸俗的藝術是肯定這個世界的,而不是擺出一種反叛的姿態”(4)阿多諾:《美學理論》,王柯平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8頁。。在文化工業的運作邏輯之下,“麻木”成為某些文化意圖塑造的結果。通過對技術與感官感知的批判,阿多諾發現在文化工業的世界中,“娛樂至死”習以為常,而麻木不仁也早已搖身一變,堂而皇之地塑造人們新的生存狀態:“社會的現實工作條件迫使勞動者墨守成規,迫使勞動者對諸如壓迫人民和逃避真理這樣的事情麻木不仁。讓勞動者軟弱無力不只是統治者們的策略,而且也是工業社會合乎邏輯的結果。”(5)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頁。
阿多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振聾發聵,但后現代社會的到來還是改變了此前的諸多文化圖景,“在后現代主義中,由于廣告,由于形象文化,無意識以及美學領域完全滲透了資本和資本的邏輯”。(6)弗雷德里克·杰姆遜: 《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 162頁。大眾文化的狂歡運動表明文化早已被資本五花大綁,商業邏輯強調對日常生活空間的殖民來實現文化與資本的聯動,韋爾施發現任何商品只要掛上所謂“美學”的名頭就能售罄一空。精神的朝圣之旅因貪戀沿途風光而喪失原初視野,泛審美化所帶來的后果并非傳統想象中“完成我們在世間的任務,實現人類的終極幸福”(7)沃爾夫岡·韋爾施:《超越美學的美學》,高建平、張云鵬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6頁。。“美的濫用”是韋爾施對審美泛化的基本看法,在他眼中,傳統美學對美的一味肯定阻礙了我們對審美泛化負面影響的考察。對美的追求原則上包含心靈感性的一切感受,而流行文化只能以精神按摩的方式舒緩現代人緊繃的神經,“媚俗”化的審美趣味日益絢麗耀眼,美卻逐步失去滋養個體靈魂的功能。當美墮落為裝飾性的“漂亮”與“精致”,膚淺的感官快感只能生產出千篇一律的審美經驗,泛化之美不僅陶醉于平面化的符號表演,它還要在日常生活的建構中顯現和把玩自己,重復大量的感官刺激異化了真正的美,它所帶來的只有麻木。
如果將20世紀看作靈光消逝的機械復制時代,那么新世紀便是數字技術的紀元,從機械復制到數字技術的“超復制”,大數據儼然成為俘虜人心的“世俗宗教”。大數據篩選為用戶打造出數字伊甸園,身處其中的人們不斷重復著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根本無法遇見具有沖擊性的他者,他者的消失帶來了同質化暴力的肆虐,韓炳哲指出我們已步入積極社會的掌控之中。“平滑”作為積極社會的時代標簽,諂媚式的“順從”與“不抵抗”顛覆了對立他者的存在意義,通過消除否定性與顛覆性所帶來的沖擊,美也變得平滑起來。“平滑”在此處被賦予了與“麻醉”相近的含義:“它使感覺變得遲鈍。欣賞杰夫·昆斯作品時的那聲‘哇哦’也是一種被麻醉后的反應,這種反應與那種碰撞與被推翻帶來的否定性體驗完全不同。后一種美的體驗在當今是不可能有的。只要喜歡、點贊躋身主流,那種只有在否定性才能帶來的體驗就會逐漸消失。”(8)⑤韓炳哲:《美的救贖》,關紅玉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頁,第3頁。“平滑”與“麻木”雖有諸多相似,但韓炳哲并非簡單地沿襲前人故智,平滑不僅被其針砭為麻痹靈魂的詭計,還被視作積極社會中的個體存在模式。韓炳哲在此對數字社交媒體做了深入思考,在他看來“分享”與“點贊”是使交際平滑化的手段,避開消極性的感知意味著愉悅與舒適,否定性的抽離使“超交際”在同者間飛速運轉,交際、信息的順暢流通為資本加速循環制造了可能。
否定性是構成藝術內核的關鍵。在伽達默爾眼中,藝術的否定性是超越“自己臆想出的感官預期”的存在,藝術作品迫使我們承認它的存在,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每一次藝術體驗都是作品同主體的對峙與顛覆。韓炳哲指出以波普藝術家杰夫·昆斯為代表的平滑美學旨在展現平滑的表面與直接的效果,由于缺乏引起距離感的否定性,觀者面對平滑表面的雕塑時會產生一股觸摸的“觸覺強迫”。平滑的積極性消除了美學批判的靜觀距離,昆斯的作品擁抱任何一個欣賞作品的人,這類平滑藝術顯然“無需評判、解讀、注釋、自省和思考,并且刻意保持天真、平庸、絕對放松、卸下武裝、忘記憂愁的狀態,沒有任何深度、奧妙和內涵。”(9)⑤韓炳哲:《美的救贖》,關紅玉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頁,第3頁。平庸之美的流行無疑是對自律藝術的一次“祛魅”,批判性與自治性被赤裸裸的資本排擠在外,具有“平滑”屬性的藝術溫馴地迎合觀者,具有獨立性的藝術家也搖身一變成為生產藝術商品的員工,討好式的快感生產取代了反思性的藝術創作。
正如韓炳哲所分析的那樣,今天我們面臨的審美危機并非是美的缺乏,而是審美泛化下美的消費與濫用,消費社會以一種“充滿肯定性的歡愉”將美打磨平滑。消費資本的興風作浪離不開技術的推波助瀾,韓炳哲在將“平滑”美學納入自身批判體系的同時也顯露出對數字技術的隱憂。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將媒介看作人的延伸。在今天,以交互、智能、聯網為基本特征的數字媒介重塑了個體的感知方式與交際形式。韓炳哲將信息視作知識的“色情”形態,知識存在于橫跨過去、未來的時間結構中,對它的獲取是一次日積月累的提煉過程,認知不是簡單地了解信息,而是與外在他者互動并生成對世界的嶄新認識與體會。而信息卻沒有知識所具有的內在性,信息只存在于當下“被刨平”的時間之中,簡單的信息交互無法生成對世界的感悟與認知,數字社會中的信息化潮流阻礙了知識的獲取。避開創傷消極性的社會要求也促生了“點贊”,類似“拍磚”式的否定性互動只會影響交際效率:“肯定社會避免一切形式的否定性,因為否定性會造成交際停滯。交際的價值僅僅根據信息量和交換速度來衡量。大規模的交際也增加了它的經濟價值。否定的評判會妨礙交際。”(10)③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14頁,第15頁。同者間的大聲嘈雜遮蓋了他者的竊竊私語,信息、交際與資本的加速循環制造出一個沒有他者、缺乏否定性的世界。
三、同質化批判:泛審美化的危機所在
“麻木”與“平滑”的概念迭代為我們理解審美泛化危機提供了新的解題思路,商業藝術的批量生產,公共空間的裝飾美化,私人身體的外科美容,種種行徑為藝術與審美“祛魅”的同時又試圖為日常“附魅”。人們可以用“日常生活審美化”同“審美日常生活化”來解釋這種現象——審美泛化亦隱含著審美世界與現實世界交融的傾向。然而,如果將審美泛化的危機置于哲學與社會學的視角之中,韓炳哲更傾向于將這種癥狀診斷為同質化暴力對審美領域的攻陷。
審美所肩負的責任使它必須“從一種消遣、一種娛樂、或是一種技術效果引入生存原則,視作生存的范疇之一。”(11)南帆:《南帆文集2·沖突的文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頁。對理性生活的感性突圍被視作維系審美基因清澈性的重要手段,一直以來,我們默認審美藝術需要與生活、與觀者保持距離以避免其溺斃于現實的泥沼之中。從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陌生化”原則到布萊希特的“間離化效果”,藝術始終保持著自身的突圍姿態,困囿于現實生活被視作無法改變的事實,藝術家時刻處在“精神返鄉”的路途上。藝術對距離的要求并不局限于對創作的要求,觀者與藝術間的距離也需要得到保證,承認藝術他異性存在的“靜觀”就成為欣賞藝術的最佳方式。但隨著本雅明帶電影逃離了層層把守的藝術珍藏館,面向大眾的電影開始重展覽價值而抑制膜拜價值。傳統藝術往往被置于玻璃柜中或是封鎖于常人所不能及的單間,這種“隔離、劃界及封鎖的否定性是膜拜價值的根本。”(12)③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14頁,第15頁。而空洞的平滑藝術卻力求消解距離,光滑舒適的感覺甚至會產生“觸覺強迫”,羅蘭·巴特認為觸覺是最能消除神秘感的器官,觸覺的觸碰消解了視覺所建構的距離感,距離的消解意味著神秘感將不會產生,藝術的祛魅杜絕了向精神維度乞靈的可能。
當大眾藝術投入“心神渙散”或是“心不在焉”的懷抱,“凝神專注”式的鑒賞就僅限于孤芳自賞。高歌猛進的平滑藝術與少數精英所操持的先鋒藝術拉開了差距,回音室內的人潮喧鬧掩蓋了思想精英的竊竊私語,藝術內容開始走進“審美日常生活化”的時代。展現日常生活趣味的藝術譏笑先鋒藝術的古板冷漠,將日常生活編入自身的創作代碼,竭力揣摩受眾的興趣所在是走向商業化成功的訣竅。作者身份的跌落也為“審美日常生活化”出力良多,數字媒介虛化了作者與受眾的距離,在如今這個互聯網時代,人人都能成為創作者與傳播者,“抖音”與“朋友圈”的風靡昭示著大眾創作的時代已然到來。對朋友圈或好友圈的苦心經營成為許多人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對虛擬自我的無效裝飾只為尋求好友的“點贊”,九宮格圖片或短視頻難以成為意義的合格載體。人們的分享與點贊只為追逐快樂,尋求同者之肯定的積極邏輯貫穿日常生活的始終,我們有理由認為,這是一個“快樂意味著點頭稱是”(13)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頁。的時代。
“所謂色情,可以說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巴塔耶試圖從被排斥的色情中尋找至高無上的意義;韓炳哲卻將色情化視作透明社會的幫兇。當然,韓炳哲口中的“色情”并非沉溺于男歡女愛的粗劣肉欲,“色情”在他眼中,更多是一種形式,是一種將自身置于過度照明下的強制展示:“透明社會將所有距離視為亟待消除的否定性。距離是加速交際和資本循環的障礙。由于其自身的內在邏輯,透明社會排除各種形式的距離。”(14)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4頁。一種趨近透明化的社會要求將展示價值捧上神壇,距離的消解為各類形象畫上平面化的臉譜,展示價值擠壓了意義的生存空間,在“色情社會”中,一切的意義都是明確的。以赤裸的姿態呼喚著觀者的到來,缺乏“引發映像、審視和思考的不完整性”的觸覺式體驗即“色情”。韓炳哲對“色情”的思考為我們檢視審美泛化危機提供了智識來源。應當指出,“色情”與泛審美化都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當代人想象力的萎縮,毫無保留的裸露呈現與裝點一切的美化行為看似格格不入,卻在本質上殊途同歸。消解距離的急迫容不得想象敘事的輾轉迂回,追求清晰的過度聚焦將想象溺斃于符碼的亂流之中。
對同質化社會的擔憂并非韓炳哲的獨屬,已有相當部分學者對同質化社會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但韓炳哲對同質化的思考獨樹一幟,通過對“暴力”的知識考古,韓炳哲以“他者的消失”為錨點,為我們揭示出同質化社會的運作邏輯。暴力最初以否定性、排斥性的面目出現,通過構筑兩極化的緊張關系,暴力以一種毫無遮掩的姿態公開亮相。彼時的排斥性暴力更多以統治階級展示其血腥權力的舞臺表演出現。但殺戮暴力在現代已失去其合法效力,暴力的拓撲式置換使暴力不再講求鳴鑼開道地鋪張排場,公開展演讓位給皮下的毛細滲透,暴力不再僅僅表現為過度的排斥。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的開篇對公開處刑與犯人作息表的對比暗含著這一暴力演變,內向化的暴力闖入主體的神經軌道和肌肉纖維,通過將統治機關移植到服從主體的內心,“紀律”和“操練”制造出馴順的、訓練有素的肉體。
相較于規訓社會的情態動詞“不允許”和“應當”,韓炳哲注意到當今社會對“能夠”的推崇。充滿積極意味的“能夠”具有打破邊界與距離的潛力,“是的,我們可以做到”這句話的背后,是積極性的擴張式暴力對邊界與距離的消解與冒犯。在韓炳哲眼中排斥暴力建立在二元關系上的免疫結構之上,例如鮑德里亞的敵對關系譜系學就認為敵人將以狼、老鼠、甲蟲和病毒的形式出現,而對抗、入侵與滲透必然激活主體的免疫機制。隨著社會同質化趨勢的加重,暴力形式有了新的發展,這種暴力并非來自主體外部的強迫,而是生于內在的擴張。肯定性通過內在的擴張將主體解散,并實現對他的去內在化,表現為“商品化的過剩、超量、城市化的擴張、耗竭、生產過剩、過度囤積、交往過度、信息過剩”的擴張暴力不會激活免疫系統的抵抗,但循環系統的堵塞與積聚使肯定性的暴力以梗阻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場沒有對手的戰爭將以梗阻導致的癱瘓收尾。
四、美的救贖:重構否定性經驗
面對審美泛化的討論激起的層層波浪,理論家們的振振有詞在客觀現實前顯得軟弱無力,對解決之道的探討大多淺嘗輒止,批評家手里雖然多了幾個概念,但一種新的思維結構并未同時產生。理論家們為美的平庸化奔走告解,殊不知審美泛化的危機背后隱藏著同質化的威脅。既然美的乏味與平庸化已成既定事實,如何對抗“平滑”以實現美的救贖?韓炳哲的回答是重視美所令人感到不愉快的部分,崇高、遮蔽、他異性,他者的復歸才能帶來審美的解放。
針對透明社會的“色情化”問題,韓炳哲也給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他直言美是一種遮蔽,“遮擋、延遲和分散注意力也是美的時空策略”(15)②③韓炳哲:《美的救贖》,關玉紅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頁,第99頁,第90頁。,美的本質棲息于“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性之中。褪去自身的遮蔽物,以赤裸的狀態展示自身的“色情”行為無法造就距離的美感,制造誘惑的把戲在于“讓自身成為他者永遠的秘密”,而“色情”的展示卻有如將自身置于商店的櫥窗中標價待售。類似的觀點在萊辛的《拉奧孔》中也有出現,造型藝術必須找到最具生發性的瞬間并加以表現,在感情上避免激情頂點的頃刻,為想象的空白留有余地,這也就是拉奧孔為何在雕刻中不哀嚎的原因。數字社會悄然改變了人們的感知模式,信息不再追求深度與廣度,而是以當下直接呈現的疊加形式拋頭露面。韓炳哲將美視作“具有敘事性的關聯”,數字社會中單純的信息串聯無法搭建敘事的橋梁,敘事關系需要“隱喻”的附魅,事物散發芬芳的本質需要漫長的回味才能展露出美的姿態。美不是霎時的光芒耀眼,“隱喻”的遮蔽性延伸了美的存在實踐,因此作家的工作即“隱喻世間萬物,也就是去詩化世界”(16)②③韓炳哲:《美的救贖》,關玉紅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頁,第99頁,第90頁。。
韓炳哲認為,近代美的感性學以平滑美學作為起點,平滑之美以一種“肯定性的歡愉”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從表面上看,“愉悅”似乎成為審美與感官享受之間的共同點,但在韓炳哲看來,將美視作快樂、滿意的代名詞意味著美正走向凋零。痛苦的否定性被視作謀害美感的鴆酒,哪怕是粗糙的表面與尖銳的棱角都會使美黯然遜色,美似乎應該理所應當地披上小巧精致或是輕盈細膩的外衣。但將美限制在積極性的范圍內無疑使人“昏昏欲睡”,韓炳哲將目光放到古希臘羅馬時期以求解決之道。通過對柏拉圖與朗吉努斯的援引,“崇高”的重新發現為韓炳哲對抗平滑美學提供了理論支撐。朗吉努斯反對因標新立異而產生的浮夸、幼稚和矯情,崇高與優美不同,它與莊嚴、偉大、激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伯克也在美與崇高的思考中,將崇高視作否定性的存在。作為一種復雜的審美體驗,崇高最初以痛苦與驚懼構成,但這種“剎時的抗拒”只維持短短的一瞬,對崇高之物的敬仰與自我持存的欣喜使得主體心潮洶涌,回歸理性的內在性讓恐懼和壓抑重新轉化為愉悅感。優美所帶來的歡愉不過是確證主體自主性與自滿性的注腳,崇高所擁有的否定性能夠喚回他者之美。韓炳哲呼吁將美與崇高重新結合,實則是為否定性之美正名。
僅僅將“平滑”視作一種麻醉也是不夠的,否定性的消失也意味著他者的消失。數字社會中一切事物都是被拍照、記錄、存儲的對象,科學求知精神手持獵巫運動的火把將所有謎團與神秘逼到無影燈下,消費邏輯捕捉具有他異性的他者并以分類的形式將其置于某綱某目中,殊不知分類與比較在創造他者的同時也摧毀了他者身上神秘的他異性。真正的他者消失了,丑陋被圈養在馬戲團或綜藝節目中嘩眾取寵,獵奇心理則在消費的庇護下得到饜足。缺乏具有陌生性、差異性的他者,藝術被指認為一場帶有異國風情的假面舞會,新奇的形式引得觀眾陣陣叫好卻無法激起心中的層層漣漪。因此,他者的復歸便是美的救贖最重要的一環,在韓炳哲看來“藝術的任務就是去拯救他者,拯救美就是拯救他者,藝術通過反對將他者固定在其固有狀態來拯救他者。”(17)②③韓炳哲:《美的救贖》,關玉紅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頁,第99頁,第90頁。s美游走于嚴絲合縫的消費主義架構之中,身上沾染世俗煙火的污漬也不足為奇,重點是如何洗凈扎根于美之上的商業標簽。韓炳哲將希望寄托于他者之上,傾聽者的出現能夠幫助交際從信息交換維度重返更深層次的意義維度,擁抱他異性與否定性也為美制造了新的可能,囿于“平滑”的泛審美危機勸誘著趨于精致與嬌柔的美自甘墮落為可消費的裝飾品,充滿神秘與隱喻的他異之美卻將人們引入深度思考的境界。
五、結 語
韓炳哲作為“互聯網時代的精神分析師”,對人的新異化現象的關注是構成其理論光譜的重要部分,自我剝削、透明展示、自戀指涉等理論都顯示出韓炳哲對當代人生存狀況的密切關注。面對數字化社會中的審美危機,韓炳哲力圖說服讀者,與否定性畫上等號的他者有望成為解決這場審美危機的救贖方案,因為它攜帶著反思、神秘與敘事結構的基因,能夠對抗審美泛化現象下的時弊。以否定性的審美經驗來解放被數字技術操控的審美感知,以他者的復歸來對抗消費社會所提倡的審美泛化,盡管韓炳哲的救贖方案無異于一次烏托邦式的救贖,但他的思考無疑為我們擺脫審美泛化的精神危機指引了一條反思路徑。
社會語境的變化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審美無功利的觀念,在此處自律之美與迎合之美分道揚鑣。通過切割審美的手術,審美泛化盡可能地避免任何帶有否定性的他者將形而上的反思重新攜入同質化的單調語境,“迎合”與“媚俗”的文化潮流催化出新時代的審美主體。審美與藝術如何在數字時代超脫刻板的日常生活?效率至上的時代里審美又該如何“慢”下來?數字科技與藝術的結合又是否會迸射出新的火花?接踵而至的問題拷打著我們的思維極限,毋庸置疑的是藝術自會在數字社會的變革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境遇的安逸不該挫傷理論銳利的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