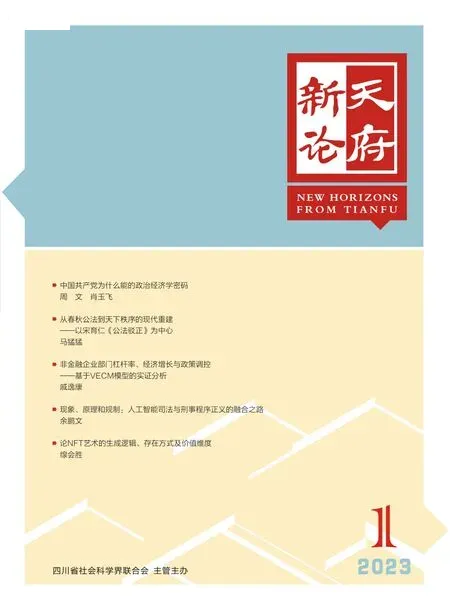論NFT藝術的生成邏輯、存在方式及價值維度
缐會勝
自2020年起,建基于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之上的區塊鏈技術從經濟領域滲透至藝術領域,實現從“同質化代幣”向“非同質化代幣”的內在轉換。“非-”不是簡單地否定,而是標識獨異性與唯一性,2021年甚至被稱為“NFT元年”。2020年12月,推特聯合創始人杰克·多爾西(Jack Dorsey)將自己第一條推特截圖在拍賣網站Valuables上以290萬美元售出,并表示“我認為幾年后人們會意識到這條推文的真正價值,就像蒙娜麗莎的畫作一樣”(1)Jack Dorsey Sells His First Tweet as an NFT for $2.9 Million,2021-03-23,www.ledgerinsights.com/jack-dorsey-sells-his-first-tweet-as-an-nft-for-2-9-million,訪問日期:2022-06-13.。2021年3月,藝術家畢普(Beeple)的NFT藝術品《每一天:前5000天》 (《Everydays:TheFirst5000Days》)在紐約佳士得拍賣行以6934.6萬美元的價格成交。2021年5月,同樣在紐約佳士得藝術拍賣會上,兩個計算機編程愛好者通過算法自動生成的一萬個被命名為《CryptoPunk》卡通人物圖像中的九個小圖像以1696.2萬美元的價格成交。盡管NFT可以代表任何數字資產,但NFT藝術大多數都屬于任何類型的數字或物理繪畫、動畫、視頻、風景、漫畫/卡通、3D藝術等等(2)Isabel Dominguez de Haro,How NFTs Are Driving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Art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in a Pandemic Age,2022-05-31,https://digitalcommons.sia.edu/stu_theses,訪問日期:2022-08-05.。揆諸目前對NFT藝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鏈拓展與數字治理、法律版權與監管等維度,缺乏從藝術本體視域、數字資本主義與元宇宙視角對NFT藝術的剖析與解讀(3)關于生態鏈拓展與數字治理、法律版權與監管的研究,參見解學芳、徐丹紅:《NFT藝術生態鏈拓展與數字治理:基于參與式藝術視角》,《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關于NFT數字資產的研究,參見陸建棲、陳亞蘭:《元宇宙中的數字資產:NFT的內涵、價值與革新》,《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8期。關于元宇宙與數字資本主義的研究,參見王陌瀟:《數字資本主義與后人類文化景觀:作為元宇宙先聲的NFT藝術》,《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22年第3期;耿盈章:《從非同質化代幣到元宇宙:數字文化工業中的“光暈”》,《文學與文化》2022年第2期。。NFT藝術作為數字藝術中的一種新型存在物,我們對此有許多未知與疑惑:何為NFT藝術?NFT藝術如何存在?NFT藝術的價值何在?NFT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數字藝術,既有相對于一般數字藝術的獨特性,又有普通數字藝術的普遍性。本文將以NFT藝術為研究對象,剖析NFT藝術的內在生成邏輯、存在方式以及價值維度。
一、“NFT化”與“權證”:NFT藝術的生成邏輯
(一)藝術的“數字化”到“NFT化”
何為NFT藝術?若要對這一核心問題進行追問,首先需要追問“何為NFT”、“NFT化得以可能的前提條件是什么”等問題。區塊鏈技術于2008年開發之時,主要是作為一種分散、破碎的金融方式在經濟領域被廣泛應用,譬如比特幣(同質化代幣)等,與藝術領域毫無關系。而NFT是區塊鏈技術自身的一種特殊應用,當藝術行業于2017年開始成功地使用NFT技術時,為藝術提供了一種存在方式,并且它存在于數字世界,而非存在于傳統的藝術館、畫廊、拍賣行等物質空間。這就表明對NFT藝術的討論要以數字世界作為基底,任何一個事物經由“NFT化”成為NFT藝術(NFT Art)的前提條件是:首先要作為以數據化形式表征的數字藝術(Digital Art)存在,在數字技術基礎上存在的區塊鏈技術通過其對唯一性的確證與不可復制性特征滲透到藝術領域。有學者指出, “所謂NFT加密藝術,是將數字藝術品通過區塊鏈方式進行著作權或所有權確權的一種方式。NFT既可以直接將數字藝術品進行加密,也可以把傳統藝術品先進行數字轉化,比如將畫作拍攝成數字照片或視頻,然后再將這些照片或視頻進行加密處理。”(4)季濤:《NFT加密藝術市場的未來》,《藝術市場》2021年第7期。萬物先要經過數字化或數碼化過程,方能對數字化的事物進行更進一步的“NFT化”。NFT藝術在本質上不是簡單的“NFT+藝術”,而是“NFT+數字藝術”,即NFT藝術是一種特殊的數字藝術。先要成為數字藝術,方能成為NFT藝術。
何為數字藝術?“所謂‘數字藝術’,一般是指以‘數字’作為媒介素材,通過運用數字技術來進行創作的具有一定獨立審美價值的藝術形式或藝術過程。”(5)張耕云:《數字藝術三題》,《美術研究》2005年第2期。數字藝術是在與傳統藝術的相互關系中顯出自身特性。傳統藝術是一種“原子性”藝術,是以可觸可感的實體化物性方式存在,而數字藝術則經過數字化過程后以一種全新的“比特”方式存在。“數字化即是克服、消解物質媒介的種種物質特性,用數字‘比特’來替代物質‘原子’作為新的構成材料或工具,把原子拆解為數字,然后經過信息編碼,重新構成一個虛擬的、沒有物性的世界。”(6)張耕云:《數字媒介與藝術》,《美術研究》2001年第1期。數字藝術的最根本特性不在于審美,而在于以比特(數據)的形式存在,它是對物質世界中物或者藝術品進行編輯與處理,以視覺化形式呈現在屏幕上。
數字藝術對現象世界的數字化重構為“NFT化”提供了基礎,而數字藝術無限復制的缺陷為“NFT化”的出現制造了契機。凱文·特拉尼恩(Kayvon Tehranian)在2021年的TED大會上作題為《NFT如何構造互聯網的未來?》的演講時,提及一位互聯網先驅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面對互聯網曾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我們擁有的東西可以被無限復制,還能瞬間免費地發送到世界各地,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所有物?我們該如何獲取自己腦力作品的報酬?”(7)Kayvon Tehranian :《NFT如何構造互聯網的未來?》,2021-11-16,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21667070,訪問日期:2022-08-05。換言之,我們的勞動成為“數字勞動”,數字藝術品不屬于創作者,數字藝術被數字平臺“挾持”。NFT的出現為數字藝術所有權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技術性的突破。NFT究其本質是一種去中心化與公開透明的數據庫技術,它是登記在區塊鏈上的所有權通證,“NFT化”的實現需要借助于區塊鏈技術(block chain technology);同時這種所有權通證還有特定的價值標識,可以在廣闊的數字空間中自由地交易。“NFTs為數字藝術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東西: 一種讓各方就什么代表對特定資產的所有權達成一致的方式”(8)Isabel Dominguez de Haro,How NFTs Are Driving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Art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in a Pandemic Age,2022-05-31,https://digitalcommons.sia.edu/stu_theses,訪問日期:2022-08-05.,“NFT化”所提供的藝術品的“權證”與“價值”的二重性使得NFT藝術自身顯示出復雜性。
(二)NFT藝術的權證邏輯
NFT的全稱為Non-fungible Token,有很多種譯名,譬如“不可互替通證” “非同質化權證” “非同質化通證” “異質代幣” “非同質化代幣”(9)秦蕊、李娟娟、王曉等:《NFT:基于區塊鏈的非同質化通證及其應用》,《智能科學與技術學報》2021年第2期。等,復雜的譯名反映出“通證”與“價值”的二重性。“NFT的出現正在讓事情變得復雜。它為原本可以同質化傳播的數字藝術打上了‘真’之印記,由此,數字藝術也可以成為收藏、投資乃至投機的對象。”(10)謝廷玉: 《“NFT”元年:“數字代幣”如何席卷了文化領域?》,2021-11-29,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3815200114002.html,訪問日期:2022-08-08。相較于同質化代幣(Fungible Token)而言,NFT在強調 “非同質化”這一特征的同時,也凸顯代幣性;非同質化指向陌異性,具體表現為唯一性與不可復制性。NFT藝術不是實物或者藝術品本身,它僅是一串元數據(Metadata),對數字藝術品進行所有權標記。
NFT藝術是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藝術存在狀態的定性,凸顯出其有別于傳統藝術與一般數字藝術的唯一性或本真性特征:傳統藝術通過“靈韻”來彰顯本真性;而現代藝術在對技術的批判中通過“概念”來凸顯本真性;而NFT藝術通過“技術”來確證原真性。
在傳統藝術中,對藝術本真性的確證往往通過藝術品本身的唯一性與自身具有的靈韻實現。本雅明認為,傳統藝術的唯一性以不可復制性作為確證方式,盡管會有贗品或仿品存在,但無礙于藝術品本身,因為還有“靈韻”作為最后的審美保證,靈韻是藝術品自身顯現出來的一種籠罩性的光暈,確保了藝術品自身的獨一無二性與不可接近的神圣性。而伴隨著機械復制時代的到來,機械的無限復制性破壞了藝術品本真的存在方式,復制成為普遍的存在方式,藝術的本真性受到挑戰。“復制技術把所復制的東西從傳統領域中解脫了出來,由于它制作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因而它就用眾多的復制品取代了獨一無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復制品能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環境中去加以欣賞,因而它就賦予了所復制的對象以現實的活力。”(11)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87頁。盡管藝術的靈韻消失了,但是現代藝術在與復制的斗爭中,通過“尋常物的嬗變”使得藝術品重新獲得本真性與唯一性,創作者通過“概念藝術”的創作將獨特的“概念”賦予藝術品,在現代藝術中獨特的“概念”確證了藝術的本真性。
在傳播與復制速度極快的數字時代,數字藝術的本真性通過“技術”手段來確證。藝術家的創作都不通過顏料、畫布、紙張以及筆等傳統的物質材料,而是通過視覺化與身體的交互過程,運用0與1的二進制數位在數字屏幕上進行創作,區塊鏈技術提供的非同質化特征是保證數字藝術本真性的技術手段,這種本真性不是通過作者的創造性來保證,也并非通過接受者感受到的靈韻來保證,而是通過區塊鏈技術及其NFT確證對數字藝術品“元數據”的完全占有為依據。(12)Jiasun Li,William Mann, Digital Tokens and Platform Building,2018-10-01,https://ssrn.com/abstract= 3088726,訪問日期:2022-08-08.NFT藝術的原真性通過具有“透明公開、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等特征的區塊鏈技術與ERC721/ERC1155/ERC998等協議實現,既非本雅明所說的藝術內在的靈韻,也非現代藝術中人為賦予的概念。NFT似乎是由藝術創作者頒布并被人們普遍認可的防偽證書,這是對數字無限復制性的一種抵抗與防衛。
此外,NFT藝術的本真性可以進行交易。交易的是一系列相關的元數據,獲得的是對這些元數據的占有權,這種元數據的所有權為區塊鏈上的交易記錄所確證。NFT從根本上來說,是數字藝術或者數字內容的權證化或通證化。區塊鏈技術由于其不可篡改性以及透明公開為整個數字世界的參與者所認可。創作NFT藝術的流程相對簡單容易,這為每個藝術創作者提供了進入NFT藝術的機會與可能性。在一些加密平臺上,創作者可以將圖片、音頻、視頻以及其他數據構成物傳送到加密平臺,建構一個交易機制,每一個數字藝術品都會獲得獨一無二的NFT權證,每個權證都擁有唯一的數字編碼,這樣就確證了創作者對該數字藝術品或NFT藝術品的所有權。(13)張培培:《區塊鏈與加密藝術》,《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6月14日。數字藝術是儲存在建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公共式平臺上,而非中心服務器上,不可能被某個單獨的個體刪除或者損壞,可以永久保存下來。另外,由于NFT權證的唯一性,每一個權證編號對應一個網絡地址,“NFT的獨特性質可以通過區塊鏈技術驗證,一旦NFT在區塊鏈網絡上創建,創建者只鑄造特定數量的代幣,這一數字永遠無法改變”(14)Isabel Dominguez de Haro,How NFTs Are Driving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Art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in a Pandemic Age,2022-05-31,https://digitalcommons.sia.edu/stu_theses,訪問日期:2022-08-05.,如此就可以通過網絡地址的變化來追尋NFT藝術品的歸屬或者所有權,每一次的交易都被記錄在區塊鏈這一記錄所有交易數據的“賬本”中。
NFT基于的區塊鏈技術通過去中心化與不可復制性特征確證數字藝術的本真性,這種確證本真性的特征與本雅明的“靈韻”確證與概念藝術的“概念”確認方式不一樣。這由“技術”手段實現,是數字化時代的一種具體表征。正如每個人在物質世界中都有獨特的身份證號一樣,每一個物質載體上的數字都在確證我們每個個體的獨一無二,萬物的數字化深層次地反映了韋伯所說的物質世界的“合理化”進程。NFT技術在數字世界中實現了確證唯一性的技術突破,這是韋伯所說的理性的“合理化”進程在數字世界中的拓展。“數字化”是“NFT化”得以成為可能的前提與基礎,從數字藝術的生成到“NFT化”的過程,彰顯了整個NFT藝術的內在生成邏輯:NFT的根本作用就是確定藝術品的所有權與稀缺性,通過技術手段賦予被NFT化的藝術品以唯一性的同時,改變其根本存在方式。
二、數碼物:NFT藝術的物性存在方式
對“何為NFT藝術”的論述主要立足于對“NFT化”進程與區塊鏈技術的深入闡發,基于區塊鏈技術的NFT機制解決了數字藝術品的“歸屬性或所有權問題”。但對于NFT藝術品的“存在問題”還需從二進制的數字技術角度進行闡釋。前文已提到,區塊鏈技術只能確保NFT藝術的本真性問題,卻無法解決NFT藝術的存在問題,NFT藝術是“NFT+數字藝術”。NFT藝術首先是一種數字藝術和數碼物(Digital Being),因此從數字技術與物質性的角度對其存在方式進行探討就很有必要。
(一)NFT藝術“傳播媒介”的物質性
作為數碼物的NFT藝術基于以數字技術為主的“傳播媒介”(15)傳播媒介與構成媒介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種存在。在藝術中,傳播媒介指的是不同的載體,譬如樹皮、紙張、竹簡以及布帛、莎草紙、石碑等,同一種藝術可以在不同的傳播媒介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而構成媒介指的是每種藝術均有其特殊的依托媒介,即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說的,不同的藝術用不同的媒介,如聲音、顏色、語言等。盡管表現形式不同,但是兩者均是物質性的存在,是藝術得以可能的物質性基礎。,是存在于一定可感性物質媒介中的“準客體”。傳統藝術中繪畫的存在需要畫布、畫框,文學的存在需要竹簡、絲帛、紙張和泥版,以及音樂的存在需要黑膠光盤、錄音機等(16)關于藝術品媒材或媒介的論述,參見巫鴻:《美術史十議》 “歷史物質性”部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41-53頁。,這些傳播媒介使得傳統藝術品能夠以不同的物質形式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同時媒介載體也使得傳統藝術品的歷史性流傳得以可能。同理,NFT藝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物質性媒介或媒材,即現實可感的物質媒材與物質關聯環境,電腦的硬件、智能手機以及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等是數字藝術品存在的根本性物質基礎。若無這些物質基礎的存在,數字藝術將會瞬間消散,失去存在之所在,但是這些傳播媒介層面的物質性經常被忽視。在數字世界中,NFT藝術作為一種基礎性數字藝術品,無論其表現為圖像、動畫、像素塊、音頻、視頻,還是GIF表情、影像、游戲等,都是一些“元數據”系統,附著在可見可感的電腦、智能手機等物性媒材所構建起來的物質性關聯環境之中。即,NFT藝術作為一種數碼物,是存在于這樣一個物質環境中的關系生成物。譬如,2021年3月西班牙涂鴉藝術家班克斯(Banksy)的藝術作品《白癡》被其持有者轉換為NFT藝術品,并焚毀了其物質性原作,從物性版本的《白癡》到NFT版本的《白癡》的轉換,盡管改變了藝術品的存在方式,但是任何一種版本都無法逃脫作為傳播媒介的物質關聯環境。物性版本的藝術品存在于由畫框、畫布等建構的物質環境中;同樣,NFT版本的存在也內在于電腦、集成電路、三極管以及通信設施等建構起來的物質網絡環境中。因此,NFT藝術品的存在不是虛擬的,而是有其物質實在基礎。如果底層物質基礎被破壞,數字世界就會蕩然無存。另外,通過燒毀物理空間中的班克斯藝術原本,宣告了NFT藝術品的唯一性,這種行為方式表面上是在宣告獨特性,更深層次來說則是在挑戰傳統的藝術存在方式,確證與保證新藝術的存在方式的合法性,就像杜尚通過小便池宣告尋常物作為藝術品的合法性地位。杜尚打破的是技術與藝術之間的區分,同時也是打破傳統與現代的區隔,并宣布現代藝術的存在身份的合法性。燒毀班克斯藝術品原本的行為確證了NFT藝術品的合法性存在,“數字化存在”是數字藝術品的根本存在方式。
(二)NFT藝術“構成媒介”的物質性
NFT藝術品“構成媒介”的物質性是其作為數碼物的另一特征。在《論數碼物的存在》中,許煜認為“數碼物指成形于屏幕上或隱藏于電腦程序后端的物體,它們是由結構或方案管理的數據與元數據組成”(17)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因此數據與元數據是數碼物的基本“構成媒介”,也即NFT藝術品的構成媒介。索緒爾的語言學為數碼物“構成媒介”的物質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索緒爾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一種對事物的命名與表征,其本身就是事物性的存在,“語言是事物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里,作為一個符號系統,語言可以被理解為能夠產生那些一度被認為僅僅能夠理解的事物”(18)凱特·麥高恩:《批評與文化理論中的關鍵問題》,趙秀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7頁。。文學藝術品是由“語言”這種“構成媒介”生成的符號編織物,文學的構成媒介的物質性既在于語言文字的組織結構,也在于語言、詞匯及其之間的關系;正如音樂是由聲音這種物性符號編織而成、繪畫是由可視化的色彩符號建構起來的編織物,“一件件作品從這種或者那種作品材料那里,諸如從石頭、木料、鐵塊、顏料、語言、聲音等那里,被創造出來”(19)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29頁。。語言作為一種基礎性符號,由能指與所指兩部分構成,能指與所指之間相互組合可以生成不同的編碼范式,就像作為數碼物的NFT藝術品就是由0和1二進制符號按照一定的結構和方案編織而成的數據或元數據,并顯現為一定的視覺或統覺感知方式,即“通過數據與元數據方案形式化的數據對象”(20)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9頁。。比如美國數字藝術家畢普(Beeple)的NFT藝術品《每一天:前5000天》。藝術家從2007年開始每天創作一幅數字藝術品,選擇13年內創作的5000幅數字藝術作品拼合成最終的作品。排除數量與時間等外在量化的形式,直接從質的維度進行分析,每一個作品都是用二進制算法表達的數據形式,數據的不同結構與組合方式決定了藝術品的存在方式,大作品就是數據的數據,即元數據。數據與元數據這一物質性的建構媒介確證了NFT藝術的物質性特征,NFT藝術品不是虛擬漂浮的存在,而是奠基于物質性基礎之上。此外,NFT藝術品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直接創作的數字藝術品,如《每一天:前5000天》;另一種是日常物或者傳統藝術品的“NFT化”,如將杜尚的《泉》從物性版本轉化為NFT版本,把傳統藝術品(技術人工物)轉化成數碼物(數字人工物),這里存在一個物的數據化與數據的物化之間的辯證關系,盡管轉換了物的存在方式與存在形態,但依舊是“物”。
另需注意NFT藝術品的儲存問題。繪畫、文學以及音樂等傳統藝術經由語言、聲音以及色彩等“構成媒介”組構之后的編織物存在于物質世界中;而NFT藝術品大多通過電子終端展示,由二進制算法經過編碼之后存在于數字虛體之中,這種虛體是在物質關聯環境基礎上生成的數字“蒂合環境”(Associated Milieu)(21)“蒂合環境”是西蒙棟技術哲學的一個核心概念。西蒙棟稱技術物體存在的外界環境為“蒂合環境”,即特定物質關聯環境,它保持系統的平衡穩定。參見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 by ROGOVE J.,Minneapolis:Univocal Publishing, 2017。而“數字蒂合環境”是專門就數字技術而言,是存在的一個數字環境,數碼物就存在于這樣的一個空間中。。這種差別顯示出兩種不同的技術人工物之間的差別。盡管人類一直生活在人造物與自然物混雜的環境中,但技術人工物畢竟是有別于山石、樹木等基本自然物的人造物,可以區分為傳統技術人工物與數字人工物,表征在藝術品領域也即傳統藝術品與數字藝術品的區別。傳統藝術品基本上存在于一定的可被視覺、聽覺以及身體經驗感知到的物質空間中,如博物館、藝術館或私人廳堂與畫廊等,均會占據一定的物理空間。觀者對傳統藝術品的欣賞即康德所說的靜觀式審美,傳統藝術品的存在方式決定了這種主客二元對立的審美。相較于具身性的體驗而言,NFT藝術以數據的形式存在于數字網絡環境中,是一種離身性的體驗,但是不同的主體可以在這個網絡中共享,這體現出從傳統藝術品走向NFT藝術品意味著從傳統的“主客對立”的靜觀走向一種“主體間性”共享。
(三)數碼物:NFT藝術的本體論
NFT藝術品作為一種數碼物,前文基于“傳播媒介”與“構成媒介”等外部視角論述數字藝術的物質性存在,這種討論依舊未進入NFT藝術作為本體論的物質性存在。NFT藝術首先是基于數字技術基礎上的數碼物,然后才是基于區塊鏈技術登記在區塊鏈上的加密藝術(Crypto Art)。對“何為數碼物?”的追問本質上就是對“NFT藝術物質性本體存在”的追問,NFT藝術品歸根結底是基于數字技術與區塊鏈技術而存在的一種數字藝術形式。
在本體論層面,NFT藝術本質上作為數碼物,從算法、結構以及方案中生成與顯現出來,關系是數碼物的本體存在,即數碼物的存在是一種關系本體論。數碼物盡管也是一種“物”,但對數碼物的闡釋不能按照傳統形而上學對自然物與現代對技術物的解釋思維進行闡釋,即數碼物是與自然物、技術物有別的新型物質形態。西蒙棟在《論技術物的存在方式》(1958)一書中提出機器學,主張通過技術物的演進及技術物與其環境的關系探究技術物的本體性存在問題,技術物是技術樣品在時間序列上的展開,即認為技術物是有機的統一體(22)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 by ROGOVE J.,Minneapolis:Univocal Publishing, 2017,pp.11-12.。海德格爾對技術物的探究主要集中在“上手性”與“在手性”這兩個概念,通過對錘子這種技術物的具體考察,解釋了技術物的存在。在手性意味著將技術物(錘子)視為意識客體并試圖達到其本質與實體;相反,上手性意味著一種人與技術物的互動,懸置對所謂本質與實體的追問,讓技術物以其功能向我們顯現。西蒙棟與海德格爾對技術物的理解從實體轉向外在環境,并主張回到物體本身。這種對技術物的討論給數碼物本體性存在的思考提供了一條思路,但數碼物作為一種新型的工業物,與技術物也存在很大的區別。
數碼物是在關系網絡中生成的“準客體”(23)“準客體”概念旨在批判傳統主客二元對立的本質主義思維模式,強調一種關系主義的思維,將“物”視作獨立自足的實體性存在,根據關系的變化顯現為不同的形態。參見Gerard de Vries,Bruno Latoui,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6,p.134.(Quasi-object)。數碼物由受方案與結構管理的數據與元數據組成,因此方案和結構是前提性的。 “方案是為元數據賦予語義或功能的結構,在計算機科學中,它們也被稱作本體——一個與哲學相關的詞匯”(24)④⑦ 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第82頁,第22頁。,但僅僅有方案無法生成數碼物。因而“在算法的意向下,元數據方案作為范疇,從數據流中創建客體形式從而向我們呈現數碼物”(25)④⑦ 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第82頁,第22頁。,數碼物是通過元數據與元數據方案形式化的數據對象。數字的物質性設施、方案與結構、數據、元數據以及其他物質性元素之間的這樣一個關系網絡使得數碼物得以從關系中呈現出來。譬如,海德格爾在闡釋“壺”這種物(26)物本身就有聚集、聚合的含義。古高地德語中的“thing”一詞意味著聚集,而且尤其是為了一件所討論的事情、一種爭執的聚集。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82頁。的時候,主張天、地、神、人這四重聚集、聚合在這一物中,使得壺的物性得以顯現,使物成其為物(27)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86-188頁。。這種對物的理解表明物就是這樣一種關系型的東西,一種通過呼喚、召集、邀請各路“神靈”來此現身的虛空之域。數碼物和海德格爾的“壺”這種物一樣,在各種關系中讓自己本真地呈現出來。從這個層面上來說, “數碼物與技術物最大的差異是,盡管一方面數碼物加速瓦解彼得·斯洛特戴克所說的西方形而上學的‘實體崇拜’,但另一方面數碼物的具體化帶來了由已形成的關系構成的技術系統,在此中任何事物都有與其他事物連接的可能”(28)④⑦ 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第82頁,第22頁。,從實體走向關系,天地神人與物的聚集都是關系,數碼物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成物;且數碼物依據一些參數、算法以及數據的聚集成形,而網絡在數碼物中誕生,所有的數碼物都存在于一個拉圖爾所說的行動者網絡當中,相互形成“客體間性”關系。
以上對數碼物的本體思考本質上就是對NFT藝術本體存在的哲學論證,這種本體是一種關系本體論。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意味著打破單一的統治關系,走向相互聯系的網絡關系,每個數碼物或NFT藝術品都是一個行動者,通過聚集、集合在區塊鏈和數字環境中使其自身顯現出來。
三、NFT藝術的“非美學”價值維度
自夏爾·巴托在《歸結為同一原理的美的藝術》中用“美的藝術”(Fine Arts)這一概念來界定藝術(29)Paul Oskar 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 12, No. 4,1951.,之后鮑姆加登、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家用美、自由、愉悅等主觀的感性判斷與主體感受解讀與分析藝術,普遍將藝術作為美學的專屬研究對象。然而,藝術作為一種自足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NFT藝術所蘊藉的內在價值的評判與分析,不能囿于感性層面的審美性、愉悅性等美學視域,而需要從“非美學”的維度對其進行考量或厘定。從整個數字資本主義的內在發展脈絡以及數字技術、VR技術、AR技術等建構的數字世界或元宇宙(Metaverse)層面來評析NFT藝術的價值,可以發現,NFT藝術的價值不是引起人們普遍的崇拜與贊嘆,也不是給人們以心靈的慰藉與救贖,而是關涉數字資本主義的價值邏輯與元宇宙中的主體性建構:一方面涉及藝術與技術、資本粘合之后的資產價值;另一方面涉及元宇宙中數字主體的身份認同與確證,NFT藝術是數字主體尋求承認與認可的媒介技術物。
(一)交易價值:從感性展示到數據占有
目前對NFT藝術價值的解讀囿于傳統思維模式對藝術價值的定性,將通過區塊鏈技術與NFT化實現的唯一性與本真性(Authenticity)視為與“原作”等同的概念,試圖用舊的框架概括新的藝術現象,導致陷入“原作”與“真跡”的迷思,進而墮入美學研究的范疇,無法正確對NFT藝術自身的價值進行厘定。“原作”更多是從創作者的視角對藝術的價值加以審定,將藝術家自身的創造力與社會地位作為藝術獨創性與價值的源頭。
藝術的價值指向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人類生存方式與活動方式的變化生成不同的價值。因此,價值作為一種意義式的存在,始終處于漂浮與滑動之中,NFT藝術的內在價值與數字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相一致。正如韓炳哲所說,“真跡不再是經由特殊身份而進行的一項特殊的創作活動,而是歷史性的變化中的生成性過程”(30)Byung-Chul Han,Shanzhai:Deconstruction in Chinese,trans. by Philippa Hurd,The MIT Press,2017,p.11.,歷史過程本身就已經為其賦予了應有的價值,不需要乞求于被歷史拋棄的作者主體。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區分了兩種不同的價值模式: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這兩種價值模式具有內在的歷史連續性與斷裂性。就膜拜價值而言,本雅明將對藝術品的膜拜歸之于附魅的世界,藝術在更多的時候充當一種中介與靈媒為巫術服務,發源于祭祀神靈。但是機械復制技術的來臨改變了藝術的生成邏輯與顯現方式,附魅的世界給予藝術的膜拜價值被無限復制的技術改變,即從膜拜價值轉變為展示價值。面對機械復制時代機械復制技術的發展,圖片充斥著人們的生活,進入海德格爾所說的圖像時代,機械復制導致圖像的增值,即德波所說的景觀社會,數字時代的超級復制特性使得擬像不斷增多,這些都是展示價值的具體表征。
通過機械復制批量化生產的藝術品指向普羅大眾,并對其進行展示;具有“超復制”特性的數字技術將大量同質化的藝術復制品向網絡世界撒播與展示。而技術與資本的勾連使得藝術品在顯現展示價值的同時,更突出交易價值,即從感性展示轉向資產占有。“藝術品在被展示出來的瞬間就失去了它們的祭禮價值(Cult Value) (筆者注:即本雅明的膜拜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展示價值(Value as Exhibition Pieces)”(31)Byung-Chul Han, Saving beauty, trans. by Daniel Steuer, Polity Press, 2018, p.144.,藝術品沒有屹立在節日慶典的大道旁,而是陳列在元宇宙中的數字博物館中,成為數字檔案,數字博物館成為藝術品的陳尸所,藝術喪失建構靈韻世界的能力。伴隨審美資本主義與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今天,藝術品主要在市場和交易所被買賣。它們既沒有祭禮價值,也沒有展示價值,正是這種純粹的被操控的價值使他們臣服在資本腳下。交易價值(Value as Object of Speculation)被證明是最高的價值”(32)Byung-Chul Han, Saving beauty, trans. by Daniel Steuer, Polity Press, 2018, p.145.,交易所就是當今的神廟,純粹的經濟收益取代了藝術本身的救贖價值。更進一步來說,雖然韓炳哲所說的更多的是存在于物理世界之中的物質可觸的藝術品,其交易價值通過拍賣行或交易所等線下中心化交易實現,但他準確判斷了向交易價值轉變的趨勢。
盡管藝術的交易可分為線上與線下兩種交易模式,但是都表明藝術的展示價值被交易價值取代。線上去中心化交易的實現依托于區塊鏈提供的技術保障,確證了NFT藝術的獨一無二,同時有西方學者指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是藝術領域新一代創新的催化劑,也是之前數字不良藝術界的轉折點”(33)③ Isabel Dominguez de Haro,How NFTs Are Driving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Art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in a Pandemic Age,2022-05-31,https://digitalcommons.sia.edu/stu_theses,訪問日期:2022-08-05.,疫情導致的物理空間中人與人、人與藝術之間的空間隔離促進了藝術交易的“數字化”趨勢。另外,NFT的初心是確證唯一性,“NFT經常被用作不同類型媒體的所有權證書……藝術品和收藏品之間的傳統藝術界區別有時似乎受到威脅”(34)③ Isabel Dominguez de Haro,How NFTs Are Driving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Art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in a Pandemic Age,2022-05-31,https://digitalcommons.sia.edu/stu_theses,訪問日期:2022-08-05.,即后來的發展走向相反的方向,NFT藝術的原真性、持有權證與藝術價值被遺忘,而貨幣通證與經濟價值則被凸顯,藝術品與收藏品之間的區分被打破,NFT藝術品由此既是一種可交易的商品,也是一種數字資本或數字資產。故而NFT技術的發展使得藝術不僅具有一種展示價值,而且通過確證其唯一性從而凸顯出NFT藝術的交易價值或貨幣價值。NFT充當虛擬契約,傳達數字資產的所有權。每一個藝術品都被上傳到一個數字分類賬號,在那里它跟蹤信息,如它被創建的日期,何時被出售,有多少和被誰擁有。這一過程中交易價值凸顯的不再是藝術本身的創造者,而是持有者,持有NFT藝術確定了其所有權或歸屬權。在交易價值中,對“誰是NFT藝術品的創作者”的回溯性追問,遠不及對“誰是NFT藝術品的歸屬者”的追問更能深入當下藝術品價值維度的思考。
通過整個交易鏈條,我們會發現關于具體NFT藝術品的交易信息都被記錄在稱為區塊鏈的數字分類賬上。通過交易獲得的既非實體的NFT藝術品本身,也非傳統意義上的有特定創作者制作的“原作”,NFT藝術僅僅具有所有權的確證,NFT藝術的背后是一串數據。NFT藝術作為數碼物,擁有者占有這些被加密的特殊數據。一方面,這些數據被獨自占有;另一方面,這些數據的視覺表現形式可以被元宇宙中的不同數字主體所共享,即展現出“數據占有”與“數據共享”之間的辯證。NFT藝術在催生交易價值的同時,并沒有摧毀展示價值存在的合法性,在元宇宙中的共享本質也是一種個人藏品的公共展示。
在“膜拜價值—展示價值—交易價值”的價值邏輯轉變中,復制技術與NFT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NFT藝術的生成邏輯與存在方式發生根本變化,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NFT藝術更多地體現出一種貨幣“交易價值”。膜拜價值是從神學或者歷史的維度進行思考,而展示價值則更多地強調一種美學與視覺主義,但是交易價值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直接將NFT藝術視為一種個人資產,這與布迪厄所說的趣味、社會階層緊密相關,與數字世界中的主體性建構緊密相關。
(二)社交價值:NFT藝術與數字主體
交易價值顯示出來的NFT藝術不是一種美學方面的審美性,本質屬于一種數字資本或數字資產,也可算作一種文化資本,暗示著社會趣味與結構的區隔。布迪厄在《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中揭示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主體審美趣味與社會身份之間的內在關聯(35)布爾迪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上),劉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57-358頁。,對特殊藝術品的創造、鑒賞、購買以及收藏等行為暗含著不同社會主體特定的價值追求與身份想象。NFT藝術的創造、購買或消費以及在特定領域中的應用等主體行為并非盲目的跟風或商業利益上的投機,也帶有社會主體自身對特定社會身份的認同。
首先,NFT藝術由于藝術家本身的特殊地位,自身呈現出一種特定的藝術或審美形式,審美形式與藝術家自身的社會趣味相勾連。最早的NFT藝術品“BAYC”“Cryptopunks”等與商業化炒作之后經過“NFT化”包裝的普通藝術品之間存在藝術形式上的差異。有學者指出, “審美形式取代政治形式而成為身份認同的主導形式,一直被視為是現代性歷史的標志性事件”(36)谷鵬飛:《審美形式的公共性與現代性的身份認同》,《學術月刊》2012年第4期。。“BAYC”等具有一定的獨創性,故而帶有創作者本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NFT藝術不僅僅意味著從“原子”到“比特”這一藝術存在方式的轉變,還意味著藝術家通過創意行為打造專屬個人品位的NFT藝術風格,并將這種特殊的藝術形式作為特殊的文化符號或文化資本,從而彰顯自身身份的獨特性與審美趣味的差異性。NFT藝術家以自己的藝術形式作為中介,不僅在物質世界中有意為自己謀求一定的社會地位,提升自身的社會聲望,也在數字世界或元宇宙中憑借獨特的審美形式建構起自身的數字主體性,為他者所認可與矚目。
其次,“天價”購買的背后除了商業層面的投機意向之外,對NFT藝術的購買或消費行為帶有消費主體明顯的社群價值意圖,即彰顯自身的社會品味。著名消費主義理論家蘭開斯特(Lancaster)曾指出,進入消費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主體屬于“消費人”,其對某件商品的購買與消費并非囿于基本的生存性需要,更多的是一種符號性消費,注重藝術符號背后承載的社會價值與意義。(37)Lancaster, K. J.,“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74,1966.從單純的交易方式層面來看,購買者通過高價購買到的是NFT藝術的持有權與一串在區塊鏈上被加密的特殊數據;但其實,購買行為、購買能力以及所購買的NFT藝術品形式具有深層次的文化意涵。對NFT藝術品的需求很多時候來自主體對社會地位、品味以及社會身份的蘄求,大多數通過“天價”進行交易的消費屬于一種“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人們爭取提高消費水準的動機是在于滿足競賽心理和‘歧視性對比’的要求,其目的不過是要在榮譽方面符合高人一等的生活習慣。”(38)凡勃倫:《有閑階級論》,蔡受百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Ⅺ頁。“如此看來,NFT購物歸根結底是關于身份和品味,而不僅僅是金錢”,主體通過購買著名藝術家的或者高價的藝術品,在獲得財富的同時獲得其他的社會身份與地位象征,彰顯出自己的藝術品位與高雅格調。整個購買行為在確證消費者社會品味的同時,也將原本平凡的NFT藝術品升入奢侈品行列,這表明“NFT可以給人們提供一些無法復制的東西”(39)Mitchell Clark,NFTs, Explained: What They Are, and Why They’re Suddenly Worth Millions, 2022-03-05,https://www.theverge.com/22310188/nft-explainer-what-is-blockchain-crypto-art-faq,訪問日期:2022-09-05.,消費NFT藝術獲得的那些無法復制的事物就是社會聲譽以及自我的精神滿足。
最后,對NFT藝術的購買與應用是兩個不同的維度,購買更多體現生活世界中的社會趣味與價值,而對NFT藝術的應用更注重在數字世界或元宇宙(Mateverse)中“數字身份”的凸顯,并建構自身的“數字主體”。在所有的NFT藝術中,NFT PFPs不僅最為出名且占據很大比例。NFT PFPs全稱為NFT Profile Pictures,譯作NFT像素風格頭像。PFPs指NFT頭像所有者在Opensea、Discord以及Twitter等互聯網平臺上使用的頭像,然而由于人們局限于對交易價值的關注,以及“對非功能性語言生態系統的整體結構和演變知之甚少,也不知道這種現象是如何由于社交網絡(如Twitter)中形成的社區而發展起來的”(40)Simone Casale-Brunet, Mirko Zichichi, etc., “The Impact of NFT Profile Pictures within Social Network Communities,”Proceedings of the 2022 ACM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2022,pp.283-291.,尚未清晰認識到頭像類NFT在數字世界與NFT社區中的社交價值。
NFT頭像通過建構獨特的數字身份,刻意制造高級文化認同,進而塑造數字主體與數字社群。在傳統藝術中,肖像畫可以明確地指代本人的社會身份與主體性地位,肖像與個體之間具有內在統一性;而在數字世界中,一般在各種社交媒體中都將主體自己的數字肖像作為社交賬號的頭像,但是NFT頭像通過獨特性與稀有性為數字景觀社會所公認,參與數字身份的塑造與建構。如果擁有一個NFT頭像,那就意味著進入了一個圈層、社區或者特殊的俱樂部,Cryptopunks與BAYC的加密NFT頭像已成為Web3社區的超強IP,持有某種特殊的頭像意味著就有了進入某個社區的“入場券”。這些頭像將代表擁有者的身份、階層與品味,頭像不再是頭像,它代表一種元宇宙中的數字身份,更可能代表一種生活方式、一個社群的共同愿景。譬如,BAYC的持有者將自己的社交媒體頭像換成自己所持的BAYC,基于這些頭像形成數字社交圈層。頭像NFT一方面通過稀有性確證頭像使用主體的獨異性,另一方面通過對象的特殊圖案被歸入特殊的群體,屬于一種身份認同。作為彰顯個人能力、地位與財富的“數字主體身份證”,帶給持有者的精神享受與榮耀感是其他NFT難以比擬的。
另外,NFT PFPs這種NFT藝術的特殊應用方式背后隱藏著社交價值,由此形成“NFT頭像—NFT社區—數字身份—數字主體”的邏輯關系。人不僅在物質性生活世界中渴望尋求他人的認可或承認,在數字世界中也同樣期望被他人承認與認可。NFT確證NFT藝術的獨一性,更凸顯NFT藝術擁有者自身在整個數字世界或者元宇宙中的地位。科耶夫在解讀黑格爾思想的作品時就曾說過,人類的存在就是一個不斷尋求承認的斗爭過程。對頭像類NFT藝術的競相購買顯現為經濟斗爭的形式,反映數字主體在元宇宙空間尋求他人承認并確證主體獨特性的重要手段。
(三)事件價值:網絡場與NFT藝術
“數字事件”(Digital Event)作為界定NFT藝術的新維度,突出NFT藝術的動態生成過程,批判主體主義與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NFT藝術生成所內含邏輯的整個歷史與社會語境完美地詮釋了“事件價值”的學理意義。
有學者指出,“從事件角度界定藝術,也就是要在規范性(Legislative)上,將藝術創作中的偶然與斷裂、流通展示過程的建構性、觀者的主動參與、藝術媒介與現實間的互動影響等因素納入‘事件’意涵,并論證由此衍生出的‘事件性’是藝術的一種內生屬性。”(41)陳漢:《當代藝術研究的“事件轉向”:議題改換與方法反思》,《浙江學刊》2021年第2期。NFT藝術作為事件性的存在,與技術、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歷史等緊密相關,處于由藝術家、觀眾、藝術市場、藝術體制以及藝術媒介、藝術監管系統、藝術交易與收藏、NFT平臺等各因素相互關聯的事件化網絡環境或元宇宙中。 “NFT藝術并不是一個具體的藝術門類,其創作、流通和交易被看作一種藝術行為的整體,在數字世界延續著杜尚精神”(42)解學芳、徐丹紅:《NFT藝術生態鏈拓展與數字治理:基于參與式藝術視角》,《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體現為一種“事件價值”。
一方面,作為“數字事件”的NFT藝術的創造是一種集體互動、參與式創造,而非單一作者的精神產物,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將相互交流的人緊密聯系在一起”(43)Sybille Kramer, Medium, Messenger,Transmission: An Approach to Media Philosophy, trans.by Anthony Enns ,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2.。博伊斯曾說在數字時代“人人皆為藝術家”,NFT藝術實踐的發展確如其言。在NFT藝術的創作中,創作者建基于技術提供的數字平臺與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藝術創作的發起者按照數字技術的內在邏輯以分包的方式吸引參與者進入藝術創作,平臺、發起者以及參與者集體完成藝術品的創作。NFT藝術品的誕生具有很強的參與性與互動性,是集體參與創作的產物。克萊爾·畢曉普將這種參與式藝術的創作過程描述為:“藝術家不再是某一物件的唯一生產者,而是情境的合作者和策劃者……觀眾從‘觀看者’或‘旁觀者’轉變為合作者和參與者”(44)Claire Bishop, Artificial Hells: Pa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London:Verso,2012,p.11.,觀眾被納入藝術行為中成為藝術創造者。每個參與者都擁有一個虛擬“數字身份”,憑借數字身份獲得藝術創作參與權。譬如,由加拿大區塊鏈項目推出的名為“重建巴別塔”的NFT藝術創作活動,吸引了全球參與者共同在去中心化的區塊鏈社區,以挖礦游戲的方式獲得相關的NFT拼圖。通過集體參與共同完成各種不確定的藝術作品,創作者、合作者以及參與者三位一體的創作標志著“事件的理解藝術”,每一件NFT藝術品成為當代藝術家諾亞·戴維斯(Noah Davis)所說的“一種在Instagram上展示的杜尚式的現成品”(45)Beeple’s opus,www.christies.com.cn/features/Monumental-collage-by-Beeple-is-first-purely-digital-artwork-NFT-to-come-to-auction-11510-7.aspx?sc_lang=en,訪問日期:2022-04-05.。
另一方面,作為“數字事件”的NFT藝術的交易與流通是一種去中心化、動態的過程。NFT藝術作為數字藝術,首先存在于數字技術與NFT區塊鏈無中心的數字世界或元宇宙中,與物質可觸且存在于物質世界中的藝術品在存在方式上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廣泛表現在生產、流通及交易過程中。NFT藝術品的交易與流通打破了傳統上被畫廊、美術館以及拍賣行壟斷的、中心化的交易與流通模式,NFT藝術使得藝術流通實現了點對點的流通和交易,并且NFT藝術從創作到交易流通的全部過程均被記錄在區塊鏈上,這種記錄本身成為藝術創作過程的一個部分。作為參與式藝術的NFT藝術,除了以這種過程記錄的方式吸引和接納大量參與者,還通過區塊鏈確證本真性與稀缺型的過程使參與者參與到藝術品的占有與共享中來。
創作、欣賞、交易、流通以及藝術過程的監管都聚集在“網絡場”中。“傳統藝術作用于形式層面,而當代藝術則作用于語境、框架、背景或新的理論闡釋層面。”(46)鮑里斯·格洛伊斯:《藝術力》,杜可柯、胡新宇譯,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42頁。NFT藝術的這種高度參與性打破了傳統單一、靜止的藝術形式,擺脫了靜觀式的對藝術的“審美”層面的研究,進而從“事件”維度對“何為藝術”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解決范式,同時相互關聯的諸行動者(Actant)擺脫了種種藝術體制與交易體制的隱性限制。從技術與藝術之間關系的探討入手,最后通過人類的活動實踐將NFT藝術作為一個建基于數字技術基礎上的行動者網絡事件,作為數碼物的NFT藝術從“數字事件”的維度重構了“何為藝術”這一經典命題。從“事件”角度對NFT藝術的闡釋旨在破除以前本質主義的定義模式,不再從固定的概念出發去解釋藝術實踐,而是用描述性的語言直接展示藝術的動態生成過程以及存在方式。
四、余論:作為元宇宙前奏的NFT藝術
NFT藝術作為數字藝術的一個特殊類型,由于其對持有者所有權的確證以及各種NFT藝術品 “天價”交易的情況,NFT藝術在最初的階段經常被人們認為是消費資本主義與數字技術之間的一場陰謀。但是在最近短短兩年的時間里,NFT藝術的成交量與購買人數逐漸回落,逐漸擺脫被資本裹挾的迅猛勢態。這種情狀使我們可以理性地分析NFT藝術自身所含有的藝術價值,在NFT藝術與主體感知、觀念以及情感等之間建立起相應的聯系,不再僅僅將NFT藝術視為一種簡單的數字資產與數字世界中的奇特景觀。
當下人類的生存模式體現為尼葛洛龐蒂所說的“數字化生存”,生活在通過技術“聚集”建構起來的世界之中,NFT藝術將成為人類未來生存方式的藝術表征。在現實的物質世界中,一方面,新冠疫情隔斷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流,造成主體間的橫向區隔;另一方面,階層、社會地位以及文化資本等的差異造成主體間的縱向區隔。數字世界成為人與人進行交往的重要場域,NFT藝術帶有一定的前衛性,賦予每一個數字世界中的成員獨特的身份,并建構合理的主體間性,通過對同一個NFT藝術品的鑒賞,重塑主體的審美經驗、審美感知與審美配置,通過在數字世界中藝術資源的共享及“可感性分配”實現數字主體個人的自由與解放。
同時,在數字世界之中“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愿望得以實現,可以自由表達個人的藝術理想,經由NFT藝術建構一個數字烏托邦,打破了物理世界中的區隔與階層鴻溝,每一個數字主體都可以參與到藝術的創作、消費以及欣賞之中,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通,使得數字世界成為一個理想性的審美世界或審美共同體(47)Manuel Castells,“Internet:Utopia,Dystopia,and Scholarly Research,”in Mark Graham and William Dutton,eds.,Sociology and the Internet:How Network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Changing Our Liv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 Ⅶ-Ⅸ.,指向對美與善的價值追求,推動這個社會的變革,進而實現現實社會中主體間的親密交往。
盡管NFT藝術作為元宇宙的一個前奏已經成為現實,但是NFT藝術依舊尚未擺脫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更多的持有者將其作為自身在元宇宙或數字世界之中的身份與符號資本,究竟未來的元宇宙是一個主體間平等、和諧共存的世界,還是NFT藝術會進一步造成元宇宙內部數字主體間的區隔與分裂,這是一個尚未得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