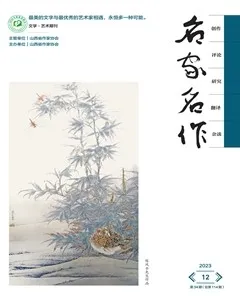《櫻桃園》中錯位的自我與時間
——談契訶夫筆下的“多余人”
喬紫菲
別林斯基在談到“多余人”這一形象時,提出:“這些人常常被賦予了偉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道德品質(zhì),他們本可以大展其才,但卻鮮有作為,或根本無所事事……”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他們彷徨在兩個階級之間,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流浪者身份,因而以否定當(dāng)下的方式,渴望一個安穩(wěn)的立足之地。契訶夫以“多余人”對時間的逃避入手,融合俄國文學(xué)的獨特文化氣質(zhì),剖析他們優(yōu)雅外表下精神的風(fēng)暴和生存處境的狹小。在錯亂的時間觀念下,“多余人”將自我鎖在過去的回憶中,造成面對現(xiàn)實的自我的缺位,從而當(dāng)現(xiàn)實問題入侵時,出現(xiàn)人格錯位和精神失控;圣愚文化傳統(tǒng)賦予俄國文學(xué)的非理性傾向的特殊氣質(zhì),在多余人身上凝結(jié)成一種對世俗秩序的否定,揭示其群體性的否定氣質(zhì)和漂泊性的生存狀態(tài)。然而契訶夫仍舊秉持著對個體獨立價值的張揚和游戲精神的推崇,試圖給予這群四處碰壁的人一次選擇的機會,消弭對時代更替本身的價值判斷,完成關(guān)于時間、現(xiàn)實和喜劇的更深入的現(xiàn)代性思考。
一、時間錯位下的精神病狀態(tài)與返童行為
人與時間的沖突是契訶夫戲劇中永恒的話題,劇中的“多余人”無力應(yīng)對時代的極速變革,能動性極弱的他們只能將自我埋藏在過去的回憶中,將回到櫻桃園視為回到過去的生存空間里。然而人的意志無法控制生活的實際進程,應(yīng)對現(xiàn)實的自我的缺位造成客觀世界的人格呈現(xiàn)的不穩(wěn)定性,從而出現(xiàn)一系列的精神失常,主要表現(xiàn)為自我意識障礙和返童行為。
劇中人對時間的流逝非常敏感,他們一點點感受著時間對他們所剩不多的安逸的吞噬,而后陷入自我意識障礙。《櫻桃園》中的柳波夫遭遇了喪子喪夫的痛苦,流轉(zhuǎn)于巴黎和俄國之間,俄國對她而言是可以逃避巴黎痛苦“現(xiàn)實”的“過去”。她想躲在美好的田園牧歌里,然而來自巴黎的電報比她還先到達,她到達之時櫻桃園已經(jīng)面臨不可挽回的破滅。她迫不及待地投入回憶里的內(nèi)心世界:“我可愛的、美麗的育兒室……現(xiàn)在,我也還像個小孩子……”現(xiàn)實卻時刻提醒著她這份期待的破碎:陸伯興傳來櫻桃園將被拍賣的噩耗,劇中人物頻繁的報時提醒她痛苦時刻的逼近。“太陽落下去了”“月亮升起來了”……時空觀念的錯亂讓她不知道自己該屬于哪種人格,她充沛的情感應(yīng)激性地紊亂,本能地去保護讓自我更舒適的精神世界,于是拋下了優(yōu)雅的社交形象,造成現(xiàn)實人格精神的失控。在收到巴黎寄來的電報時,在柳波夫的心理世界中,過去與現(xiàn)實交織,她做出了“撕碎電報”的戲劇動作,而后又回到“我聽著遠處好像有音樂吧”的話題,這個音樂性看似是將她帶回來現(xiàn)實時空,實際上是將現(xiàn)在時空的物理真實性再一次抽離,回到了她這段一開始的狀態(tài)“我總是像瘋子一樣的”,她的精神再一次飛走了。[1]她的情緒大起大落,上一秒還是“多么可愛的花園啊”,下一秒便可以“輕聲啜泣”;當(dāng)彼楷提醒柳波夫櫻桃園必然會被拍賣時,柳波夫開始在過去與現(xiàn)實的時間中自我掙扎,她瘋狂地攻擊彼楷,好像這樣就能擊退殘酷的命運,“您簡直是個怪物”“不成器的東西罷了”。這過激的言行無論與她優(yōu)雅矜持的身份還是天真多情的內(nèi)心都有極大的反差,柳波夫在錯亂的時間觀中也迷失了自我人格的歸屬。
“多余人”沒有奮斗的概念,這份成長的缺席讓他們活在空想的羅曼蒂克里,飽經(jīng)挫折又無法克服內(nèi)心與現(xiàn)實的沖突,于是他們將自我封閉在最自在的童年狀態(tài)里,出現(xiàn)一系列返童行為。柳波夫用逃避來延續(xù)對未來的期待,然而“她所逃避的每一段過去都讓她的現(xiàn)在變成了痛苦的折磨,而她所逃避的每一個當(dāng)下又都變成了痛苦的過去”[2]。在對自我的本能保護機制下,她用孩子的心理來遮擋痛苦的風(fēng)暴,她的一舉一動像極了少女——“(以手掩面)我好像在做夢吶!”“瞧,去世了的母親在花園里來回溜達呢!”而對于加耶夫而言,他的返童行為透露著一種宿命性的可悲,穿衣服都要別人照顧的巨嬰?yún)s總突然開啟理想和浪漫的演講,即使什么都不做還會沾沾自喜。家族身處困境,身為男人的他仍然活在溫室的幻夢里拒絕成長,由此可以看出契訶夫?qū)λ钌畹氖蛯@類人必然滅亡的預(yù)見。
對話的無效化是返童行為最多的體現(xiàn)。安涅和董涅莎相見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自說自話;柳波夫只能聽到“賣花園”卻自動忽視“還債”的問題;加耶夫總幻想著可以依賴別人天降橫財;柳波夫即使已經(jīng)沒錢了還借錢給別人……不止一次有人說過櫻桃園是必然會被賣掉的,但他們無法取舍,就像孩童一樣將問題甩開,期待被大人拯救。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自欺與放棄行動的方式來對抗這種無能為力感,然而時間并不會因為人物行動的停滯而停滯,困在過去的“多余人”在向前流動的時間中必然會如逃犯般心驚膽戰(zhàn),最后被無情擊斃。
二、俄國圣愚文化下“多余人”群體的否定性氣質(zhì)
王志耕教授的《圣愚之維:俄羅斯文學(xué)經(jīng)典的一種文化闡釋》一書中認(rèn)為,圣愚傳統(tǒng)框架下的俄羅斯文學(xué)以其非理性傾向?qū)硇灾髁x加以否定和制衡。這種否定的力量在多余人身上體現(xiàn)為對世俗秩序的否定。[3]盡管“多余人”身上缺失了圣愚文化中苦難與信仰相通的肯定性精神,但圣愚文化中,生命的意義往往以逃離、漂泊和對世俗秩序的破壞的形式存在,這與多余人的生存理念相切合,這種生命的存在形式塑造了俄國文學(xué)中多余人抗拒與瘋癲的否定性氣質(zhì)。
契訶夫筆下多余人的抗拒行為往往是以理想而非理性的防御機制否認(rèn)客觀的秩序,以一種叛逃乃至狂歡的形式來否定真實的、世俗的世界。“多余人”貪戀短暫的安全感,也對這份感覺高度敏感,當(dāng)來自外界的壓力試圖入侵時,便會無意識地開啟防御姿態(tài)。櫻桃園的衰亡觸發(fā)了他們無意識中的否認(rèn)機制,他們盡力縫補起每一個話語的空隙,隨便什么都要拿來消遣,維持世家大族的熱鬧體面。陸伯興說完“櫻桃園和別的地產(chǎn),可全都要拍賣了”,柳波夫不愿面對,就馬上將注意力轉(zhuǎn)移到干櫻桃的秘方上;劇中的多處停頓已成為整部劇的特色所在,在現(xiàn)實的重壓下,無聊的話題無法進行,所以在短暫的停頓里尋找新的話題支點來否認(rèn)危在旦夕的現(xiàn)實,每一步停頓都承擔(dān)著被殘酷現(xiàn)實乘虛而入的風(fēng)險。然而任何否認(rèn)都說明了拒不承認(rèn),他們在自我的意識域中接受衰落的莊園,又在無意識域中守護理想化的信念。圣愚文學(xué)中對苦難的焦慮書寫,在“多余人”群體身上體現(xiàn)為對殘酷現(xiàn)實的無力感與一次次的出逃失敗,將這類人對世俗秩序的否定態(tài)度具象化的同時昭示“多余人”生存處境的狹窄。
圣愚形象在俄國文學(xué)中常常被賦予狂歡化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多余人”身上體現(xiàn)為幻想特質(zhì)的徹底解放和抗拒態(tài)度的頂點宣泄。他們自戀,認(rèn)為自己可以靠閃爍的人格魅力獲得拯救,用空洞的最佳期待回擊尖銳的現(xiàn)實問題。當(dāng)莊園的毀滅越來越勢不可當(dāng)時,他們則辦起了狂歡的舞會,用最莊園化的儀式來發(fā)泄內(nèi)心的欲望,在結(jié)局到來之前徹底麻醉自我。因為每一分一秒都過得不安,所以汲取更濃厚的貴族痕跡作為幻想的依托,以稀釋濃烈的危機感。以漂泊和苦修來堅定精神追求的圣愚精神,在“多余人”身上呈現(xiàn)為如小丑一般掙扎于現(xiàn)實時空卻陶醉于幻想世界,凝結(jié)成一出“丟棄船槳漂泊于幻想世界而無法停泊歸靠”的悲劇。
瘋癲是對理性主義的一種直接棄絕的表現(xiàn),契訶夫以他者視角描寫“多余人”與社會文明的悖論,又以瘋癲的“多余人”的視角刻畫他們在棄絕中的成長演變之路,完成了圣愚精神關(guān)于在否定中探索自我、在否定中超越自我的精神品格詮釋。旁人視角下的加耶夫說話像烏鴉一樣吵鬧,是像小丑一樣供人取樂。柳波夫固執(zhí)地維持著早不屬于她的浪漫天真,活在貴族時間里的她逐步放棄了在現(xiàn)實時間里的話語權(quán)。“多余人”與社會秩序的悖論,是對所處的現(xiàn)實生存空間的一種無力的否定,一旦被認(rèn)定為瘋癲,他們的話語權(quán)就被剝奪了,這等于將他們永久地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成為被忽視和遺忘的對象。
而在瘋癲人物的視角下,無法理解的社會秩序正在慢慢適應(yīng)自身,個體的尊嚴(yán)和價值在成長中正在慢慢回歸,他們在與世俗的相互否定中完成了生命意義的探尋。加耶夫被大家討厭,高呼著陳詞濫調(diào),但始終想辦法籌錢,最后在社會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處;柳波夫是情感上的巨人,但在最后慢慢回歸理性來接受現(xiàn)實;安涅從高呼著美好的世界到最后真正踏上新世界的道路……瘋癲的存在的意義不在于瘋癲本身,而在于為什么會有瘋癲,瘋癲給人們帶來了什么問題。在這一層面上,契訶夫不拘泥于對“多余人”與圣愚文化中生命存在的外在形式聯(lián)系起來,而是統(tǒng)領(lǐng)人物完成了與圣愚文化里超越的精神品格和永恒的生命價值的內(nèi)在融合,以對理性社會秩序的否定,獲得“多余人”群體超越性的成長意義。
三、契訶夫殘酷精神下的喜劇期待
契訶夫毫不掩飾地刻畫出他眼中“多余人”的脆弱和病態(tài),然而他站在社會、世紀(jì)之交,看著麻木迷茫的青年人無法對自己的良知撒謊:失智的“多余人”是否活該淪為犧牲品?資本主義的暴政是否借了貴族的消亡來掩蓋?殘酷的現(xiàn)實囚禁了“多余人”的出路,契訶夫選擇用他所擅長的喜劇精神給予這群被裹挾的人一次選擇的權(quán)利。
“個人意識形態(tài)對霸權(quán)主義意識形態(tài)不畏懼、不迎合、不巴結(jié)、不屈服,而是報以輕蔑,立志顛覆之、解構(gòu)之,使其變得荒謬可笑。這種精神便接近了喜劇精神的境界。”[4]契訶夫在劇中引導(dǎo)性地讓“多余人”尋找自己的個體獨立價值。盡管契訶夫冷酷的筆觸下展現(xiàn)了“多余人”在非理性命運中的掙扎,但人物命運的荒誕都來自他們無法割舍掉生活本身的悖論,而并非自我能力的低下和人性的扭曲,甚至他們總是善良和天真的。契訶夫鼓勵每個主體都看護好自己的個人價值,甚至殘忍地將他們踢出荒誕的幻夢都可以視為是對其個體價值有效性的保護。觀眾心理預(yù)期里會發(fā)生的巨大的不幸并沒有發(fā)生,老人卸下負擔(dān)死去,青年的悲傷很短暫,來自資本社會的對他們毀滅性的打擊并沒有降臨,時間依舊向未來走去,契訶夫沒有讓柳波夫一行拜倒在資產(chǎn)階級的足下,而是給予他們一次平等的選擇現(xiàn)實的機會。“多余人”最后仍舊保持著的內(nèi)在優(yōu)越感,實際是在精神上擺脫了環(huán)境的束縛——即使不生存在幻想的烏托邦,也仍舊認(rèn)同自我的價值,使試圖創(chuàng)傷自己的時代顯得滑稽可笑,這是契訶夫送給“多余人”的喜劇禮物。
喜劇精神的另一個特點是崇尚快意的游戲化的生存狀態(tài)。“游戲精神是一種鼓勵生命力自由揮灑、自發(fā)創(chuàng)造的精神,為生活增加喜劇色彩直至將生活藝術(shù)化。”[5]在莊園易主這件事上,人物所做的決定全憑自我感受,不顧及理性思考,只在意當(dāng)下喜憂,哪怕經(jīng)歷了守舊時代的掙扎和疲憊的精神內(nèi)耗后,他們也只是在“離開—歸來—離開”的圓形結(jié)構(gòu)里回到起點。他們一腔激情地到處“惹禍”,卻不用承受過多代價,反而在體驗過生活的風(fēng)暴后成長了不少,仿佛人生是一場“萬般皆備于我”的游戲。柳波夫可以如釋重負地接受櫻桃園易主的現(xiàn)實,感性的情感與冷靜的現(xiàn)實得到了平衡;費爾司臨死前還在惦記加耶夫的冷暖,卻不知加耶夫已經(jīng)學(xué)會自己穿上外套。他們的生活跌宕起伏,卻又蕩漾著哲理的回味,他們夾在時代變革的縫隙里,但他們的身上卻被契訶夫賦予了未來屬性,不在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中沉淪,而是擁有快意地向前走的機會。
契訶夫清醒地認(rèn)識到每個時代必然會面臨美好珍貴的曾經(jīng)與歷史前進的必然之間的悖論,他想要讓我們每一代人透徹地認(rèn)識生活的全貌。得到莊園的陸伯興放肆地狂喜:“(譏諷的)新的地主,櫻桃園的領(lǐng)主來啦!(無意中碰了一只茶幾,差點沒把燭架弄翻)什么我都賠得起!”他全然忘記里往日對櫻桃園的敬重、對柳波夫的愛戴,內(nèi)心壓抑的“庸俗的自我”暴露無遺;而柳波夫一行人,在錯亂的時間和精神中飽受煎熬,卻已經(jīng)整裝待發(fā)奔向新生活。新世界的誕生必然會以母體的撕裂為代價,新的罌粟園未必不會被其他花園所摧毀,陸伯興也未必不會成為下一代的“多余人”。但離開的“多余人”未必會是永遠的“多余人”,他們擁有了重新選擇的權(quán)利。契訶夫拒絕對時代更替本身做出價值判斷,工業(yè)社會的飛速發(fā)展無法掩蓋資本的罪惡,貴族階級的庸俗麻木也無法否定人本身的獨立價值。蘇珊·朗格曾經(jīng)斷言: “除了悲劇,是沒有永久的失敗,也沒有人類永久的勝利的。因為只要生命在行進,自然肯定就會發(fā)展。”[6]這句話是對契訶夫喜劇精神的終極詮釋:永恒的生活無法守護,但改變的機會永遠存在。
四、結(jié)語
《櫻桃園》里“多余人”與時間的矛盾成就了其“內(nèi)在戲劇性”,在湍急的外部時間和凝固的心理時間的相悖下,人與人的外部沖突被消解,環(huán)境所產(chǎn)生的壓力造成人的自我失格和精神創(chuàng)傷。契訶夫殘酷的客觀性讓他跳出感性的視野觀察世界,新時代必然會刺傷來自舊時間維度的“他者”,然而新時代也無可避免地刻有無力和罪惡的烙印。契訶夫始終保持著一種距離感來洞察最深刻的問題,他冷靜地剖析著“過去”與“現(xiàn)在”在“多余人”精神里兩敗俱傷的場面,描繪了個人面對時空的渺小,然而他所加入的關(guān)于“未來”的書寫則消解了悲劇的意蘊,勝者和敗者都淪為綿延時空里的玩笑、游戲。契訶夫在人與時間的悖論下審視著,卻不刻意批評判斷,他認(rèn)識到時代交替不過是最自然的事情,每次時代碰撞下都會有個體被困在精神牢籠,但在良知與責(zé)任感的驅(qū)使下,他將有未來屬性的喜劇精神送給夾縫中生存的“多余人”,若愿意重新選擇則是實現(xiàn)個體獨立價值的機會,若仍舊庸俗無為也不過是漫漫時間里的玩笑。在生命的末期,契訶夫借《櫻桃園》完成了對現(xiàn)代喜劇的探索,于世紀(jì)之交對人類生存與時間進行了最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