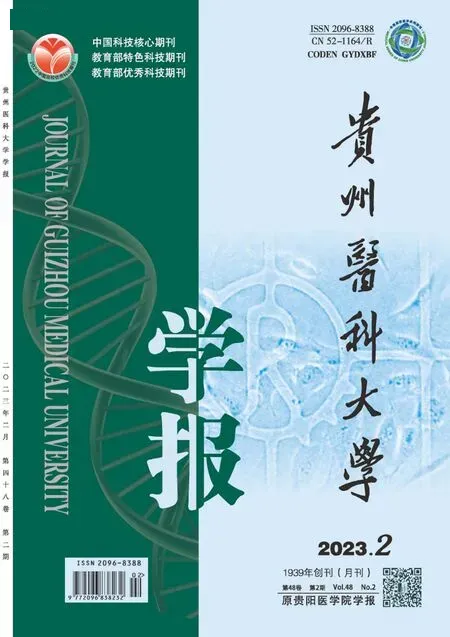血清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類抗原19-9水平對Ⅲ期結直腸癌復發或轉移的預測價值*
苑琴,強黎明,秦金玉
(四川大學華西廣安醫院 消化內科,四川 廣安 638000)
結直腸癌(carcinoma of colon and rectum,CRC)是消化道惡性腫瘤,表現為便血、腹瀉、腹瀉及腹痛等癥狀[1],CRC在我國的發病率、病死率在全部惡性腫瘤中分別位居第3位和第5位[2]。TNM分期是CRC分期體系,Ⅰ期CRC術后5年生存率在90%以上,Ⅱ期5年生存率為60%~80%,Ⅲ期5年生存率為30%~60%[3]。Ⅲ期CRC患者主要行根治術治療,但部分患者術后可出現復發或轉移,早期發現CRC復發轉移、并及時切除病灶對改善患者預后至關重要。目前血清腫瘤標志物在腫瘤診斷中已獲得認可,其中的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及糖類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均屬于CRC診斷和預后判斷的參考指標。AFP是肝細胞中糖蛋白一類,可促進肝細胞增殖,能夠反映疾病程度和治療效果標[4];CEA是消化道惡性腫瘤的腫瘤標志物,具有輔助腫瘤細胞聚集、黏附、侵襲及轉移的特性。有研究發現,當血清CEA>15 mg/L時會增加CRC遠處轉移風險[5];CA19-9是黏蛋白型的糖類蛋白,能促進腫瘤細胞粘附到血管內皮細胞,常用于CRC診斷[6]。本研究對Ⅲ期CRC患者術后隨訪1年,分析CRC復發轉移與患者病理特征的關系、分析CRC術后復發的危險因素,探討血清AFP、CEA、CA19-9水平對Ⅲ期CRC患者術后復發或轉移的預測價值,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1月—2020年1月100例采用根治術治療的Ⅲ期CRC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符合文獻[7]中CRC的診斷標準(腹痛、便血、腹部包塊、腸梗阻,伴或不伴貧血、發熱及消瘦、指檢可觸及腫塊,X線顯示鋇劑充盈缺損、腸腔狹窄及黏膜破壞征象,經腸鏡活檢及病理學確診);(2)年齡25~75歲、術后TNM臨床病理分期為Ⅲ期;(3)術前經影像學檢查排除肝轉移、肺轉移及其他遠處轉移者;(4)患者或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1)合并心、肺、腎等臟器功能不全者(通過臟器功能檢查評估);(2)合并其他惡性腫瘤者;(3)依從性欠佳者。所有患者均采用門診、電話等方式隨訪1年并記錄復發轉移情況,根據有無復發轉移分為復發轉移組(n=16)和無復發轉移組(n=84)。
1.2 觀察指標
1.2.1一般資料收集 收集2組患者年齡、性別,腫瘤組織學類型、部位、直徑、分化程度、浸潤深度、侵犯部位,腸梗阻和穿孔、術后輔助化療。
1.2.2血清AFP、CEA、CA19-9水平檢測 2組患者均于入院后第1 天采集空腹靜脈血5 mL,3 000 r/min離心10 min,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測定血清AFP、CEA、CA19-9水平。
1.2.3危險因素及預測價值分析 采用logistic分析影響Ⅲ期CRC復發轉移的因素,采用ROC曲線下面積(AUC)分析其水平對Ⅲ期CRC術后復發轉移的預測價值,采用 pearson分析Ⅲ期CRC術后復發轉移患者血清AFP水平與血清CEA、CA19-9水平的相關性。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特征及血清AFP、CEA、CA19-9水平
結果顯示,復發轉移組患者入院第1天的血清AFP、CEA、CA19-9高于未復發轉移組,分化程度低于未復發轉移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組患者年齡、性別,腫瘤組織學類型、大體類型、部位、直徑、浸潤深度、脈管侵犯、神經侵犯,腸梗阻、腸穿孔及術后輔助化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行根治術治療的Ⅲ期CRC患者一般臨床特征及血清AFP、CEA、CA19-9水平Tab.1 Gener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AFP,CEA,CA 19-9 levels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radical surgery for stage Ⅲ CRC
2.2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將表1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P<0.05)的影響因素進行賦值,賦值見表2。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分化程度及AFP、CEA、CA19-9水平是Ⅲ期CRC復發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2 Ⅲ期CRC復發轉移的影響因素賦值Tab.2 Value of factors affecting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stage Ⅲ CRC

表3 Ⅲ期CRC復發轉移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stage Ⅲ CRC
2.3 血清AFP、CEA、CA19-9水平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的ROC曲線分析
ROC曲線分析顯示,血清AFP、CEA、CA19-9水平聯合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的敏感度為96.40%,AUC為0.906,均高于上述指標的單獨檢測(P<0.05)。見表4和圖1。

圖1 血清AFP、CEA、CA19-9水平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的ROC曲線Fig.1 ROC curves of serum AFP,CEA,and CA19-9 levels to predict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stage Ⅲ CRC

表4 血清AFP、CEA、CA19- 9水平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的ROC曲線分析Tab.4 ROC curve analysis of serum AFP,CEA,and CA19-9 levels to predict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stage Ⅲ CRC
2.4 血清AFP水平與CEA、CA19-9水平的相關性
pearson分析顯示,血清AFP與CEA、CA19-9水平呈正相關(r=0.834、0.868,P<0.001)。見圖2。

圖2 血清AFP水平與CEA、CA19-9水平的相關性Fig.2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AFP levels and CEA,CA19-9 levels
3 討論
手術是目前治療CRC的重要手段,但術后有30%~50%患者出現復發轉移,從而增加患者的病死率[8]。據報道顯示,CRC患者5年生存率為56%,而肝轉移的CRC患者5年生存率下降為30%[9]。因此早期預測CRC復發轉移對降低死亡率至關重要。
腫瘤標志物作為特異性存在,與腫瘤發生、發展密切相關[10]。其是由腫瘤細胞產生或由非腫瘤細胞經腫瘤細胞誘導產生,存在于患者組織、血液及分泌物中,能反映腫瘤發生、發展,并用于檢測治療效果和判斷患者預后[11]。AFP、CEA、CA19-9為臨床常用的腫瘤標志物,其中AFP是由肝細胞合成的糖蛋白,肝細胞受損時控制AFP合成的基因被激活,在肝細胞內大量合成,可反映肝細胞受損程度,其水平上升提示腫瘤復發,但對于轉移性腫瘤,其表達可低于檢測閾值,因此需結合其他診斷[12-13]。CEA是可溶性多糖復合蛋白質,可存在于癌腫細胞表面,可促進細胞聚集,與腫瘤細胞黏附、凋亡及免疫密切相關,被認為是消化道腫瘤標志物[14]。有研究顯示,CEA可阻止腫瘤細胞凋亡,并抑制細胞分化,保持腫瘤細胞的干性能力[15]。CA19-9是黏液性糖蛋白,在胰腺癌、CRC、胃癌等患者血清中升高,可抑制T細胞增殖,并參與腫瘤的局部浸潤和轉移[16]。有報道顯示,CA19-9能促進腫瘤細胞黏附到血管內皮細胞,還與可誘導血小板聚集[17]。本研究結果顯示,復發轉移組AFP、CEA、CA19-9高于未復發轉移組,與林雪丹等[18]研究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為:術后復發轉移患者腫瘤細胞可持續發育,如此機制下促使血清AFP、CEA、CA19-9水平升高。且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顯示,血清AFP、CEA、CA19-9水平為Ⅲ期CRC復發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進一步證實了血清AFP、CEA、CA19-9水平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臨床應對其水平進行監測,并進行針對性干預,以期降低CRC患者病死率,延長生存期。同時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也顯示,分化程度為Ⅲ期CRC復發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與國外[19]報道一致,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原因可能為:分化程度低的患者惡性程度越高,手術時區域淋巴結已出現轉移,因此術后易復發轉移[20]。ROC曲線將靈敏度與特異性以圖示法結合,可準確反映特異性和敏感性關系。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分析血清AFP、CEA、CA19-9水平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的效能,ROC曲線分析顯示,血清AFP、CEA、CA19-9水平聯合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的敏感度為96.40%,AUC為0.906,均高于上述指標的單獨檢測,說明血清AFP、CEA、CA19-9水平聯合檢測可預測Ⅲ期CRC復發轉移。此外,本研究分析血清AFP水平與CEA、CA19-9水平的關系,pearson分析顯示,血清AFP水平與CEA、CA19-9水平呈正相關性,提示血清AFP水平與CEA、CA19-9水平具有相關性,血清CEA、CA19-9水平隨AFP升高而升高,由于本研究納入例數較少,下一步將擴大樣本量進一步論證血清AFP水平與CEA、CA19-9水平的關系。
綜上所述,血清AFP、CEA、CA19-9水平聯合對Ⅲ期CRC復發轉移具有預測價值,值得臨床推廣應用,且血清AFP水平與CEA、CA19-9水平具有相關性,臨床監測其水平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