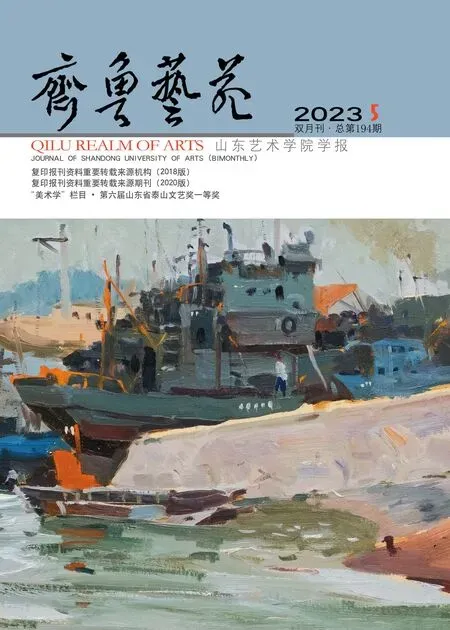被忽略的影像虛擬與現實存在間的對位邏輯
——論留守兒童影像的群體性錯位現象
于 昊
(聊城大學傳媒技術學院,山東 聊城 252000)
留守兒童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一類群體,我們通過對其現實境遇的認定,以及現實與影像中留守兒童形象的對照,能夠發現兩者間的差異性。“‘影像’是一個知覺心理學詞匯,某物的影像就是它的精神復制品, 影像是認知與現實的關聯。”[1](P37)留守兒童形象不僅僅是導演對現實存在的摹仿,而是導演對現實和影像的主體性重塑,并通過受眾的接受過程生產其意義的影像符號。 同時,“敘事不僅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動,某人在某個場合出于某種目的對某人講一個故事”[2](P14)。問題在于,并非所有導演都具備留守兒童群體的切身性經驗,他們感知經驗的形成多依賴于現實生活中的刻板印象。 這就導致一批導演在留守兒童形象塑造層面,表現出對其群體現實狀況較為一致的錯位遮蔽及失真現象。
電影是導演將其在日常生活中所積累的經驗,運用視聽語言手段“還原”于影像畫面中的倫理活動。 銀幕上所“還原”的留守兒童形象、場景等是導演的心理意象,是存在于其主體意識中的“印象”,而且會隨著主體意識層面上想象的浮動而相應發生變化。 然而對于觀眾而言,則沒有這么復雜,電影是僅作為其單純的體驗對象存在。 “不論商業動機和美學要求是什么,電影的主要魅力和社會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屬于意識形態的;在避開日常生活的逃避主義的消遣的幌子下,電影實際在協助公眾去界定迅速演變的社會現實,并找到它的意義。”[3](P1)觀眾在電影中所觀察到的一切,不僅是創作主體意識層面的人物形象或事件,也是創作主體有意識“還原”后的產物,即“將日常生活經驗中所見的‘現實’‘還原’為主體意識當中的‘現象’”[4]。 導演在塑造人物形象過程中的主體性是難以抹除的,幾乎所有在電影中出現的元素都為其敘事目的服務。留守兒童形象作為影像敘事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哪些人物特征可以讓觀眾看到,哪些人物信息又是模糊不清的或曖昧的,又突出了哪些信息,均展現出導演的主體意識以及情感取向。 導演對于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包含了其意識層面上“留守兒童現象”的主觀投射,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導致現實與影像的錯位。 電影中的情節編排、敘述活動等都是虛構的,不存在真實的可能,但這些內容生發的藝術效果,卻成功將它的虛構性予以遮蔽,觀眾也因其內容迎合了心理預設而接受認可。 因此,對電影中的留守兒童形象塑造進行真實性辨析,成為揭示導演深藏于影像敘事背后的創作動機、心理意象的有效手段。
“留守”作為與“外出”完全對立的狀態存在。“社會急劇變遷的影響正日益入侵至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單位——家庭。”[5]留守兒童、婦女或老人的出現,使得農村原生家庭本已在經濟上承受現實壓力的現實境遇中,又平添了親情缺失所帶來的心理層面上的傷害,而傳統意義上的家庭概念,此時不得不面臨著瓦解消失的風險。 作為某類農村現實環境中所存在的兒童群體,“留守”不僅成為其被標簽化的稱謂,同時,其也被視為帶有故事情節線索的敘事元素,參與到導演的情節邏輯建構之中。 在以留守兒童為主人公的電影作品中,他們往往是被代言、被塑造的,其自身難以發聲,正如斯皮瓦克的說法,“底層人無法說話”。 長此以往,電影中的留守兒童形象被植入了過多導演主觀意圖,而這些或刻板或扭曲的形象塑造對受眾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并建構了觀眾對留守兒童的心理認同。 在這些既有認知觀念影響下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一種錯誤或刻板印象的再現。
作為來源于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客體,電影中的留守兒童形象,卻往往難以讓觀眾對其擁有切身性的感知。 換言之,導演對于留守兒童形象進行何種塑造,部分決定了觀眾對于此類形象的感性認知。 因此,無論是積極正面抑或是消極負面的留守兒童形象塑造,都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觀眾的既有認知產生影響。 毋庸置疑,影像再現過程中的留守兒童形象,勢必與客觀現實之間有著一定距離,電影中完全契合留守兒童群體的形象并不存在。 因為,“‘再現’并不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reflection)或‘模擬’(mimesis),而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建構’(construction)”[6](P27)。 影像敘事中,符號的意義不僅在其表層,而且還必須與生成文本的社會、歷史、文化等語境密切相關,“意義并不在事物之中,而是被建構的,被產生的。 意義是被再現的實踐和運作產生出來的,通過再現系統得以建構”[7](P19-28)。 這就表明,一方面,導演對于場景、人物看似隨意的選擇,實則隱藏了明顯的指涉功能;另一方面,電影畫面中出現的任何元素,都必然受到社會語境、權力、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 如果說,運用“典型化”策略塑造的留守兒童形象,最大程度符合了現實生活內在邏輯的話,既有的負面刻板認知,一定程度上會得到部分瓦解。 但同時,導演加深了觀眾對于這類群體的失實化認知。 “電影不僅是社會現實的呈現者,同時也可以通過鏡頭語言揭示社會被遮蓋被忽視的一面, 電影對社會具有‘反分析’ 作用。”[8](P22)因此,如果留守兒童形象缺乏真實性的再現,則會對觀眾起到認知上的誤導作用。 易言之,對電影中留守兒童形象的真實性進行辨析,則顯得尤為必要和關鍵。
電影中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過程中,導演如果盲目追求人物形象的刻板化、主觀化再現,必定會引發觀眾的質疑:劇中人物形象的語言、行為,是否與現實生活的內在規律相契合? 在現實生活中,受各方條件的約束,觀眾難以直接觀察、深入感知留守兒童群體內問題的復雜性與多樣性,而影像敘事則為觀眾近距離切身觀察提供了路徑。 與此同時,由于創作主體對于社會現實的認知程度及情感體驗的不同,導致其在對于留守兒童形象進行塑造的過程中,不僅在影像敘事內容的建構、敘事主體的選取,還在影像所蘊含的價值取向、敘事策略的選擇層面,都具有鮮明的指涉特性。
對于電影中的留守兒童形象而言,以“留守”為邏輯起點,可以衍生出“尋找”或“等待”的行為選擇。 這一方面將其中蘊含的個人情感予以最大程度的畫面呈現,使觀眾能夠真切體會到隱藏于人物內心深處的真情實感;另一方面“等待”與“尋找”作為解決“留守”問題的兩種方式,可以此作為切入點,更全面、深入地辨析留守兒童形象塑造中的真實性問題。 現代城市空間中光鮮亮麗的生存圖景,誘惑著身處農村空間中守望父母回歸的留守兒童,長時間守望無果的客觀現實,促使他們燃起離開農村前往城市找尋家人團聚的欲望。 “鄉村一直被定性為前現代的農業文明的產物,它與以城市化為標志的工業文明處于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9]相較于城市社會文化而言,鄉村文化在現代城市流行文化的沖擊下,被公眾標簽化為“落后”“衰敗”“愚昧”的社會形態。 在這種境遇下,傳統鄉村文化的處境、鄉村文化的發展以及鄉民對于自身生長環境的歷史記憶,都出現了些許被“質疑”甚至是“反叛”的思維認知。 這為電影中選擇外出尋找父母的留守兒童形象提供了看似充分的行為動力。 然而,現代都市生活的絢爛圖景以及熱鬧繁華的商場街道,將來到城市之中的外來務工者和追隨父母的留守兒童等底層人群拋入其間,在市場經濟或物質文明所主導的社會現實中,“焦慮和騷動,心理的眩暈和混亂,各種經驗可能性的擴展及道德界限與個人約束的破壞,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亂,大街上及靈魂中的幻想等等”[10](P19),一系列誘惑持續沖擊著外來務工者及其子女的世界觀。 電影中,身居城市空間中邊緣一隅的留守兒童及其父母,早已忘卻或放棄了渴望完成身份上升的夢想,他們將能否攝取足夠多的物質經濟資本,作為其日常生活的最高訴求。 而此時來自于農村,前往城市空間中尋求親情復歸的留守兒童,在面臨城市文明突如其來的沖擊時,也逐漸迷失在光鮮亮麗的櫥窗之中。 總之,通過文本細讀,我們試圖深入探討電影中留守兒童形象在城鄉二元空間內遭遇到的現實問題,進而將虛構影像與客觀現實進行比照,最終完成對留守兒童塑造層面群體性錯位現象的辨析。
一、影像建構與現實邏輯間的錯位
21 世紀以來,中國電影市場上逐漸出現了一批以留守兒童為主人公的作品,如《留守孩子》(劉君一,2006)、《指尖太陽》(黃河,2012)、《念書的孩子》(原雅軒,2012)、《念書的孩子2》(原雅軒,2013年)等。 留守兒童群體是特定社會階段的產物,如今作為很難被忽視的一類形象,在現實主義題材作品中屢屢出現。 通過對不同作品中留守兒童形象的分析不難發現,導演塑造留守兒童形象的過程中,往往過分強調某一類人物特質,導致其遮蔽了整體性。 即便由于創作主體的主觀介入,作品中的留守兒童形象難以完全與客觀現實相匹配,存在某種遮蔽亦是合理;但縱觀20 余年來,不同導演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上,卻出現了一種群體性的遮蔽或失真化現象——他們往往將留守兒童塑造為具有同質化、模式化傾向的形象。 最終,導致了作品中形象主體與客觀存在物之間的錯位。
錯位,即與客觀存在并非完全契合的狀態、身份或位置。 所謂留守兒童形象塑造上的錯位,即相較于真實存在而言的失真化再現。 某一部作品中,留守兒童形象塑造與現實群體間錯位不可避免。但是,當我們將研究范圍擴展至目前已有的影視作品時,這種錯位就成為一種存在于眾多作品或導演創作中而較為一致的傾向。 例如《鳳山村的孩子》(張毅,2011)中的小鳳、《親親噠》(馬雍,2016)中的親親、《堅強的小孩》(李楊,2016)中的李自強等,導演為凸顯留守兒童勇于承擔家庭責任的“小大人”形象,而導致兒童群體應有的天真爛漫、活潑頑皮的天性被刻意遮蔽。 《留守孩子》中的杜小葦、王小福,《穿過憂傷的花季》(金舸,2012)中的向華萍等,他們因常年與父母分離而導致的反叛情緒或行為,卻又使可能存在的“閃光點”被導演予以隱匿。 由此我們發現,不同導演在留守兒童形象塑造過程中,卻呈現出某種共同的錯位或遮蔽現象。 這種具有相似性特征的錯位或失真,被稱為群體性錯位。
在表現留守兒童形象的電影作品中,除了反映城市中外來務工者以及來自農村老家留守兒童的生存境遇之外,也將鏡頭聚焦于城市現代化過程中留守兒童在進入城市后所遭遇的現實問題。 他們面臨著由現實生存壓力所帶來的挫敗感與失落感。電影中留守兒童對于城市/農村空間的不同態度,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他們是否到城市之中尋找父母,以求與家人重聚的選擇。 對于往返于城鄉之間的留守兒童而言,他們在城鄉之間往返運動的最根本出發點——對家庭結構由破碎向重歸完整狀態轉換的訴求。 這種渴望在電影作品中被表現為:長時間留守經歷的壓迫下,為了尋求與父母的團聚,毅然走出農村,進而通過自身生活區域的轉換,完成與父母在城市空間中走向團圓的行動;由于自身在年齡、經濟條件以及對于社會認知等方面的局限性,不得不在農村的老家承受“留守”所帶來的負面情緒的同時,等待父母從城市歸來。 他們對于不同生存空間的選擇,隱含著其對現代城市文明/傳統鄉村文明的接受態度。 “現代城市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是多族群擺脫農業生產后共同生活、交流思想的場所。 城市空間并非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只涉多重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的文化建構。”[11](P9)
無可否認,對于家庭結構完整的渴望,是電影中留守兒童內心深處最為殷切的期待與盼望。 這種渴望是長時間親子分離影響下的必然結果。 因此,它是我們分析電影中留守兒童形象塑造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邏輯前提。 的確,在以留守兒童形象為主人公的電影作品中,這種家庭結構完整性的期待,直接將主人公的行為選擇,導向了默默等待抑或主動尋找兩類。 這種敘事邏輯在觀眾認知觀念中得以確認。 導演也借此完成了引導觀眾沉浸于影像內容之中的首要環節。 某種意義上,以約定俗成的思維習慣為邏輯前提的敘事發生機制,能夠拉近身處影院之中的觀眾與銀幕中虛構的場景、情節之間的距離,進而引導觀眾產生心理認同,最終產生情感共鳴。 “根據大衛·波德維爾的電影敘事理論,敘事是一個藝術家和觀眾互動的完整‘過程’(process),觀眾的‘認知建構’是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 由于認知建構模型十分倚重人類認知處理信息的作用,波德維爾敘事理論中的‘觀眾’(viewer or spectator)較先前敘事理論中的觀眾有著更強的主動性。”[12](P235)“在劇情片中,敘述是影片情節和風格互動的過程,它不斷提示觀眾,并引導其從事故事的建構。”[13](P127)由此可知,波德維爾對于敘事的觀點是建立在觀眾對于整體敘事的認知方式之上的,他認為觀眾通過自身的觀影過程,經由影院/室內視知覺活動對電影所呈現畫面信息的獲取,對信息進行個人主觀化的處理,而后完成自身對于影像敘事的最終建構。 留守兒童之于家庭內部結構回歸完整的渴望,必然襄助于我們剖析其行為產生的動因。
嚴格來說,對于家庭內部結構回歸完整的渴望,屬于內含于留守兒童形象中的共性。 從留守兒童形象的整體性來考量,可以得知,親子分離必然帶來對于回歸的渴望。 但此時,電影中是否以這種渴望主導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并非必然要求。 作為留守身份必然導向的心理情緒,它可以衍生出一系列行為選擇的原始動機,也可以僅僅是塑造不同類型留守兒童形象的背景存在。 無論是家庭責任的承擔者,抑或是行為失范的失足者,當我們排除掉這份渴望,冷靜客觀地分析導演通過“典型化”策略所塑造的留守兒童形象時,被留守身份過分遮掩的兒童身份、天性就顯露出來。 因而,以此為切入點進行分析,便于我們發掘出隱藏于回歸渴望背后可能存在的有違現實內在邏輯的失實化表現。 如前所述,電影中留守兒童形象實現家庭內部結構重歸完整的訴求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追隨父母的腳步離開農村,前往城市中尋找異地空間內的家庭圓滿;二是迫于現實束縛,無奈留在農村家中,苦苦守望親人的回歸。 每一類行為選擇,都會衍生出不同的人物命運,這為我們提供了不同角度,對留守兒童形象塑造層面出現的群體性錯位現象進行剖析。
二、尋找家庭圓滿的影像建構
以留守兒童為主人公的電影作品中,往往會呈現他們因長期飽受由情感缺失導致生理、心理雙重傷害的現象。 因而,留守兒童試圖借助前往城市中與父母團聚的行為選擇,彌補心靈創傷的動機,就自然出現了。 留守兒童在現實社會中的話語權,往往是被“喪失”的,他們無力針對自己的所處境遇發聲。 眾所周知,貧寒的家庭出身、落后的農村經濟現狀,成為推動留守兒童父母外出務工的原始動力。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持續推進,無數成功者的神話鋪天蓋地的襲來。 當深陷貧窮落后且文化衰敗的農村空間內的大多數青壯年勞動力,通過電視和網絡了解到城市生活的五彩斑斕時,他們心中對于現代化的向往促使他們遠赴他鄉,尋找生活的新希望。 “軌道鋪進了深山,尖銳的火車長鳴聲打破了山村固有的寧靜,以城市為代表的工業文明漸漸滲透到了閉塞保守的山村”[14],經濟發展的驅動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往鄉村之外的生活,去往大都市拼搏的抉擇,在他們心中成為了改善貧苦生活的美好希望。 電影中深陷衰敗、落后農村空間里的留守兒童,選擇前往城市尋求家庭圓滿的內心訴求,不僅契合了對于更高層次生活品質追求的生存需要,同樣也與自身渴望親情復歸的情感呼喚相迎合。 在此,建立在生存與情感雙重需要基礎之上的行為選擇與現實生活過程中的內在邏輯相匹配。 因此,是否產生此種行為選擇動機的真實性問題,在此處并不作為考量的重點。 如果說,我們排除了行為選擇動機的真實性問題的話,那么,隱藏于人物內心的欲望訴求是否轉換抑或如何轉化為實質性外在行為的問題,則成為我們考量人物形象真實性與否的關鍵。
在眾多電影文本中,我們難以通過某一類留守兒童形象的呈現,對其進行整體性概括。 無論是《親親噠》中勇于承擔家庭重任的親親,還是《留守孩子》中調皮頑劣的王小福,抑或是《穿過憂傷的花季》中行為失范的向華萍,再或者《空巢里的孩子》(王鯨,2009)中守望父母回歸的“北京”“青島”等,他們都是社會客觀存在的一隅。 因此,不難發現,留守兒童這一在現實中有明確指向的人群,在電影文本內具有類型多樣的形象及多重能指,這也從側面展現出影像再現本身的復雜性以及內涵的多義性。 對于現實生活中的留守兒童群體而言,他們沒有“發聲”的空間,或者說其“發聲”空間是多數受眾日常生活經驗中較難涉及到的。 因而,導演通過影像再現后的留守兒童形象,可被看作是代替喪失“發聲”空間和權力的留守兒童群體,向大眾訴說的一種方式。 但是,這種“‘代表’或‘代言’,是建立在它們具有話語權的基礎上,因此也承認了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之間的階層差異”[15](P30)。 拋開階層差異性不談,作為“代言人”存在,導演所選擇的藝術再現內容,與此類社會群體的情感傾向及價值判斷息息相關。 導演主動將自身的感性認知與情感體驗隱匿于敘事之中,電影文本內的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則成為其表達自身主體性價值取向的顯現形式。 留守兒童形象的真實與否,不僅在于其與現實之間的距離,還在于導演試圖通過“典型性”塑造策略再現的形象,選擇性地突出了何種真實。 因而,當我們對電影中的留守兒童形象進行真實性辨析的同時,依然需要額外關注導演為何選擇將這般形象呈現于銀幕之上的緣由。
對于電影文本呈現的留守兒童形象而言,城市空間于其精神世界中,被建構為“烏托邦”般的存在。 “‘u’‘topia’來自希臘文,前者表示否定,后者的意思是某個地方或地區。 ‘u’可以與‘eu’聯系起來,表示‘美好’‘完美’,這兩種意思聯系起來,也就是一個虛擬的值得人們向往的至善至美的地方或國度。”[16]在以表現留守兒童的生活境遇為主的電影作品中,往往并未選擇全景式地展現城市空間亦或城市圖景的方式,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留守兒童對于城市空間帶有自身明顯主觀想象的認知。 電影主創者在建構影像畫面時,甚至選擇將一部分城市空間中真實存在卻殘酷的現實圖景予以抽離,從而描繪出近似烏托邦似的“想象域”。 但是,當留守兒童毅然踏上前往城市尋找父母的旅途時,隨之而來的現實問題便逐一出現。 《城市候鳥》(魏曦銘,2010)中,當外來務工者面對子女學籍問題時,遭遇到的是由于自身工作地點的非固定狀態,而使來到城市上學的子女不得不處理留級、甚至是不得不在初高中或高考時回到農村老家的問題。 《小彪與狗》(周浩,2015)中,“小彪”所說的自己在小學時期隨父母輾轉各地的現實經歷,也從另一個層面證明了這一點;曾隨父母漂泊在外的小彪最終還是在家鄉一個人與一條狗一起生活,早年間隨父母一起的漂泊經歷給予他的只有學業上的影響,即不得不因為頻繁轉校而留級。 《留守孩子》中,當王小福因遲到站在班級門口時,他口中念出的是給父母的一封信,是對于父母常年外出給其帶來的情感缺失以及怨恨,電影作品將這種因留守經歷所帶來的負面情緒予以充分呈現。 這種負面情緒的釋放,直接展現出留守兒童對于家庭團圓的強烈渴望。 但是,為了追求家庭內部的重歸團員,主動或被動地前往城市與父母相聚后,他們的生活是否真如自我想象的一般美好? 電影作品所刻畫的留守兒童的父母,在城市中往往被視為難以融入當地生活的“他者”,而對于生活在農村之中的留守兒童而言,他們在同輩非留守者的視野中,恰恰也作為“他者”存在。 正如英國學者丹尼·卡瓦拉羅所言:“他者就在我們之中。當一個文化、社會或社群把某些個體當成他者加以邊緣化時,它試圖排斥或壓迫的實際上是它自身的一部分。”[17](P123)然而,當留守兒童為了彌補內心需求而對家庭缺失的親情予以追尋之時,種種現實困難卻阻礙了他們跟隨父母遷徙至城市的愿望實現。
電影作品對于家庭惡劣經濟條件的展現,與父母前往城市的務工選擇相契合,其同樣符合現實生活邏輯。 但是,值得關注的一點是,由于家庭內部父母角色的缺席,上一代祖輩老人的在場,也是以留守兒童形象為主人公的電影作品里不可或缺的設置,然而問題在于同樣留守農村中這些老人形象的塑造,往往與疾病纏身、年邁體弱的特征相關。比如《留守孩子》中,身患肺心病的爺爺;《童年的稻田》(朱曉玲,2012)中,在麥秸旁去世的奶奶;《遙望南方的童年》(易寒,2007)中,影片開始便已重病纏身的祖輩老人等。 毋庸置疑,現實農村環境中確實不乏此類體弱多病的老人,但電影作品中,同樣留守家中承擔照顧留守兒童責任的老人,卻具有如此相似的人物特征,就不能不讓人心生疑惑。 因此,導演為了突出作品中留守兒童形象的苦情命運,主觀上刻意塑造了具有嚴重同質化傾向的留守老人形象,其也與現實形成群體性錯位存在。 這種以留守兒童形象苦難命運催生觀眾心中對其憐憫之情的方式,不僅未能營造出憂傷、悲涼的氣氛,反而導致人物形象的真實性被削弱。
對于親情的渴望、長時間分隔城鄉兩地的生活現狀,被導演作為建構留守兒童行為合理性的基礎,這種看似符合思維邏輯的因果關聯,卻忽視了兒童本身行為的邏輯性。 如果說,提議租車看望父母的想法,尚且與渴望和父母團聚的殷切希望相契合的話;那么,當這種想法轉換為現實行為予以實施時,我們就難以僅僅以留守者身份,來考量人物行為的合理性。 因為看似縝密的敘事邏輯,卻忽略了作為孩子的他們,根本無法完成租車的行為的現實,脫離兒童身份限定的行為選擇,勢必導致觀眾對人物形象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另外,前往城市后,是否能夠真正滿足他們心中渴望,在作品中同樣沒有直接呈現。 導演恰恰用最符合現實生活情感的邏輯構建,打破了電影作品中的真實。
《小彪與狗》(周浩,2015)、《米花之味》(鵬飛,2017)、《留守孩子》等對于此類問題進行反思與呈現的電影作品中,留守兒童的進城尋親經歷、農民工父母失敗的城市體驗,以及留守在家無力遷徙的低齡段留守兒童的現實境遇,都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身處偏遠山村的農村留守兒童及其外出務工父母奮斗的失敗結局。 “從家庭社會學的視角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是伴隨社會變遷而來的家庭結構斷裂、家庭功能紊亂、家庭關系淡化、家庭生活方式變異的綜合體現,它反映的是農村家庭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一種特殊的文化失調現象。”[18]對于留守兒童群體而言,由于父母外出所造成的家庭內部親情的缺失,勢必會讓他們對外出的務工父母產生更為深切的思念。 這種長時間的情感缺失狀態,導致了留守在家的子女,對于前往城市尋找父母,進而完成親情復歸的欲望訴求日趨強烈。 農村相對落后衰敗的場域設定,也為這一切的發生設置了合理的前提。 正是因為城鄉之間巨大的經濟差距,才使得外出務工、留守,進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生成的邏輯,顯得順理成章。 “于是,在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的雙重刺激下,新老一代農民的背鄉棄土,鄉村的傳統人際關系迅速解體,鄉村的生活意義和吸引力逐漸喪失。”[19]現代城市文明對于農村文明的全面影響,使得現代性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身處農村之中的留守兒童們傳遞農村文化落后愚昧的觀念。 “城市空間并非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只涉多重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的文化建構。”[20](P9)無論是對于城市現代文化的積極擁抱,還是說對于日益衰敗的傳統鄉村文明的默默堅守,都被導演放置于留守兒童期待與父母團聚的內心渴望中予以再現。 觀眾對于留守兒童形象的既有認知所衍生出的憐憫之情,被導演通過苦情化的人物命運構建予以放大,最終將人物形象塑造的失實化表現,埋藏于不易被察覺的情感宣泄之中。
電影作品中留守兒童與父母形象設定,同樣受到了經濟發展以及城鎮一體化建設的影響。 戶籍歸屬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他們在城鄉之間跨區域流動的不穩定性,即使其長時間生活在城市,流動狀態卻是難以改變。 追尋城市空間中家庭圓滿的留守者,也同樣因為留守農村而產生了遠行城市的心理訴求。 衰敗落后的農村空間與其中的留守兒童之間形成了某種呼應,農村作為與城市發展比較的相對落后者,與留守兒童一樣成為“家庭”離棄之地的隱喻。 留守兒童形象,作為身處社會、家庭倫理之中的社會底層邊緣人物命運選擇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現出市場經濟原則以及商品邏輯占據社會主要評價體系的現代城市的不確定性特征,同樣是身處其中的人們對于現代都市性文明的理性反思,對于逐漸逝去的傳統鄉村文明的感性懷念。 “留守”一詞這個帶有豐富內涵的稱謂,作為與“外出”完全對立的兩個詞,成為導演或社會大眾對于由同一家庭內部所分裂出的兩種群體的稱謂。“留守”不僅成為其被標簽化的稱謂,同時,它也作為帶有故事情節線索的敘事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了導演對于電影作品創作之初的敘事建構之中。 留守兒童自身情感缺失的現實境遇,在導演建構敘事過程中成為主人公的臺詞、行為等方面設計的起點。 對于留守兒童而言,除了俊男靚女、光鮮亮麗的繁華生活圖景外,城市吸引他們的,更是遠在其中的父母,這也成為他們身在農村老家,卻對城市生活產生無限渴望的根本原因。 思念父母的情感訴求、關于城市圖景的主觀個人化的想象,構建起了每一個留守兒童心中對于城市的渴望。 此時的農村成為一切故事發生的起點,也成為故事中主人公感傷性結局的最終歸宿。 但是,導演在表現前往城市尋求一家團聚的留守兒童形象時,卻并未將這種客觀現實呈現于畫面之中。 他們僅以過程艱辛替換隨時可能到來的未果而終的現實命運,試圖用由留守身份牽動的行為選擇,遮蔽社會現實中客觀存在的某種阻礙。
導演在建構影像敘事活動時,一定程度上會考量觀眾對留守兒童群體的刻板印象。 但是,其被自身價值取向驅使的藝術再現,同樣存在著與客觀現實嚴重錯位的風險。 作為創作主體的導演,其對于留守兒童形象的主體性建構,不僅內含自身創作意圖,而且“意在對讀者的世界觀造成影響,這種影響在倫理上絕對不是中立的,而是或隱或顯地引出一種對世界和讀者的價值重估”[21]。 換言之,觀眾作為觀看實踐的行為主體,進入影像敘事的閱讀之后,必然會對經導演主觀選擇后呈現的內容予以判斷,當其產生心理認同時,自身對于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留守兒童群體認知,也會產生相應變化。 因此,這種失實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一定程度上必然存在著刻意誤導/定向引導觀眾價值取向的可能。
結語
導演一味為主人公構筑外出尋找父母的行為選擇,由此而進行情感和邏輯上的鋪墊,即便確實能夠建構起行為與現實邏輯之間的合理關系,但因為其過度關注留守兒童形象悲情命運與感傷結局的再現,反而形成了影像與真實間的錯位,消解了影像再現過程中人物形象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