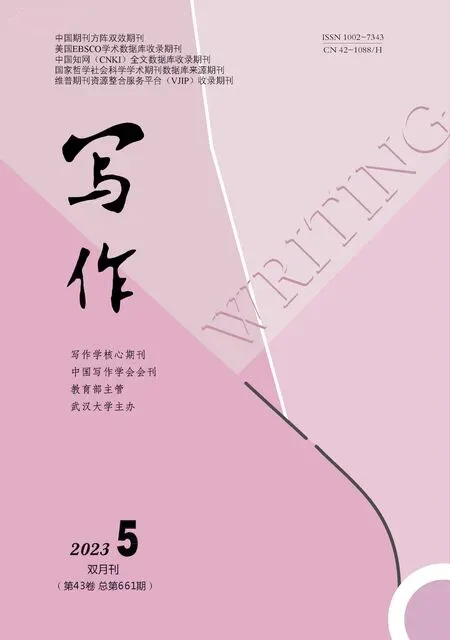描摹時代光影,或?qū)懡o世界的書信
——文珍訪談錄
劉啟民 文 珍
筆者于2023 年6 月對青年作家文珍進行了一次線上訪談。在訪談中,文珍談到了自己的閱讀史,以及作家勾勒時代生活的寫作路徑。以貼近大城市中各色人物心靈世界和捕捉時代氣息見長的文珍,這次分享了自己進入社會之中進行田野調(diào)查、最終寫成小說故事的經(jīng)驗,在今天這個時代,這樣體他人之存在、之狀態(tài)的寫作路徑既珍貴又典型,值得更多作家、批評家們的注意。
一、閱讀史:“我看書的脈絡(luò)一直都很錯雜”
劉啟民:文珍師姐好!很高興有這樣一個采訪師姐的機會。作為略小一些的“小同代人”,我算是一個跟蹤閱讀師姐小說的“粉絲型讀者”,有一些很感興趣的問題,想請師姐來談?wù)劇J紫认胝垘熃慵氈乱稽c地分享一下閱讀史。
文珍:我看書的脈絡(luò)一直都很錯雜。如果出門在外沒什么選擇,就會像小時候一樣,能到手什么書就看什么書,比如酒店一樓的藏書,當?shù)貓D書館的書,或者在微信讀書上隨意瀏覽。我微信讀書的書單、家里書柜最外層,茶幾上和床頭的書,都會經(jīng)常更換。閱讀相對隨機,其實是希望從不同的書里尋找到未知的靈感。現(xiàn)在因為在寫長篇,所以也會有計劃地列一些書單,但時不時還是會被偶然得到的其他書吸引過去。
我父母都是工科大學生,所以其實家里最早除了《紅樓夢》和魯迅的《吶喊》《彷徨》以外,文學類藏書很少。最多給我一點錢讓我自己去新華書店挑書,也給我訂了《小朋友》之類的雜志。自己買得起的書畢竟有限,好在祖父當本地中學校長以前是語文老師,家里有些古籍,鄰居中也有一個高中語文老師,給自家女兒買了很多書,包括全套二十幾本的《奧茲國歷險記》,令人非常艷羨。因為長期處于對書的饑渴中,所以從小就養(yǎng)成了能弄到什么書就看什么書的習慣,讀書興趣比較駁雜也是那時留下的后遺癥。爺爺是個舊文人,會和友人結(jié)成詩社唱和,受他影響我也很早就對詩詞感興趣,初中就會把“三言二拍”、《紅樓夢》里的詩詞都抄寫下來,可能也是里面的詩詞并不太難的緣故;也會把語文書后附錄的詩詞倒背如流。實在沒合適的書,連《科學哲學導論》《數(shù)學花園漫游記》這樣的科普書也不放過,小學高年級還去爺爺中學的閱覽室借到過聞一多的《中國神話史》,還有《尼爾斯騎鵝歷險記》和全國優(yōu)秀中短篇獎合集,后者相當于現(xiàn)在的“魯獎”,是當時的中短篇最高獎。還有《當代》《佛山文藝》,在書店里站著翻過《蘇童文集》,甚至半懂不懂地看了莫言的《豐乳肥臀》,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兒童不宜的部分還蠻多的,也不求甚解地讀完了。初一從高年級同學那里弄到過一本《三國演義》,看到曹操把呂伯奢一家殺了就棄讀了。這是四大名著里唯一一本沒有在中學讀完的書。初二隨父母從湖南到了深圳,媽媽帶我去深圳市圖書館,那可比小城的中學閱覽室大多了,宛如打開了阿里巴巴的寶藏大門。后來偶爾上學遲到了,怕老師責罰,索性就逃學到圖書館或書店去。
除了不適合小孩子的書,最喜歡的就是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覺得比《格林童話》動人。楊靜遠譯的《永無島》,任溶溶譯的《洋蔥頭歷險記》《假話國歷險記》《豆蔻鎮(zhèn)的強盜與居民們》也都極好。我似乎很早就有偏好民國語文的傾向了,就覺得和其他書面語或口語都不一樣,有一種陌生的新異感,但同時也很典雅。
當然也會看言情和武俠,小學看瓊瑤,初中看亦舒、金庸、古龍,高中看張愛玲也看陳丹燕。讀《連城訣》同時,也讀據(jù)說直接影響了金庸寫連載的《基督山伯爵》。我一直相信開卷有益,現(xiàn)在那些家長那么擔心孩子讀不好的書,甚至對世界名著也戴了有色眼鏡去挑里面可能誨淫誨盜的部分,這完全沒有必要。要相信小孩子的鑒賞力和理解力。光看書是學不壞的,出去交不讀書的壞朋友才可能學壞。
劉啟民:我一直覺得你的文字有不著痕跡的古典氣,可能跟你的古典詩詞閱讀有點關(guān)系。
文珍:大概就是受了爺爺?shù)挠绊懀瑥男【烷_始背唐詩宋詞,大學又迷上了元曲。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一本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婉約詞》,封面上有一個古裝仕女,里面很多詞我都倒背如流,還會記在本子上。初二去深圳后,語文老師在課堂上抓過我看《唐伯虎詩詞全集》,是我的表妹幫我在她就讀的紅嶺中學的圖書館借的港版書,我自己插班的小破初中根本沒有圖書館。那本書也很“神”的,一本港版書不知怎么輾轉(zhuǎn)流落到深圳重點中學的圖書館,最后又被我讀到。其實里面很多都是偽作,比如其中一首《菩薩蠻》:“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一向發(fā)嬌嗔,碎挼花打人。”這首艷詞根本就不是唐伯虎寫的,卻被當時的我深深記住了,一直到今天。
劉啟民:那西方現(xiàn)代文學你有接觸嗎?剛剛談到的都是中國的。
文珍:童話、寓言和《希臘神話與傳說》大都是西方的,當時本土童書還很少。我記得后者是一個外國人寫的,因為是繁體字版,所以看得半懂不懂,長大后才發(fā)現(xiàn)作者是德國的古斯塔夫·斯威布,那個版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版。初中就開始大量地看各種探險故事,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等等,還在我爸當時工作的先科激光公司的工人宿舍順手拿過一本《查來泰夫人的情人》,也沒人管我,哈哈。還有兩套書印象很深刻,一套是“世界科幻小說精品叢書”,總共有十幾本,我最喜歡的是里面的一本《海底樂園》,詳細描寫了很多海洋生物做的點心和糖果,看得我垂涎三尺。另一套是《哈爾羅杰歷險記》,也有十幾本,英國作家威勒德·普賴斯寫的,我記得寫到哈爾和羅杰去珠穆朗瑪峰時遇到神秘的雪人,以及轉(zhuǎn)經(jīng)筒是什么;另一本寫到去亞馬遜叢林探險,夜間出沒的黑豹從樹枝間一把薅掉了哈爾的頭發(fā),作者這么寫:“他可不想讓它當自己的理發(fā)師。”這些都非常有趣,也可以說那就是我們那個時代的《哈利·波特》吧。無論什么時代,青少年永遠是鐘愛冒險的,我到現(xiàn)在還是非常愿意去各種陌生古怪的地方,好奇心一直相當過剩。
高中開始看《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槍手》《紅與黑》《簡·愛》《呼嘯山莊》之類的世界名著。大學之后就看得更多,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在看各種外國翻譯小說,反而中國的書看得相對少了;也開始和很多讀書人一樣,知道挑剔譯本的好壞,比如王道乾老師是我格外喜愛的法文譯者,他翻譯的無論是杜拉斯的《情人》還是米歇爾·圖尼埃的《禮拜五——太平洋上的靈簿獄》,都反反復復看過很多遍,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背誦。我出第一本書《十一味愛》的時候,有人說我的文字有古風,也有人說帶有一點翻譯腔,這些個人閱讀史留下的影響,對于一個文學的新手來說大概很難避免。
二、寫下時代:“一定要實地感受一下那種空氣”
劉啟民:師姐最早是寫都市里的愛情故事的,《十一味愛》《我們夜里在美術(shù)館談戀愛》和《柒》里的小說,大都圍繞著這個主題呈現(xiàn)出城市里各式各樣的愛情。也有批評家認為,“愛情”是你探照都市青年精神世界的獨特抓手。你自己寫作愛情故事的心路歷程是如何的?創(chuàng)作“愛情”敘事的意義,你又如何考慮,是否有一個從自發(fā)到自覺描繪它身上的“社會性”“時代性”的過程?
文珍:其實我最早想寫的也不完全是愛情故事,還是試圖書寫城市生活中年輕人從滿懷理想到幻滅的過程。但第一本書《十一味愛》的發(fā)布會,編輯當時問我起什么題目,我想了很久,說還是叫“年輕的時候還有什么比愛更可說”吧,也就是說,其實我當時也模模糊糊意識到愛情可能是自己書寫這些幻滅故事的最早切入口。但時隔十多年,對愛情和人生的看法已經(jīng)很不一樣了。從我自己身上,就有很明顯的時代、社會和個人的變化。除了對少作的自我反省,也會慶幸并不成熟的自己如實寫下了彼時的體察和認知,似乎是一個未充分熟成的人在作品里留存了青春。
劉啟民:《夜的女采摘員》這本集子跟之前的愛情寫作已經(jīng)不同了,打開了一個幻想類的虛構(gòu)世界。我能看到弱者不再自悼而是出現(xiàn)對同類者——人、動物、靈——的共情共感;在形式層面,也撐破了原來的現(xiàn)實敘事,引入了靈魂、動物們的敘述。師姐當時是因為什么樣的契機,轉(zhuǎn)而去書寫鬼魂和動物的世界?
文珍:與其說我相信鬼魂的存在,毋寧說我希望自己盡量不害怕這種存在,能夠坦然面對黑暗世界的拷問。對動物也是如此,不是我想要把動物擬人化,而是一直覺得人也只是動物之一,只是更自私自以為是罷了,自詡食物鏈頂端,但真的有權(quán)任意處置這個星球上其他動物的命運嗎?在放棄人類中心主義之后,我想試著以更低的視角寫出人類活動的荒謬和非理性。
劉啟民:我留意到師姐在采訪時會稱自己非幻想類的寫作為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不知你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文珍:其實現(xiàn)實主義也是需要想象力的,但帶有更多幻想色彩的故事會留給想象更多空間。
劉啟民:《找鑰匙》是師姐最新的小說集,收錄的是北京城里零余者、邊緣者們的故事,許多篇目,在經(jīng)驗的層面都寫得很“瓷實”,師姐仍然還是非常體己地,貼著人物內(nèi)在的感覺、心理和精神世界來寫,比如《張南山》寫快遞小哥,《有時雨水落在廣場》寫一位來北京投奔兒子的老人。一直對文珍師姐“體他人之世界”的寫作追求保有敬意。但也想知道,這種寫作會遇到怎樣的困難?
文珍:最大的困難可能還是一些具體的細節(jié)若非親歷,需要做更多的田野調(diào)查和盡量調(diào)動共情力才能得到。
劉啟民:能分享一些你印象很深的田野調(diào)查的例子嗎?
文珍:比如《張南山》里的快遞員。其實一開始沒想寫這個題材,但在出版社工作時偶然聽說有個小哥給一位女同事留了紙條,表達了希望進一步認識的意愿。這件事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因為那個女同事是英國海歸,可以說得上嬌生慣養(yǎng),平時連公交車都不會坐,她家人本來住在西城區(qū),為方便她就近上班,直接在東直門買了一套400 萬的房子全家一起搬來。當然過了幾年那房子迅速就上了千萬了。也就是說,這個女生的生活其實是和快遞小哥很遙遠的,只是她從國外回來,對人一律非常禮貌,因此也許給了小哥某種可以交往的幻覺。一旦起念,我就跟相熟的一位韻達小哥說,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送快遞。他答應(yīng)了,我就坐他的三輪車跟著送過兩三次,每次一個小時,去過均價13 萬一平的小區(qū),也去過群租房,親眼看過他聯(lián)系不上收件人的氣急敗壞。我表弟聽說我想寫快遞員,也給了我一個順豐小哥的電話,但我沒加。除了自己去送,后來就是一直留意報紙網(wǎng)絡(luò)各種關(guān)于快遞員的新聞,大概做了好幾年的準備,才終于動筆完成。
另一篇《寄居蟹》是寫三和大神的。寫這個小說也有個緣起,就是在富士康發(fā)生“十五連跳”后的2010 年年底,我有一次回深圳探親,在寶安機場正好遇到一群關(guān)心工人的朋友要去富士康搞座談,就跟著去了,結(jié)束后在園區(qū)外的街上偶然看到一個赤裸上身的年輕男孩,拿著一把很長的西瓜刀四處敲打,所有攤販都嚇得面無人色。因為一直無法忘記這一幕,后來就把它寫進了《寄居蟹》這篇小說的結(jié)尾。為了寫這篇小說,我也去過好幾次三和市場。第一次坐地鐵過去沒有找到,很多地鐵里出來的人都不知道三和是什么東西,很奇怪,在高德地圖上也找不到。第二次一出地鐵站就打了一輛摩的,摩的師傅還以為我是去找工作的,對我說你沒問題,肯定能找到。
到人才市場以后,因為事先做過一些功課了,甚至小說輪廓都已經(jīng)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其實沒有怎么跟人聊天,就是四處看看,看到想象之外的場景就拍照,也不多,總共就拍了四五十張照片。這種田野調(diào)查方式大概和非虛構(gòu)那種主要以訪談為主的路徑不太一樣。但不同小說家的習慣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做田野調(diào)查的方式,就是會跟太太去一個地方找人聊天,他說前四個人也許都不搭理他,第五個人卻可能會突然滔滔不絕地把所有的都說出來,這樣他就得到了一切他想要的。但我寫《寄居蟹》的時候,其實三和市場早就有很多記者去明察暗訪過了,日本NHK 電視臺都已經(jīng)拍了紀錄片了。我就本能地覺得,其實這邊很多人大概都已經(jīng)對記者和任何問東問西的人產(chǎn)生了戒備心,再去問可能會造成當事人的困擾,也會很引人注目,恐怕很難得到我想要的。還不如不動聲色地就在人群里當一個隱形的觀察者,一邊驗證二手材料的真實性,一邊校正自己此前不夠準確的想象。其實能否采訪到某個人具體的故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定要實地感受一下那種空氣、聲音、氛圍,親自嘗掛逼粉的味道,看看有沒有漲價,清藍大水是不是還是兩塊錢一瓶。
劉啟民:我覺得還挺神奇的。作家跟記者、跟非虛構(gòu)作者還是非常不一樣。你首先會有一個自己的想象,然后你再介入到現(xiàn)實當中,并且,就像師姐說的,其實你是去現(xiàn)場感受一種氣息。
文珍:對,就是一種氣息、溫度,看一群人站在一起聽天由命地等日結(jié)工作的場面,以及聽到誘人的機會,突然集體向某個方向移動的速度,甚至可以看到每個人面部很細微的表情變化。這樣我回去就可以更切身地想象主角的生活,他和他的同類的日常狀態(tài),每個人之間相似和不同的部分,分別從什么地方來,又可能各自往什么地方去。
劉啟民:所以我覺得你不同時期的小說,總是留有所描寫的時代里大量的生活痕跡,像不同時期的電影和暢銷的小說、不同地方的吃食、不同階層性別職業(yè)的人物用的香水之類的。生活各個方面的細節(jié)都會留存在小說里。有時候我會覺得你小說里有古典文學里世情小說的意味,類似《紅樓夢》那種。
文珍:如果用世情小說的標準,我想我以前寫得還不夠細致,之后還可以更精確一些。比如說現(xiàn)在要寫21 世紀初的大學校園生活,就要去重新找到那個時候的報紙雜志,看那個時候的廣告和新聞。
物質(zhì)是重要的錨定生活的細節(jié)。比如說,Vera Wong 的婚紗在歐美流行了很多年,但現(xiàn)在已有更高級的高定了,國內(nèi)的明星和中產(chǎn)階級也不再只追捧這個牌子。還有21世紀初超市里到處都是的伊卡璐洗發(fā)水,味道很香,但是洗完以后頭發(fā)特別干,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太常見了。六神花露水也是。大眾日用品大抵有一個由新興到消亡的接受史,包括人們的消費偏好也會隨著生活水平的改變而變遷,從每個人都在用,若干年后就可能變成時代的眼淚,也變成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的集體記憶。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泰坦尼克號》電影的結(jié)尾,大船將覆之時,廚房里大量瓷器從碗柜里傾瀉而下,碎成齏粉,那一幕也許只有幾秒,但卡梅隆為了鏡頭不穿幫,就設(shè)法找到了那個時代的若干瓷器并真的讓它們在拍攝時粉身碎骨。寫小說可能成本沒有那么高,但對物質(zhì)細節(jié)的要求是一樣的,必須盡可能真實。
劉啟民:嗯,我覺得世情小說還有另外一層意蘊,就是從整體來看,你的寫作是貼著城市里的世態(tài)和生存寫的。那天重讀師姐的創(chuàng)作,發(fā)現(xiàn)作品里寫到老年人,之前寫青年人的愛情,然后《柒》里面更多地寫到中年人,后來會慢慢把寫作的觸角伸到這個世界里特別細微的角落里。你的人物譜系是非常豐富的,在一個城市空間里面,不管是從年齡、從階層、從職業(yè)來看都是很豐富的,感覺快要窮盡城市里的情感樣本。
文珍:光北京城里就有幾千萬人,一個作家肯定是沒有辦法窮盡城市里的樣本的,我最多只是寫到了自己真的看到且有所感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人。比如為什么會想到寫《安翔路情事》,就是因為2010年6月有一天我看完演唱會回家,已經(jīng)晚上11點半了,經(jīng)過家附近的安翔路時,發(fā)現(xiàn)小胡還在攤灌餅——所以老胡灌餅是真實存在的灌餅店,只是小胡并不真的認識小玉——電光火石的那一刻,我又意識到他第二天五點多六點還要起床,繼續(xù)攤一天餅。而小胡的生活對我來說卻是從演唱會興盡而歸路上的一瞥,這種對比讓我非常難過。
我的意思是,自己并不是有意識地要去窮盡所謂城市里的情感樣本,類似一種收集癖,而是真的突然看到了某個具體的人,如鯁在喉,不寫會死。很多人群,很多階層,很多生活方式是我完全不了解的,平時生活里既沒有機會看到,事實上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全部了解。作家只能寫好自己“真正看到”并且對自己有所觸動的那部分人。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chuàng)立新世界觀思想體系的第一個成果《神圣家族》首次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yè)”[13]P104。以后,這一思想貫穿于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論著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就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的根本宗旨,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chuàng)精神,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團結(jié)帶領(lǐng)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歷史偉業(yè)。習近平同志再三強調(diào)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fā)展理念正是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在當今的新境界。
三、多樣的寫作:“同樣是寫給世界的嚴肅信札”
劉啟民:除了不斷探索外部世界的小說,師姐還以詩歌、散文的文體保留了自己生命的痕跡。詩集《鯨魚破冰》、散文集《風日有清歡》里,藏著師姐非常“文青”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這種“自留地”式的私人書寫,對于師姐來說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文珍:其實我覺得作家不該界限分明地劃為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任何文體一旦決心拿出來示人,也就不僅僅是“自留地”的私人書寫,而和小說一樣,同樣是寫給這個世界的嚴肅的信札,是希望被懂得、孜孜以求喚起更多心靈的共鳴的。一定要說分別,只能說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的狀態(tài)不太一樣。寫小說需要尋求理性和熱情的平衡,寫散文則像是和朋友促膝夜談,相對更加親近;而詩歌則更多地來自所謂“必要的時刻”,更倚重靈感的勃發(fā),不想寫強寫多半不會有好結(jié)果。
劉啟民:有時我會覺得你的某些短篇很像詩,其實是因為你的短篇一直注重情緒體驗和氛圍渲染,這在文壇是獨具一格的。創(chuàng)作中短篇小說時,師姐是否對小說的形式有自覺的考量?
文珍:我在不同時期寫過形式截然不同的作品,有偏重書面語陌生化的,也有相對口語化的嘗試,其實不太知道你說的注重情緒體驗和氛圍是指什么。世界上的優(yōu)秀短篇很多,在我看來,短篇小說因為篇幅短小,本來就有如吉光片羽的詩的特質(zhì),但這并不代表它們是只看重形式的短制,相比那些已說出來的部分,更重要的,也許在于那些沒被真正寫出卻得以充分暗示的來處和去路,主角被光照亮后復又隱入黑暗的一生。也就是說,所有形式都需為具體意義服務(wù)。很難說我追求什么,只能說語言可以無限自我繁殖又戛然而止的形式大于內(nèi)容的短篇,不是我想寫的。姿態(tài)很酷,很好。和小說同理,華麗空洞的詩我以為也是沒有意義的。
劉啟民:還有一個我很感興趣的問題。師姐初二之前是在湖南婁底生活吧?
文珍:是的。婁底是一個新興工業(yè)城市,20世紀70年代才設(shè)市的。
文珍:我確實缺乏鄉(xiāng)村生活的經(jīng)驗。除了城市文學的標簽,也有一些評論者說我一直有南方青年的視角,作品也有新僑寓文學的感覺。聽得多了,我反而會漸漸生出一點南方的鄉(xiāng)愁,感覺經(jīng)歷了一個很漫長的被北方話語體系規(guī)訓的時期,但最終還是想寫出被遮蔽的南方前史,甚至更豐富的南方青年的在京群像。
劉啟民:最后還想問問,師姐接下來還有哪方面主題或是形式的作品,會跟讀者們見面?
文珍:我目前正在寫一個長篇小說。沒完成的作品還是不要說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