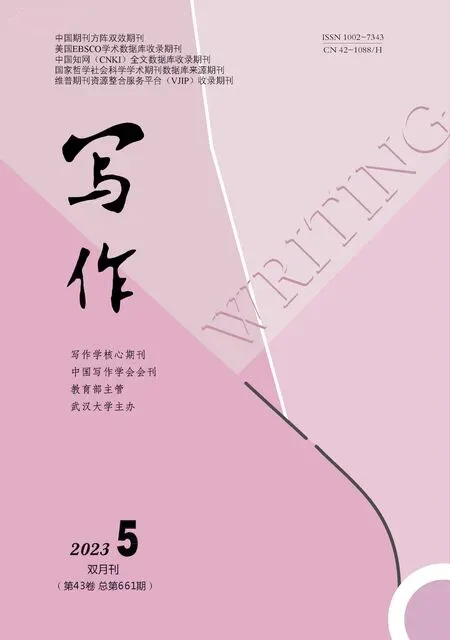寫作,是為了在大地上翩翩起舞
——阿人初訪談錄
白哈提古麗·尼扎克 阿人初
阿人初的詩集《頂碗舞》入選中國作家協會2022年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出版發行后,引起文學界不俗反響。筆者對詩人進行了一次訪談,除了要進入阿人初的詩歌世界,挖掘出阿人初的創作理念之外,還希望通過他拋磚引玉,認識當前新疆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創作情況。
一、在創作上,決不能“原地踏步”“故步自封”
白哈提古麗·尼扎克(以下簡稱“白”):你好,非常感謝接受這次訪談,同時祝賀你最新詩集《頂碗舞》入選中國作協扶持項目。我們已經很熟悉了,以前有朋友給我推薦過你的作品,你是一位少數民族詩人,用漢語創作,作品內容豐富、深刻,很有意思,值得一看。后來,我看了你不少原創詩歌和翻譯作品。在為《頂碗舞》寫書評的過程中,我進一步深入你的創作世界。正如沈葦老師所說,你“從新疆和田偏遠鄉村里怯生生的小男孩到‘內高班’的成名詩人,從連一句漢語都說不流暢到嫻熟掌握漢語并出版詩集”①阿人初:《頂碗舞》,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頁。,實現了人生的重要飛躍,如今,你成為“甚至比新疆許多同齡的90 后漢族青年詩人、作家都要出色”②阿人初:《頂碗舞》,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頁。的當代青年詩人。你能否向讀者介紹一下自己的創作歷程?童年經歷或者說成長環境,對你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阿人初(以下簡稱“阿”):很高興跟您交流。如果真要追溯一個源頭的話,應該要從上小學的時候說起。我出生于新疆皮山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我們的村子位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上,那是神話與傳說的故鄉,很多神話傳說都是關于無邊無際的沙漠和非常緊缺的水的,我也對那一望無盡的沙漠充滿了無盡幻想。還有,家鄉的月夜十分美麗,滿天繁星,大地上的一切事物,樹木、房屋、道路、農田還有人,都沐浴著柔軟的乳白色月光,清澈的月光讓一切事物都發光。現在回想,文學的種子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播撒在我的心中的。我尚在上小學時,就喜歡看書。當時家鄉很窮,很落后,我們家買不起書,學校又沒有圖書館,所以我努力學習語文教材,能找到的課外書籍一本不漏地認真看,由此開拓了自己的眼界。我在老家上完初中,考上了內高班,去了北京讀高中。高中母校的圖書館很大,我如同久旱遇甘霖般,一頭扎進了圖書的海洋里。而且給我們上課的都是北京優秀老師,我的視野進一步開拓了。以前在老家,我主要看維吾爾文書籍,去了北京后,開始閱讀漢語書籍,漢語水平也突飛猛進,我開始用漢語寫日記。后來,青春的朦朧情愫促使我按照課本上的古詩詞,寫了一些模仿作品,再后來,我開始嘗試寫現代詩,來表達自己因為生活環境變化而產生的心理變化和感受。那時候我開始讀海子、顧城、北島、帕斯等詩人的詩歌。一次偶然的機會,校文學社的指導老師張麗君得知我在寫詩,讓我把詩歌拿給她看。張老師看了以后,給予很高的評價,并把我的作品推薦給其他老師和北京的一些詩人、專家,他們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對我來說這是最初的鼓舞。寫得多了,我開始以一種詩性的姿態審視世界、審視自我。我多說一句,高中母校北京潞河中學是百年名校,學校有很多百年老建筑、百年大樹,由灰、紅、綠三種基本色相輔相成的整個校園如同一個古樸的公園,當“詩和遠方”成為當代人的一種追求,一種奢侈品時,我們作為學子詩意地“棲居”在潞園里,做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求知求學。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我在本子上寫了一百多首詩歌,由張老師整理成冊,有些投稿,詩歌處女作《風的故事》2012年發表在《詩刊》上。后來在學校的鼎力相助下,我出版了首部詩集《返回》。再后來,我的作品先后發表在《人民文學》《詩刊》《民族文學》《詩歌月刊》《草原》《詩歌選刊》《大家》《民族文匯》《塔里木》等刊物上。我想成為一位詩人,所以斷斷續續都在寫,一直到現在。
白:正如你說,你的作品不斷發表在各大刊物上,也獲得了一些獎項,你如何看待他人的評價?他人的評價對你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阿:在信息泛濫的當代生活中,“伯樂”固然很重要,在古代,作品是“口口相傳”,盡管現在作品傳播的載體很多,但好作品需要“被發現”,同樣需要“口碑”,不然很有可能被信息和流量所淹沒。但是,對一個作家而言,最重要的還是作品本身,需要“拿作品”說話。對我而言,寫詩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即我在大地上翩翩起舞的方式,我的詩歌是給自己寫的,也是給那些喜歡詩歌的讀者——閱讀詩歌,至少說明他們是有所思考的——寫的。所以,我對發表作品不是很積極,跟從心聲,把詩歌寫好就是。當然,寫一首詩歌可能需要幾分鐘,但一首詩歌的誕生過程是漫長而復雜的,我需要保持這個過程的連續性。
白:除了作品的發表和獲獎,我還注意到你參加了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習等文學交流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你有著怎樣的感受和體驗呢?這對你的創作有什么影響?
阿:是的,我參加了不少文學交流活動。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觀念形成后,是很難改變的。文學的本質決定了文學/創作觀念的多樣性。跟不同的作家詩人交流,不難發現,他們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我參加文學交流活動,聽名家的演講,與自己的觀念進行比較,不斷豐富我的知識,不斷開拓我的眼界,努力從他們的看法中發現新視點和切入點。這對創作大有幫助。如果仔細閱讀我的三部詩集,創作風格每部都不同。這是不斷學習探索和積累的結果。總之,在創作上,決不能“原地踏步”“故步自封”,因此,作家需要活到老學到老。也就是說,在文學創作中,學無止境,如果停止了學習,其必然結果是“靈感之泉枯竭”,絞盡腦汁也“寫不出一個字”。
白:環顧中外作家的創作生涯,不難發現,他們往往也是某些作家/詩人的讀者,好像你也不例外。你最喜歡哪些詩人的作品?從中受到過什么樣的啟發?
阿:是的,一個作家首先是一位忠實的讀者。這里所謂的“閱讀”,指的不僅僅是文字的閱讀,一個作家必須閱讀生活,觀察人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思考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和人性的起伏,并把所思所想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我讀中外名家的詩歌,也讀微信公眾號里發出來的作品。我一直讀小說比詩歌多。因為在內容的呈現、語言的使用、結構的設計上,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有著先天優勢,如果一個詩人的閱讀只限于詩歌,那他會很容易成為“井底之蛙”;同樣,如果一個作家不閱讀詩歌,那他寫出來的作品是“有氣無力”的。在我的經驗中,在人生的每個階段,喜歡的作家和作品是不一樣的,但一些經典作家和作品永不會過時。至于吸引我的作品,它們一定能夠給我想象的空間,作品的構成要素一定有著與眾不同之處。一個作家剛開始走向文學創作之路時,可能會特別喜歡某些作家,深受其影響,但成熟之后,要形成自己與眾不同的創作風格和個性。只有這樣,才能走得更遠,走得更高。
二、“非遺”的《頂碗舞》:我的詩會帶著我的愛,跳著頂碗舞,去撫慰每個靈魂
白:你的第三部詩集《頂碗舞》入選了中國作協協會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項目“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2022 年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詩集的創作過程是怎樣的?這部詩集與前兩部詩集有什么不同?
阿:我初中畢業便離開位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緣的故鄉,開始了漫長的求學征途,上完高中,接著上大學,兩次考研失敗后,回到新疆,在離老家1500 公里多遠的大城市烏魯木齊定居下來,不知不覺過去了8年的時間。實際上,每一首詩歌都是我在不同時期的心靈史、精神自傳。我在我的創作中,一直探討著“人何為”的問題,并試圖把自己的理解表達出來,這是貫穿所有詩歌的一個內核。在創作第一部詩集《返回》時,我從近乎原始的生活和精神狀態瞬間跨入現代大都市和生活模式中,對我產生的影響還是非常巨大的。當時我在上高中,每每下雨我便跑到校園里的湖邊,泡在雨水中,目不轉睛地盯著一滴滴雨水消失在湖水中,這時我的心是靜的,也是孤獨的。我時常陷入巨大的孤獨中。在孤獨中我看到,我們的生活已經不再純粹了,人類也已經面目全非,人與精神、與物質的關系被割裂,產生了一種真空狀態,人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在此背景下,我寫了第一首漢語詩《絕望的城市》,試圖帶著身上僅有的一切返回,以重塑自己的身份和人類的夢——因為種子在土地上萌芽,而人類的夢延續在每個人身上——在我看來,這也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另一種意義所在。在第一部詩集《返回》中,我試圖返回最初的生命體驗中。我的生命體驗源于故鄉的一切:強烈的陽光、蔚藍的天空、熾熱的土地、純真的身體、輕盈的靈魂,還有緊缺的水、一望無際的沙漠。我愿再重復一次:“信念、土地、沙漠、水、陽光、綠色與生活交織在一起,編織出一種既透視古代又映現未來的雙重畫面,這就是我最初的生命體驗。”①阿人初:《愿每個靈魂都是翩翩起舞的》,《文藝報》2023年2月3日第7版。創作第二部詩集《終結的玫瑰》時,我在上大學,生命的體驗較高中階段有了很大變化,閱讀經驗也有所提升,在追問中我找到了玫瑰——盡管此玫瑰扎根在靈魂里,綻放在詩中,但終究是要終結的——因此,我們需要不停地創作,創作詩歌、小說、散文、音樂、繪畫、戲劇、雕塑。創作第三部詩集《頂碗舞》時,我已經踏入社會,作為一個普通的成年人,這些年來,我結婚買房,經歷著一個普通人要面對的所有風風雨雨。這些年來,我經歷過不少的事情,來來回回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在傳統文化觀念中,在走過的足跡上能夠長出花兒來,是一個人莫大的幸福,因為我們祝福他人時會說“愿在你走過的足跡上長出花兒來”。但是,這段旅途上陪伴我的是愛、反思、語言和不堪重負的靈魂。在我的足跡上,長出的不是花兒——于是便誕生了我的第三部詩集《頂碗舞》。
白:在《頂碗舞》中,每一首詩歌的素材和藝術表達具有獨特性、新穎性和現代性。尤其是首先映入眼簾的書名《頂碗舞》。名字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看上去充滿了濃厚的“非遺”性,又有濃厚的民族特色,你在給詩集起名時,有怎么樣的講究呢?
阿:有一次我們到新疆麥蓋提縣觀看演出。當我看到頂碗舞表演時,一股電流穿過全身——那是我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頂碗舞——那一刻,水、瓷碗、舞蹈、女人、音樂等因素匯聚起來;那一刻,我看到了大地上一切輕盈的物體都在翩翩起舞。于是,我把“頂碗舞”作為第三部詩集的書名,也是想盡一切可能,把異化的、物化的負重不堪的人拉回人的最初的狀態——因為只有靈魂純粹、快樂和輕盈的人,才能翩翩起舞,才能愛。
白:《頂碗舞》的封面設計有著濃厚的民族特色,你能說這個封面的來歷,以及你的感受么?
阿:《頂碗舞》進入出版環節后,在責編發過來的兩套封面設計方案里面都有頂碗舞元素。我把封面發給沈葦老師等人征求意見后,對顏色和舞蹈演員的服飾細節進行了一些調整,最后將具有古代巖畫效果的紅黑二色頂碗舞圖片確定為封面。頂碗舞本身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這個毋庸多言。但是,頂碗舞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與詩歌遙遙呼應,對我而言,詩不僅是詩本身,它還是人類思維的結晶。因此我堅信,無論人生如何跌宕起伏,詩依然會讓我們感受到振奮和鼓舞,把詩的美好傳達給每個熱愛生活的人。我以前也說過,“我的詩也會帶著我的愛,跳著頂碗舞,去撫慰每個靈魂”①阿人初:《愿每個靈魂都是翩翩起舞的》,《文藝報》2023年2月3日第7版。。
白:你認為《頂碗舞》中詩歌有哪些與眾不同的特色呢?
阿:對任何作家詩人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與眾不同的。這也是文學創作的本質要求。至于我的詩歌與他人作品不同的特色,這個問題最好留給讀者去評判,學者去研究吧。我應該做的,就是踏踏實實地把詩歌寫好。
白:在《頂碗舞》中寫了鄉村經驗的詩歌為數不少,如《盲腸與故鄉》《遠方》等。對你來說,“鄉村”對于你的生活和創作有著怎樣的意義?
阿:正如前面所說,我出生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上的一個村莊里,那里的人們很樸實,生活和思想觀念處于近乎樸素狀態。我在那里度過了快樂的童年時光,有了最初的生命體驗。現在我離開故鄉已經15 年了,現在回想,盡管當時物質條件差了一些,但人是快樂的、輕盈的,那種貼近自然、貼近大地的詩意生活狀態是人類最理想的生活模式。這也是最近幾年興起的“返鄉熱”的原因吧。但是,我們一旦離開鄉村,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在文字中返回。
白:再看這部詩集中,不難發現現代意識中的“舞蹈”“愛情”“生命”等意象融入每一首詩歌中,尤其是對“愛”的表達中讀到了一種無限的力量,你是如何構思與完成這種“愛”的?對你來說,這些“意象”究竟意味著什么?對于你的三觀和創作有什么影響么?
阿:當代科技重塑了人類,為人類生活提供種種便利的同時,也導致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就像布滿蟻穴的大壩,處于崩潰的邊緣。當我嘗試用漢語的、維吾爾語的詞語活靈活現地表達詩思,我想用我腦海中的所有詞匯來表達對生活的熱情,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那就是死亡。是的,每個優秀作品的塑造都離不開死亡的話題。詩作為一種追問,當然會追問母親、舞蹈、愛和死亡。我的詩充滿著對生活的探索,因此顯得些許沉重,一首優秀的詩往往取決于詩歌創作人持久的思考,對待大地蒼生的敬畏之心,其中不乏死亡。
三、詩人的工作是創造愛
白:正如沈葦老師說說,你在新疆90后詩人中算是很出色的,你有什么創作習慣嗎?
阿:我剛開始創作時,喜歡用筆寫在本子上。后來,就開始用電腦和手機。我會在腦子里一直思考著,并試著把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表達成詩歌,在最終以文字的形式呈現出來之前,我會經過一個較漫長的醞釀過程,一旦成功把第一句寫出來,那么這首詩歌便會一氣呵成。有時候,我會把突然閃現在腦海中的關鍵詞句記錄下來,運用詩歌形式、結構、修辭等知識,進一步創作出讓讀者認可的作品,不斷激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熱愛。我在寫詩之前,會處于一種持續的亢奮的狀態。我的很多詩歌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寫的,這樣的夜晚我往往會失眠。所以說,寫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白:你讀高中時出版過第一部詩集《返回》,中間隔了幾年時間,去年年底才出版了第三部。社會身份和生活場景的轉變對你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創作過程中是否遇到過一些困難?又是如何克服的?
阿:離開校園后,我開始了角色轉換的過程,對我而言,這個過程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因為在讀書期間我對人類社會只有幻想,對社會的復雜性、運行機制、人心善惡等都沒有明確的概念,對我而言一切都那么美好,可以說我一直活在文學世界里,將自己與現實生活隔離開來。步入社會之后,角色轉換、適應社會等耗費了我大量時間和精力。再者,我面臨談戀愛、結婚、買房等“人間煙火”的問題,同樣耗費了我大量時間和精力。解決這些問題沒有捷徑,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去經歷,去解決。萬幸的是,我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比較成功,生活已經步入正軌,以后按部就班去生活,抽出時間把寫作搞好即可。這些經歷在收錄《頂碗舞》中的一些詩歌中有所反映,但我的整體創作還是以“人何為”的問題為主,表達自己的觀察、思考和反思。可以這么說吧,我傾向于表達“宏大主題”而不是“日常瑣碎”。另外,創作中,有時候需要慢下來,靜下心來觀察和思考,反思所積累的人生經驗。而這些都需要時間的考驗和饋贈。
白:你是理科生,專業跟文學沒有任何關系,你上大學以后怎么堅持文學創作的?遇見了一些對你有影響的人么?
阿:文學創作跟所學專業沒有必然的聯系,它靠的是勤奮和汗水。只要你愿意付出,善于學習,并堅持不懈,文學不會虧待你。我愿意再重復一遍,文學創作是我的一種生活和存在方式,因此,一直在堅持。但需要把現實生活和文學創作的關系平衡一下,因為目前僅僅靠文學創作還不能養家糊口,但這不能影響對文學的熱愛。
白:在《愛的宣言》《深重的愛》《創造愛》等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了一種非常強烈的“愛的宣言”。這樣的結構你怎么想出來的?
阿:我可以大膽大聲說,詩人的工作就是要創造愛。因為愛不僅是人類永恒的文學主題,不僅是維吾爾詩歌最重要的主題,它是命運齒輪的潤滑劑,是我們能夠一直活下去并抵抗無意義的動力。我不能想象沒有愛的人間。盡管以前有很多詩人寫過“愛的宣言”,我也想把自己的“愛的宣言”公布于眾,這完全是一種創作驅動力所使然,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創作活動,就像愛也是一種自然的事情。而我在我的《愛的宣言》中,吸收了中外詩歌中有關愛的一些表達因素,從而構造了自己的愛的世界。
白:在你的心目中,詩人最理想的寫作狀態是怎么樣的?對于未來的生活和寫作創作,你有什么樣的規劃?
阿:最理想的寫作狀態對每個作家詩人而言是不同的,這個從他們對詩歌或者文學的定義中能看出來。而對我而言,最理想的寫作狀態是整個房間里或者整個空間里只有我一個人,聽不見其他聲音,看不見其他人和物。這個時候我會處于一種亢奮狀態,近乎狂躁,這種情況也是難熬的。當把不停地膨脹起來的句子寫出來,心里才會恢復平靜。當前,我邊從事詩歌寫作,一邊在從事文學翻譯,將來,我計劃嘗試一下小說寫作,已經有一些小說提綱和思考。如果說,詩歌寫作是為了在大地上翩翩起舞,那小說寫作是在大地上馳馬試劍。從小說的敘事容量、結構的設計、語言的使用等來看,小說寫作是提升寫作能力、超越自我的一種途徑,我想,我的詩歌創作和文學翻譯已經為此打下了基礎,我必須試一試。
白:十分感謝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做訪談,今天的訪談讓我收獲頗豐,祝你今后的事業蒸蒸日上,再次致謝。
阿:謝謝,也祝白老師學業順利,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