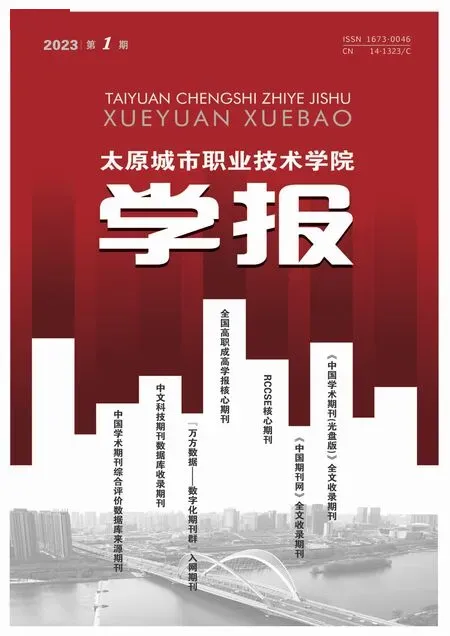論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
■ 謝鑫娟,阿依加馬麗·蘇皮
(新疆財經大學法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隨著商品經濟和大眾傳媒的發展,商業宣傳中使用公眾人物或明星的肖像來推廣自身產品和服務的情形,已隨處可見。在我國,學者關于死者肖像保護的研究重點集中在肖像的精神利益,對于實際案例中出現的肖像財產利益糾紛的關注度不足。《民法典》第993條和第994條分別規定了肖像許可使用制度和死者肖像保護制度,侵害死者肖像,死者近親屬具有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權利,但此種請求權的性質并不確定,死者的肖像是否具有財產利益以及死者近親屬是否享有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請求權?《民法典》第994條對死者肖像保護的規定比較模糊,而司法實務中利用死者肖像獲取商業利益的案例屢見不鮮,如“魯迅肖像權案”“鄧麗君肖像權案”。對于上述問題的研究不能僅從死者肖像精神利益角度出發,而應在司法實踐中發現問題,從現實的侵權類型出發,明確保護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對于維護社會公平具有重大意義,然后結合司法實踐的需求展開理論層面的反思與構建。因此,本文重點按以下思路進行討論:首先在總結司法實踐的基礎上,闡述了我國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的現狀;其次對比較法上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制度進行分析;最后針對我國具體的法律規定,論證用財產權模式來保護死者肖像財產利益,提出了司法適用的具體途徑,即明確死者肖像具有財產利益并可以被繼承、受到侵害時請求權主體以及保護期限。
一、我國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
我國死者人格財產利益保護是通過司法實踐一步一步確立的。1988年,在“荷花女案”①中,一審法院判決被告魏錫林、今晚報社各賠償原告400元,但法院沒有解釋該賠償是精神損害賠償,還是侵權損害賠償;1996年,在“魯迅肖像權案”中,被告未經魯迅之子周海嬰許可,出售鑲有魯迅肖像的筆筒,后原被告在法院達成和解協議:被告向原告補償1.5萬元,但仍無從知曉該補償屬于精神損害賠償還是肖像的許可使用費。張紅教授[1]認為這是肖像的許可使用費,該行為既沒有使魯迅的名望降低,也沒有給其繼承人產生精神痛苦,被告通過利用魯迅肖像來推銷自己的服務和產品,從而進行獲利,也說明,死者肖像具有一定的財產價值,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1999年,王某等訴中國老年基金會北京崇文松堂關懷醫院等侵犯肖像使用權案中,被告醫院未經許可,擅自使用死者孫某肖像的行為侵害了其親屬的合法權益,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②。該判決認為死者沒有肖像權,但死者肖像具有財產利益,可以由其近親屬繼承,商業化利用死者肖像,侵害了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理論上,學者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方式有兩種觀點,第一種是人格權擴張模式,即傳統人格權只具有精神利益,將人格權的內涵擴張后,人格權包含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并且財產利益依附于精神利益。學者王利明認為:“承認人格權中包含財產利益和精神利益兩部分,財產利益可以進行商業利用并作為交易的對象。”[2]人格權其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既相互關聯又相互獨立,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可以被承受,該承受不等于繼承,因為人格權不可以轉讓、繼承。死者近親屬可以對死者肖像進行商業化利用得到相應的財產價值,但是該財產利益不具有財產屬性,不能被繼承;第二種是公開權模式,即死者的肖像財產利益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可以繼承、轉讓。死者肖像上的財產利益并不隨著自然人的消亡而消失,其背后承載的價值來自于本人生前的努力,該財產利益受到法律保護。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并不是保護作為人身識別符號的肖像,而是作為商業利益承載著的一項財產,將死者肖像財產利益類比為一種可以由近親屬繼承的無形財產權。張紅[1]認為:“人格上財產利益應予保護,利用死者生前人格特征獲利之權利為死者生前人格上之無形財產權,應由繼承人繼承取得。”
《民法典》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和學理討論的基礎上通過第994條正式規定保護死者人格,相比《精神損害賠償》中對肖像的精神利益賠償,《民法典》賦予死者近親屬相應的請求權,但是該條款對死者人格財產利益的保護作了模糊處理。民事責任包括財產責任,請求權人既可以要求賠償經濟損失,也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法律法規的模糊性會引起司法實踐中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存有爭議,同時法官在應對相關案件時會遭遇一些困境。
二、比較法上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格權中經濟價值逐步受到法律保護,目前比較法上大多認為,人格權中同時包含精神利益與財產價值[3]。《民法典》第994條沒有明確規定保護死者肖像財產利益,通過了解比較法上的制度,以英美法系為代表的美國和以大陸法系為代表的德國為參考,可以在我國死者肖像保護規定的基礎上設想對其財產利益的保護。美國和德國較早就開始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給予關注,并且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法律保護制度,通過梳理兩國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的脈絡,比較兩國的保護制度,結合我國的司法實踐,可以更精準對我國死者肖像財產利益法律保護模式提出設想。
(一)美國——公開權
美國用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來保護姓名、肖像等人身專屬性質的精神利益,用公開權(the right to publicity)來保護姓名、肖像等人格財產利益。1953年,Haelan案的判決宣告了公開權理論的誕生[4]。1954年Nimmer教授在《當代法律問題》上發表了《公開權》一文[5]。公開權可以被繼承是美國法院保護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前提。1975年的“普萊斯案”中,法官明確公開權與隱私權不同,隱私權不可繼承、轉讓,而公開權可以繼承、轉讓,屬于一種財產權[6]。“馬丁·路德·金案”是第一個涉及公眾人物的公開權案件,佐治亞州最高法院明確表明公開權的可繼承性。美國有16個州在州法律中明確規定了公開權,例如1985年的《名人權利法案》,該法規定繼承人在被繼承人去世后70年內可以繼承其公開權,而紐約州則規定,公開權不能繼承,只能由死者在死前行使。死者肖像上的財產利益可以繼承,具有一定的保護期限。給予死者的保護期限因州而異,對死者公開權的最長承認在印第安納州為100年,在田納西州為10年。除明確決定保護死者公開權的國家外,也有些國家對死者的公開權給予有條件保護,例如,死者死后的公開權,只有具有商業使用公開權的人才會受到保護。
(二)德國——一般人格權
德國法上,對于死者人格利益保護是通過判例和立法確立的。較早涉及死者肖像保護的第一個案例是“俾斯麥遺體偷拍案”③,但帝國法院沒有正面回答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問題,而是通過不當得利制度,判決照片的所有權屬于俾斯麥家屬并沒收照片底片和禁止公開這些照片,因此該案被學者稱為“鴕鳥政策”。隨后,德國于1907年制定《關于肖像藝術與攝影作品著作權法》,突出對死者肖像的保護,其中第22條規定,死者肖像的保護期限為肖像權人死亡后10年,對死者肖像的利用,必須經其親屬同意。在1956年“Paul Dalhke案”④中,法院承認了肖像權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本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其照片用作商業使用,一審法院判決被告賠償原告一定的經濟損失,二審法院推翻了一審判決,改判被告勝訴,終審法院恢復了一審法院判決結果,并認定原告的肖像具有一定的物質利益。在1999年“迪特里希案”中,德國聯邦法院判決表明,死者的肖像財產利益可以由其繼承人繼承⑤。繼承人繼承此項財產利益,應符合死者明知或推知的意思。
無論是以英美法系為代表的美國,還是大陸法系的德國,都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給予了保護,盡管保護的模式不一樣,美國通過“公開權”的方式保護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德國通過擴張人格權的內涵來保護,將人格利益解釋為包括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但兩國都沒有通過立法的形式直接規定,而是以司法判例的形式來確認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公開權具有財產權、可得讓與、得為繼承三個性質[7]。雖然美國各州均在確認死者人格財產利益應當受到保護的同時也對存續期限進行了限制,但對公開權存續期限的規定并不相同,10年、100年均有規定者,多數州認為公開權類似于著作財產權,故規定了50年存續期限。在德國,對死者肖像保護規定在藝術著作權法中,死者死后10年內,其肖像依然受到法律保護,但必須征得所有親屬的同意才能獲得許可使用死者的肖像,同時任何親屬都可以對他人非法侵犯采取保護行動權利。親屬指尚存的配偶、子女,若無配偶、子女,則由其父母。兩國不同制度的規定是經過本土實踐案例中一步一步確定并適用的模式,無論是美國的公開權保護還是德國的人格權擴張保護,都也認可肖像具有經濟價值。美國創設公開權來保護死者人格財產利益在于其沒有一般人格權的概念,對于侵犯姓名、肖像等人格精神利益案件,其通過隱私權來保護其精神利益。德國采用的是擴大人格權的內涵,將財產利益包含在內,但側重于保護死者肖像的精神利益。認可死者肖像具有財產價值,并不是否認肖像背后的人格尊嚴,更不是將其物化,而恰恰是通過保護死者肖像背后的價值來保護人的尊嚴。
三、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的司法適用具體途徑
在實踐中,司法往往最先接觸社會變遷中相關權利的需求,沒有立法的指引,實務中法官造法式的“法律續造”并不能完全適應我國重視制定法的傳統。《民法典》第994條確認了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護,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妥之處:第一,該條沒有區分保護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而是進行了統一規定;第二,該條將請求權主體限定在近親屬范圍內,那么當死者沒有近親屬或者近親屬不愿行使權利時,則死者利益不能得到保護;第三,該條沒有確定保護期限,而是間接將近親屬的生存期限作為保護期限,但財產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不依賴死者與近親屬密切的情感利益而存在,近親屬的生存期限不能完整地保護死者的財產利益。本文結合司法實踐,探索適應我國司法適用的具體模式,提出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條款進行詳細化解釋。
我國應該采取公開權模式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給予保護,采用人格權擴張模式保護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無法解釋為什么死者還具有人格權,與我國現有的關于民事權利能力的制度相沖突。自然人死亡之后,人格權消滅,人格利益也就隨之消滅,無論是人格上的精神利益還是財產利益,都歸于消滅。人格權擴張模式強調人格財產利益依附于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存在,而財產利益也將不復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公開權制度下,可以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進行完全保護,財產權可以繼承、轉讓,使其價值最大化地在社會流通。個人勞動的商業產品應受到法律保護,因為這種法律保護會強烈激勵個人投入必要的時間和資源來提高其價值。在財產理論下,公開權得到更好的承認,該理論將為未經授權的剝削提供報酬,當自然人奉獻了一生來獲得一定的地位之后,讓一個商業企業從其勞動中獲得意外之財將是不公平的,考慮到基本的公平性,確保了繼續防止不當得利,同時作為個人一生中額外的職業激勵,將有價值的財產利益留給其繼承人或受讓人的能力也應該得到法律保護。自然人對自己的宣傳權進行了更多的投資,同樣也應該對這些宣傳權享有更大的利益。因此,法律保護并鼓勵花費時間和資源來發展這些先決條件的技能,同時也向個人保證,他將能夠從這些努力的成果中獲益。自然人死亡后,肖像上的精神利益隨之消亡,還剩下財產價值,故德國法上人格權擴張保護方式對我國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不適用。
(一)確定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具有財產屬性并可以被繼承
《民法典》第994條開放性立法為死者肖像利益留下了解釋的空間,而肖像具有財產屬性是解釋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法律保護機制的理論依據。《民法典》第993條規定了肖像的許可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肖像的經濟價值。就肖像的許可使用而言,除本人肖像外,基于肖像權所包含的財產價值的可繼承性,死者肖像可以由繼承人許可他人使用來獲取經濟利益[8]。根據人格自主理論,自然人可以支配自己的肖像,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具有財產屬性,且可以被繼承,理由如下。
第一,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具有財產屬性。《民法典》第993條規定,民事主體可以將自己的肖像許可他人使用,并因此取得財產利益。如果允許自然人死后,其肖像可以隨意被他人商業化利用,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生者,生前努力所創造的形象價值不能留存給后代,而只能是在社會中消亡。自然人的民事權利始于出生,終于死亡。自然人肖像權在死后并不存在,但肖像客觀存在,死者肖像中的財產利益依然存在,該財產利益具有財產屬性,可以繼承。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支持死者肖像具有經濟價值,在王金榮訴北京松堂關懷醫院一案中,法院明確承認死者近親屬對死者肖像享有特定的經濟利益;在“鄧麗君肖像權案”⑥中,法院酌定賠償經濟損失2萬元。判賠的理論依據是鄧麗君的肖像具有財產價值,并由近親屬繼承,公司擅自使用,損害了這一財產性權益,因此應當賠償,在此后的魯迅肖像案中,盡管以調解解決,但都是給予了一定的經濟賠償。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實務中,法院支持死者肖像具有經濟價值。
第二,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由繼承人繼承,以獲利為目的使用死者肖像,必須征得繼承人的同意,未經其同意,繼承人可以提出損害賠償。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可以繼承,并明確死者繼承人繼承的是一項財產權,更能保障自然人對其人格上財產利益自主決定的權利,也是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繼承人是繼承的是死者去世前對死者人格肖像進行商業利用的權利,還是商業化的經濟利益?《民法典》第994條對死者肖像的保護比較模糊,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實務判例中找到依據。在湖北漢家劉氏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與GUAN-VEN KANDARELI(中文名光文·堪達雷里)肖像權糾紛一案中,一審和二審法院都支持原告請求被告停止使用死者的肖像⑦。試想一下,如果繼承人繼承的僅是一項商業利用后的獲益,那么繼承人是沒有請求權基礎去要求被告停止使用死者肖像,法院也不可能支持原告對被告享有的停止侵害請求權,顯然繼承人繼承的是一項權利,并能夠對死者肖像進行處分。根據《民法典》第992條,人格權不可放棄、轉讓和繼承。我國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自然人死后無肖像權,因此繼承人繼承的是死者肖像的處分權,例如許可使用權,具有可支配性和獨占性。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可以被繼承,當死者肖像被商業利用時,繼承者繼承的是死者肖像財產利益,即對肖像的處分權(如許可使用、轉讓),但同時仍負有維護死者人格尊嚴和保護死者肖像精神利益的義務。此義務的履行可以按照德國對于死者肖像保護的約束,即“繼承人利用死者肖像不得違背死者生前明示或暗示的意思表示”。因此,實務中法院在繼承人作為原告的判決中承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可繼承性。
(二)確定請求權主體
根據《民法典》第994條的規定,在死者肖像受到侵害時,請求權主體要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有一定的順位限制,第一順位是配偶、子女和父母,第二順位是其他近親屬。但此處的順位規定主要是保護死者肖像所承載的精神利益,在財產利益受到侵犯的情況下,繼承人可以在內部協商要求賠償,法律不需要規定每個索賠人行使權利的順序。死者肖像所承載的財產利益由死者的繼承人繼承,當有多個繼承人時,無論請求是由一個繼承人還是由多個繼承人同時提出,都屬于當事人私法自治的范圍,法律無須加以限制。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第25條的規定,侵害英雄烈士肖像所承載的人格利益,如果涉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起訴主體除了近親屬外,還可以是人民檢察院。成立公益訴訟主體,不僅為了保護死者肖像承載的個人利益,更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眾利益和民族尊嚴。權利人生前簽訂了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被授權人在權利人死后是否可以基于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而繼續使用其肖像利益呢?根據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則,被授權方可以在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范圍內繼續履行。如果被授權方超出合同內容,繼承人可以提出防御保護請求權和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主體在繼承順序上,應先按照死者生前的意思表示,通過遺囑或者遺贈的方式,繼承主體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死者生前無意思表示,可以按照法定繼承順序。
(三)確定保護期限
法律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期限并不是無期限的。首先,隨著時間的流逝,死者肖像價值會逐漸減少,進行過長的保護將不利于司法資源的有效利用;其次,死者肖像的財產價值,不僅來自個人的生前努力,也離不開大眾傳媒和社會公眾的參與,過長的保護不利于社會公共利益;最后,繼承人持續對死者肖像獨斷使用,也不利于社會的創新發展。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期限,學理上有兩種觀點。第一,應類推適用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限,即死者財產利益保護期限為死后50年[9]。第二種觀點認為,參照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期限,即死者近親屬的生存期限[10];《民法典》第994條賦予近親屬相應的請求權,該條文顯然是以近親屬的生存期限為死者肖像的保護期限,這會產生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如果死者沒有近親屬,法律是否對其肖像就不予保護?第二,近親屬的生存期限不一致,就導致法律予以保護的期限也不一致,違背了法律平等保護的原則。學者楊巍[11]認為,死者人格的財產權益是可繼承的,對死者人格的侵犯實際是侵害繼承人的利益,對于該利益的保護,不是繼承人的生前期,而是取決于立法政策對這種財產權益的存續期。因此,應該設定一個固定期限,有利于平等保護死者肖像利益。這種無形財產權與著作財產權的性質類似,故參考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限為死后50年,將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期限設定為50年。
四、結語
當然對死者肖像的保護也不是沒有邊界的,其同樣應當受到《民法典》第1020條關于肖像合理使用的限制,特別是在第三人使用肖像是基于公共利益且使用行為在必要范圍內的情形下,不應當認為相關行為侵犯了死者近親屬或繼承人就死者肖像所享有的權益。在“魯迅肖像傳案”中,魯迅作為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去世后所留下的照片不僅為家人所擁有,更因其史料價值而為社會所擁有,進入社會公共領域,讓公眾了解和研究魯迅文化的公共資源。在“溥儀肖像權糾紛案”中,原告以溥儀的近親屬名義向法院起訴,認為被告未經許可將溥儀的照片用在展覽中,侵犯了溥儀的肖像利益,請求停止侵權并賠償相關損失;被告認為溥儀作為歷史公眾人物,其肖像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而成為社會公共資源,公民對此享有知情權,自己的行為是報道活動和傳播歷史,屬于在合理適用范圍之內,不構成侵權,最終法院采納了被告的抗辯理由。
《民法典》第994條規定了對死者肖像的保護,但沒有明確對死者肖像財產利益的保護以及如何保護。實際侵權類型中,多是行為人未經許可對死者肖像進行商業化利用,從而推銷自己的商品和服務來賺取經濟利益;司法實踐中,法院更多偏向于對死者肖像精神利益的保護。立法解釋的缺失引發法院在解決糾紛時出現一系列的困境,而當事人的利益難以得到保障。為了防止出現同案不同判,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為法官公正裁判民事案件提供重要的裁判依據和裁判規則,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出臺司法解釋、發布指導性案例的方式,創設死者肖像財產利益保護的具體裁判規則。
注釋:
①原告陳某是已故曲藝演員吉某(藝名荷花女)的母親,吉病故后,被告魏某以吉為原型,創作小說《荷花女》,于《今晚》報社發表,小說虛構了有損吉名譽的一些情節,其母親起起訴訟,請求被告魏某和《今晚》報社承擔民事責任。
②北京市崇文區人民法院(1999)崇民初字第1189號民事判決書。
③享有“鐵血宰相”之稱的政治家俾斯麥,于1898年病世,兩名記者在夜晚偷偷潛入其家中,為追求最佳擺拍效果,隨意擺動俾斯麥的遺體,甚至將墻上的指針撥動至死亡的時間。隨后,在各大報紙上宣稱,有大量獨家遺照,可以通過高價購買。俾斯麥的家人得知消息后,立即起訴了兩名狗仔,要求歸還照片的底片,禁止泄露。
④VGL.BGHZ 20,345.
⑤BGHZ 143,214-Marlene Dietrich.
⑥被告在演出的地鐵海報、售票廣告、燈箱廣告等眾多位置商業使用鄧麗君肖像。鄧麗君的哥哥鄧長富向北京東城區法院起訴,認為被告侵犯了鄧麗君的姓名、肖像等人身權益,請求賠償經濟損失2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
⑦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終1465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