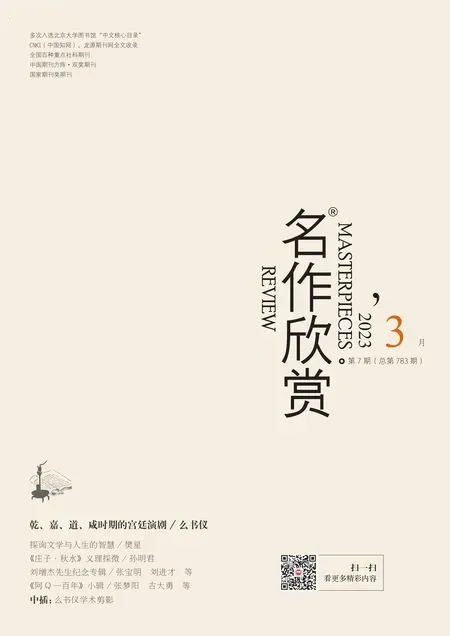關愛陶化二十年
北京 王達敏
2003 年,暗香盈袖的三月,我邁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那道窄門,懷著繽紛的學術之夢。一日,在熙攘的文學所古代室的深紅橢圓桌前,一位長輩靜靜端坐,肅穆而莊雅。這不是我的師母么書儀先生么?我慌忙鄭重趨前,低聲道:“么老師,我是洪子誠老師的學生王達敏,剛來。我拜讀過您的《元代文人心態》。”么先生慢慢轉來,澄澈的眼睛深處,都是干凈和熱情,看了我一會兒,微笑著低聲道:“知道你來了。呂薇芬已經告訴我,北大又來了個傻的。”我一愣,應和似的憨笑著,眼前晃動的,盡是師母早生的華發。
1979 年秋天的一個傍晚,我沿著未名湖畔的林蔭道,做環湖運動。在湖的北岸,灑落著一片銀杏樹,樹林北面自西向東綿延著一脈蒼郁矮山。就在山前林間隙地上,我看見了教我“當代中國文學”課的洪子誠先生,還有年輕的師母,正在揮拍。夕照的霞光從銀杏葉上瀉下,在洪先生和師母騰挪的身影上閃爍,映著明滅的平湖秋光,織成一幅燦爛畫面。多年后,面對二老的滿頭蕭蕭,那幅在我心中從未褪色的畫面,總在腦海浮現。
我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仍然是洪子誠先生,題目也為洪先生所擬——“論汪曾祺的小說”。汪曾祺深受桐城派淘洗,筆觸氤氳著一團古雅風韻。一個研究者學術方向的選擇,冥冥之中也有定數。后數十年,我陷入桐城派論題而不能自拔,也可謂命中早已注定。1983年夏初一天,我和同學穿越勺園一塘田田蓮葉,走過蔚秀園內搖曳生姿的垂柳,來到27 樓313 號洪先生的家,接受論文定稿前的最后一次誨導。師母打了個照面,就不見了。我當時的感覺:師母好高冷。
再見師母,就是那次在古代室的深紅橢圓桌前。從2003 年春至2023 年春,這二十年間,么先生對我關懷備至,許多生動的片段和美麗的場景刻在了我的心靈深處,成了我永遠的感動。
么先生住藍旗營,在東;我住燕東園,在西。營和園之間,只隔了一條通往圓明園、頤和園的路。路的兩邊矗立著碧森森的白楊樹,樹的近旁栽植著各種灌木,點綴著各色小花。道狹且長,幽深而安靜。么先生在這條道上散步時,常常會踱到我家。我的那個家,兩小居,使用面積不足42 平方米,住著三代五口人,還堆疊著好些書籍,雙腳倒還是下得了的。么先生好像從來對寒舍之寒渾然不覺,每每挨著書桌坐定,慢啜粗茶,論學,憶舊,談家庭,談人生況味,時而舒展,時而低昂。沉浸在么先生的言說所營造的氣氛里,我亦寧靜,亦激動,亦憤懣。每當么先生的講談達于出神入化那一瞬,我就仿佛自家的屋舍也不寒了,空間也不窄了,胸次也頓時灑脫豁亮起來。
一次,么先生來了,氣喘吁吁,命我趕快將她肩頭的掛包卸下。么先生年輕時候本來體質還好,干活從來不惜力,木工手藝尤其出色:會鋸、會刨、會鑿又會漆,但在新疆奇臺農場時,不幸患上風濕性心臟病。如今這掛包沉甸甸的,如何禁得起?喘定后,么先生說:“給你帶來一個筆記本電腦,多一臺電腦處理材料方便。這個筆記本沒怎么用過,你試試。”我一試,很靈,從此工作效率顯著提高。后來,我的侄兒在大學需要電腦,我就把這臺筆記本電腦送給了他,他的學習條件得到了改善。
一次,么先生未到,電話先到了。電話那頭傳來斷續的聲音:“達敏,來幫一下,在北大附小東門。”北大附小的東門,就開在那條幽深道路的西側。我急急出門,老遠瞅見,么先生倚著一株大白楊。近前,么先生擦著額頭的大汗說:“都是你們洪老師,只顧著忙他自己的。”原來,么先生見三伏天,我們和女兒還鋪著棉褥,就起心將家里一張新席送給我們。這席子可比電腦包沉重。洪先生正忙,一時騰不開手相助。么先生就不顧天熱,毅然上道,結果拋錨中途。我濕潤著眼睛,搶前扶住了么先生。那張大席展開,翠竹細細,淡金色綢緞鑲邊,委實漂亮。我們哪里舍得用,一直珍藏至今,成為永久紀念。
還有一次,么先生一進門就開顏道:“達敏,你想要的在這里。”我趕緊捧過來,是一條純毛圍巾,不禁一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懷著虔敬,心心念念想請到洪先生素日戴的那條圍巾,希冀借得老師靈氣一縷,時時激勵、警示自己。但洪先生說:“舊的怎么可以?”因而,二老賜予的這一條,是嶄新的。
2020 年春節期間,在臺灣上大四的女兒回來度假,因疫情被封在了家門。她如何畢業,如何申請攻讀碩士學位,已在未定之天。洪先生和么先生曾在臺灣講學、游歷,對那里有深切了解。早在2016 年夏,經二老點撥,女兒最終報了臺師大英語系,并被錄取。中小學階段,女兒演習京劇六載,上大學后又喜歡上莎劇,所以一心想入臺大戲劇所上研究生。我對此茫然,只能請教戲曲研究權威么先生。么先生一聽女兒想修習戲曲,非常歡喜,立即行動起來:與臺大戲劇所的專家溝通,介紹女兒資質;琢磨女兒的材料,寫下周至的推薦書。感人至深的是,么先生撰寫的這份推薦書,既經洪先生字斟句酌,也有師妹洪越博士添上的筆墨。女兒最后雖未能如愿,仍留在臺師大深造,但二老和洪越博士的一番苦心,則令我們永遠銘記。
2003 年春至2023 年春,這二十年間,么先生影響我最深的,是學術。她以良史之筆,寫心態史,寫戲曲史,寫家族史。其輝煌的著作,令我欽敬,是我潛心學習的楷模。受么先生熏陶,我也喜歡上了京劇,也愛閱覽有關文獻。不知多少次,我甚至萌生出研治戲曲之念。
么先生是職業學者。她說:“我喜歡這個職業:看書、發表論文、著書立說都是我的向往。”“我喜歡文學所的不坐班:一個星期到所一次,借書、還書和拿信,這樣可以有大塊的時間看書不受干擾。”“我很努力,不甘人后。進了文學所后,我每天的上午、下午和晚上三段時間都趴在桌子上看書、寫卡片,每天過得都一樣,我的日子里沒有了節假日、暑假和寒假。”辛勤勞作的結果,就是一部部光耀學壇的著作。
么先生是一位創造力很強的學者。顧炎武認為有魅力的研究論題,必是“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么先生的每個選題正是如此。在她涉足的幾個學術領地,地上本沒有路,是她披荊斬棘,開疆拓土,才使舊貌換上了新顏。她的《元代文人心態》1989 年竣工交稿。該書在學界最先從心態史的角度,探討文人在異族統治下復雜的精神世界及其文學史意義,對于具有同樣背景的北朝文學和清朝文學的研究尤具啟發。她的《晚清戲曲的變革》撇開流行已久的以戲曲文本為中心的研究范式,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探討晚清戲曲的變革,一新學人耳目。她論斷“宮廷戲曲對于整個清代戲曲的興衰變易,無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她研究“明清男旦的興衰”“晚清戲曲與北京南城的‘堂子’”等專題的創獲,精彩絕倫。該書已成學術經典,其所達到的高度,在近代戲曲研究界至今無人超越。
么先生下功夫最深的是羅掘資料。首先,她對研究論題所關涉的紙質文獻力爭竭澤而漁。為撰寫《元代文人心態》,她從文學所將一部一部元人文集往家里扛,將一摞一摞卡片和稿紙往家里背。她也時常穿梭于京城各家圖書館之間,借書還書,伏案閱讀。一年有半,單是她抄錄的卡片,就裝滿了七大盒。其次,她特別看重口述資料。為撰寫《尋常百姓家》,她協助雙親錄制的磁帶就達三十六盤之多。為了辨證雙親留下的口述資料,她還不厭其煩地去查考文獻,找知情人反復核對一些事件發生的具體日期和細節。昔者,司馬遷撰寫《史記》所用的史料既有文字載記,也有調查訪談所得。么先生在資料搜求上的殫精竭慮,正與太史公所開辟的史學傳統一脈相承。
么先生將自己的人生閱歷和體驗全部揉進了她的著作,她的著作因之成為“這一個”而獨步學壇。么先生的父親酷嗜京劇,年輕時勁頭十足地追星,曾請名滿京城的時慧寶題寫扇面,曾乘坐火車千里迢迢趕往上海只為欣賞楊小樓演出;年長后還與兒子為譚富英、楊寶森的高下而爭得面紅耳赤。么先生的兄長最愛楊寶森,以為其嗓音之美猶如云遮月,在大學經常粉墨登場,出演的楊派名劇包括《四郎探母》《群英會》《李陵碑》等。因有這份家族性遺傳,么先生上高中時就喜歡上了京劇,先“粉”馬連良,后迷梅蘭芳和張君秋,每天守著收音機跟學“教唱京劇選段”,一跟就是好幾年。在北大,她與研究京劇的名家吳小如先生對唱過《打漁殺家》;與金開誠、裘錫圭兩位行家一起表演過《沙家浜》;在辦公樓禮堂清唱《二進宮》時,一聲“你道他無有篡位的心腸,封鎖昭陽為的是哪樁”唱下來,臺下雷鳴般的掌聲竟然嚇了她自己一跳。在新疆,她到連隊,到農村,到吉木薩爾縣城,唱《杜鵑山》,唱《海港》和《龍江頌》。京劇藝術浸入骨髓,早已化為了她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晚清戲曲的變革》《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清代至民初京師戲曲的輝煌》的誕生。沒有舞臺經驗的學者也可以研究戲曲,但么先生劇內論劇,更比別人多出了一份激情、微妙和深刻。在《尋常百姓家》中,么先生投入巨大心力,以驚采絕艷之筆,將么家數代人的奮斗,將雙親和自己經歷過的悲歡離合、輾轉際遇,一并帶進20 世紀中國的歷史書寫之中。
么先生在學術研究中,一貫堅持知識分子立場。她對“知識分子”概念有過清晰界定:“按照現代西方學術界的看法,‘知識分子’主要不是指有一定知識,并以某種知識技能謀生的那部分人。他們傾向于從社會職能的角度來定義‘知識分子’,認為只有那些超越一定的社會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富于使命感,作為社會良心的代表,企圖以自己的思想、人格給社會以影響、啟示的人,才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堅持知識分子立場,使么先生的人生道路平添幾多曲折,卻也成就了她的人格和學術。在《元代文人心態》中,明知那群文人不能不有所依附,但她仍然竭力揭示出他們對道與義的信仰及其由此所做出的奮斗與犧牲。這一揭示為建構當代知識者的現代性提供了傳統資源。
我愛讀么先生、洪先生和洪越博士為《尋常百姓家》撰寫的三篇序言。洪越博士說:“在姥姥姥爺的講述中,早已有了不同的視角,再加上媽媽自己的角度,在一本書中,我們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在正文現有三種聲音的基礎上,三篇序言對正文又進行了補充,并做出新的闡釋。而三篇序言之間又構成互釋關系。三位學者的言說涉及一個頗具深度的理論問題:史家呈現歷史真實的限度。讀罷三篇序言,我意識到,么先生追求歷史真實時,遇到了多少困難,為克服這些困難又耗去了多少精力。
么先生自1981 年登上學壇后,一直蝸居書齋,只問耕耘。20 世紀90 年代,鄧紹基、陳毓羆、李修生、寧宗一和徐朔方等前輩稱譽《元代文人心態》不容口,但比起那些墻內開花里外香的學者,么先生終究是寂寞的。進入新世紀,早先問世的《元代文人心態》,連同后來付梓的《晚清戲曲的變革》《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清代至民初京師戲曲的輝煌》和《尋常百姓家》等,一版再版又再版,供不應求。其中,后三部作品還走出大陸,去了臺灣。2022 年11 月,在北京,么先生的學術高光時刻,沒有預兆地到來:12 日,在中間美術館,李浴洋博士主持召開關于《尋常百姓家》的討論會,會議從下午兩點一直延續到新月在天,出席者有黃子平、夏曉虹、楊聯芬、賀照田、賀桂梅、周瓚、陳均、黃文倩、袁一丹、吳丹鴻、盧迎華和石巖等;18 日上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文學所古代室、當代室聯合舉辦《尋常百姓家》新版發布會,會議由鄭永曉教授主持,線上線下,出席者主要有劉玉宏、安德明、吳光興、李超、田美蓮、楊早、劉倩、李芳、薩支山、朱曦林和王達敏等。兩場討論會上,專家們從各自視角,論述了《尋常百姓家》的特色和么先生在文人心態、戲曲研究諸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回首么先生的學術生涯,涌上我心頭的,是杜甫的詩“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詩賦動江關”;是韓愈的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么先生是最孝的女。平日里對雙親噓寒問暖,病床前奉羹進藥,自不必說了。么先生的大孝,是在另一層面。她接過由雙親傳下來的家族世代相守的生活倫理,虔信善良和誠實、責任和自尊、羞恥心和不懈的勤勉等人生價值永恒不變。么先生之母出身望族,雙親在艱難竭蹶中仍然支持子女攻讀,為的就是使子孫能回歸書香門第。么先生為實現雙親的理想,數十年焚膏繼晷,以追求學術真理為職志,崇尚獨立與自由,終于取得不朽成就,與洪先生、洪越博士一門風流,成為當代學壇的一段傳奇。這,正是她對雙親最神圣的獻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