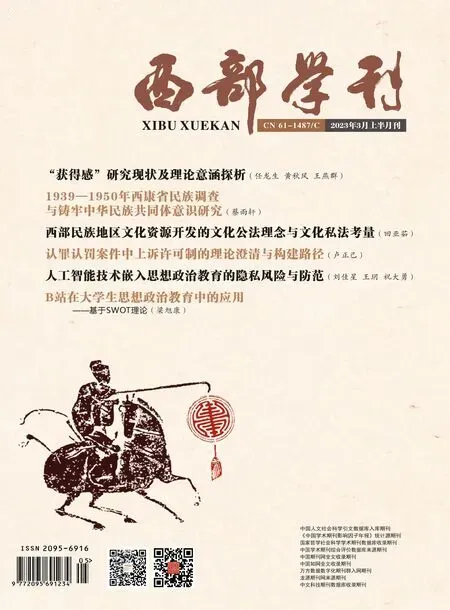清代海關漢人監督制度探究
——兼論粵海關初置首任漢人監督成克大
曾志遠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起,清政府陸續開設粵、閩、浙、江四省海關管理對外貿易,最初派遣滿、漢監督各一人,至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改為僅差一人。也就是說,粵海關漢人監督①一職共設立了四年時間。粵海關監督作為粵海關的主管,負責征收海稅、管理粵省對外貿易,學界對其多有研究,且成果豐碩。彭澤益對雍正時期粵海關監督與行商的勾結及貪污案進行專門研究[1]110-144;金國平[2]對粵海關監督別稱之一的“Hopo”一詞進行了細致考察;陳國棟對粵海關監督的身份、任命、就職等情況及其與廣東地方官員的關系作了大量研究[3]3-65;任智勇[4]重點論述了道光、咸豐兩朝粵海關監督的出身與任期;羅亮亮[5]分析了清前期政府對粵海關監督的監察制度;在章文欽關于澳門史的研究中,提到第一位漢人監督成克大與廣南韶道勞之辨巡視澳門一事[6]。此外,還有大量學者在粵海關與十三行的研究中涉及對粵海關監督角色與功能的論述。然而,前人研究多集中于康熙朝以后的粵海關監督,對設關之初出現的漢人監督一職則鮮有涉及,僅在追溯粵海關監督制度淵源時提及設關初年派有兩名監督,尚未有專文對康熙二十四至二十八年的粵海關漢人監督一職的設廢緣由、第一任漢人監督成克大在任期間參與的事務進行研究。粵海關漢人監督這一官職雖然只存在了四年,但其作為粵海關監督制度的一部分,值得加以研究。本文通過梳理粵海關漢人監督的相關史實,探討這一制度的設廢緣由,及首任漢人監督成克大在任期內所擔任的各項職責。
一、粵海關漢人監督一職出現的原因
在設立粵海關以前,清政府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為市舶司,設立海關后,改派稅關監督進行管理。要說明粵海關漢人監督一職出現的原因,首先要對清政府為何以稅關監督取代市舶司進行解釋。
滿人入關之初,對沿海居民出海經商并未明文禁止,而是沿襲明末的貿易制度[7]。在廣東地區,專門設有市舶提舉司對貿易進行征稅,“粵東向有東、西二洋諸國來往貿易,系市舶提舉司征收貨稅。”[8]449為防止東南沿海居民通過海路接濟抗清勢力,清順、康二帝于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十三年(公元1656年)及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年(公元1665年)、十四年(公元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7]。日益嚴格的禁海政策,不可避免地對市舶司職能的履行造成影響,最終導致其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被裁并,對外貿易由廣東鹽課提舉統一管理[9]。至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三藩平定,東南沿海地區真正被納入清朝版圖,清帝順勢同意了西洋貢使本多白勒拉的請求,準許澳門與香山于關口進行陸路貿易[10]212。為此,清政府復置市舶提舉,由吏部郎中宜爾格圖任市舶使[11]。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臺灣戰事結束,清帝開始計劃開放海禁,發展對外貿易以資國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閩、粵二省率先籌備設立海關,并“設滿、漢海稅監督各一人”[12]6289管理收稅事宜。至此,清政府對外貿易的管理制度完成了由市舶制度向海關制度的轉變。以粵海關代替舊日歷代管理對貿易稅項的市舶提舉司制度,可以說是清代對外貿易在關務制度上進行改進的第一步[1]56。
首先,市舶提舉司制度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清政府之所以將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改為榷關,是因為市舶司經過清初多次設立與廢黜的變更,已不能滿足清朝中西貿易管理的現實需求[13]。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以前,朝貢貿易是當時唯一合法的海外貿易形式[14],管理朝貢貿易就成了當時市舶司的主要職能。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復置的市舶司僅僅負責澳門陸路貿易貨稅的征收。康熙帝對開海貿易寄予厚望,他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曾兩次發布諭旨進行說明:“海洋貿易,實有益于民生”[15]“開海貿易,謂于粵閩沿海一帶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各省俱有裨益”[8]151。可見,開放對外貿易,一是為了滿足沿海商民的貿易需求,緩和社會矛盾;二是為政府開辟新的稅收來源,若繼續沿用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顯然難以達到清帝的期望。
其次,由海關負責征稅更符合清政府的利益需求。市舶司和海關雖然都有征稅的職能,但二者所收稅銀的去向有所不同。市舶司官員多由地方官員兼任,其貨稅收入多被地方官府直接使用[13]。清代海關是隸屬戶部的榷關,負責征百貨稅,以資國用[16]359,其所征稅銀上繳戶部。就粵海關監督來說,其完整職稱為“督理廣東省沿海等處貿易稅務戶部分司”,是由戶部派駐在廣東省負責收稅的司員[3]4。也就是說,海關監督由清廷派出,其所征貨稅直接解交中央政府。相較之下,把征收對外貿易貨稅的任務交給稅關監督負責,更符合清政府加強中央集權的要求。
既然海關的設置源于榷關,海關監督自然參照榷關官員進行派遣。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對榷關關差的任命亦幾經調整。總的來說,主要經歷了入關之初的專差漢司官,到順治時兼派滿洲、漢軍、漢官,最后到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不論滿洲、漢軍、漢人,每關差司官一員三個階段[16]364。從這方面來說,粵海關設立時本應只差一官進行管理,雖然漢人也有機會出任,但不是必占一缺,而清帝卻特令“設滿、漢海稅監督各一人”。這或許是因為清政府雖然在內地榷關收稅方面積累了相當的經驗[13],但對于海關設立后的管理沒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參照順治時期的辦法,將關差交由熟悉情況的戶部漢司官管理[17],同時為了防止稅務獨攬于漢人,另派一滿人監督進行制衡。最終,就出現了粵海關漢人監督一職。
二、成克大在任期間參與的事務
在粵海關漢人監督一職存在期間,擔任過此官職的只有成克大一人。史籍中關于成克大的記載并不多,記錄其擔任海關監督的內容則更加少見,現以筆者所見的史料對成克大擔任粵海關監督期間參與過的事務作一略述。
成克大,字子來,直隸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縣)人,“時創設粵海關,克大受命監督。過里門受教,兄少傅克鞏曰:‘勿厭清貧。’”[18]601在任期間,其主要事跡有參與海關稅收制度的確立與完善、管理對外貿易稅餉征收、處理與外國人相關的案件、巡視澳門等。
其一,參與海關稅收制度的確立與完善。開關之初,粵海關在對外貿易征稅方面的制度還處于比較混亂的階段。如澳門陸路貿易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停止,但市舶司征收的“旱稅”直到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仍未取消,而由粵海關已經開始征收“海稅”。此時“到粵洋船及內地商民貨物俱由海運直抵澳門,不復仍由旱路貿易”[10]214,實應只征“海稅”而取消“旱稅”,不然重復征稅之下,必會打擊商人的積極性,從而影響海關稅收。面對此種情況,成克大會同滿人監督宜爾格圖、巡撫李士禎、總督吳興祚合上《請除市舶澳門旱路稅銀疏》[10]211-216,以期貨稅征收更為合理,以通商路。再如粵海關初創之時,對貨物征稅時“住、行二稅不分”[10]729。住稅即外地運來廣東地區發賣貨物應納之稅,行稅則是外洋進口貨物及外地運來廣東出口貿易貨物應繳貨稅,如不加以區分,商人有重復納稅的可能。為此廣東巡撫李士禎特發布告《分別住、行貨稅》曉諭商人,而成克大所在的關部亦應“給示通飭”[10]730。
其二,管理對外貿易稅餉征收。粵海關本就為取代市舶司對貿易征稅而設,“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候出海時洋商自赴關部(粵海關)納稅”[10]730,“船舶稅務奉有欽差吏部郎中宜(爾格圖)、戶部員外郎臣成(克大)臨粵監督管理”[10]213-214,成克大作為粵海關監督參與其中事務自不必說。
其三,處理與外國人相關的案件。廣東南韶連道勞之辨在其《自序》中記有一事:“乙丑(康熙二十四年),初設海關,額未定。商人仗新榷立威,乘澳夷演炮誤觸其船,以夷人劫貨傷人起訟端。”[19]672-673澳門葡人的商船在演習開炮時誤傷華商船只,華商卻借題發揮,稱葡人企圖劫貨傷人,向官府提起訴訟。為此成克大與宜爾格圖、勞之辨共同前往澳門處理此事,最后以澳葡賠償華商三百兩修船銀結案,結果“夷人扶老攜幼送及關,感激涕零而返。自此商舶、澳夷兩相貼服”[19]673。此外,還發生過華商激怒澳門葡人,向成克大求救,亦被他妥善解決,“鬼卒蜂擁至門不可測,克大神色自若,手繳通釋,集酋長,責以大義,事遂解。”[18]601粵海關到澳門設立關部行臺時,還發生過澳門葡人唆使一批葡兵前來鬧事,亦是由粵海關監督負責處理[20]。
其四,巡視澳門。開關前的陸路貿易時期,澳門與香山的陸路界口成為唯一的中外貿易場所,澳門葡萄牙人借此基本上壟斷了這一時期的中外貿易。開關后,澳門葡萄牙人喪失這一特權,清政府亦加強對澳門經濟的管理,引起了澳門葡人的強烈不滿[20]。在此背景下,成克大初次巡視澳門時澳門葡人的態度并不友善。《大名縣志》有載:“粵之香山澳為洋人所居,名為鬼卒,俗尚火攻。其酋長率隊來迎,刀劍森列,嚴若勁敵。克大宣上威,群皆懾服。”[18]601文中所說的居住在澳門的“鬼卒”,就是葡萄牙人。由引文可見,成克大這次巡視澳門時,或是因為上述緣由,澳門葡人對這位粵海關監督幾有刀劍相向之勢,而成克大并未被嚇到,反以“上威”使葡人懾服。此外,《國朝畿輔詩傳》[21]還收有成克大三首與巡視澳門相關的詩作,分別為《仲冬赴澳》二首及《濠境即事》,前兩首為抒情之作,后一首則記載了他在澳門的一些見聞。可見,成克大不止一次到澳門巡視,《大名縣志》所記載的應該是成克大就職之初巡視澳門的情形。
澳門史研究專家黃啟臣指出,澳門關部行臺創建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漢人監督成克大巡視澳門之時[22]。但清帝于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6年)議準“四省海差,一年更代”[12]6290,根據閩、浙、海三省海關所在地方的地方志,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起各海關滿、漢監督的任期都變成了一年[23]1195[24]4989-4990[25]4977-4978。《粵海關志》《廣東通志》的《設官》《職官》卷對于成克大任粵海關監督一事都沒有記載[8]123-124[26],《大名縣志》只記載了成克大任命的時間,并未說明其卸任粵海關監督的具體時間。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清政府停止了向海關同時派遣兩位監督的做法,而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成克大仍以海關監督的身份前往澳門設立關部行臺。成克大連任四年粵海關監督的具體原因暫時不得而知,但在漢人監督一職設立的這段時間內,粵海關的漢人監督只有成克大一人。
三、粵海關漢人監督的停派
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對海關監督任期作出調整后,康熙帝于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再諭“嗣后海差著各差一人”[12]6290,此后除浙海關仍時差二員、時差三員外,其余三省海關都只差一員。清帝的這一次調整,既是為了避免重蹈之前的覆轍,也是出于對現狀的考慮。
首先,對榷關關差的兼派曾造成許多問題。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改直省關差“專差戶部漢司官一人”[12]6286為“增設滿洲官一員、漢軍官一員”[27]2046,關差人數的增加導致“書吏多行不法,甚至沿河盤貨,商賈畏縮不前”[27]2046。除了關差所帶書吏的行為影響了商貿,不利于收稅,關差本人亦有不當之處,“榷關之設,原有定額,差一司官已足,何故濫差多人?忽而三員,忽而二員。每官一出,必市馬數十匹,招募書吏數十人。未出都門,先行納賄。”[8]2于是在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又改回“各關專差漢官,每關一人”[12]6286。可見順治時期就出現過因為差官過多而導致商路阻塞和關差納賄等問題。康熙即位后,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題準各關兼差滿漢官筆帖式各一人,六部各咨送滿漢官筆帖式各一人輪掣”[12]6287,部分恢復了滿漢兼差的做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將各關稅交給地方官管理;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覆準各關仍令六部滿漢官論俸掣差”,對關差的派遣進行調整,最終恢復了滿漢并差的做法[17]。這樣一來又出現了“商賈以鈔關為第一大害”[28]2543的情況,其原因仍是“官多役多事多”[28]2543。故有官員指出,關差“或滿或漢,止差一官足矣。若必滿漢并差,多官則多費,多費則多加派,其勢然也”[28]2543。于是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清帝再次對關差人數進行調整,“不論滿洲、漢軍、漢人,序俸掣簽,每關差漢司官一員。”[29]5077粵海關各口亦“由監督及兼管關務之督、撫分派家人帶同書役管理”[8]117,這里的“家人”即與此前關差所招募的“書吏”類似,負責管理監督所不能顧及的除省城大關、澳門外其他五個總口所轄的諸小口的業務[3]51,這就難免重復此前的情況。
其次,隨著粵海關對外貿易稅收、管理等制度日漸完善,“督理榷關,不過照額征收,本無難事”[28]2543,已不需要同時派遣兩位監督進行管理,但海關監督相對于內地榷關關差而言,除同樣負責貨稅征收外,還要面對前來貿易的外國人。在“華夷之辨”觀念的影響下,清政府的官員并不希望直接與“外夷”交涉。于是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春夏之間,粵海關建立起洋行制度協助外貿管理,即后來的十三行制度[1]58-60。洋行行商需要將進出口貿易貨物的貨稅在洋船出海前交到粵海關[10]730[30]88,這既減輕了粵海關管理壓力,也減少了監督與外國人的接觸。稅收上,貨稅方面,前有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照關差例,差部院賢能司官,前往酌定則例”[8]151,后有李士禎等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發布公告將住、行貨稅分別征收[10]729-730,初步奠定對貿易貨物的征稅方式。除貨稅外,粵海關另一項重要稅收——“船鈔”的征收也已經明確下來[30]87。在這種情況下,各海關只差一名監督也能管理好對外貿易事宜。
最后,將海關監督裁去一人與清帝希望增加滿人在稅關的占比從而加強對海關稅收的控制也有很大關系。需要注意的是,清初清政府就形成了偏重于任命滿官掌管榷務的傾向[16]364。從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開始,清帝就陸續將張家口、殺虎口、潼關、山海關、鳳陽關等榷關改為只差滿官一人[12]6287,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規定榷關關差派遣在六部司官論俸掣簽外增加中央各衙門均分差遣[12]6290。這樣一來,漢人擔任關差的機會無疑被大大降低了。對于新設的四省海關,最初規定派遣滿、漢監督各一人,也就是各海關中必有一漢人監督,這顯然是與康熙此前的政策相左的。除了在康熙二十四至二十八年(1685—1689年)在四省海關派遣兩位監督外,清朝基本上停止了對榷關兼差[16]364。康熙曾將所有關稅交與地方官管理,而后在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規定“關稅多者將各部院賢能滿漢官員差遣,關稅少者仍交地方官征收”,張家口、殺虎口二關分別以稅額一萬兩和一萬三千兩躋身“關稅多者”之列②[29]5075-5077。對比四省海關,粵海關定額九萬一千七百四十四兩五錢③[8]281,閩海關定額六萬六千五百四十九兩五錢四分[23]504,浙海關定額三萬二千余兩[24]3626,江海關定額二萬三千一十六兩三錢三分[25]3898,均遠超稅收較多的內地榷關。定額是清政府對榷關稅收潛力的一種估計,面對稅收潛力如此之大的四個海關,清政府想把漢人從中排擠出去也就不難理解了。
四、結語
總的來說,設關之初派遣滿、漢監督各一人不過是清政府出于對開海后新形勢不確定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在對外貿易的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四海關展現出巨大的稅收潛力后,清政府就決定裁去一人,漢人擔任海關關差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也是清政府偏重任命滿人掌管榷關這一傾向的延續。歷時四年,粵海關漢人監督一職即宣告廢止。
注 釋:
①本文所論述的粵海關漢人監督是康熙二十四至二十八年滿漢兼差時相對于另一位滿人監督而言的,與康熙二十八年后以漢人身份擔任粵海關監督的漢人監督不同。
②在抽稅溢額議敘制度下,關差所征稅收超過規定額度會有加級、優先差遣等獎勵,若按極端情況計算,此二關稅收可能達到一萬五千兩、一萬八千兩以上,但絕不會經常發生。
③后經康熙二十七年、三十八年兩次調整,仍有四萬兩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