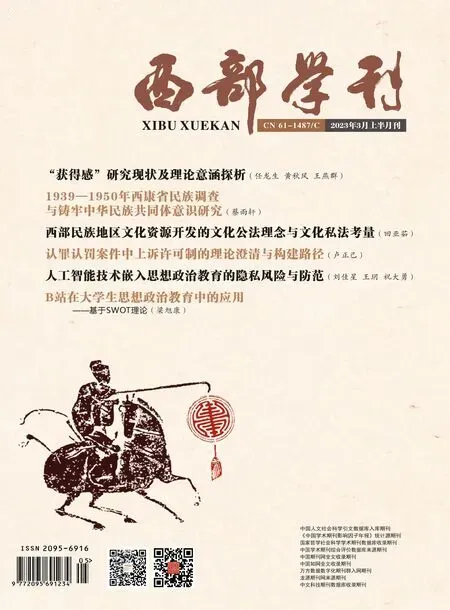清代揚州水利治理中鹽務與民生的矛盾及解決措施
汪杏莉
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小農經濟社會,農業是國家的頭等大事,關系賦稅征收和王朝的穩定。因此,歷朝歷代各地都十分重視農業問題。農業的發展仰賴水資源,歷代統治者都大力倡導興修水利設施,以達到防洪治河、灌溉農桑和保證農業生產、百姓安居的目的。與其他絕大多數城市相比,位于長江與大運河交匯處的揚州,農業水利治理在國家水利治理中卻退射一箭之地,保障漕、鹽運道的水利治理反是首要之務。在揚州水利治理的過程中,存在中央與地方、漕運與鹽務、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與地方社會等多角度的復雜矛盾。關于清代揚州境內水利治理研究成果較少,且人們的關注重點在水患治理,對水利治理引發的各方矛盾以及解決措施則甚少提及[1-3]。本文以清代揚州府境內水利治理為中心,對清代政府與地方社會的治理做考察,以期還原當時揚州地方社會史,填補相關研究盲區。
一、清代揚州水患情況
揚州境內河湖眾多,沿大運河東西兩堤,以西為上河,東堤以東為下河,上河有白馬湖、邵伯湖等湖泊十七個,下河有射陽湖、廣陽湖等湖泊三十六處,“統計下河之地不下三十萬頃,為田者十之四,為湖者十之六。”[4]這些大大小小的河、湖串接大運河,溝通黃、淮、長江三大水系。黃河、淮河泛濫時,與洪澤湖相通的寶應湖、高郵湖、白馬湖等承擔宣泄洪水的任務;運河干涸之際,邵伯、黃子、赤岸、朱家、白茆、新城、艾陵諸湖,又是引水濟漕的重要水源。泰州、興化境內的三汊河、角斜河、蚌沿河、得勝湖等串聯各鹽場,是淮鹽出場的運道,因此又名串場河。兩淮各鹽場南北運鹽渠道大致有六條:“自淮安歷寶應、高郵抵揚州至儀征為漕鹽運河;自揚州灣頭分支入閘,東經泰州,歷如皋抵通州為上河;高、寶以東,泰州以北,興化、鹽城之境陂湖演迤,眾水匯注,則為下河;上河自如皋南折而東達通州十場,是為通州串場鹽河;下河自泰州海安徐家壩,下起歷富安等十二場,至阜寧射陽湖出口為泰州串場鹽河。”[5]140
特殊的地理條件使得揚州境內各州縣防洪壓力較運河下游其他各府州更大。一是形如釜底的地理地貌。光緒時的《泰州鄉土志》描述泰州“州境之北界興化至凌亭閣七十二里,東北至東臺武卞莊四十里,西北到高郵州一百五十里,此三面均屬下河,形如釜底”[6];興化方志言及本地地形:“地勢四面皆高,形如釜底”[7];靳輔在回答康熙皇帝詢問河工時提及揚州“洼下如釜”。這種地形使得揚州境內水道極易產生泥沙淤墊,河床日漸增高,“自邵伯而北,歷高郵、寶應,由山陽、安東皆受湖患,而城低于堤者丈有四尺。”[8]充沛的水源、復雜的地形因素,加之明末敗政河工廢弛,導致清初揚州境內河堤年年決口:
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夏,決江都運堤,六月運堤再決數百丈;十六年(公元1659年),歸仁堤決水;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淮水東下,堤決,州境水患不息;康熙四年秋,高郵大水,決運堤,七月大汎湖水漲,城市水涌丈余;六年(公元1667年),決江露筋廟,次年堵塞;七年(公元1668年)決江都運河之崇灣堤;八年(公元1669年),周橋未閉,清水潭決,民田仍被淹沒;九年(公元1670年),決高郵運河之茶庵、清水潭;十年(公元1671年),清水潭再決。十一年(公元1672年)四月清水潭復決;十二年(公元1673年),清水潭西堤將竣復決;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水潭決口塞;十四年(公元1675年),決江都運河之邵伯;十五年(公元1676年)漕堤崩堤,高郵清水潭、陸漫溝、江都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余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十九年(公元1680年),決興化漕堤,水入高郵城。
頻發的水患,使得揚州各州縣受災相當嚴重。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沿河州縣,悉受水患……水勢盡注洪澤湖,高郵水高幾二丈,城門堵塞,鄉民溺斃數萬”;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高家堰決口,“以數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高之堤,值西風鼓浪,一瀉萬頃,而江、高、寶、泰以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郭室廬”;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夏,“漕堤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之大澤灣,共決三百余丈,揚屬皆被水,漂溺無算”[9],“淮揚兩府水災滔天漫地,如高、寶、興、鹽、江、安、山、桃等處十一州縣之民田地陸沉,房屋倒塌,牛畜種糧漂浮。父子、兄弟、夫妻、兒女死于洪波巨浪者不計千百人。”[10]
揚州是通江達淮要津,淮鹽的產運銷是否暢順關系國家賦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兩淮巡鹽御史赫碩色奏報兩淮食鹽停引的緣由為“連年下河地方水淹,場灶產鹽不足,又兼運鹽之河久不挑浚,淤淺難行”[11]。但農業為民生之本,在這樣的背景下,鹽務與地方社會特別是民生之間的矛盾尤為凸顯。
二、清代揚州水利治理中鹽務與民生的矛盾
水利治理的本意是解決頻發的水患,保障民生,維系王朝統治。但兩淮鹽課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是保障民生的基礎。因此,保障兩淮食鹽的產運銷暢通與當地農耕存在矛盾。關于清代揚州境內水利治理中鹽務與民生的矛盾在地方志、相關朝臣的奏疏、文集中都有反映,為我們勾勒出當時矛盾的大致經緯。
鹽場多在運河下游,水大往往影響兩淮鹽場產量:“上年西水下注時,正值海潮頂托,垣鹽被浸,多有消耗。秋冬雨雪更甚,場灶全淹,灶丁無計攤淋。”[12]248缺水也影響食鹽生產,“淮南通泰二屬場河,因暵干日久,乏水濟運,其煎鹽各場地亦因雨少,鹵氣不升,以致缺產甚多。”[12]275芒稻河閘是運河泄水入江第一捷徑,但“因蓄水運鹽,故水大亦不啟放。高、寶、邵伯民田多受其害”[13];有些運鹽河道,“河水僅深二三尺,于是白駒等閘專事閉蓄,以資鹽運”,蓄水保障鹽船航運導致“官河及梓新各河又皆淺窄,容納無幾,湖蕩停洄不下,先已漫溢民田”[14]。
水旱災害的利益受損方不僅僅是地方社會,有時鹽務也處于劣勢。清初實行“永不加賦”“攤丁入畝”政策后,人口呈現爆炸式增長,使得人地矛盾日益凸顯,河道、水利用地多被周邊豪強百姓占用,各鹽場出口的灘涂“為勢家所占,奸民營種堤外草蕩為稻田”[5]149。儀征是漕糧、淮鹽必經之所,每年糧船、鹽船經過無數,河道本就擁擠,時人為圖輕便,隨意將朽爛糧船丟棄在河道,阻礙鹽船行運。另外,河道兩岸居民借以牟利故意堵塞河道、破壞水利設施的事情也不少見。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江都縣境內白塔河閘至泰州馮甸一段河道墊塞,就源于兩岸居民肆意向河道拋擲磚瓦,以圖“鹽船遷阻,得以添夫加價,并借起駁為偷爬之計”[15]。
揚州境內水道繁多,一些閘壩在承擔水利保障作用的同時,也扮演稅卡的角色。為躲避關稅,各閘壩經常發生夾帶偷稅行為,更有出現私挖壩口借以翻壩逃稅的事件,以滕家壩最為典型。滕家壩曾名濟川壩,位于泰州南門外濟川橋東,明代時供運鹽船只通過。順治年間改名為滕家壩,為揚州關分口,原本無定額稅銀,又因離揚州較遠,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歸泰州管轄,只允許征收落地零星稅銀并附近泰興的土特產。由于滕家壩稅率較低,且經由該壩可使航路縮短,沿途商民多喜由此通行。這導致揚州關稅收銳減,因揚州關稅為全額悉數盡繳國庫,關稅短少多由管轄官員賠付。為保證揚州關的關稅征收數額,官府令商民凡經江北里下河到江南,或江南船只北上,必須由轉至揚州關中閘和白塔河稅卡通過,一律不得從滕家壩繞行。在這種政策下,商人和周邊百姓私挖壩口,借以翻壩,甚將蘇杭雜貨繞至滕家壩,直達里下河州縣各場,不僅導致揚州關所屬的中閘、白塔兩處稅卡稅額銳減,“實為揚關第一漏卮”,而滕家壩所處的濟川河“又高于上官河,一經啟放,官河立枯,農田鹽運兩有妨礙”[16]。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高郵武生劉鑣稟告四角墩總河向北通各蕩入海要道近被附近居民為私利,私自在河中筑壩,根據己需阻遏水源,“遇水小則筑于下口,以專利而下游旱;遇水大則筑于上口,以免害而上游潦。”[17]
三、清代揚州水利治理中鹽務與民生矛盾的解決措施
揚州所在的兩淮鹽區是清代最大的鹽場,賦稅占據國家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保障食鹽生產運銷的策略與以農為本的基本國策存在矛盾,為平衡兩方之間的矛盾,清代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再到商人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分宜處理這些矛盾。
興建水利設施,及時挑浚河道,保障河道暢通,達到淮鹽順利運輸與農田豐收兩者兼顧是最為理想的措施。康熙年間,儀征知縣馬章玉重浚閘河,“河既廣深刻納,兩岸田疇足資灌溉,一舉而商民均利焉。”[18]儀征江口至江都、甘泉三汊河是通江達淮之要津,一向規定三年大挑一次,撈淺一次,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又規定,不必拘定三年之限,如遇應浚之年,著派鹽政委員確估,實力挑浚。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筑壩挑浚儀征烏塔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挑深通、泰兩屬運鹽河,培筑泰州一帶倒塌纖堤。
但鹽務與民生矛盾的解決更多則是通過鹽商們的一些義舉來緩解。清代鹽業經營是一種壟斷、高盤剝的經營模式,鹽商與官府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密,依附、逢迎和仰攀官府成為鹽商維系利益的最主要手段,鹽商捐資河工和賑濟,可謂以解燃眉之急、急公所急。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瓜洲花園港一帶江堤被淹,需要加固,“其工料銀兩,俱兩淮鹽商認捐完工”,鹽商江楚吉等“愿再捐九萬八千余兩,以認料工之需”。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鹽商出資挑浚“揚州自三汊河至儀征縣河道”,并令總商江廣達(江春)等經理,“再,儀所天池系鹽船泊候擡掣之所,近因淺窄,商人亦一體公捐公辦。”
不過,鹽商更多的是參與串場河的修筑河工,如項憲“開浚串場河工程浩大,商苦重累,幸逢圣駕南巡,倡首疏請,奉旨減十分之八,商實賴之”;江演“免數百里串場河之役,皆有力焉”;歙縣鹽商程國明的墓志銘記載:“黃水舊為淮揚患,泰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囑)商人疏浚,費以鉅萬計,力不支,將以誤公獲罪。會圣駕南巡,駐蹕茱萸灣。君率眾跪迎道左,具陳所以。上嘉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困以蘇。”
賑濟一般是發生水旱災害后,鹽商出資賑濟災民。《兩淮鹽法志》中有大量鹽商出資賑濟的記述,先摘抄幾條略微說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栟茶場先后遭遇海潮,坍決蕩地,折銀計價一千八百一十二兩,灶民無力繳納田賦,“淮南眾商情愿代輸”。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兩淮鹽商以揚州遇旱,“淮商公同捐資施賑四個月,自十一月起至二月止,于四門分設粥廠八處,遠近相繼,每日各處就食之民不下二十余萬人……有淮南商人光祿寺少卿汪應庚具呈,情愿將揚城八處粥廠一月內煮賑散賑之米,獨力認捐,共計米一萬七千石盡數捐出。”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動用河庫、鹽庫以及采取商捐的方式挑浚淮揚通三地十一州縣的河道、堤、壩、閘等水利工程,高郵地方志記載:“乾隆五年,我皇上特遣大理寺卿汪漋、通政使德爾敏統滿漢官辦理下河水道,溝洫之利,四野均沾。”商人在災荒年間積極出資,緩解災情,有利的緩和鹽商與普通百姓的矛盾。
與最高統治者、中樞廷臣、鹽政官員不同,揚州地方官員往往敢于直言,維護當地利益,如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大水泛濫,甘泉知縣龔鑒請芒稻河閘開閘泄水,“閘官以鹽漕為辭不可”,后遇河道總督嵇曾筠視河,龔鑒當面陳述,嵇曾筠從其請,當即下令開閘,又“定以鹽、漕二程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當啟閘,毋得以鹽漕借口,致多蓄水為民田害”。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高郵湖盛漲,興化知縣魏源星夜前往兩江總督陸建瀛行署擊鼓,請開運河東岸二十四閘分路宣泄,“下河七邑獲慶更生源之力也。”
清代統治者對河工十分重視,每遇河工大修,皇帝均遣派欽差大臣監督,但河臣只能提出意見,實際上還是由皇帝親自指揮或決定最終治理方案,甚至連河工用料、各壩何時開閘放水悉聽最高統治者的決定。包世臣論及河臣時稱:“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為上,能明錢糧者次之,重武職者又次之。其侈言工程,袒護廳員者,大抵工為冒銷納賄而已……自潘、靳之后莫能言河者,其善者防之而以。”這種情況導致清廷最高統治者、參與決策的中樞大臣缺乏實地經驗,在決策的過程中往往忽視地方利益。
清代鹽務與地方社會特別是民生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中央與地方、商與民之間的利益沖突。康乾時期,鹽商獲利豐厚,愿意主動捐輸賑濟,極大地緩解了矛盾。但到清末,已經很難見到商人主動報效河工的記載,更多的是官府強硬指派并與行鹽數量掛鉤。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兩淮鹽運使劉瑞芬循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之例勸兩淮鹽商捐助黃河河工,已經強硬下派,按引分攤,“淮南統按每引八錢,連同各食岸共捐銀四十萬兩”,當時商情已經十分困乏,連劉瑞芬在上奏時都稱“報捐能減一分,即沐一分之惠”,對此,地方社會也只能各自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