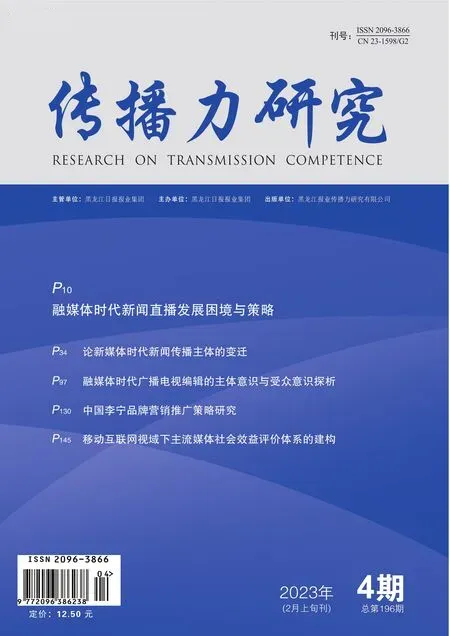古籍圖書出版的發展現狀及改進策略
◎李 琳
(線裝書局,北京 100078)
1981年9月17日,對我國古籍出版社的從業者來說是一個值得永遠記住的時間,因為這一天一個重要的關于古籍出版的文件下發執行,這就是《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文件強調“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該文件發布至今已有40多年,更為關鍵的是自2010年以來的這十年間,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豐碩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且這個重要文件更是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說承上,往前可以上溯到1958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成立,這個小組成立以后,馬上就推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進行,并在它的領導下制定了有關工作規劃,如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業界稱之為“九年規劃”),與之呼應的則有其他省市根據本身現有的條件也成立了各自的古籍出版工作小組,并且制定了各自的規劃,我國的古籍整理出版由此蓬勃開展。這一古籍出版界的喜人現象在1966—1976年間,卻一度陷于停頓,直到1981年才恢復。啟下則有2017年中辦國辦頒布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這個文件對整理古籍出版的許多方面,比如具體到某家古籍類出版社、某個印刷廠,甚至某位學者、編輯都產生了從點到面的影響。接下來又有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個關于古籍整理發展的重要文件與1981年的《指示》前后相距40年,卻能遙相呼應。《意見》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就如何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做出過重要指示,強調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推動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經之路。《意見》的發布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指示精神的重要舉措,體現了中央對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視,必將推動古籍工作邁入全面繁榮興旺的新時代,文件的發布為做好新時代古籍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我國古籍出版的總體現狀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1年,新中國整理出版的古籍圖書達5萬種。以1981年《指示》發布為時間節點,40年來,古籍整理出版總體能力翻了好幾番。《指示》發布后,古籍整理從業者受到極大鼓舞,使古籍整理出版迎來了新的高峰,成果豐碩,以《十三經注疏》《二十五史》《新編諸子集成》《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等為代表的經史子集傳世文獻得以呈現在讀者面前。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是我國編制的第7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有文章針對這一階段的執行情況分析后指出:《規劃》執行期間,一批有分量、高質量的規劃項目一經出版便成為精品圖書,獲得了出版界、學術界的多項殊榮,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截至目前,已有百余種項目成果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國家級獎項,如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顧炎武全集》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201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2015年鳳凰出版社出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201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陸游全集校注》獲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這些古籍規劃的精品項目出版后具有多種特質,貫穿了古籍整理出版事業60多年的整個過程。
更為具體一些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收錄古籍5 000多種,是現代編纂的規模最大的一套古籍叢書,榮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系列古代名家作品的校勘注釋本,如《孟浩然集校注》《孟郊詩集校注》《李商隱詩集疏注》《李璟李煜詞》《蘇軾和陶詩編年校注》《李清照集校注》等,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像《儒林外史》《鏡花緣》等也在很長時間內是獨家注釋本。鳳凰出版社也有10余種圖書榮獲全國各級獎項:《冊府元龜(校訂本)》《趙翼全集》《陜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李太白全集校注》等圖書榮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全元文》《陸士衡文集校注》《宋代文學編年史》《文心雕龍解析》等榮獲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岳麓書社出版的《敦煌愿文集》《船山全書》《湘綺樓日記》《海國圖志》等獲得國家圖書獎;《魏源全集》《中國古代圖書印刷史》《能靜居日記》等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還有巴蜀書社的《中國水書》《周原出土青銅器》《韓詩外傳箋疏》《三國志校箋》《戰國策新校注》《廣韻疏證》《大明一統志》《輯補舊五代史》《周詩新詮》《羌族石刻文獻集成》等一大批國家重點項目。三秦出版社成立近40年來共出版石刻文獻類圖書近200種;文史經典文獻整理類圖書400多種;舊志整理類圖書10多種;古籍及國學經典普及類圖書近千種。另外,該社也有3種古籍圖書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提名獎。
上述所舉部分古籍出版社在人員規模上、資金財力上有大有小,它們基本上是1981年因為《指示》的發布而成立的,其目前所取得的成績,只是我國古籍整理巨大出版成就的一個側面,距離《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工作統計的20萬種還相去甚遠,并且海外散失的古籍還約有10萬種。古籍出版人肩負重任,我國古籍整理出版道阻且長。
二、古籍出版中存在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并且十八大以來,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但整個出版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較小,具體到古籍出版這一板塊就更為渺小。各古籍類出版社,尤其是中小型古籍社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在出版業日益收緊的環境下,難以持續發展下去。
(一)重復同質化出版現象嚴重
各出版社為本社效益考慮,爭相出版常見品種。在網上搜尋“四大名著”,基本上各社科類出版社都出版過這套名著,還有類似“四書五經”“二十四史”“詩經”“楚辭”“唐詩三百首”“宋詞”“元曲”等典籍,均重復出版,只不過換了封面、開本等,只是存在全本或簡潔版本的不同而已。
(二)出版質量不高,尤其是翻譯水平不高
因為古籍內容是公版,網上有大量可復制的文字,這就給了一些文化公司可乘之機,他們恣意從網上復制粘貼古籍內容,稍作加工,就拿到出版社出版,碰上不負責任的編輯,一本質量不高的古籍圖書就面世了,更有可能走進校園,誤導中小學生,產生可怕的后果。為了“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讓出版的古籍使年輕人愿意看、看得進去、看得懂,古籍今譯必不可少,一些出版社為了趕時間,所組織的稿件存在翻譯不準、與網上雷同等現象,個別甚至連標點的錯誤都一模一樣,長此以往,勢必會損害古籍出版的聲譽。
(三)古籍類出版社整體經濟實力偏弱
全國目前出版社共有586家,古籍出版社在里面是少數,而且除去少數幾家大的古籍出版社,其他二三十家古籍社基本是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指示》發布后才成立的,這些出版社家底薄、實力弱,在計劃經濟年代還能靠撥款開展業務,市場經濟之后,特別是轉企之后,面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重壓力,經營困難,在紙質圖書銷售銳減的今天,更是舉步維艱。
(四)專業人才少、培養困難
做出版的人有個共識,即編輯是為人作嫁衣,這是對一般普通編輯而言的。對古籍編輯來說,即便想為人作嫁衣,也并不容易,古籍出版對人才的要求更嚴更高,不懂版本、不懂古漢語,很難在古籍社做一個出色的編輯,更難以與作者溝通。但現實是,古籍社里滿足這類編輯要求的人少之又少,多數是半路出家。高校里漢語言專業不是熱門專業,報考此專業的人數在減少,畢業后能到古籍社工作的更是少數。
(五)古籍出版周期長、投資大、回款慢、利潤低
這種困難局面其實是整個出版業都面要對的現實,但因為古籍的整理、匯編、點校更為費時耗力,投資更大,需要更為深厚的學養人才,而且古籍類圖書是小眾性的,很難在市場上大批銷售,因此,陷入回款慢、利潤低的惡性循環,導致古籍出版社難以發展壯大。
(六)影印類出版品種過多,沒有經過加工整理、匯編、點校、翻譯,直接影印出版,加大了古籍圖書的使用難度
畢竟古籍圖書對讀者的學識學養要求較高,這些圖書有高度、有深度,較多地考慮了為學術服務、為專業研究服務,考慮一般受眾的需求比較少,古籍內容不易被普通讀者讀懂、理解。
三、改進策略
針對以上古籍圖書出版中存在的問題與困難,結合出版企業的整體環境,提出以下幾點改進策略。
(一)加強出版人才培養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才會上講過,國家發展需要人才,民族振興需要人才,出版也要靠人才隊伍,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文化強國。創新出版人才培養基礎,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關鍵在于抓好現有效制度的落實,要優化出版人才的培養激勵機制,多渠道發現培養人才,對于極其緊缺的古籍專業人才、復合型數字出版人才、國際出版人才、出版翻譯人才有用武之地,加快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出版人才評價體系,健全完善職業資格評定標準,為優秀人才配置必要的支撐團隊,提供可協調的資源。研究建立符合出版行業特點的工資管理體系和薪酬分配機制,增強出版工作者的職業自豪感。全面打通結合發展、行業管理、產業升級等各個環節的人才培養,形成產學研相互支撐的出版人才培養體系,為新時代出版工作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二)國家有關部門加大古籍整理出版資金補貼力度,加強數字化建設
在目前已有古籍整理補貼基礎上加大力度,并由國家層面牽頭,系統加強新時代古籍工作,由有關部門做一個中長期的古籍工作規劃,召開全國性的古籍工作大會。在現有古籍工作領導統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充實完善,把古籍的保護整理研究和古籍版本、古籍數字化工作統籌起來,把重點領域的古籍工作統籌起來,把古籍隊伍建設工程項目資金保障工作統籌起來,推動各方面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形成全國古籍工作一盤棋的新格局。在內容建設上,可以加強搶救整理研究利用,實施精品戰略,吸取信息,加快推進重大文化價值典籍的整理出版,抓好古籍善本孤本、珍惜古籍的搶救性修復、整理、出版,加大古籍權威版本普及推廣力度,讓古籍從故紙堆里活過來,以新面貌、新生機呈現給現代讀者。在數字化建設方面,著力建設國家古籍數字化總平臺,以及中國古籍總部網絡版、古籍資源專題數據庫,惠及共享優質古籍數字化的資源等。國家正在進行的復興文庫、永樂大典和敦煌文獻等重點主題整理出版等一批重大出版項目,很好地體現了國家對古籍出版的重視,以這些重大出版工程和項目為抓手,來打造體現時代高度、表達文化傳承、彰顯示范精神的高峰之作,自覺守護文化根脈,傳承文明。
(三)古籍出版社與文科院校加強社校合作
古籍編輯深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加強版本方面知識的學習,編輯出版專業或漢語言文字專業學生到古籍社實習,早一步參與到出版工作實踐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更能提高學生走上出版工作崗位后的實際能力。同時,有關部門正在推動出版學一級學科的建設,在相關高校加強學科理論和體系建構,編寫新專業教材和加強實踐教學培養全面人才;優化古籍學科專業布局,加強古籍課程體系建設,推進高校古籍學科專業建設,擴大專業人才隊伍的規模,提升培養質量;引導高校將古籍工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完善古籍整理研究專業機構建設。但出版一級學科涉及的問題較多,困難目前還有不少,可以做到的是大學推動二級專業學院的建設,大學資源豐富的地方項目可以與大的出版企業進行合作。
(四)目前在健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機構之后,有必要推動各地建立省級古籍出版領導機構
目前,上海、吉林、四川、山東、安徽等省市已成立相關領導小組,領導各地方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并整理出了一批具有時代特征的古籍出版物。在這些地方機構的領導下,各專業古籍社可以聯合起來做單個出版社難以完成的大項目,比如黃河文獻、運河文獻、敦煌文獻等大型項目。
(五)加強古籍圖書質量檢查,設立專項內容檢查主題
目前,我國的出版管理機構已經加強了每年的圖書質量檢查,并且每年都設一個專門的檢查主題,這是一個很實用的管理方式,應該持續下去。目前所知的有青少年兒童讀物年度質量檢查、教輔圖書質量檢查、字辭典質量檢查,也可以開展古籍圖書質量檢查,以此促進古籍類出版社提高古籍圖書出版品質。
(六)加強培訓
管理機構已經加強了對編輯的注冊和年度培訓,對學時不足者不予續聘,這對編輯加強日常學習非常有益。類似的專題培訓班已經穿插其中,就筆者而言,曾參加了2021年度的古籍編輯專題培訓。在培訓中,不僅有專業的高校老師,更有大的古籍出版社的資深編審來教學,參加培訓的編輯也有機會交流,起到互通有無的作用。
四、結語
以上分析了古籍圖書出版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策略,只是筆者力所能及了解到的情況和給出的建議。也許情況并沒有這么嚴重,也許情況更為糟糕,但作為出版人尤其是古籍出版人要堅信的是,無論是古籍圖書出版還是現代圖書出版,它的底蘊是文化,它的根本使命是傳播文化、賡續文明,出版社的最終目標是文化,即它要為傳承知識、創作文化、創新文化、發展文化而服務,而中國文化的根源在五千年的古典精華里,它需要作為出版人的我們去挖掘整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還說:“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文化的傳承綿綿不絕,對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是社會發展永恒不變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