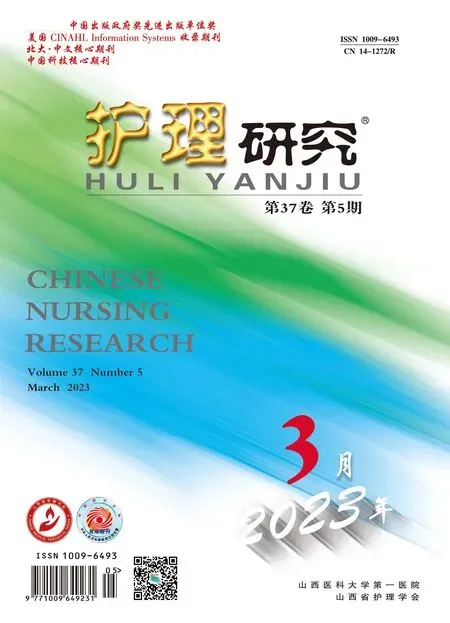元認知療法在癌癥幸存者中的應用研究進展
程春燕,崔盼盼,鄭美瓊
1.河南省人民醫院,河南 450001;2.鄭州大學
全球數據顯示,癌癥發病率仍逐年上升,癌癥負擔不容忽視[1]。癌癥幸存者在遭受軀體損害的同時,焦慮、抑郁、恐懼、創傷后應激障礙等心理問題日漸凸顯,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2]。研究表明元認知與焦慮抑郁、癌癥復發恐懼等情緒困擾顯著相關[3]。元認知是個體對自我認知內容的思考過程,其對個體情緒發展起調節和引導作用,通過修正個體不良認知信念可改變病人元認知水平從而緩解情緒困擾[2]。元認知療法(metacognitive therapy,MCT)是基于認知行為治療,以修正個體消極元認知信念,重建積極元認知信念并發展有效元認知策略為目的的心理治療方法[4]。國外將元認知療法應用于乳腺癌、前列腺癌、白血病等病人中,結果顯示元認知療法可有效緩解癌癥病人情緒困擾[5-6]。但目前國內相關研究鮮見報道,現通過對國外元認知療法在癌癥病人中的應用狀況進行綜述,以期為我國癌癥病人心理護理提供新視角。
1 元認知療法的理論基礎
1.1 元認知模型 心理學家Tarskin[7]提出了元認知模型,該模型從個體認知形成的內在機制出發,明晰了負性情緒產生的過程。該模型指出元認知包括元認知知識、元認知體驗、元認知目標、元認知策略4 個方面[8],而元認知體驗是使病人疾病應對方式發生改變的根本。元認知理論指出知識、經驗、目標和策略的不適應結合從而導致無益的思維模式形成,從而導致心理障礙。對癌癥幸存者而言,元認知知識即病人具備的癌癥相關知識,元認知體驗即罹患癌癥后對癌癥的應對過程,元認知目標即癌癥相關元認知信念的形成,元認知策略即病人對元認知體驗和目標的不斷總結、反思、評價等信息的往返交流。元認知模型為元認知療法干預框架的確定提供了依據。
1.2 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 1996 年,Wells 等[9]提出了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 Model,S-REF),該模型著重闡述認知改變的過程,強調個體的情緒障礙因其不良的信息處理方式引起。該模型指出當個體出現消極信念應對不良時,會導致負性認知強化而形成認知注意綜合征,即反芻、無益的注意力策略及無用的應對行為。2009 年Wells[10]以S-REF 模型為理論基礎構建元認知療法,對癌癥病人認知注意綜合征進行了擴展:①反芻(擔憂、沉思、過度分析、反復質疑自己的想法);②無益的注意力策略(如焦慮的產生);③無用的應對策略(如搜索癌癥幸存者的積極預后,避免癌癥提醒)。以S-REF 為理論依據,確定了元認知療法的核心內容。
2 元認知療法的具體內容
元認知療法以修正積極和消極的元認知信念并發展有效的元認知策略為目的,其開發和實施以理論和臨床證據為基礎,保證了干預的科學性,且已在癌癥人群中驗證了有效性、可行性與接受度。Wells[10]于2009年制定了元認知療法治療手冊,其內容主要涉及元認知模型、認知注意綜合征、注意訓練技術[11]、超然正念的心理干預技術。干預共分為6 步。①構建概念化案例,識別認知注意綜合征:建立問題清單,以問題清單和元認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通過訪談、提問、測評及問卷評估,識別病人的認知注意偏差。②元認知模式社會化:以病人的認知注意偏差為基礎,采用蘇格拉底式提問,讓病人暴露在消極的元認知信念中,幫助其認識自我元認知,并引導病人理解其情緒困擾是由認知注意綜合征和消極的元認知信念產生的。③注意力訓練:通過選擇性注意、快速轉換注意力或分散注意力的注意力訓練技術,幫助病人學會中斷反芻,并使其意識到中斷反芻和不斷反芻帶來的影響。④超然正念:通過正念訓練,修正消極的元認知信念,進而消除適應不良的應對行為。⑤預防復發:檢查病人元認知信念,鞏固應對策略。針對未解決的擔憂,研究者與病人共同制訂治療計劃,預防復發。⑥計劃總結:強化應對策略,鼓勵病人制定中長期計劃,向其提供治療計劃和本次干預總結。第1 步為干預準備階段,其余5 步為干預實施階段。每次干預后布置家庭作業以提高治療效果,每次干預前檢查家庭作業,根據完成情況對病人進行個性化指導。
干預可采用團體或個體形式開展,但因元認知療法著重于病人個體化情緒障礙,故目前研究多采用面對面、個體化干預模式。干預工具多樣化,如書面資料、視頻、音頻等。目前,多項研究顯示,干預次數為6~8 次效果最佳,干預每周進行1 次,個體干預每次時長多為45~60 min,團體干預每次持續90~120 min[12-14]。然而,研究者可根據干預特點對干預形式、次數、時長等具體內容進行適當調整。此干預需由心理咨詢師或具備資質的治療師進行,通過對治療師的監督及對治療保真度的評估進行質量控制,以保證干預的真實效果[8]。
3 元認知療法在癌癥幸存者中的應用效果
3.1 提高癌癥幸存者元認知水平 元認知療法主要針對改善病人元認知信念,對提高元認知水平效果顯著。Elham 等[15]對24 例輕中度抑郁的乳腺癌病人開展了一項為期8 周的團體元認知療法隨機對照試驗,干預每周進行1 次,共進行了8 周,每周的干預主題分別是制定治療目標、練習正念、回顧認知注意綜合征、注意力訓練、識別無效應對、延遲思考、制定克服恐懼計劃及預防復發。每周干預后病人需對訓練技巧強化練習。干預后病人元認知水平顯著變化,病人的抑郁得分也由(21.60±4.83)分降至(13.83±8.12)分,可見元認知療法適用于伴有抑郁癥狀的癌癥病人。Mary等[16]對確診超過半年且存在焦慮、抑郁的19 例實體腫瘤幸存者進行干預,元認知療法共進行6 次,采用縱向定性研究法干預結束時及干預后3 個月、6 個月對病人進行效果評價,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病人元認知信念發生明顯改變,如“忘記那些不好的想法”“我可以控制我的想法”,病人認為在治療后“現在可以過好自己的生活”“我會欣然接受疾病”,病人元認知水平明顯提高,焦慮、抑郁水平顯著降低。該定性研究不僅詳細描述了元認知療法個體化干預過程,而且可為干預策略的開發、評估和實施提供依據。
3.2 有效緩解癌癥幸存者焦慮和抑郁情緒 焦慮和抑郁是癌癥病人普遍存在且突出的心理問題[17],而元認知是其焦慮、抑郁發展和維持的關鍵因素[18]。系統綜述、橫斷面調查等多項研究結果顯示,元認知對癌癥病人焦慮、抑郁、癌癥復發恐懼等情緒困擾具有預測作用[19-21],故元認知療法可通過改變癌癥病人元認知有效緩解其情緒困擾。
英國利物浦大學Fisher 教授團隊致力于探討元認知療法對緩解癌癥幸存者焦慮、抑郁的效果,同時通過開展小樣本隨機對照試驗對元認知療法的可行性、可接受度、干預依從性、干預效果持續性等內容進行全面評估。2013 年對27 例成年癌癥病人實施了個體化、面對面元認知療法,干預根據個體差異由3 名治療師實施,干預次數不超過6 次,每次干預1 h,干預后3 個月、6 個月進行隨訪。結果顯示,約75%的病人完成了所有干預,干預前后病人焦慮、抑郁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干預后3 個月及6 個月分別有59%、52%的病人焦慮和抑郁仍為緩解狀態,證明病人對元認知療法的依從性和接受度較好[22]。2015 年Fisher 教授又在12 例18~23 歲的青年癌癥幸存者中對元認知療法可行性進行了全面評估,干預8~14 次,每次45~60 min。在治療前、治療結束時、治療后6 個月分別進行測評,意向性分析結果顯示焦慮和抑郁在各時點均存在顯著時間效應,治療后干預效應量為1.83,隨訪結果與干預后效果相當,提示元認知療法對緩解青年癌癥幸存者焦慮、抑郁有效且干預效果持續性良好,元認知療法有望成為癌癥幸存者轉診的重要中介因素[23]。2017 年Fisher 教授團隊在4 例轉診到腫瘤心理科的病人中開展了元認知療法,干預由治療師根據治療手冊進行,共6 次,每次45~60 min,干預后病人焦慮和抑郁總得分迅速下降,干預后3 個月和6 個月隨訪,其中3 例病人隨訪效果仍維持良好[24]。提示元認知療法有可能成為成本效益較好的心理干預措施,有效降低治療成本。
3.3 降低癌癥復發恐懼 有研究顯示,癌癥病人癌癥復發恐懼與元認知相關且元認知可解釋高水平癌癥復發恐懼,而積極元認知和消極元認知在中國癌癥病人癌癥復發恐懼的發生發展中同樣起重要作用[25]。此外,Danielle 等[26-27]研究指出,元認知可通過認知注意綜合征間接影響癌癥復發恐懼的發展軌跡。2013 年,Kirsten 等[5]報告了元認知療法在1 例青年女性白血病病人中的應用,研究將病人元認知進行概念化,以其擔心癌癥復發為案例,介紹了干預的具體過程,干預每周1 次,共進行6 次。治療半年后隨訪,病人表示“內心仍感到平靜、舒適”,表明該病人焦慮、抑郁得到有效緩解,且病人未出現其他元認知信念問題,說明元認知療法有助于從本質上緩解病人情緒狀態,可能與元認知療法幫助病人掌握自我分析及自我調控的方法,也與干預后加強效果進行指導有關。此外,研究指出應設立針對癌癥幸存者的治療服務機構或可用于其他慢性病病人。該研究也為元認知療法可應用于癌癥病人提供證據支持。Simone 等[28]將元認知療法應用于38 例處于緩解期的乳腺癌病人,通過8 周的干預及干預后1 個月的隨訪,標準化測量及質性訪談結果均顯示病人復發恐懼感顯著下降,表現為病人對疾病進展的擔心減少、主動尋找興趣愛好、配合醫生檢查時緊張感降低等。Louise 等[29]將以元認知療法為核心的干預應用于152 例癌癥幸存者,干預后結果顯示癌癥復發恐懼水平較高的病人從中獲益較大。中介分析發現,元認知療法干預后癌癥復發恐懼的改善很大程度與病人消極元認知和侵入性思維的減少有關,這與S-REF 框架一致。
4 小結
元認知療法起源于精神心理學,目前癌癥負擔日益加重、癌癥病人臨床水平情緒困擾顯著,且可能還存在未被識別的心理狀況,社會心理護理已然成為高質量癌癥護理開展的必要條件,護理人員必須采用跨學科方法為病人提供有效應對。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精神腫瘤學主任Holland[30]指出癌癥病人心理社會干預將成為創新研究的重點。目前,國外元認知療法在癌癥幸存者中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開展,而國內尚未檢索到元認知療法應用于癌癥病人中的相關研究。對此,筆者提出以下3 點建議:①應根據研究人群特殊性,干預實施時可調整元認知療法核心內容順序;②本土研究可從個體化干預著手,逐步將干預內容系統化;③干預結局指標的選擇應從情緒困擾開始,后續可探索對健康行為的影響。未來可結合我國癌癥病人突出且亟需的心理問題制定貼合國內文化背景下的元認知干預措施,為促進病人心理健康進行科學化嘗試,對促進癌癥病人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臨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