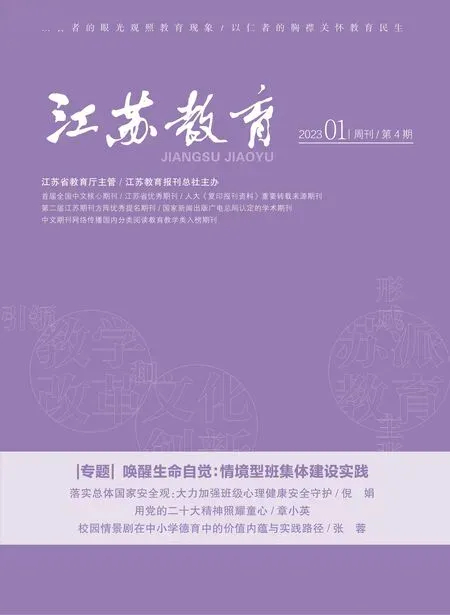信任的力量
郭文紅
來情去意
那年,我新接了一個五年級的班級。這是一個語數外平均分落后于平行班級近10 分的班級,雖說學習成績比不過別班,但打架、惹事的頻率算得上是全年級第一名。
剛接班不多久,班上就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打架事件。
體育課上,一群男生正在教師的組織下踢足球。其他同學有的在操場邊加油吶喊,有的在操場一側的器械邊自由鍛煉,也有的無所事事,在一旁溜達閑逛。
足球比賽現場熱火朝天,突然,球被一腳踢飛,砸中了正在球場邊看熱鬧的小翔。猝不及防地被正中面門,小翔疼痛難忍,卻又不知該跟誰發作。
這情形剛好被一旁閑逛的小徐看見,他覺得小翔的模樣很滑稽,“噗嗤”一下笑出了聲。小翔本來就有些惱火,聽見小徐的笑聲,立刻就有了出氣的地方。于是,他立刻沖了過去,揮拳就打。小徐自然也不會束手待斃,兩個人就這樣扭打在一起。體育老師趕來時,發現兩人的額頭、臉頰、胳膊上都有撓痕,即便是這樣,他們也都不肯撒手。無奈之下,體育老師只能將兩個人強行分開,送到我的辦公室。
先進來的是小徐,我一看見他就嚇了一跳,嘴角掛著血,頭發亂得跟雞窩一樣。我趕緊迎上去,端詳著傷情,心疼地問道:“究竟發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能打成這個樣子呢?我帶你去醫務室看看吧……”
可能是沒有想到我會這么關心他,小徐臉上的表情似乎放松了些,他沖著我擺擺手,說去洗手間沖洗一下便好。我有些不放心,想跟過去,卻看見了一瘸一拐地走進辦公室的小翔。
冰雪漸融
我讓小翔趕緊坐下,輕輕拭擦他臉上的血痕。孩子非常委屈,對自己的傷情并不在意,而是急著向我傾訴剛才發生的一切……這時,處理好血跡的小徐也回到了辦公室。看見小徐,小翔的情緒又激動了起來。我安撫好他,繼續檢查兩個人的傷情。在稍稍平息之后,我分別對兩個孩子的情感表示了理解:一個被球踢疼了還被別人嘲笑,自然生氣;另一個看見有人被球踢中的變形的臉孔,確實和平時看到的不一樣,覺得好玩也無可厚非。這份理解讓兩個孩子都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了,如何才能引導兩個孩子學會換位思考?如何才能恢復兩個孩子之間的同學情誼,與其他同學建立起團結、友愛、互助的人際關系呢?
五年級的孩子自尊心強,迫切希望得到尊重。如果只是簡單籠統地說上幾句,或者批評教育一番,很難走近他們的內心,也很難真正解決問題。我告訴他們:“老師很理解你們的情緒,但你們這種方式帶來的后果就是眼下這樣——體育課被中斷,雙方損失慘重,接下來還可能被老師批評,被家長責備,你們覺得自己今天解決問題的方式合適嗎?”
“吾日三省吾身”,反思屬于自我思考的一部分,要想孩子有所成長,必然離不開自我反思。我又繼續道:“如果剛才的事情再來一遍,你們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嗎?你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嗎?”話音剛落,小翔就迫不及待地開口了,他一臉鄙棄地瞥了小徐一下,憤然說道:“對他這種人,根本不可能有第二種方法!”
小翔的這個態度我完全沒有想到,心中有些失望;再看小徐,好像也被這句話給擊中了,他神情落寞地垂下了眼簾。我輕輕地拍拍他,用鼓勵的語氣問道:“那么你呢?你有更好的方法嗎?”小徐抬眼看了看我,猶豫著張了張嘴。我強忍住急切的心情,靜靜地等待著。小徐終于開口了,他低聲說著:“他被球踢中應該很疼,我不應該去笑他的。”小徐能夠主動反思自己,我夸獎道:“孩子,你真是太棒啦,你能換位思考,能體會別人被球踢中后的痛苦,實在是太了不起了。確實,如果你不笑,你們就打不起來,就不會有后面的事情發生了。你看,你自己想出了一個比剛才更好的方法,說明你原本就是這樣一個能夠為別人著想且富有同理心的人啊!”
聽到這樣的夸贊,小徐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一旁的小翔有些沉不住氣了,他說:“嗯,我也不應該去打他的,踢球的人并不是故意的,而且也并不是他踢的。”聽到小翔的話,我心中的石頭落了地,立刻表揚小翔:“你雖然被砸得很疼,卻能站在別人的立場上反思自己,這是很難得的。的確,如果你不因此遷怒他人,你們也是打不起來的。”
聽著我的贊美,兩個小家伙一掃剛才的僵硬,變得輕松起來。我接著追問:“你們剛才的做法確實比體育課上要進步一些,你們都從自身的角度進行了思考,那現在想請你們再想一想,還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式呢?”
兩個孩子沒有辜負我的期待,一個表示“他被球踢中應該很疼,我可以走過去安慰他。”另一個表示“就算別人嘲笑我了,我應該想到當時的自己的確很滑稽,如果能跟他一起大笑起來,氣氛肯定會很融洽的。”可能是想到了那個大笑的場面吧,兩個人相視一笑,繼而大笑起來……
看著眼前笑成一團的兩個孩子,我也忍不住跟著笑了起來。我拉起他們的手,真誠地說:“你們兩個太讓我驕傲了,你們兩個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很強,說明你們自身的素質都很高!今天的事情雖然因為有點沖動沒有處理好,但我相信,今后如果再遇上什么事情的話,你們一定可以展示出各自的聰明才智!”
意外之喜
一方面,我對孩子們的成長和進步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很擔憂,這撕破的衣服和滿身的傷該怎么向家長交代呢?我猶豫著問他們要不要請家長來校,由我向家長解釋一下,他們卻自信滿滿地說自己會和父母解釋清楚,不用老師再出面了。我雖然有些將信將疑,但還是同意了。
那晚,我一直在等著家長的“問責”電話。孩子被打成這個樣子,家長肯定要找老師要個說法。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那個晚上風平浪靜,沒有一位家長聯系我。
可沒想到,第二天早上,我進辦公室,就有同事跑來告訴我:“你們班門口一大早就來了一位家長,一直沒走,好像在等什么人一樣。”我一聽,匆忙來到班級門口,一看果然是小翔的母親。我硬著頭皮走上去,問她是不是為昨天的事情來的。她說是的,還說昨晚回去就發現小翔傷痕累累,追問半天,孩子也不肯說,一直到晚上十點多,才慢慢將事情原委說了出來。
接下來,小翔的母親說了一句讓我終生難忘的話,她說:“我看見自己的孩子傷得不輕,我猜對方的孩子一定也傷得不輕,我今天就是來向對方孩子道歉的……”而小翔的爸爸聽兒子說完全過程后,就對孩子說了句:“郭老師處理過就行了!以后不要再打架了。”“郭老師處理過就行了!”這些話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這句話里蘊含著家長的一份厚重的信任。這份厚重的信任帶來的必將是家校協同一致、合力育人的和諧畫面。
學生們聽到我講兩個孩子的高素養、大格局的處理方式后,流露出贊許的神色來。我想,這種能夠換位思考的意識,這粒謙讓、寬容、友善的種子,已然悄悄地播進了這個班級的每一個同學心間。
后來,我們班是全年級進步最明顯的一個班,打鬧的行為減少了很多,學生的學習成績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別人問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想,無非就是“相信”二字——相信孩子內心深處本身就有真善美的種子。正如蘇霍姆林斯基在《要相信孩子》一書中的觀點,我們的教育對象的心靈絕不是一塊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經生長著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師的責任首先在于發現并扶正學生心靈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讓它不斷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