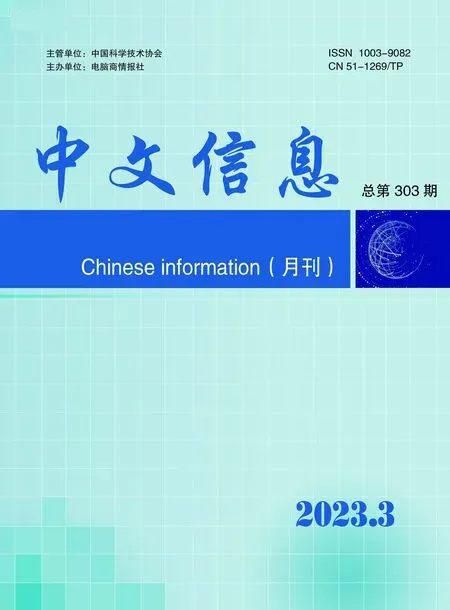拓撲翻譯視角下中醫(yī)英譯翻譯策略研究*
孫靜雨
(新鄉(xiāng)醫(yī)學院三全學院,河南 新鄉(xiāng) 453000)
引言
在文化多元化的趨勢下,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逐漸走出國門,并在世界范圍內(nèi)大放異彩。中醫(yī)文化是中華文化史上璀璨的明珠,傳承和傳播中醫(yī)文化,將對我國提升文化軟實力,提高國際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而中醫(yī)文化能走出多少,走出多遠,中醫(yī)英譯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一、拓撲翻譯理論
1.起源與發(fā)展
拓撲學(topology)屬于數(shù)學范疇,是一門研究空間基本特征關(guān)系的學科。拓撲空間在運動過程中保持不變的性質(zhì)就是拓撲性質(zhì),也就是拓撲變換。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最先把拓撲學引入到文化和翻譯領(lǐng)域。他認為,文化具有多重的表達方式,但其深層次的恒量或常數(shù)是保持不變的,因此,文化具有拓撲性。要保留文化,就需要對過去的東西進行翻譯,因而翻譯也具有了拓撲的性質(zhì)。拓撲翻譯學屬于交叉學科,陳帆、陳浩東在《拓撲翻譯學》一書中對拓撲翻譯(topotranslatology)的定義及相關(guān)要素進行了詳盡地闡述,開辟了國內(nèi)翻譯研究的新視角[1]。
2.互文性
翻譯和互文性具有緊密的聯(lián)系。互文性認為,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同程度但又必然地與其他文本發(fā)生聯(lián)系。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互文性的影響,互文性引起的翻譯拓變使得翻譯活動順利進行,從而實現(xiàn)文化傳承和傳播的目的。
1966年,受結(jié)構(gòu)主義的影響,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她認為,“互文性”是指影響其他文本意義的文本,也可以指作者對向前文本的借用和轉(zhuǎn)換,或者在閱讀時指涉到其他文本。”這一概念的提出對人文學科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許多學者認為,人文學科的研究和發(fā)展離不開互文性,如翻譯、文學等[2]。一直以來,學者們熱衷于對互文性進行研究,并將其引申到人文學科的諸多領(lǐng)域。西方翻譯理論學家巴茲爾·哈蒂姆(Basil Hatim)甚至認為,“廣義的互文性是翻譯一切文本的先決條件。”喬治·斯坦納認為,互文性“囊括了文學作品之間相互交錯,彼此依賴的若干表現(xiàn)形式。”由此可見,互文性和翻譯具有緊密的聯(lián)系。
根據(jù)拓撲翻譯理論,從語言和文化兩個層面,翻譯中由互文性引起的拓撲狀況可以分為結(jié)構(gòu)性互文(constructive intertextuality)和顯性互文(manifest intertextuality)。本文將從這兩方面對中醫(yī)文化翻譯中的拓撲狀況進行研究。
2.1 結(jié)構(gòu)性互文和顯性互文
結(jié)構(gòu)性互文引起的文化拓變狀況主要體現(xiàn)在人類文化所共通的地方,即不同文化中相似的地方,例如,不同文本中的主題、題材、語言的篇章、段落、句式結(jié)構(gòu)等,這些要素在翻譯中屬于守恒狀態(tài),是翻譯中的恒量。在本文中,筆者將主要研究結(jié)構(gòu)性互文中語言形式層面的翻譯拓撲狀況,如詞匯、語法、辭格等。
不同于結(jié)構(gòu)性互文,顯性互文性主要描述的是狹義的、文本間的、語篇層面的互文關(guān)系。顯性互文性大致可分為六類,即參照、陳詞濫調(diào)、文學暗指、自我引用、套語、習語。這些內(nèi)容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創(chuàng)新性和獨特性,是翻譯中的變量,也是翻譯中的難點。中醫(yī)文化是為中華民族特有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顯性互文性的特征十分突出,因此,顯性互文概念在中醫(yī)英譯中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3]。
綜上所述,互文性理論的概念與翻譯存在契合之處,而翻譯實踐中譯者也確實會面臨處理具體互文指涉的問題。由此可見,將互文性理論與翻譯研究相結(jié)合,不僅可行也有其必要性。
3.研究現(xiàn)狀
拓撲翻譯理論作為一種新穎的翻譯理念,它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國內(nèi),陳帆、陳浩東團隊對拓撲翻譯理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在2016年出版的《拓撲翻譯學》一書中,該團隊對拓撲學的起源與發(fā)展、文化拓撲與翻譯的關(guān)系、翻譯中互文性引起的翻譯拓變情況等內(nèi)容進行了詳細闡述,為翻譯拓撲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目前,已有一些作者將翻譯拓撲理論應(yīng)用于傳統(tǒng)文化的翻譯實踐中,如茶文化、謎語、歇后語、諺語等,但總體而言,研究數(shù)量較少,不具規(guī)模。在已發(fā)表的文章中,將拓撲翻譯理論和中醫(yī)文化相結(jié)合的研究尚未出現(xiàn)。因此,拓撲翻譯理論下的中醫(yī)英譯研究不失為一種新的探索[4]。
二、中醫(yī)英譯
1.中醫(yī)英譯的意義和研究現(xiàn)狀
中醫(yī)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結(jié)晶。中醫(yī)藥學凝聚著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yǎng)生理念及其實踐經(jīng)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2016年,國務(wù)院發(fā)布了《中醫(yī)藥發(fā)展戰(zhàn)略規(guī)劃綱要(2016—2030年)》,該綱要從戰(zhàn)略層面部署,提出要推動中醫(yī)藥進校園、進社區(qū)、進鄉(xiāng)村、進家庭,將中醫(yī)藥基礎(chǔ)知識納入學校傳統(tǒng)文化課程,旨在實現(xiàn)振興中醫(yī)藥發(fā)展的目的。2021年3月,“十四五”規(guī)劃中指出,要推動中醫(yī)藥傳承創(chuàng)新,大力發(fā)展中醫(yī)藥事業(yè),強化中醫(yī)藥特色人才培養(yǎng),加強中醫(yī)藥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2021年7月,國家中醫(yī)藥管理局、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國家廣電總局聯(lián)合印發(fā)《中醫(yī)藥文化傳播行動實施方案(2021—2025年)》。由此可見,傳承與傳播中醫(yī)文化,提升中醫(yī)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在中醫(yī)文化走向世界的背景下,中醫(yī)英譯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步。
隨著國家對中醫(yī)藥文化的重視,中醫(yī)英譯也逐漸收到了學者們的青睞,中醫(yī)英譯的翻譯實踐和研究已初具規(guī)模。中醫(yī)典籍英譯、中醫(yī)英譯類書籍和教材的出版為中醫(yī)英譯的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相關(guān)論文也不斷涌現(xiàn)。目前來看,對中醫(yī)英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醫(yī)文本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方面,如從生態(tài)翻譯視角、目的論視角、跨文化視角、譯者主體論等對中醫(yī)英譯翻譯策略研究,研究層面大多停留在語言層面,鮮少深入。因此,從新的視角、新的層面研究中醫(yī)英譯是大勢所趨[5]。
2.中醫(yī)英譯的難點
翻譯的兩個基本方面是理解與表達,在中醫(yī)英譯的實踐中,這兩方面都有其難點。一是是理解階段,譯者應(yīng)當認識到現(xiàn)代醫(yī)學術(shù)語與中醫(yī)術(shù)語具有相似性,但在傳遞信息、表述病癥方面卻不完全相合。如中醫(yī)術(shù)語“納差”,指進食欲望降低、食量減少;現(xiàn)代醫(yī)學英語術(shù)語“anorexia”一詞也有食欲減退之意,但卻指的是由于某種精神性疾病或重大疾病而導(dǎo)致的食量減少,如年輕女子害怕肥胖而引起的厭食等。如果直接將“納差”譯為“anorexia”,則不符合原意。因此,譯者應(yīng)充分、準確地理解中醫(yī)術(shù)語,避免誤譯,為中醫(yī)英譯奠定基礎(chǔ)。
二是表達階段。翻譯的表達階段要求譯者把自己對源語文本的理解的內(nèi)容用目的語重新表達出來,表達的好壞主要取決于譯者對源語文本理解的深度及對目的語及其文化的認知程度。中醫(yī)文化極具原創(chuàng)性,中醫(yī)文化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具有較大難度,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結(jié)合中英文化,仔細推敲,找出合適、恰當?shù)淖g文,最終達到傳承和傳播中醫(yī)文化的目的。
拓撲翻譯理論為中醫(yī)英譯的翻譯實踐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譯者可以在該理論的指導(dǎo)下,通過研究中醫(yī)文本內(nèi)的互文性,明確中醫(yī)英譯中的恒量和變量,采用恰當?shù)姆g策略,最終找出較為忠實、妥帖的譯本。
三、拓撲翻譯理論下中醫(yī)英譯的互文性研究
1.結(jié)構(gòu)性互文引起的拓撲狀況
結(jié)構(gòu)性互文引起的拓撲狀況主要體現(xiàn)在語言層面。筆者將從詞匯意義、語法、辭格三方面進行討論。
1.1 詞匯。詞匯意義具有客觀性、概括性、模糊性、相關(guān)性和民族性的特征,其中前三個特征在不同語言中具有共通性,屬于翻譯中的恒量,后兩個特征在不同文化中具有差異性,屬于翻譯中的變量。
中醫(yī)文化中有很多術(shù)語具有恒量和變量的特征。例如,“金、木、水、火、土”和“心、肝、脾、肺、腎”因其詞匯意義的客觀性,可將其直譯為“metal,wood,water,fire and earth”,及“heart,liver,spleen,lung and kidney”。這屬于翻譯中的恒量,可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現(xiàn)已形為約定俗稱的譯文。再如,“陰”、“陽”、“氣”這幾個術(shù)語,在目的語中找不到對應(yīng)詞匯,這屬于翻譯中的變量,可以采用音譯加注的翻譯方法。
1.2 語法。英漢語法有相似之處,如主、謂、賓等句子成分;陳述句、疑問句、感嘆句等句法結(jié)構(gòu)。同時,英漢語法存在較大差異,如性、數(shù)、格、時、態(tài)、式、級等不同。此外,英漢的句子結(jié)構(gòu)和語序也不同,如漢語中動詞使用較多,而英語中可以用介詞、副詞等代替動詞;漢語注重價值判斷,英語重事實判斷;漢語單句較多,短句相連,英語則結(jié)構(gòu)繁雜、語法嚴密。
因此,在中醫(yī)英譯時,譯者要充分考慮英漢語法的差異,辨別文本中的恒量和變量,將漢語句子融匯整合、化散為聚,最終實現(xiàn)優(yōu)化譯本的目的。
1.3 辭格。辭格,亦稱為修辭格,英漢語中常見的辭格有比喻、擬人、排比等。拓撲翻譯理論認為,拓撲變化越小,辭格翻譯的難度越小。換言之,英漢中越常見、越相似的辭格,越好翻譯。辭格的翻譯可分為三類,分別是可譯、難譯、不可譯。
例如,“用藥如用兵”是漢語中的比喻,在翻譯時,譯者可使用英語中的明喻或暗喻,既保留辭格,又傳遞原文意義。該句可譯為“use medicines as soldiers”。再如,“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泄,陰陽和,故能生子。”這里的“二八”采用的修辭格叫析數(shù)。析數(shù)指的是在一定語言環(huán)境下,利用數(shù)字之間的關(guān)系,將較大數(shù)字拆成較小數(shù)字進行表述,從而達到增加語言含蘊的目的。“二八”即為“十六”,這里具體指男子十六歲,故而可翻譯為“at the years of sixteen”。
在翻譯辭格時,譯者可盡量保留原文的辭格和意思,但當辭格無法翻譯時,譯者可舍棄辭格形式,以傳遞文本信息為主要目的。
2.顯性互文引起的拓撲狀況
顯性互文性指存在于特定文本中或特定文本與其他文本所體現(xiàn)出來的互文關(guān)系。顯性互文多屬于翻譯中的變量,翻譯難度較大。筆者將從文學暗指、套話、習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2.1 文學暗指。文學暗指指的是文本中指涉或引用某一名著或與之相關(guān)的內(nèi)容。《格物余論》是我國一部著名的醫(yī)藥專著,由元代醫(yī)學家朱震亨所著。該書因“古人以醫(y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而得名。“格物致知”出自《禮記·大學》,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這里,“格物”就屬于文學暗指。
源語讀者擁有本民族的文化功底和知識底蘊,因此對中醫(yī)文化中的文學暗指較為熟悉,易于理解。但是對于沒有任何中醫(yī)文化基礎(chǔ)的目的語讀者來說,文學暗指難于理解,甚至無法理解。這時,譯者就需要采用意譯或者直譯加注的方法實現(xiàn)交際目的。
2.2 套語。套語指的是因不斷重復(fù)使用而變得不知出處或以形成習慣的表達方法。文化中的意象往往是套語中的主體,英漢中有意義相同或相似的意象,如“綠色”代表希望、和平;夕陽代表衰老、死亡等。英漢中的不同意象占了多數(shù),如“龍”在漢語中具有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在英語中則沒有深層次的含義。
中醫(yī)文化中也有豐富的套語。其中中醫(yī)話語中的“火”就是套語。由于重復(fù)使用和習慣,我們認為,“火”是身體內(nèi)某些熱性的癥狀,相關(guān)的表達有“上火”“清火”“心火”等,該詞與英語單詞“fire”并不相同。由于形式和內(nèi)涵都發(fā)生了變化,在翻譯時,譯者可采用意譯的翻譯方法,以表達原文意義為首要目的。因此,“上火”可翻譯為“suあer from excessive internal heat”。
2.3 習語。習語是文化的重要載體,通常包括諺語、俗語、成語等等。這類在翻譯中發(fā)生的拓撲變化較大,屬于翻譯中的變量,如“小菜一碟”翻譯為“a piece of cake”,形式、內(nèi)涵都發(fā)生了拓變。
中醫(yī)文化中有很多習語,如“飯吃八成飽,到老腸胃好”“識得山種草,百歲還太早”“寒從腳起,病從口入”等。這些寫習語主要反映了中醫(yī)的養(yǎng)生之道、健康理念,大多合轍押韻、對仗工整,給翻譯帶來了很大的難度。譯者需要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礎(chǔ)上,準確表達原文意義,必要時舍棄形式,保留意思。
結(jié)語
本文以拓撲翻譯理論為基礎(chǔ),從互文性的角度討論了中醫(yī)英譯的翻譯策略。總結(jié)來說,中醫(yī)英譯以直譯、音譯加注、意譯為主,以表達意思為主,保留形式為輔。中醫(yī)文化源遠流長,它涉及醫(yī)學、哲學等學科知識,中醫(yī)英譯任重道遠,筆者將在中醫(yī)英譯的道路上繼續(x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