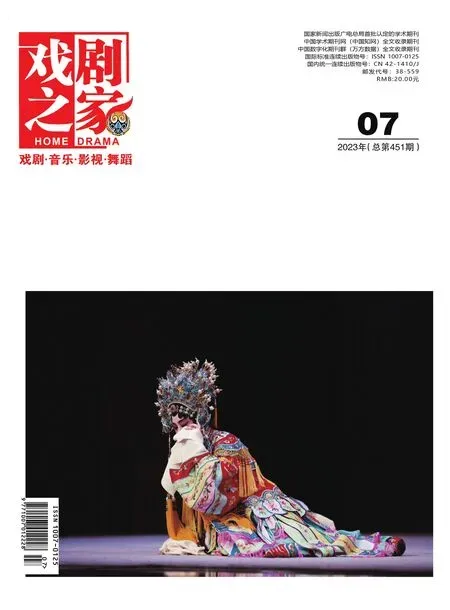巴洛克時期“兩種常規”音樂思想研究
付寶超
(云南藝術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克勞迪奧·喬瓦尼·安東尼奧·蒙特威爾第(Claudio Giovanni Antonio Monteverdi,1567—1643)是杰出的意大利作曲家。其音樂創作包括牧歌、歌劇、世俗音樂、宗教音樂等領域。根據史料記載,蒙特威爾第《牧歌集》第四卷中出現了許多不協和音的使用,隨后在1605年的《牧歌集》第五卷中提出了“兩種常規”(“prima pratica”和“seconda pratica”)的思想。“prima pratica”和“seconda pratica”在西方音樂史著作中,翻譯版本有多種,最常見的是“第一種音樂實踐”和“第二種音樂實踐”①,“第一實踐”和“第二實踐”②,“第一常規”和“第二常規”③等。本文使用國內常用的概念“第一常規”和“第二常規”翻譯版本。“兩種常規”的出現,標志著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音樂風格轉變的重要歷程。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研究發現,國內音樂學界對于“兩種常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種常規”產生的背景、原因和兩者的區別,以及“兩種常規”在牧歌中的運用等方面。本文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相關文獻中所涉及的異同點進行研究。
一、“兩種常規”產生的原因
“兩種常規”概念的產生不是偶然現象,也不是作曲家突然的創作沖動,其出現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基于16、17 世紀社會文化的發展,宗教音樂與世俗音樂互相影響的背景之下。第二,持續了10年之久的阿圖西與蒙特威爾第之爭。1598 年,意大利作曲家安東尼奧·高萊迪(Antonio Goretti,1570—1649)在家中舉辦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的內容包括蒙特威爾第創作的牧歌,這場音樂會成為“阿圖西—蒙特威爾第”之爭的導火索。“兩種常規”的出現不僅促使蒙特威爾第的音樂為人所知,還使其成為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音樂風格轉變的重要因素。
阿圖西(G.M.Artusi,1540—1613)的老師扎利諾(Gioseffo Zarlino,1517—1590)出版的《和諧的規則》(1558)是阿圖西在這場爭論中的重要依據。“扎利諾以‘對位聲部的美’為目標,制定了和聲進行的原則,明確要求音程必須有變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還提到不協和音在對位音樂中的美學價值及相應的安排方式,并為多聲部創作中如何運用調式、判斷調式提出了更為明確的看法。顯然,扎利諾的這本論著對于多聲部音樂的創作,有很多新穎的不同以往的獨到見解。”④在聽到蒙特威爾第的牧歌后,阿圖西產生了強烈的反應,他在1600 年出版的《阿圖西,或現代音樂的不完美》中引用蒙特威爾第的牧歌《冷酷的牧羊女》的片段,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新的手法違背了扎利諾的對位規則。此后,阿圖西在1603年出版的《阿圖西,或現代音樂的不完美,第二部分》中繼續批評對方。
蒙特威爾第在1605 年《牧歌集》第五卷中對阿圖西的觀點做出了回應,并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的內容大致是:蒙特威爾第認為除了扎利諾的理論之外,還有其他的方式出現,提出“兩種常規”的思想,認為扎利諾的理論是“第一常規”,自己的新作曲手法稱之為“第二常規”。隨后,蒙特威爾第的弟弟——朱里奧·凱撒·蒙特威爾第(Giulio Cesare Monteverdi)發表言論支持自己哥哥的觀點,他認為“第一常規”中和聲是歌詞的主人,“第二常規”中歌詞是和聲的主人。阿圖西于1608 年發表《論音樂》之二,再次提出自己的觀點并對蒙特威爾第的觀點進行抨擊,然而蒙特威爾第以及他的弟弟并沒有任何回應,長達10 年的爭論就此落下帷幕。
吳新偉《兩種作曲實踐的論戰——對“阿圖西—蒙特威爾第”之爭的分析、評價和再審視》將“兩種常規”背后爭論的原因擴展到更深層次。第一,商業利益的驅動。蒙特威爾第和阿圖西背后的出版商存在競爭關系,有可能是出版商為了增加商品的銷售量,在背后煽風點火,作為一種吸引注意力的方式。兩個出版商從經濟利益出發,通過出版爭論的書籍吸引大眾的目光,在此過程中,《牧歌集》的出版也使蒙特威爾第的名聲和成就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第二,教會與世俗的博弈。博洛尼亞是一個天主教控制的城市,世俗宮廷的力量在音樂方面的影響要小很多。相反,在費拉拉、曼圖亞等城市中,宮廷對于音樂藝術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兩個城市的文化氛圍完全相反。阿圖西是天主教的神職人員,蒙特威爾第是宮廷的人文主義者,兩人在諸多方面存在著對立。兩種勢力通過爭論在此碰撞,不一定理解為哪方獲勝,而是蒙特威爾第代表了當時音樂發展的主要趨勢。
二、不同視角下對“兩種常規”的研究
“兩種常規”代表了當時不同的作曲風格。“第一常規”以文藝復興時期喬瓦尼·皮耶路易吉·達·帕萊斯特里那(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為代表的16 世紀音樂風格,謹慎使用不協和音,嚴格限制二度、七度等音程的使用,又稱作“古老風格”或“嚴謹風格”,“第二常規”指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在創作中,更好地體現歌詞內容在音樂中的表現,又稱為“現代風格”或“裝飾風格”。“第二常規”的出現“與卡梅拉塔會社成員10 多年前提出的藝術主張一致,音樂能夠愉悅人們的心靈,牽動心靈情感的愿望。蒙特威爾第強調歌詞的表現力,強調音樂中旋律對情感的表現,不協和音自由處理等。其創作的作品在音樂的表現力上超過了同時代作曲家的創作思路,這些方面為之后“激動風格”概念的出現埋下伏筆。”⑤
“第二常規”的思想,源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的著作《理想國》,柏拉圖提出:音樂的旋律和節奏應該追隨歌詞,強調歌詞是第一位的。曹耿獻《“兩種常規”與十六世紀“歌詞與音樂的關系”變化及觀念發展的研究》對于“兩種常規”的區別,以詞曲關系的視角,通過兩個方面進行深入闡述。第一是歌詞的清晰,第二是歌詞情感的表達。作者首先提到,中世紀時期格里高利圣詠是歌詞與音樂緊密結合的形式,音樂服從于唱詞,但是與蒙特威爾第提倡的“音樂能更好地表現歌詞內容”這一理念完全不同,格里高利圣詠僅僅是宣傳宗教儀式的一種方式。其次,隨著復調音樂的發展,直至1545—1563 年在意大利舉行的特倫托公議會,而會議內容只是要求復調音樂中的歌詞應當使眾人聽清,要激發聽眾內心的虔誠、去除一些不純潔的內容等,并沒有強調歌詞情感在音樂中的表達。最后,對扎利諾、V.伽利略(V.Galilei)、蒙特威爾第三位作曲家之間的觀點進行分析。16 世紀扎利諾雖然意識到歌詞在音樂中的重要性,但是受到文藝復興晚期音樂思潮的影響,并沒有蒙特威爾第“第二常規”中強烈的觀念。V.伽利略1581 年出版的《古今音樂對話》中提出:作曲家應該到現實生活中去注意傾聽各種人物的語言音調,當今的復調音樂,對通過歌詞表達內心的情感沒有太大價值,它只對管弦樂器有價值。蒙特威爾第的理念介于扎利諾和V.伽利略之間,在復調音樂中開始實踐一些新的作曲技法,目的是更好地表達歌詞的意義及情感。三者的共同點在于受到柏拉圖《理想國》的影響,他們都提到“歌詞的情感表達”,但是三人對于歌詞、旋律的理解各持己見。“兩種常規”的概念“并不是完全對立的概念,只是音樂“和諧”程度的不同,這個結論和當代國內通用的很多西方音樂史書中對“兩種常規”的解讀的定義和理解是不同的”。⑥
吳新偉《兩種作曲實踐的論戰——對“阿圖西—蒙特威爾第”之爭的分析、評價和再審視》提到:“兩種常規”來自不同的立場,以蒙特威爾第的弟弟在辯護的過程中引用柏拉圖的理論作為依據,從而提出羅勒(Ciprino de Rore)是“第二常規”的先驅。認為蒙特威爾第提出“第二常規”之所以是“第二”,不是“新”,是蒙特威爾第對傳統方式的完善和發展,并沒有拒絕傳統,又或者是對已經存在的“第一常規”的復興。而兩者爭論中所展現的,是文藝復興時期不同美學觀念的碰撞。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第一常規”強調以人耳的聽覺為審美判斷的依據,這是一種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審美標準,追求的是在聽覺感官上的和諧、悅耳,“第二常規”以音樂中對人的情感表現的“真”為審美判斷的依據,這是一種建立在內心情感體驗上的審美標準,追求的是喚起聽眾內心真實情感。⑦
三、“第二常規”在牧歌中的運用
國內學者對于蒙特威爾第“第二常規”在牧歌中運用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坦克雷迪與克勞琳達之爭》《冷酷的牧羊女》《讓我死吧》這三首牧歌。收錄在《牧歌集》第五卷中的《冷酷的牧羊女》反映了蒙特威爾第的音樂美學觀念及創作手法,也是“阿圖西—蒙特威爾第”之爭就“兩種常規”創作手法爭論的主要對象。《牧歌集》第五卷的前言也是蒙特威爾第首次回應阿圖西的批判,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二常規”是他關于協和及不協和音程的運用,不同于以往作曲方式。《牧歌集》第六卷中的《讓我死吧》復調織體開始變化,支持上方聲部,低音區與上方聲部建立一種新的調性關系。《牧歌集》第八卷《坦克雷迪與克勞琳達之爭》節奏運用得更加隨心所欲,旋律上呈現出新穎的片段式,更是以“激動風格”聞名于世,為蒙特威爾第的牧歌作品又添上了光輝的一筆。這首牧歌在音樂美學上,完美地呈現出蒙特威爾第“第二常規”的觀念,在“歌詞與音樂的關系”方面詮釋得更為出色。
在音樂中對位手法是寫作的核心,教會調式以及和聲作為主要的織體語言。在終止式方面,終止式不僅在調式以及調性中起到重要作用,還作為和聲表達的集中體現,屬三和弦到主和弦進行,依舊是調式和聲的性質,也體現出調式和聲向調性和聲過渡的表現。屬七和弦到主和弦的進行,也標志著調性和聲的到來。在調式方面,在牧歌中以教會調式為基礎對和聲加以改變,伊奧利亞和愛奧尼亞調式的使用,音樂中具有濃郁的調性和聲色彩。蒙特威爾第代表性的三首牧歌,“第二常規”音樂思想貫穿其整個牧歌創作過程,從教會調式逐漸向大小調調性轉變,可看出調式調性上呈現從教會和弦材料呈現出音程對位性質的和弦向大小調功能和弦由簡到繁的運用。
四、結語
蒙特威爾第作為橫跨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杰出的作曲家,他的牧歌作品體現出16 世紀至17 世紀音樂風格的變化。從早期的對位復調風格到中期風格提出的“兩種常規”音樂觀念,再到后期“激動風格”的牧歌創作,蒙特威爾第的創新實踐也將牧歌體裁的音樂創作推向了頂峰,牧歌中呈現出的和聲特征不僅是他“第二常規”創作風格的重要體現,也是音樂作品發展中調性、和聲的“前奏曲”。“兩種常規”在西方音樂史發展的歷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標志著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音樂風格轉變的重要歷程,反映了由宗教音樂占主導地位的時代,轉向世俗音樂蓬勃發展的過渡,也驗證了人性解放的漫長過程。
注釋:
①[美]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M].顧連理,楊燕迪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②[美]唐納德·杰·格勞特,克勞德·帕利斯卡.西方音樂史[M].余志剛,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199.
③于潤洋.西方音樂通史[M].上海音樂出版社,2012.
④曹耿獻.“第一實踐”和“第二實踐”研究[D].上海音樂學院,2007.
⑤翟源,楊九華.阿圖西與蒙特威爾第間的論爭背后[J].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2,(04):57-61.
⑥曹耿獻.“兩種實踐”與十六世紀“歌詞與音樂的關系”變化及觀念發展的研究[J].人民音樂,2011,(12):86-88.
⑦吳新偉.兩種作曲實踐的論戰——對“阿圖西—蒙特威爾第”之爭的分析、評價和再審視[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2,(04):6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