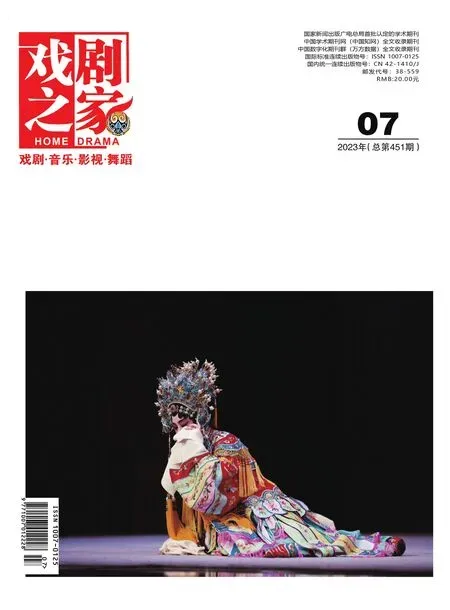古箏重奏中不同聲部演奏的共性化處理及藝術價值表現
——以重奏曲《翡翠》為例
王 琛,陰明娟
(太原師范學院 山西 晉中 030619)
《翡翠》是由作曲家王丹紅女士創作的一首民族彈撥樂合奏曲,該作品采用了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后由演奏家周展先生將合奏曲改編為古箏四重奏作品。[1]該重奏曲擁有動感十足的節奏,四個聲部中縱向的大三和弦不斷變換,旋律線條此起彼伏,運用較高難度技法的同時加入變化音,獨特的音響效果使西南少數民族的音樂形象更加飽滿。
一、不同聲部演奏的共性化藝術處理
如果情感是音樂的靈魂,那么技巧則是音樂的根基,只有打好基礎,才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對于古箏重奏而言,各位演奏者首先需要解決的難題是各聲部要在復雜多變的技法中找尋音色的融合。
(一)搖指
在樂曲的第一樂段中,作曲家運用大量的搖指技法,持續的旋律音型以及四聲部音區上的色彩變換使旋律風格展現了若隱若現的感覺。因此,在開始演奏之前,各個聲部之間互相看一眼對方,同時吸氣抬臂,隨后統一演奏第一個搖指音符,要求過弦時要自然且旋律連貫同時注意音樂走向上強弱的變化。樂曲開始部分四個聲部保持“p”力度的整體音響,展現一種朦朧的畫面。隨后四個聲部以“pp”的力度呈現,隨上行音符的進行使力度逐漸增加,搖指的音色逐漸明亮,宛如撥開煙霧一般。因此,要格外注意控制好整體的搖指力度,并且每個聲部保持均勻的搖指頻率和統一的音符時值。每個樂句結尾處注意統一以弱音收束,使大家的情緒保持在同等的層面,從而使整體音樂和諧。
(二)拍板
時代的發展促使人們的審美需求發生轉變,許多作曲家在古箏技法方面進行一系列創新,促進古箏藝術的發展,例如所有手指集中力量擊打琴弦、拍擊琴盒的不同位置發出不同的音響效果以及指尖敲擊琴板等一系列拍板技法。這種拍板技法在現代古箏創作中廣泛使用,例如陳哲創作的《蒼歌引》、王建民創作的《幻想曲》等。
箏Ⅱ聲部與箏Ⅳ聲部在樂曲中結合了大撮與拍板的演奏技法,每位演奏者在開始時同時吸氣,注意手腕的彈性,拍擊后的力量迅速反彈回原來的位置,手指繃緊富有彈性,賦予聲音活力,動作、速度以及力量的統一使得視覺與聽覺方面都達到整齊的效果。箏Ⅱ聲部的拍板采用的演奏形式是用義甲敲擊琴盒,模仿敲擊鼓邊的音響效果,律動性的節奏展現多彩的音樂場景,與箏Ⅰ聲部的主旋律發生碰撞,表現了當地人民圍著篝火隨著鼓點舞動的熱鬧場景。
(三)人聲伴唱
該作品最突出的特點是加入了人聲的伴唱,通過人聲的“啊”和“嗚”增強了樂曲的律動性,不同的發音方式呈現了不同的情緒,使音樂色彩豐富起來。人聲伴唱“啊”的音高與古箏演奏的音高相對應,充分將兩者融合在一起,表現出和諧的生活狀態。人聲伴唱“嗚”使整個情緒走向低沉且黯淡,“嘿嘿嘿”襯詞與拍板相結合,節奏鏗鏘有力,表現了當地人民熱烈狂歡的場景。在演奏襯詞“嘿嘿嘿”的同時進行獨特處理,加入了雙手在身體的右前方拍擊三下,此時身體坐直,眼睛看向前方,雙手的位置大致與視線在一個水平面上,隨后演奏后面的拍板,將熱鬧的景象持續下去。
二、不同聲部演奏的共性化處理要素分析
一首完美的古箏重奏需要各聲部成員的統一部署和精心安排,每名演奏者的分工不同,在各個聲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盡相同,弄清楚每個聲部的演奏規律能使演奏者更準確地演奏整首作品。重奏練習的要素有許多種,包括聲部的分配符合每位成員的能力水平、各聲部之間的配合達到視覺和聽覺方面的統一等。
(一)了解樂曲和各聲部分配
在拿到一首新作品時,每個人都應對曲目的背景進行充分了解,掌握作品本身的音樂風格。在音樂表演中,各聲部與演奏者的對應是一首樂曲成功演出的最基本的條件,對于聲部的分配要仔細分析,更多的是要注意各個聲部之間旋律的配合。[2]在《翡翠》這首作品中,每個聲部各有其職責,尤其是第一聲部和第三聲部之間,無論是節奏還是音符都完全不一致,四個聲部融匯到一起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也恰好說明了現代重奏作品正在蓬勃發展。
了解樂曲的每個聲部后,演奏者需根據自身的情況來選擇聲部,熟練掌握自己聲部的同時也必須熟悉各個聲部的分配。
(二)各聲部之間的配合
古箏重奏,顧名思義,是由多個聲部演奏樂曲的一種演奏形式,各聲部之間互相襯托,既有獨立性又具備整體性,共同促進音樂旋律的發展進行。由于聲部增加,演奏人數也必須增加。各個聲部之間的默契配合需要通過后天訓練、每個演奏者不斷進行磨合才能完成,這便要求每個聲部的演奏者在節奏上是同步的。[3]同時,演奏者們要善于聆聽,在了解自己聲部的同時也要熟悉他人聲部,在相互配合中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演奏中做到“百戰不殆”。
1.氣息
在氣息方面,氣息的準確應用是樂曲連貫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各聲部之間默契配合的必要因素。演奏中若沒有氣息的配合,那音樂便失去了活力。不同氣息的運用會產生不同的音樂情緒,從而直接影響到樂曲的速度,這就要求所有演奏者的氣息統一,通過氣息的運用來控制整個力度的變化,尤為注意呼吸的強弱,才能呈現出完美的演奏效果。在樂曲開始之前,演奏者首先要調整好氣息,達到“未成曲調先有情”的表演狀態,隨后凝聚所有氣息的同時帶動手臂運動,演奏出第一個樂音。
2.舞臺表現力
在舞臺表現力方面,古箏重奏最重要的是演奏整齊,想要實現良好的舞臺演出效果,每位演奏者的肢體動作也需要達成統一。這就要求演奏者在日常排練中加入身體動作的訓練。抬手的高度、主旋律聲部的重音位置以及伴奏聲部律動時的頭部運動、結尾時的收束動作等都是演奏者需要練習的。
(三)音樂本體方面的統一
音樂作品構成中的各種音響構成因素,就是音樂本體[4]。音樂本體的研究關乎什么是音樂、音樂的功能以及音樂的內容與形式等一系列問題,任何一首重奏作品都要經過一次次的排練才能達到相對成熟的默契感,因此,演奏者在排練時要格外注意以下幾點:
1.音準
在音準方面,確定各個聲部之間的音準統一是演出或排練前必做的準備工作,一絲細微的音準偏差在聽覺上是尤為尖銳的,因此在開始前所有的演奏者需利用調音器校音,保證每個聲部所有音準的統一性,并且音準的把握要服從整體音準需要。同時《翡翠》這首樂曲中存在轉調的情況,要清楚變動哪個聲部的哪根琴弦,并且轉調后的音準也是統一的,這就要求預留出變動琴弦所移動位置的間隙,找準變調后琴碼的新位置并做好標記。另外,由于古箏調性的特殊性,需要通過左手的按弦來表現變化音,左手按弦的力度或深淺決定了變化音的高低,這需要進行系統訓練,培養演奏者的綜合音準感,避免樂曲中出現音準偏差導致聽覺的混亂。
2.速度
在速度把握方面,尤其是快板部分,由于速度很快導致演奏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彈奏的音符上,容易出現搶拍等情況,演奏者控制不住自己的速度那么整體的節奏便會混亂,由此可見速度統一的重要性。古箏重奏作品《翡翠》的多個樂段中,不斷變化的節奏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音樂的律動感,但也加大了演奏者速度統一的難度。在練習的過程中,采用跟著節拍器慢練的方法,精確到四個聲部每一拍的每一個音,熟練后慢慢加速,每個演奏者心中的速度逐漸統一,這樣一步步訓練形成良好的默契,那么速度把握也就一致了。
3.強弱
在強弱控制方面,每個演奏者的強弱表現應是一致的,采用“均衡式”的力度處理可以準確地表現出音樂所表達的意境,并展現出不同的層次感。在排練時所有演奏者準確區分力度的強弱變化,并機敏地對待強弱的處理,服從于整體音量均衡的需要。將處理弱與強、漸強與漸弱等力度記號統一起來。例如,在演奏“p”記號時,所有演奏者的演奏區域集中到琴弦的中間位置,身體微微向下低;在演奏“f”記號時,演奏區域集中在靠近前岳山的位置,身體向上,腰背挺直;在演奏“p<f”記號時,演奏區域從琴弦中間位置逐漸移向邊緣處,音色逐漸放亮,身體逐漸立起來。強弱控制的穩定性與準確性需要每一位演奏者高度集中注意力,增加對音樂情感變化的敏銳性,呈現出音樂的多個層次,更加貼近音樂所要表達的情緒。
三、藝術價值
(一)彰顯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的特色
我國的西南地區聚集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每個少數民族對西南地區的文化底蘊和風土人情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各民族之間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5]古箏重奏作品《翡翠》以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素材為基調,將苗族的“飛歌”音調、侗族的“大歌”合唱、人聲伴唱和敲擊拍打等特殊音響相融合,充分彰顯了西南地區的文化底蘊與風土人情,描繪出絢麗多彩的美好景象,讓聽眾從音樂中感受到當地的山明水秀和文化氣息。
(二)豐富音樂的表現力
作品運用的創作手法為西方多聲部織體,中國傳統音樂元素與西方創作手法相結合,并加入了人聲哼唱和伴奏樂器,打破了傳統民族器樂的曲式結構和創作理念的約束。四個聲部相互競爭演奏后又回歸到了統一,橫向多線條的旋律色彩體現出每個聲部之間既交錯又融合的特點,描繪出當地人民的熱情態度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促進創新性發展
該重奏曲通過一些演奏技巧制造出的音響效果,無形之中營造濃厚的氛圍,表達深刻的情感內涵,豐富了作品的音響效果,擴大了音樂的表現力,使觀眾在欣賞的過程中,可以體驗到視覺和聽覺的雙重美感。同時,重奏的演奏形式不僅對我國未來古箏的發展指明了探索的方向,還帶來了無限創新性的可能。依靠音樂動機的發展,憑借多個聲部呈現,放大創作空間的同時也使得音樂基本框架變得高級且復雜。
四、總結
本文通過對古箏重奏作品《翡翠》的探究,總結重奏作品需要演奏者們對一首樂曲有同樣的見解,在聲部配合之中有同樣的理解方式,充分了解不同風格作品所蘊涵的音樂情感和音樂形象,提高自身的藝術素養。每位成員探索演奏中所蘊含的共性化演奏處理,把音樂整體效果擺在首要位置,增強個人的集體意識。古箏重奏曲《翡翠》新穎的樂曲形式和獨特的技法運用突出了音韻之間的融合,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為其他研究古箏重奏的學者提供思路,進而更好地培養古箏藝術人才,推進古箏藝術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