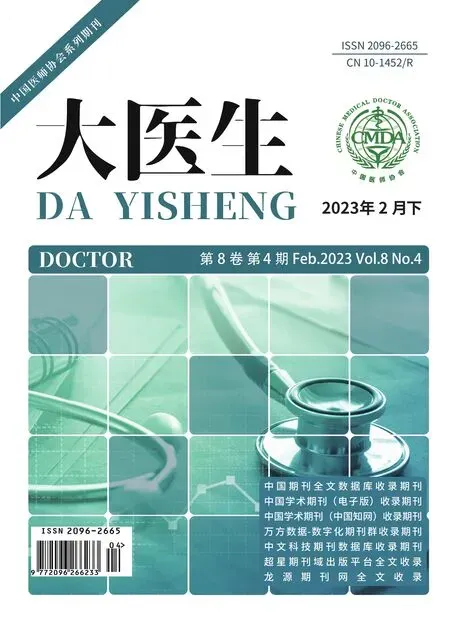伏邪理論指導潰瘍性結腸炎的中醫藥治療
王格格,邱雪瑩,陳新勝
(1.湖北中醫藥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5;2.湖北中醫藥大學附屬鄂州中醫醫院消化內科,湖北 鄂州 436000)
潰瘍性結腸炎是一種主要累及結腸和直腸的慢性腸道炎癥性疾病。臨床表現為間斷性腹瀉、黏液膿血便、腹痛及里急后重等。牟強[1]以60 例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為例開展相關研究,結果表明相比常規的西醫治療,加入中醫藥的治療,不但能緩減不良作用而且對患者后期身體恢復有極高的價值。現階段西醫對潰瘍性結腸炎的治療雖在短期內有成效,但潰瘍性結腸炎易復發的特點提示對其的治療注定是一場“持久戰”,而長期的西醫治療對患者的胃腸道刺激較強,尤其對于體質較差的患者還可能誘發其他并發癥,加重病情的復雜性;中醫藥治療能夠在改善潰瘍性結腸炎癥狀的同時,注重調節脾胃的平衡,其優勢顯然。而張莉敏等[2]基于伏邪理論對潰瘍性結腸炎的治療的研究提示,應用中醫經典理論“伏邪理論”治療現代難治病例如潰瘍性結腸炎安全有效,值得深究和推廣。
“內傷伏氣致病”流派代表性傳承人朱祥麟教授認為發病病機為濕熱毒邪蘊結于結腸。飲食不潔,濕熱邪氣感而內伏,過期而發病。本文總結潰瘍性結腸炎多年診療經驗,收集潰瘍性結腸炎的中西醫結合診治相關古今文獻、臨床病例,擬定特色中藥方劑,為其臨床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1 潰瘍性結腸炎的傳統中醫認識
潰瘍性結腸炎無具體的中醫病名,對其類似臨床癥狀的論述可見于“腸澼”“泄瀉”“便血”等多種疾病[3]。最早出現是在《黃帝內經》中關于“腸澼”的描述。如《素問·通評虛實論》中“腸澼便血何如”“腸澼下白沫何如”“腸澼下膿血何如”,后世也將其稱為痢疾[4]。《素問·太陰陽明論》中記載“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入五臟,則脘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5]。”《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為痔[6]。”皆表明飲食起居不節,脾胃內傷而易于致病。《諸病源候論》云:“凡痢皆由榮衛不足,腸胃虛弱,冷熱之氣,乘虛入客于腸間,腸虛則泄,故為痢也。”可見該病發病基礎為脾胃大腸虛弱[7]。李永成教授認為潰瘍性結腸炎是以濕熱瘀等邪為標,臟腑失調為本,標本同病,《溫病條辨·濕溫》中有:“穢濕著里……氣機不宣,久則釀熱……穢濕著里,邪阻氣分……穢濕著里,脘悶便泄”,濕熱之邪互結,熱邪易灼傷血絡,濕邪性黏趨下,蘊結腸道,久而成毒,脂膜腸絡受損,肉腐釀膿,則見帶下黏液血便[8]。《證治匯補·痢疾》言:“惡血不行凝滯于內,侵入腸而成痢疾,純下紫黑惡血。”瘀血是潰瘍性結腸炎發病的驅動因素,瘀血日久,客于腸內,易于復發,陽氣逐步虛損,血液運行無力,且氣血壅滯后致血敗肉腐成膿,整個病程遷延難愈[9-11]。《景岳全書·泄瀉》有云:“脾弱者,因虛所以易泄,因瀉所以愈虛……下必及腎……所以泄瀉不愈,必自太陰傳于少陰。”脾為后天,腎為先天,脾主運化,將飲食水谷轉化為水谷精微,并將其吸收、轉輸到全身臟腑;腎陽助脾陽吸收、轉輸精微。腎陽不足,不能溫煦脾陽,會致脾陽不振,而脾陽若是久久虛弱,又會進一步影響到腎陽,導致腎陽虛衰,故脾腎虛弱是久瀉久利的重要病因[12]。
古今醫家一致認為潰瘍性結腸炎以本虛標實為主要病機特點。國醫大師李佃貴教授認為素體脾虛,運化不利,水濕等邪氣內生,蘊結于腸,郁熱內生,濁毒阻滯氣機,最終傷及腸壁脈絡而致病[13]。李乾構也認為潰瘍性結腸炎以濕熱痰瘀為標,以脾虛為本,久而及腎[14]。王長洪亦言脾虛為發病基礎,濕熱毒邪誘發致病,氣滯血瘀等病理產物貫穿整個發病過程[15]。潰瘍性結腸炎的發生與環境、飲食、五志等后天因素密不可分,其病位主要在腸,與五臟關系緊密,尤與脾胃為甚,久而及腎[16]。故中醫主張“益氣健脾,澀腸止瀉”的治法[17]。
2 基于伏邪理論認識潰瘍性結腸炎
2.1 伏邪理論的內涵伏邪又稱伏氣,為潛伏而暫不發之邪。最初屬于伏邪溫病的范疇,即狹義的伏邪,因外邪入體、正氣被遏或正氣虛弱不能鼓邪外出,使邪氣潛藏于脂膜、膜原、肌腠部位,伺機而發[18]。且伏邪非指六淫,專指癘氣內伏,邪伏膜原[19]。《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冬傷于寒,春必溫病”的論述,為伏氣學說之肇端,指出感寒未及時發病可成為伏邪,潛藏于體內,遇感而發,且發病與否取決于人體正氣是否充沛。隨著溫病學說迅速發展,伏邪不僅局限于伏邪溫病,還逐漸擴展到一切體內伏而不即刻發病的邪氣,即廣義的伏邪。《王氏醫存》載:“伏匿諸病,六淫、飲食、諸郁、結痰、瘀血、積氣、蓄水、諸蟲皆有之”,又進一步提出伏邪不僅局限于外感六淫,還包括內傷雜病,主要為濕熱、瘀血、痰濁、內毒等內在的致病因素[20]。總之正氣虛損,邪氣伏存,正氣勝邪,故邪雖伏存而不發,正不敵邪,故發而為病[21]。
2.2 伏邪理論與潰瘍性結腸炎的相關性郭富彬等人通過因子分析研究,調查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癥狀的多元性及高度復雜性,誘發因素的規律性及反復發作的疾病特性,發現傳統的單一發病機制很難解釋潰瘍性結腸炎中醫病機,而中醫相關“伏邪”理論依據病邪所伏部位和性質的不同,其癥狀及多重易感性也存在差異,這與潰瘍性結腸炎癥狀多樣性及復發的規律性有很高的一致性[22]。杜曉泉教授認為潰瘍性結腸炎的發病機制與濕熱之邪所伏部位有關,腸道因層面較深,氣血流動慢,故而邪易伏于此[23]。董時潔等通過對活動期潰瘍性結腸炎血液流變學檢測實驗研究表明:潰瘍性結腸炎患者血液濃度及黏稠度偏高,血液不能充分營養腸道黏膜,導致細胞缺血、缺氧而變性壞死,腸道黏膜組織因此損傷,加之血液黏稠度高使毛細血管因血運不暢而阻塞,血液凝結,血栓形成,腸道黏膜組織壞死,形成潰瘍[24]。潰瘍性結腸炎始發經治療后多有濕熱之邪未除而藏匿于體內,具有一定的活動性,一旦素體正氣虛損,加之感受外邪,則容易復燃,甚至累及他臟[25-26]。黃雅慧教授提出對于潰瘍性結腸炎的治療需根除伏邪,謹防留瘀,同時需扶助正氣,正盛邪退,根本上應祛除誘因,預防再發[27]。
2.3 以伏邪理論為指導治療潰瘍性結腸炎
2.3.1 健脾燥濕,清熱解毒,和血生肌 主證:晨起腹瀉,一日多次,日久不愈,黏凍便或夾膿血,腹脹,里急后重,納谷欠佳,形瘦乏力,口干少飲,舌黯紅苔白黃膩,脈濡緩。
方藥:朱氏自擬健脾愈瘍湯(黃芪15 g,白術10 g,薏苡仁20 g,升麻6 g,黃連5 g,五倍子10 g,地榆15 g,赤石脂20 g,三七粉3 g,木香10 g,白及10 g,甘草9 g)。
按語:潰瘍性結腸炎復發活動的關鍵在于濕熱蘊腸,脂膜血絡受傷,氣血不調,大腸傳導失司。濕為陰邪,重濁黏滯,濕與熱合,熱熾濕郁,充斥三焦。熱入濕中,如蜜之黏滯,膠結不解。濕熱伏藏,膠結于體內,難以清解,遷延難愈,成為“濕熱伏邪”。濕重則陽微,熱重則陰竭,致正氣耗損,無力驅邪外出,使“濕熱伏邪”潛藏于體內,每遇誘因而發。《景岳全書·泄瀉》云:“泄瀉之本,無不由于脾胃。”[24]脾虛是濕熱伏邪的前提和基礎,也是誘發濕熱伏邪反復發作的重要因素,因此,針對濕熱伏邪,當補益脾胃之氣,合以燥濕,助邪外達。方用黃芪、白術、薏苡仁、升麻補脾益氣升清;白術、薏苡仁、黃連燥濕利濕,清熱堅腸;木香行氣以除后重;三七和血止血;白及活血生肌;地榆活血、涼血、止血;改善結腸陰絡血液循行而止血便;五倍子、赤石脂涼血澀腸固下。而黃芪配黃連能治膿便,黃芪配白及去腐愈瘍,甘草調和諸藥。現代藥理研究證實甘草具有消炎、抗氧化、抗癌、免疫調節等多種藥理作用,在調和全方藥效中發揮著卓越的作用[28-29]。
2.3.2 理氣活血、化瘀消滯、蕩滌濁邪 主證:腹痛即瀉,瀉后痛緩,日久不愈,腹脹甚,兩脅不舒,腹鳴,膿血粘凍,里急后重,納少噯氣;面目下黯,舌瘀苔白黃,脈弦滑。
方藥:膈下逐瘀湯《醫林改錯》減味(赤芍10 g,當歸10 g,川芎10 g,紅花10 g,玄胡10 g,五靈脂10 g,烏藥10 g,香附10 g,枳殼10 g,甘草6 g)。
按語:邪毒內困既久,肝失疏泄,氣機塞滯,久病入絡,瘀結于腸,則瘀血與邪毒膠結難解,損傷結腸肌膜,形成潰瘍而不愈。故治法應以理氣活血、化瘀消滯、蕩滌膠濁之邪為主。方用王清任膈下逐瘀湯去桃仁、丹皮。原方治“腎瀉”“久瀉”“百方不效”者,謂有“瘀血過多”所致。方中香附、烏藥、枳殼疏肝理氣行滯,當歸、川芎、紅花、玄胡活血化瘀,尤其五靈脂腥味入絡,化瘀血,祛膠濁;合用之使腸道蘊結日久之瘀滯消除,使潰瘍能祛瘀生新以愈。此“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之理。氣血調和,脾胃亦健,腸腑通順,頑疾可漸痊愈。根據相關藥理學研究表明,結腸黏膜病理異常的情況通過調氣活血中藥的治療后有明顯改善,例如方中川芎具有抗炎、改善血液循環、抗血小板凝集等作用[30];香附具有極佳的抗炎鎮痛作用[31]。紅花能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所誘發的血小板聚集、釋放[32]。
2.3.3 補腎溫陽,活血復膜 主證:腹瀉一日二三次,久不愈,腹痛綿綿,待暖則舒,便多黏凍、少膿血,里急后重,肢末畏冷,尿清長或尿頻澀,腰酸,舌黯瘀、少白苔,脈沉細微。
方藥:自擬補腎復膜湯(黃芪15 g,補骨脂10 g,肉豆蔻6 g,五味子10 g,淫羊藿15 g,當歸10 g,三七粉3 g,兒茶6 g,赤芍10 g,木香6 g,白及10 g,炙甘草6 g)。
按語:濕熱伏邪,內伏日久,耗傷臟腑陰陽,至陰陽虛損,氣血虧虛,繼而出現脾腎陽氣俱衰,病程后期形成寒熱、虛實交雜之證。方用黃芪大補元氣,淫羊藿、補骨脂、五味子補腎溫陽,木香行氣,當歸、赤芍、三七和血消瘀,白及、兒茶和血以復腸膜潰瘍,肉蔻溫中,炙甘草補中并和諸藥。合方有補腎溫陽,和血消瘀,修復結腸潰瘍以止瀉的功用。
2.3.4 清熱解毒,通腑存津 主證:突發腹瀉,一日數次,膿血黏便,腹痛腹脹,里急后重,并發熱,口渴欲飲,甚者心悸,舌紅乏津,脈芤數。
方藥:金花丸合小承氣湯加味(黃連5 g,黃柏15 g,黃芩10 g,梔子10 g,厚樸10 g,枳實10 g,大黃10 g,地榆10 g,金銀花10 g,人中黃10 g,天花粉10 g)。
按語:金花丸即黃連解毒湯,具有很強的清熱燥濕解毒作用,合小承氣湯通因通用。通腑逐邪,加金銀花、人中黃增強透熱解毒之功,地榆涼血活血止血,花粉清熱生津止渴。合用以清解伏于結腸之毒邪,存正氣而愈病。若兼心悸神昏者,加服至寶丹。熱解癥緩后,用芍藥湯加減調治。
2.3.5 生肌斂瘍,寧絡止血 方藥:外用苦參五倍灌腸方(苦參30 g,黃連15 g,地榆30 g,白及30 g,五倍子15 g)[33]。每日或二日一劑,以水濃煎,每次取100 mL,溫度37~39 ℃,輸液瓶裝,用導尿管插入,緩慢滴注,控制在60~80 滴/分,1 次/d,7 日為1 療程。配合內服藥,可提高療效。相關研究發現,潰瘍性結腸炎患者機體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8(IL-8)等炎癥介質釋放會因核因子κB(NF-κB)活性上升而增加,從而引起炎癥反應。而苦參等中藥灌腸可以下調抑制蛋白α(IκB-α)蛋白水平,降低NF-κB 的活性,抑制TNF-α、IL-6、IL-8 等炎癥介質的分泌,減輕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的局部炎癥反應[34]。
3 臨床治驗病案
易某,女,56 歲。1998 年4 月26 日初診。數年前因發熱、腹瀉、腹痛,中藥治療后熱退癥緩解,后常腹痛,每日大便3~5 次,量少,糊狀,夾黏凍膿血,里急后重,便后腹痛減輕。曾多次查大便,排除痢疾病。結腸鏡檢查:“結腸黏膜水腫、糜爛、潰瘍、出血”,診斷為“慢性非特異性潰瘍性結腸炎”。經服多種中西藥及成藥,時好時發。終未能愈。刻診臍周及右下腹時痛,痛則欲便,便后腹痛緩解,兩脅時脹滿,噯氣,大便糊狀,夾黏液、膿血、里急后重,面黃晦,舌黯紅,熱蘊結腸,少白黃苔,脈弦細,腹軟,左下腹輕度壓痛。
方用膈下逐瘀湯減味,每日內服1 劑。餐前服。另用自擬苦參五倍灌腸方,1 次/d。
1998 年5 月3 日二診:經1 周治療,腹痛減輕,脅脹滿已除,大便次數每日2~3 次,里急后重,黏液膿血大減。仍用原方去枳殼、紅花、玄胡,加蒲黃、白及、薏苡仁,服藥7 劑,灌腸5 日。
1998 年5 月10 日三診:腹痛已消失,大便日一二次,軟而成形,無黏液膿血便,肢軟,納谷不香,舌淡黯黯紅、苔薄白,脈細。久病脾胃虛弱,乃以異功散加山楂、訶子,五劑善后。年后隨訪患者癥狀未復發。
按語:具悉患者病史,結合中醫舌脈象等,認為其肝失疏泄,氣機塞滯,久病入絡,瘀結于腸,則瘀血與邪毒膠結難解,損傷結腸肌膜,形成潰瘍而不愈。故治法應用理氣活血、化瘀消滯、蕩滌膠濁之邪為主,結合患者舌黯紅、少白黃苔,脈弦細,脈滑數,辨病為瘕泄病,辨證為氣滯血瘀證,腸道氣滯,濕熱內伏,緊扣濕熱伏邪深伏腸絡之病機,運用膈下逐瘀湯加減。方中香附、烏藥、枳殼疏肝行氣導滯,當歸、川芎、紅花、玄胡活血祛瘀,尤其五靈脂腥味入絡,化瘀血,祛膠濁;合用之使腸道蘊結日久之瘀滯消除,使潰瘍能祛瘀生新以愈。全方疏肝理氣消瘀,促使邪氣外出。二診,考慮患者腹痛減輕,脅脹滿已除,故于去枳殼、紅花、玄胡,加蒲黃、白及、薏苡仁以滋止血健脾滲濕之功。三診,腹痛已消失,大便日一二次,軟而成形,無黏液膿血便,肢軟,納谷不香,考慮患者病程較長,久病入絡,瘀阻絡傷,故以異功散加山楂、訶子,益氣健脾,行氣化滯,補而不滯。本案臨證巧妙運用“濕熱伏邪”理論。對于濕熱伏邪潛藏日久致氣滯血瘀從而導致的慢性反復發作的潰瘍性結腸炎,辯證選方,加減化裁,補行并施,以防病情進一步發展損傷陰陽氣血,體現中醫治未病的觀念。
4 期待與展望
上述對于潰瘍性結腸炎中醫辨證分型標準缺乏統一性,相關研究文獻之間缺乏借鑒性;近年來,中醫藥在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方面雖取得很大進展,但在實驗研究方面仍有欠缺,主要表現在不同證型對藥物的選擇、藥物劑量以及治療療程等方面較為模糊,使得中醫藥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缺乏規范與嚴謹。因此,今后研究應完善統一潰瘍性結腸炎中醫辨證分型標準,建立符合中醫藥特點的評價模型及更加科學的藥效評價標準將成為此病的研究目標,為中醫藥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提供更好的研究平臺,深入探討中醫藥針對不同證型的具體治療作用機制及靶點。另外,對于潰瘍性結腸炎的臨床治療遠期療效的追蹤較少,考慮到這是一種反復發作的疾病,應加大對其遠期療效的隨訪力度,結合臨床探索總結適合潰瘍性結腸炎的規范化中醫外治診療方案,以更好地防治潰瘍性結腸炎,為臨床上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提供明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