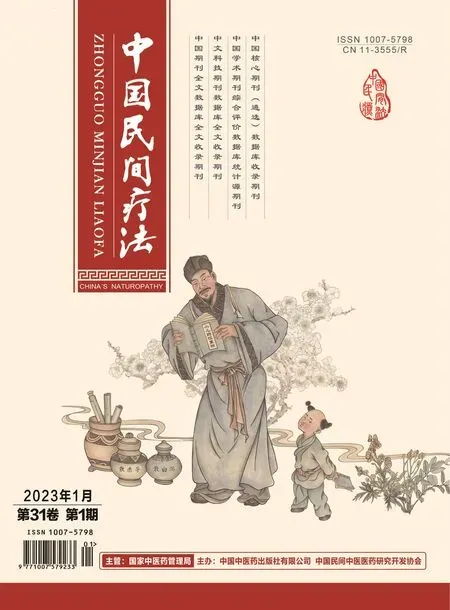基于心神理論認識心律失常的中醫藥治療※
李 旭,程 剛,李國臣,鄭金紅
(1.湖北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湖北 荊州 434020;2.湖北省十堰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湖北 十堰 442011)
心律失常是臨床常見病證,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心源性心律失常,多由心血管器質性病變引起;另一類為非心源性心律失常,由心臟之外的其他全身性疾病引起。心律失常可歸于中醫“心悸”范疇,但各有其特點。中醫認為,一部分的心悸與精神心理因素有關,并非實質意義上的心律失常,即僅有心慌、乏力癥狀,而無心電圖異常表現。心律失常除了心悸,甚至怔忡外,還有不寐、眩暈、喘促、汗出等不適,或以之為首發癥狀,或以之為伴隨癥狀出現。近年來,中醫對心律失常的認識有一定進展,治療優勢突出,今基于心神理論重新梳理與簡述心律失常的中醫藥治療方法,希望對臨床有所幫助。
1 病因病機
中醫所謂的“神”,包括先天之神(元神藏于腦神)和后天之神(識神藏于五臟)。“心神”為后天之識神,藏于心,為五臟神之一,且占據主導地位,又可分為生理之神和心理之神兩大類[1]。心律失常相當于中醫“心悸”“眩暈”“不寐”等病證,病位在心,包括神志之心與血脈之心,與腦腑及肝、脾、肺、腎相關。心主血脈、主神志,各種邪氣導致血脈不通,或心血不足導致心神失養,均可出現心悸、怔忡,嚴重者出現汗出、喘脫等危象。中醫認為,心悸病因病機大致為外感六淫、內生五邪及七情內傷導致的心脈失通(不通)和心神失養(不榮)[2]。心(血)脈不暢多因實邪,即與外邪、血瘀、氣滯、痰濕、火熱有關[3];心神失養多責之于虛,無外乎氣血陰陽之不足,尤以陰血虛損為主。此外,陽(氣)虛導致的實邪(氣虛邪戀、氣虛氣滯、氣虛血瘀[4]、陽虛水泛),即虛中夾實、虛實并存,也為常見病機。
2 基本證型
從陰陽屬性和八綱辨證角度看,心悸涵蓋以下8個獨立類型,即邪毒犯心[5]、水氣凌心、瘀阻心脈、痰火擾心、心虛膽怯、心血不足、陰虛火旺、心陽不振。在這8個證型中,有表證(邪毒犯心)、里證,寒證(水氣凌心、心陽不振)、熱證(痰火擾心、邪毒犯心),虛證、實證,燥證、濕證。從燥濕層面上講,陰虛火旺、痰火擾心偏于燥,水氣凌心、心陽不振偏于濕[6]。此8個證型中涵蓋表里、寒熱、虛實和燥濕之八綱屬性,而臨證大多兼證常見,純粹的單一證型少見。
3 脈象評述
心律失常的脈象多見于二十八脈中的結脈、代脈、促脈、澀脈和散脈。遲而不齊為結脈,數而不齊為促脈,規律停頓為代脈,脈流不暢為澀脈(澀脈可見脈律不齊,有人認為澀脈類似于緩慢型房顫脈[7]),雜亂無章為散脈(危重陽脫時可見)。從脈之胃、根、神角度講,上述5種脈象可稱為失神或無神之脈,即脈象一往一來失去常態,或有來無往,或有往無來,乃元神(氣)虧虛所致。從更大視野范圍看,上述5種脈象僅指脈律異常,而遲脈、數脈所代表之脈率異常,也應涵蓋在脈失神的范疇之內[8]。因此,中醫認識心律失常的落腳點仍在于治神,涵蓋調心神與養心神兩個方面。
4 方藥縱橫
關于治療心悸所涉及的方劑,既可選用炙甘草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苓桂術甘湯、甘麥大棗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經方[9],也可選擇歸脾湯、柏子養心丸、天王補心丹、安神定志丸、黃連溫膽湯等名方。這里重點介紹一下《傷寒論》的炙甘草湯。《傷寒論》言:“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炙甘草湯組成:“甘草四兩(炙),生姜三兩(切),人參二兩,生地黃一斤,桂枝三兩(去皮),阿膠二兩,麥門冬半升(去心),麻仁半升,大棗三十枚(擘)。”用法:“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本方具有滋陰養血、益氣溫陽、復脈定驚之功。方中炙甘草、大棗、生地黃共為君藥,具有益氣助陽、滋補陰血、陰陽并補之功。阿膠、麥冬、麻子仁滋心陰、養心血,人參補心氣,上述藥物共為臣藥。桂枝、生姜、清酒為佐使藥,溫通復脈。目前可以效仿天王補心丹、柏子養心丸之意,用太子參、芍藥、酸棗仁、柏子仁、山茱萸、五味子等藥替代阿膠。本方含有桂枝甘草湯之意,同時甘草本身也有溫陽之功[10]。本方與歸脾湯相比較,滋陰養血之功突出,后者益氣安神之力更佳。炙甘草湯治療心悸側重于心神失養,即不榮層面,臨床若有郁滯、痰濕、血瘀、火熱所致心脈不通之時,可配伍行氣、祛濕、活血、清心等相應藥物。陰虛明顯者,或伴隨不寐者,可參照不寐論治,如用黃連阿膠湯以安神定驚;氣虛伴汗出者,予以甘麥大棗湯;緩慢型心律失常者,可配伍桂枝甘草湯或麻黃附子細辛湯治療。《傷寒論》言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柴胡四兩,龍骨、黃芩、生姜、鉛丹、人參、桂枝、茯苓各一兩半,半夏二合半,大黃二兩,牡蠣一兩半,大棗六枚。”本方功效主要為和解少陽,通暢三焦,鎮靜安神,通腑降濁。與炙甘草湯比較,本方偏于重鎮瀉實以治標,后者養血以治本。
5 治療拓展
依據炙甘草湯治療心悸的脈絡,結合大多數醫家的臨床經驗,研究發現其中有一定規律,今將用于治療心悸的中藥大致分為“參”“草”“棗”“子”“仁”五大類,此歸類不僅涵蓋全面而且便于記憶。其中,“參”有丹參、人參、黨參、太子參和苦參之屬;“草”為甘草,證屬熱者生用、虛者炙用;“棗”為大棗;“子”有五味子、山茱萸、枸杞子、蓮子和桑椹等;“仁”有柏子仁、酸棗仁、益智仁、苦杏仁和桃仁之屬。氣虛者可選用人參、黨參、太子參及蓮子、甘草、大棗等益氣補虛,陰虛者用麥冬、五味子、枸杞子與桑椹、酸棗仁、柏子仁滋補津血,血瘀者可選用牡丹皮、丹參、桃仁、當歸、延胡索和赤芍等活血,痰濕者用絞股藍、甘松、山楂和郁金之屬健脾化濕。心率偏快者(多氣陰雙虛)選用蓮子心、五味子、黃連及苦參、麥冬、玉竹之屬益氣養陰,心動過緩者(多陽氣不足)選用附子、麻黃、桂枝、甘草、細辛和益智之類溫陽散寒。陳子茵等[11]挖掘國醫大師治療心悸經驗發現,丹參、黃芪、炙甘草、麥冬等中藥應用頻次最高,主要以益氣通陽、養陰補血、化痰祛瘀為組方規律,標本并治。顧平等[12]分析文獻發現,治療心悸的方劑中出現頻次較高的中藥主要為炙甘草、桂枝、丹參、麥冬、黃芪、茯苓、黨參等,治療原則以益氣養血為主,輔以寧心安神、清熱解毒、活血化瘀。以上研究所歸納的藥物與上述筆者總結的5類中藥基本一致,治療上也以益氣活血通其脈(實則不通)、滋陰補血養其神(虛則不榮)為主。相關研究表明,上述所提及的中藥如人參、丹參、苦參、酸棗仁、甘草、五味子和大棗等在不同層面、不同環節上發揮著不同程度的抗心律失常作用[13-14]。
6 神病說略
中醫認為,疾病從輕重程度、新病久病、急癥緩癥、單一復合等角度可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從生命無形的部分(精神、信息層次)開始出問題,即神病;第2階段,到氣的部分,能量格局和運行規律發生紊亂,即氣病;第3階段到有形的疾病層面,即精(形)病。也就是說,一個人得了很重的病,絕不是由某一單一因素引起的,還有時間的積累,沿著精神-能量-形體的次序擴展、固化,最后所有層次都出現問題[15]。關于神病,可歸納為神散到神亂(失常或反常)、神弱(少神)到失神(無神)兩類,神散、神亂偏實,神弱、失神多虛,神散、神弱較輕,神亂、無神較重。至于心悸,屬于神病范疇,可分為單一的神病(較輕、新病、緩癥)和形神并病(偏重、久病、急癥)兩類。實際上,心悸的病機是心神不寧,或血脈不通,或血虛失養;輕者單純心悸,重者形神并病,呈現怔忡、心悸,或在此基礎上合并眩暈、不寐等病證,甚至神亂導致汗出、喘脫,危及生命。杜雪翠等[16]也認為,作為五臟之君,心不單是一個具體的器官,也是一個“形神合一”的系統,心臟諸疾尤其是心悸的發病與形神失常密切相關。李令康[17]研究認為,雙心疾病是人體臟腑氣血功能失常在“心主血脈””和“心藏神”兩個方面的反映,發病過程符合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規律。在治法上,雙心疾病初期應注重調和營衛;發展期注重解郁疏機,固護中焦;深入期一方面注重扶助真陽、交通心腎,另一方面注重扶正祛邪,利水、活血、化痰,以恢復神明之職,通暢經脈。
7 小結
心律失常可歸于“心悸”范疇,病位在心,病因病機不外乎內外之邪,或邪毒、痰火、水飲、血瘀等擾亂心神,或陰陽氣血不足而導致心神失養,心神不寧。早期以血脈不通為主,中后期以虛為主,虛中夾實為常見證型。該病的治療重點在于調心神和養心神。所用方劑不離炙甘草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等經方,以及天王補心丹、柏子養心丸等名方。常用中藥多選“參”“草”“棗”“子”“仁”類,“參”“草”“棗”類藥多選黨參、人參、甘草、大棗等,以加強補氣之功;“子”“仁”類藥多用于滋補津血且為治療的基礎與重心。加減用藥方面,若夾瘀者,加牡丹皮、丹參、桃仁之屬;痰濕明顯者,加郁金、甘松、絞股藍之屬;若心慌伴煩躁、不寐等癥狀者,輔以龍骨、牡蠣鎮靜,黃連、苦參清心。總之,不榮者補之,不通者疏之,以調養元神、識神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