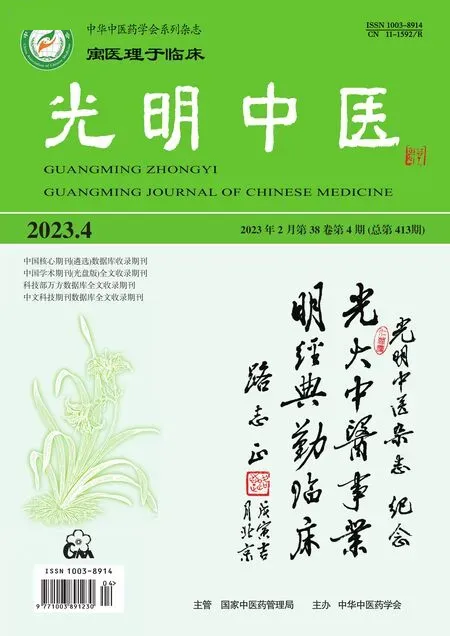中藥外敷法治療橈骨遠端骨折的研究進展*
劉金鵬 周 穎 錢宏岳 俞云飛 吳 毛△
橈骨遠端骨折(DRF)是常見的腕部損傷,約為急診骨折總量的1/6[1]。在全球范圍內,DRF發病率逐年上升,且與人口老齡化呈正相關[2]。低能量損傷導致DRF的老年患者是該病發生的主要人群之一[3]。美國骨科醫師協會等在2021年《橈骨遠端骨折臨床實踐指南更新與臨床意義》中指出,橈骨遠端骨折的老年患者采用非手術療法后的長期結果與手術療法相同[4]。中藥外敷法是治療DRF的常用中醫特色非手術療法之一,具有消除患肢腫脹、促進骨折愈合,較快地恢復患肢腕關節功能的作用[5]。此外,中藥外敷法采用經皮給藥的方式,具有使用快捷簡便、避免首過效應、減少患者用藥次數及維持血藥濃度長期平穩等優勢[6]。中藥外敷法所用的中藥制劑一般由外敷中藥、賦形劑、承載物3部分組成,外敷中藥發揮主要治療作用,賦形劑黏合外敷中藥使成形并影響整體治療作用,承載物承載外敷中藥及賦形劑。中藥外敷法治療DRF療效確切,便捷經濟,發展空間廣闊,創新潛力巨大,值得深入研究與探索。文章綜述了近年來中藥外敷法治療DRF的研究進展,為其進一步創新和臨床應用提供新思路。
1 中藥外敷法治療DRF的歷史探索
中藥外敷法治療DRF可追溯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肘后備急方》:“地黃搗爛熬之,以裹傷處,以竹編夾縛”。現存最早的骨傷科醫著《仙授理傷續斷秘方》中亦明確記載了DRF經整復后使用中藥外敷法治療:“凡傷損重者,大概要拔伸捺正,或取開捺正,然后敷貼、填涂、夾縛”。藺道人所用方劑黑龍散與葛洪所用生地黃等相比豐富了活血類藥物,療效更佳。治療DRF的外敷中藥組方不斷演進,中藥外敷法的賦形劑也在演變。宋金元朝時期開始使用黃米作賦形劑,其目的在于減少不良反應如皮膚過敏、張力性水泡[7]。清朝時期《醫宗金鑒》規范統一了以油或蠟作賦形劑[7]。承載物在更貼合腕關節的基礎上,綜合考量了經濟性、舒適性及透氣性等因素,從帛、麻紙、皮紙、油紙等不斷改良成現代的無菌紗布、薄綿紙等。
2 中藥外敷法的作用機制
中藥外敷法的共性作用機制研究較少,目前認為與藥物透皮吸收、經絡腧穴學說等有關。藥物透皮吸收指藥物透過皮膚表皮及附屬器,進入體循環到達靶點發揮療效,藥物透皮吸收的主要途徑是藥物透過角質層細胞或角質層細胞間隙,而少部分難以跨過角質層屏障的離子型和極性大分子藥物則主要通過皮膚附屬器傳導[8,9]。經絡腧穴學說認為對局部穴位刺激和經絡傳感可調節機體免疫,而中藥外敷法有利于放大相應組織的藥理效應[10]。
近期有學者提出三微調平衡學說[11]:中藥外敷法是對局部微作用、微刺激、微吸收,調節機體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從而發揮療效。微作用指藥物對病灶的直接療效如降低炎癥因子,改善血液流變學指標;微刺激指通過藥物刺激穴位等方式影響神經功能、平衡機體免疫系統,提高抗病能力,同時促進藥物滲透皮膚;微吸收指皮膚角蛋白結合或吸附少量藥物發揮調節微循環、緩解組織粘連等功用。微作用、微刺激、微吸收三者之間相互交叉,協同發揮作用。
3 中藥外敷法對DRF的療效及常用中藥分析
中藥外敷法治療DRF遵循中醫三期辨證分型治療原則,多項研究顯示[12-14],中醫三期辨證分型治療DRF可明顯消除患肢腫脹,促進骨折愈合,提升患者生活質量。目前中藥外敷法對DRF的療效及常用中藥研究多集中在前期消除患肢腫脹與中期促進骨痂生長2方面。
3.1 中醫三期辨證前期消除患肢腫脹DRF中醫三期辨證分型前期多采用涼血消腫、活血化瘀等治法以消除患肢腫脹。段超等[15]使用冷露涼消散(組方:黃芩、黃柏、大黃、梔子、乳香、沒藥、五加皮、澤蘭葉、木瓜、伸筋草、陳皮、川芎、冰片等)對經整復后C3型DRF的患者進行干預,與經整復后使用冷紗布外敷對照,計算治療后第1、4、7、10、13、15天時骨折處腕周徑與健腕周徑的差占據健腕周徑的比率,以此評估患肢腫脹的消退程度,得出在治療第4天后,冷露涼消散組腫脹率明顯低于冷紗布外敷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周琴等[16]對60例DRF患者進行隨機對照研究,對照組采用靜滴七葉皂苷鈉行消腫治療,觀察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外敷治傷三黃酊(組方:黃連、黃柏、大黃、梔子、當歸、川芎、生地黃、赤芍、桃仁、紅花、白術、蒼術、白鮮皮、車前子、白芷等)治療,記錄治療后第1、3、5、7天患者雙側第一至第五掌指關節連線的周徑作腫脹判定依據,比較治療后患側掌指關節周徑與治療前雙側掌指關節周徑差值的比率,得出治傷三黃酊顯著提升消腫速率。劉康等[17]應用消腫止痛膏(組方:乳香、沒藥、梔子、川烏、血竭、紅花、赤芍、兒茶、膽南星、土鱉蟲、地膚子、冰片等)外敷治療53例伸直型DRF患者,依據皮紋表現記錄患者腕部和手背部腫脹消退時間,得出7 d左右腫脹消退,療效顯著。
目前中醫三期辨證分型前期消除DRF患肢腫脹的外敷中藥組方[15-19]多含有黃芩、黃柏、大黃、梔子、乳香、沒藥等具備改善微循環、抗炎等藥理功效的中藥:黃芩中的黃芩素可以明顯抑制炎癥反應,下調血清中白介素-6、腫瘤壞死因子-α含量[20];黃柏含有的生物堿成分可改善多種炎性介質的表達水平,減輕機體炎癥反應[21];大黃的有效成分大黃素具有抑菌、鎮痛、抗炎的功效[22];梔子可參與機體免疫調節,減少炎癥因子產生,改善血管內皮功能紊亂[23];乳香含有β-乳香酸可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環[24];乳香和沒藥的有效成分均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25]。有研究表明,改善骨折處微循環、降低骨折早期機體產生的白介素6、腫瘤壞死因子α等炎癥因子水平,可促進患肢腫脹消退[26]。
3.2 中醫三期辨證中期促進骨痂生長DRF中醫三期辨證分型中期多采用祛瘀生新、接骨續筋等治法以促進骨痂生長。邢明祥[27]在對照組的基礎上運用化瘀接骨散(組方:桃仁、紅花、三七、大黃、當歸、兒茶、白及、自然銅、骨碎補、血竭、全蝎、土鱉蟲、珍珠末等)外敷治療DRF,比較2組治療后第5周X線片骨痂生長狀況,得出中藥外敷組總有效率優于對照組,化瘀接骨散有效促進了DRF的骨痂生長。張勇等[28]經隨機對照研究發現接骨續筋膏(組方:乳香、沒藥、大黃、天南星、杜仲、續斷、自然銅、當歸、冰片等)外敷6周,可明顯提升血清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胰島素樣生長因子、骨形態發生蛋白2等含量,從而促進骨痂生長,縮短骨折愈合時間。
目前中醫三期辨證分型中期促進DRF骨痂生長的外敷中藥組方[27-29]不僅多含有改善微循環、抗炎等藥理功效的中藥,還多含有具備提高機體骨形態發生蛋白2、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等骨生長因子水平的藥理功效的中藥:杜仲促進骨髓間充質干細胞的分化和骨痂毛細血管再生,增進骨痂生成[30];自然銅的主要物質二硫化亞鐵進入機體后產生的硫化氫參與內質網應激,從而促進成骨分化[31];骨碎補的黃酮類成分促進成骨細胞的分化與增殖加速骨痂形成[32]。
4 中藥外敷法賦形劑對療效的影響
中藥外敷法的賦形劑一般具有性質穩定,對人體無害,與外敷中藥無配伍禁忌的特點。中藥外敷法治療DRF的常用賦形劑有凡士林、蓖麻油、甘油、飴糖、野菊花汁、蜂蜜等。
4.1 賦形劑的特殊作用賦形劑有提升外敷整體療效、提高外敷安全性、增強外敷黏附性等特殊作用。華志佳等[33]運用吊傷膏外敷治療DRF,以飴糖作賦形劑黏合諸藥,加強吊傷膏對DRF的止痛療效。酒濤等[34]使用野菊花煎汁與蜂蜜以10∶1配比作賦形劑調和四黃散,從而提升四黃散外敷治療DRF的消腫作用。此外,蜂蜜作賦形劑具備抑菌抗炎的作用,同時可降低外敷中藥對皮膚的刺激,提高了中藥外敷法的安全性,麻油作賦形劑可增強外敷中藥與皮膚的黏附性[35]。
4.2 賦形劑增強中藥外敷法療效的研究探索目前主要從2個方面對賦形劑增強中藥外敷法的療效進行研究探索。①探索對病證的更優賦形劑。秦鳳華等[36]經隨機對照研究對比中藥外敷時分別使用醋、蜂蜜、凡士林作賦形劑對濕熱瀉大鼠的療效,發現使用醋作賦形劑療效最優,分泌性免疫球A在大鼠腸道黏膜及白介素-10在大鼠血清中的表達最高,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得出相比蜂蜜、凡士林,醋作賦形劑更能較快修復濕熱瀉大鼠的腸道炎癥,且隨時間推移對大鼠的免疫影響遞增。②探索發揮或保留外敷中藥療效的更優賦形劑。姜維等[37]檢測姜黃素經不同賦形劑治療慢性應激模型大鼠的咬肌組織中的白介素-6、白介素-1β、腫瘤壞死因子-α等水平,發現可可脂比花生油作賦形劑更促進姜黃素藥學作用的發揮。蔡良等[38]考慮安全性、經濟性等使用姜汁、凡士林、二氧化硅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對四黃散賦形,通過對比賦形后中藥有效成分含量、人體感官評價等得出四黃散與賦形劑的最佳配比為3∶2,三種賦形劑姜汁、凡士林、二氧化硅的最佳配比為5∶2∶1,此時有效成分保留最多,賦形性、皮膚追隨性與剝離性佳。
5 展望
DRF發病率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逐年提升,老年DRF患者采用非手術療法的長期結果與手術療法相同。中藥外敷法是中醫特色非手術療法,具有“簡、便、廉”的特點,安全性高,在臨床治療DRF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尤其有效補充了急診DRF初期處理的消腫止痛治療方法。中藥外敷法的作用機制目前研究較少,多為理論到理論的論證探討,于微觀層面的探索尚待進一步發掘。中醫三期辨證分型治療DRF療效確切,中藥外敷法在前期和中期治療DRF的常用中藥的用藥規律亟須進一步研究分析,如在常用單味中藥或常用藥對配伍等方面探析成方規律,以期取得突破性進展。賦形劑影響中藥外敷法對DRF的整體治療效果,但目前在精準適用病證及中藥組方的賦形劑的研究較為稀少,尚需進一步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