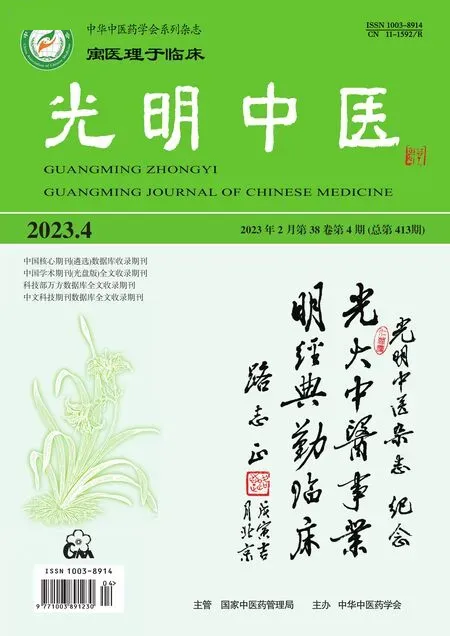基于治中焦如衡理論談泄瀉治療
田曉鵬 陳珍珍 趙 丹 劉竺華
泄瀉是指以排便次數增多, 糞質溏薄或完谷不化, 甚至瀉出如水樣為主癥的病證[1],相當于現代醫學中急性腸炎、炎癥性腸病、腸易激綜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等以泄瀉為主癥的疾病,均可按泄瀉進行辨證論治。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飲食結構和生活環境發生改變,該病患者人數逐年增加。其臨床癥狀復雜多變,或可伴有精神癥狀,遷延反復,給患者身心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本文基于“治中焦如衡”理論探討泄瀉的治療,旨在為臨床中診療泄瀉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1 病名
泄瀉最初多以泄或瀉代稱,且以糞質的性狀或泄瀉緩急而與其他詞匯并稱。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太陰之復,濕變乃舉……甚則入腎,竅瀉無度”,《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濕勝則濡瀉”,《素問·生氣通天論》謂:“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等。《傷寒雜病論》將瀉下的癥狀稱為“利”“下利”或“下痢”。隋唐時期,“泄瀉”與“痢疾”以“痢”統稱之;“泄”與“瀉”合用首見于《太平圣惠方·卷第二十六·治脾勞諸方》:“治脾勞,胃氣不和,時有洩瀉(“洩”作“泄”)”。后陳言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下設以“泄瀉”為名的《泄瀉敘論》進行論述,“泄瀉”之名正式確立。將大便溏薄而勢緩者稱為泄,大便清稀如水而勢急者稱為瀉。
2 病因病機
《素問·脈要精微論》曰: “胃脈實則脹,虛則泄”。《素問·宣明五氣》曰:“大腸小腸為泄”,指出泄瀉病位在脾胃、大小腸,與肝腎相關。《素問·氣交變大論》中有“騖溏”“飧港”“注下”等病名,指出風、寒、濕、熱皆可致瀉,如《素問·舉痛論》曰:“寒氣客于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認為外感寒濕暑熱之傷及脾胃,使脾胃升降失司,脾不升清;或直接損傷脾胃,導致脾失健運,水濕不化,引起泄瀉。因濕邪易困脾土,以濕邪最為多見,故有 “無濕不成瀉”之說。《素問·太陰陽明論》:“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月真滿閉塞,下為飧泄”。 認為飲食不潔,使脾胃受傷,或飲食不節,暴飲暴食或態食生冷辛辣肥甘,使脾失健運,脾不升清,小腸清濁不分,大腸傳導失司,發生泄瀉。《素問·舉痛論》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明代張介賓《景岳全書·泄瀉》[2]曰:“凡遇怒氣便作泄瀉者必先以怒時夾食,致傷脾胃”。長期憂思傷脾,脾失健運,清陽不升,水谷不化,或情志不暢導致中焦氣機逆亂,均可引起泄瀉。《景岳全書·泄瀉》曰:“泄瀉之本,無不由于脾胃”。指出年老體弱,臟腑虛弱,脾腎虧虛;或大病久病之后,脾胃受損,腎氣虧虛;或先天稟賦不足,脾胃虛弱,腎陽不足,均可導致脾胃虛弱或命門火衰。脾胃虛弱,不能腐熟水谷,運化水濕,積谷為滯,濕滯內生,清濁不分,混雜而下,遂成泄瀉。
泄瀉常由感受外邪,飲食不節,情志失調,脾胃虛弱等導致脾失健運,水濕不化,腸道清濁不分,傳化失司而成。泄瀉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2017)》[1]將泄瀉分為寒濕困脾證、腸道濕熱證、食滯胃腸證、腎陽虧虛證、脾氣虧虛證、肝氣乘脾證等。而在臨床上病證復雜,單一證型者少見,多兩證或多證兼夾出現。其中脾虛濕熱及肝郁在發病中占主導地位,《黃帝內經》云:“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土,其病從長夏始也,長夏亦屬土,濕熱為主,脾為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且疾病后期,脾虛甚,喜燥惡濕,濕邪滯留,最易熱化。此外機體并非處于絕對的平衡狀態,而是動態自我調節,此消彼長。素體脾虛,肝氣相對旺盛,則肝氣趁機乘脾,人體處于相對平衡。正如《醫方考》云:“瀉責之脾,痛責之肝,肝責之實,脾責之虛,脾虛肝實,故令痛瀉”。
隨著生活水平提高, 人們嗜食肥甘厚膩之品,極易生濕生熱,脾喜燥惡濕,水濕內停,脾失健運,脾虛無力運化水液則濕盛,二者相互影響,發為泄瀉,加之現在人們生活工作壓力大,情志不暢,肝失疏泄,橫克脾胃,脾氣不升,則胃氣不降,中焦氣機失衡,升降失宜,故脾虛濕熱肝郁證常多見,三者常相兼為病。臨床多表現為泄瀉腹痛、瀉下急迫、糞色黃褐臭穢、身倦乏力、食少納呆、胸脅脹滿、焦慮抑郁、煩躁等。
3 理論認識
“治中焦如衡”理論出自《溫病條辨》,是由清代吳鞠通汲取葉天士大量治療理論經驗,參考《黃帝內經》編著而成。《黃帝內經》有云:“陽道實, 陰道虛”[3], 其中“陽”指陽明胃腑, 六腑以通為順, 胃主降濁, 病則腑氣不通, 濁氣不降, 糟粕不行, 易從燥化、熱化, 易與邪結而見痞滿燥實等陽明腑實證;“陰”指太陰脾臟, 五臟以升為順, 脾主升清, 病則清陽不升, 精微不化, 脾虛則濕盛, 濕盛則傷陽, 故脾病多虛。而在《臨證指南醫案》中,葉天士也對脾胃兩個臟腑的虛實、寒熱、升降、潤燥等生理異同特點做了概述:“蓋胃屬戊土, 脾屬己土;戊陽己陰, 陰陽之性有別也。臟宜藏, 腑宜通, 臟腑之體用各殊也……觀其立論, 云納食主胃, 運化主脾;脾宜升則健, 胃宜降則和。太陰濕土, 得陽始運, 陽明陽土, 得陰始安。以脾喜剛燥, 胃喜柔潤也”。吳鞠通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總結概括,提出了“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理論,“中焦”者,《溫病條辨》[4]中論述十分明確:“上焦病不治, 則傳中焦,胃與脾也”。其“衡”者,平也,意為平衡。他認為“補中焦以脾胃之體用, 各適其性, 使陰陽兩不相害為要”。后世醫家通過不斷發展,將其推廣至內傷脾胃病的治療,成為治療脾胃病的總則,意指在治療脾胃病時應全面考慮其體用屬性不同, 做到用藥兼顧:虛實兼顧、寒溫得宜、升降并調,從而恢復脾胃臟腑。筆者認為中焦乃氣機升降之樞紐,脾升胃降,平衡的脾胃功能狀態共同完成水谷消化吸收,“平”不是簡單地補虛瀉實、溫寒清熱等,而是要使脾胃的功能恢復平和,和其陰陽,暢其氣機,從而達到良好的療效。泄瀉一病,病情復雜,其病機多見虛實夾雜,氣機失調,寒熱錯雜等,治療無論何種治法,最終都達到中焦脾胃“平”“衡”的狀態。
4 臨床辨證用藥經驗
在對脾虛濕熱及肝郁型泄瀉的治療上,筆者臨證依據“治中焦如衡”之經典理論,自擬復衡止瀉湯,組方源《自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之四君子湯與《增補內經拾遺方論》之柴平湯加減而成。組方為黨參9 g,茯苓9 g,白術9 g,防風6 g,姜半夏9 g,厚樸9 g,陳皮9 g,炒蒼術30 g,柴胡9 g,白芍9 g,紫蘇梗10 g,甘草6 g。整方益氣健脾,祛濕清熱,疏肝理氣,做到了虛實兼顧、寒溫得宜、升降并調。首先,筆者認為脾虛和濕盛是本病的2個主要方面,虛實夾雜者多見,《景岳全書》中也提到:“泄瀉之本, 無不由于脾胃”。故在治療時首先要做到虛實兼顧,強調脾胃為后天之本,以健脾為本,常選四君子湯加減,此方中人參、白術、甘草都是補藥,有益氣健脾之功,茯苓有利水滲濕、健脾和胃的功效,在健脾的基礎上佐以淡滲下行的藥物,虛實兼顧,共奏健脾祛濕之功。方子雖小,但溫而不燥。有研究表明,四君子湯可從保護胃腸黏膜、調節消化系統的信號通路和維護胃腸道微生態等多方面對脾氣虛證進行改善治療[5]。此外,筆者認為“補氣防壅”,故在四君子湯基礎上加入紫蘇梗,既可和胃止痛,又可理氣寬中,引藥入脾經。
針對濕熱致病纏綿,復雜多變的特性,需辨別是濕重于熱,還是熱重于濕,濕為陰邪,屬寒,耗傷陽氣,熱為陽邪,耗傷陰液[6]。故當濕重于熱時,癥見瀉而不爽,黏膩,伴周身困重, 頭重頭痛, 胸脘痞悶, 納呆,嘔吐,苔膩不黃,脈濡緩不數,治療以苦溫燥濕、健脾運氣為主,用陳皮、蒼術、厚樸、姜半夏等。熱重于濕時,癥見瀉下急迫糞色黃褐臭穢,伴口干,口臭,肛門灼熱,小便溲赤,苔黃膩,脈洪大或滑數等,治療以清熱為主,辨證加減葛根、黃芩、黃連等藥,葛根善從里以達于表,從下以騰于上,正如《本草新編》云:“葛根輕清,少用則遂其性而上行”,故可通過升發清陽,鼓舞脾胃清陽之氣上行而奏止瀉之功。黃連能清熱堅腸,李時珍稱“黃連治目及痢為要藥”,并舉例曰:“古方治痢:香連丸,用黃連、木香;姜連散,用干姜、黃連;治肝火,用黃連、吳茱萸……治下血,用黃連、大蒜”。黃芩降火清金,黃芩、黃連配伍,堅毛竅而止汗,堅腸胃以止瀉。佐以苦溫藥如木香、蒼術等,木香辛苦溫,能溫中行氣止痛,與黃連相伍,寒溫協調,黃連得木香寒而不滯,木香得黃連溫而不燥;伴有反酸、燒心者,加海螵蛸、白芷、煅瓦楞子等。筆者認為疾病發展,濕熱兩邪交爭,熱由濕邪所蘊, 濕去則熱清, 用苦溫燥濕法, 不可太過溫熱, 太過則助熱, 適得其反, 所以在用藥上時時掌握“中焦如衡”之原則要根據邪氣之偏性,辨證下藥,從而使脾胃安和協調。
針對肝郁導致的情緒緊張、抑郁伴胸脅脘腹脹滿等癥狀,筆者認為木之所以克土,并不是木太過,而是脾土太虛,故治療多在健脾的基礎上佐以疏肝的藥物,如柴胡等,對于腹痛較明顯, 肝郁較重者常配伍白芍、柴胡性辛散,疏泄肝氣;白芍性酸柔,濡養肝血,柴胡得白芍之柔,不至疏散太過,白芍得柴胡之散,不至阻滯氣機。其次泄瀉應注重風藥的使用,正如《醫宗必讀·泄瀉》提到治泄九法之升提法即用“升麻、柴胡、防風、葛根”之類風藥以鼓舞清氣上升,則泄瀉自止[7]。即取風藥輕揚升散,同氣相召,脾氣上升,運化乃健,泄瀉則止;其次脾氣上升,陽氣得升,濁陰自降,達到了祛濕的效果;再者肝為風木之臟,性宣發沖和,風藥屬木,善條達木氣,入厥陰肝經而助疏泄,暢達肝氣乃順其性[8]。如此,風藥可達到健脾祛濕疏肝的功效。最后脾虛所致的泄瀉患者,運化水谷能力下降,可有食滯腸胃之兼癥,故疾病恢復期可用炒雞內金,取其消食導滯及收澀之功。
5 醫案舉隅
靳某,男,37歲。2021年11月3日初診。患者反復腹瀉腹痛1年余,日行2~3次,昨日與人發生爭吵后腹瀉腹痛加重,日行6次。患者自訴大便時溏時瀉,稍進食油膩食物則大便溏稀,次數增加,有排不凈感,黏膩,周身困重,胸脘痞悶,納差眠可,苔膩不黃,脈濡緩不數,喜甜食,腸鏡示:結直腸黏膜無明顯異常。既往史:既往體健。舌脈:舌淡,苔白膩;脈弦細。中醫診斷:泄瀉。證型:脾虛肝郁,濕重于熱。治法:疏肝健脾,燥濕止瀉。處方:黨參9 g,茯苓9 g,白術9 g,防風6 g,姜半夏9 g,厚樸9,陳皮9 g,炒蒼術30 g,柴胡9 g,白芍9 g,紫蘇梗10 g,甘草6 g。7劑,水煎至400 ml,日2次,早晚分服。
2021年11月13日二診:大便日2次,成形,粘馬桶,腹部不適基本消失,晨起口干,無惡心,偶有心煩,舌紅,苔淡黃,脈滑。處方:黨參9 g,茯苓9 g,白術9 g,防風 6 g,厚樸9 g,陳皮9 g,炒蒼術30 g,白芍9 g,黃連2 g,竹茹15 g,葛根10 g,甘草6 g。7劑,水煎至400 ml,日2次,早晚分服。
11月29日三診:大便日1次,成形,偶爾粘馬桶,晨起口干,惡心,自覺腹脹,舌紅苔淡白,脈滑。處方:黨參9 g,茯苓9 g,白術9 g,防風6 g,厚樸9 g,陳皮 9 g,炒蒼術30 g,白芍9 g,黃連3 g,竹茹15 g,葛根 10 g,甘草6 g,炒雞內金15 g。7劑,水煎至400 ml,日2次,早晚分服。
隨訪:上方加減治療2個月, 患者腹瀉腹痛癥狀顯著緩解, 囑其注意合理飲食, 調暢情志,防止復發。
按語:泄瀉一癥,與體質、飲食、情志密切相關。該患者素體脾虛,脾失健運,無力運化水液生濕,喜食甜食,又易生濕生熱,加重脾虛,二者互為因果,故患者反復腹瀉;與人爭吵后,肝失疏泄,橫克脾胃,加重脾虛,且中焦氣機失衡,升降失宜,泄瀉加重,氣機失常,不通則痛,故見腹痛;脾虛無力運化水液生濕,故見周身困重,胸脘痞悶,納差。用四君子湯合柴平湯加減,以健脾益氣、化濕清熱,加白芍以緩急止痛、疏肝理氣,配伍防風,取其輕揚升散,同氣相召以及促進肝之陽氣升發的作用,既可助脾氣上升,運化乃健,同時疏散肝氣,可達到調暢肝脾,恢復中焦之氣機,從而止瀉。二診患者腹瀉癥狀緩解,腹部不適基本消失,大便粘馬桶,晨起口干,無惡心,舌紅,苔淡黃,考慮化熱,前方去柴胡加黃連清熱堅腸止瀉,竹茹清熱除煩,葛根生津止渴以緩口干。三診患者諸癥狀皆有緩解,考慮患者脾虛日久,食滯腸胃,故加炒雞內金以消食及收澀止瀉。
6 結語
綜上,基于“治中焦如衡”理論治療泄瀉,做到用藥兼顧:虛實兼顧、寒溫得宜、升降并調,衡法貫穿始終,效益非常。筆者認為不僅是泄瀉,在脾胃病乃至整個中醫疾病的治療當中,“治中焦如衡”理論所體現的“衡法”思想都可以應用,正所謂“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只有從整體觀出發,進行辨證論治,審證求因,靈活施治,隨癥加減,通過藥物以及飲食與精神方面的調攝使機體達到一個安和協調的狀態,才能邪去病除,身體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