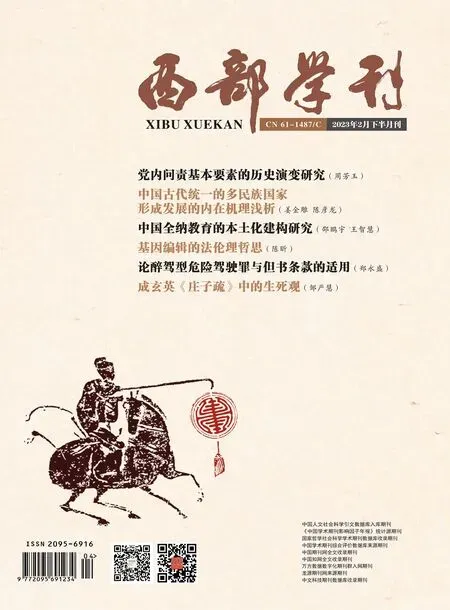新時代青年工人身份研究
——對熱詞“打工人”的分析
王鵬烽
一、“打工人”的提出
“打工人”一詞的流行,始于2020年10月,《青年文摘》將“打工人”列為“2020十大網絡熱詞”。“‘打工人’從字面可以拆解為‘打工’和‘工人’,這是兩個在中國社會發展和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十分重要的概念”[1]。“打工”一詞最初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人員流動、農民工群體形成有關;“工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下,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后同資產階級相對立的階級群體,即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再從當代中國國情出發理解“打工人”:憲法明確規定,“我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正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主體,中國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始終發展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接受無產階級政黨先進理論的指導。新時代青年正是社會主義中國工人群體的新血液,他們在信息時代、大數據資源條件下,有新的生產生活形式。
綜上所述,對“打工人”一詞產生的理解需要從兩條邏輯出發。從內容形式來看,“打工人”是在互聯網空間聯系高度發達條件下,生長于信息時代的青年在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基礎上,結合他們對改革開放以來工人群體生產生活的綜合認識,以輕松的網絡流行語的形式創造出來的;從形成過程來看,“打工人”是新時代青年基于對改革開放以來工人生產生活變化的不斷認知,在自我勞動過程與身份確認過程中創造出來的。
二、新時代青年的工人身份
20世紀80、90年代,在城鄉戶籍二元制條件下,迎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農村外來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形成“農民工”群體,“打工妹”“打工仔”等詞語便開始流行。這些觀念深刻反映了當代中國工人群體的生產生活狀況及其變化,是中國不同年代對工人身份的不同認知。“打工人”便是新時代青年于自身生產生活體驗過程中產生的對工人身份的相應認知。
(一)改革開放以來對工人群體認知的問題
工人階級與無產階級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下是等同概念,工人階級之所以被能稱為無產階級,關鍵在于工人階級是生產資料與之相分離又必須參與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組織的生產而能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出賣勞動力換取維持其生活最低層次的生活資料的階級。工人生產的超過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也被資本家所占有,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工人階級最終一無所有,是無產者。
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下,對工人群體的認知處于不斷構建的狀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受大量西方思潮涌入的沖擊,對工人群體一開始難以形成較為正確的、科學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90年代的工人群體主要包含著大量“生產性勞動者”——產業工人,即一般從事無需經過一定復雜的科學文化教育及技能培訓就能進行的簡單勞動的產業工人。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界定,產業工人主要是指在工廠、礦山和工地等場所從事生產、制造、建筑等的勞動者,特別是指工業生產過程中的制造業工人,產業工人即“藍領”。“從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初期,機器制造業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先后開始了向大規模經營的過渡,從而出現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2],“他們在110年中使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50倍。”[2]可見,產業工人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1978年至2012年,中國的產業工人由占就業人數的17.3%上升到30.3%”[3],因此在改革開放開始后,產業工人成為中國現代化生產的強有力支柱。
產業工人是典型的“體力勞動者”,與“知識型勞動者”相對應。知識型勞動者顧名思義就是既掌握一定科技、專業知識,又能實地動手操作的勞動者,成為知識型勞動者需要經過一定復雜的科學文化教育及技能培訓,所以“非生產性勞動者”,即知識型勞動者,與產業工人在改革開放30年中產生了明顯區分,如此便造成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對工人群體的不正確、不科學的理解。
即使是低級的知識型勞動者,也要受過高中、中專、中技、大專或同等教育,不掌握一門或幾門專業知識,就不可能適應現代社會現代科技發展的需要。知識型勞動者就是所謂的“白領”,而“中產階層主要指從事白領職業、受過良好教育、生活比較優越的人群。”[4]客觀上越高級的知識型勞動者越接近中產階層,在產業工人就業人數中占比逐漸下降之前,“白領”與“藍領”,即“知識型勞動者”與“產業工人”有著明顯社會地位的區分,這種區分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西方思潮的影響。義務教育的普及給予了來自于農村、落后地區或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與富裕家庭的子女同等通過智力和勤奮獲得地位提升的機會,但“西方意識形態長期滲透,煽動階層焦慮,擾亂群眾思想”[5]。在西方國家設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語境下,這種機會被視作來源于資本家的施舍,資本主義社會對此種“施舍”的認知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其階級統治所營造的觀念上層建筑,將中產階層當作資本營造的享樂主義、機會主義的代表,產業工人在面臨他們想象中的“中產階層”時,因為文化、品位、消費等方面的差異,產生了羞恥和不自信的心理以及“社會的不公平感和相對剝奪感”[5]。所以,在改革開放30多年內,中國社會還未完全將產業工人歸入中產階層的范圍。
這種對知識型勞動者、整個工人群體不正確的認知,客觀上造成了工人群體內部的分裂,不利于中國工人、人民群眾內部的團結,“打工妹”“打工仔”等詞也并不能概括整個中國工人群體,而“打工人”這一熱詞的出現反映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條件下,中國社會對中國工人群體的正確認知與工人群體意識的科學構建。
(二)“打工人”:新時代青年對工人群體的科學概括
2012年后,中國產業工人占就業人數的比率逐漸降低,“到2017年,中國產業工人占就業人數的比率為28.11%”[3],“2015年白領占城鎮人口的66%”[4],產業工人的數量相對下降,而知識型勞動者數量相對大幅度上升。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便是機器大工業的繼續高速發展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數據時代導致的資本技術構成提高,進而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使產業工人相對剩余,加上新時代青年擁有了能通過教育和技能培訓追求良好生活品質的更多的機會,更容易從事復雜勞動,也就是更容易地成為了白領。總的來說,新時代,產業工人比例下降,被“排擠”出的人員進入銷售、教師、會計等崗位,大多數受過學校教育的青年工人社會地位得到了“提升”,這是工人群體內部結構的挪移。知識型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導作用日益顯露。
白領群體內部分化較為明顯,一部分白領雖然職業地位較高,但是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無法躋身中產階層。“2015年符合中產階層標準的白領僅占54%”[4],哪怕是這些符合中產階層標準的白領,獲取生活資料的勞動也不是輕松的,包括產業工人、知識型勞動者,所謂的中產階層、中低階層在內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均未達到相對高水平,“至步入新時代后的2015年,中產階層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為44155元,中位數(位居第50%分位的家庭人均收入)為30000元,中低階層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只有17292元,中位數僅為12800元”[4],這并不能支撐中國家庭實現非常優渥的生活。科技升級下的工人地位并未實現質變性的提升,勞動者為了達到更好的生活品質,仍需付出一定努力,促使新時代的中國社會對工人群體的認知逐漸廣義化、科學化。
新時代青年作為勞動者的新生力軍,他們是在有一定標準與條件的、普及化的科學文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被教導要用奮斗去追求美好生活,并被賦予了這樣的機會,也印證了新時代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轉變。正是由于我國當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關頭,新時代青年正是需要用奮斗去追求美好生活,主要矛盾也體現在衍生出的次要矛盾上,城市“白領”、大學畢業不久進入工作崗位的年輕人等青年勞動者原本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工作地位上的主動性,但在工作后卻遭遇某種貶低,“搬磚”①“寫字樓民工”②等自嘲就是他們面對這種貶低時的典型反應。即使是接近于中產階層,甚至是已經躋身中產階層的城市“白領”,也無法通過“躺平”③或輕松的工作方式來獲取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享受中產階層所代表的較高品質的生活,當代青年產業工人更是如此。因此,新時代中國社會對工人群體的科學認識宏觀化、科學化了,不論是作為產業工人的青年,還是作為“白領”的青年,都逐漸統一認識到中產階層并不是資本營造的享樂主義、機會主義的代表,即使是躋身中產階層的“白領”,也要經過大量的努力與不懈的奮斗才能追求高品質的生活,而不是一開始就坐擁高品質的生活,認識到在生產力未高度發達條件下,不論是何種形式的勞動者,都要通過勞動創造價值,來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所以工人群體勞動、奮斗的形象,就覆蓋到了中國社會的全體勞動者。
20世紀80、90年代流行的“打工仔”“打工妹”這樣的流行語,主要是形容進行生產性勞動的體力勞動者,特別是形容來自于異鄉外來人員的產業工人,帶著貶低的態度,是對中國社會工人群體的狹義認知。而新時代青年作為新時代工人群體的主要成分,在信息時代、大數據條件下,更能客觀地體驗到、了解到包括自身在內的中國社會全體工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新媒體條件下,為了凝聚人民大眾的關注,詼諧有趣的流行語文化便盛行了起來,這種可以直接表述但又具備趣味性的對應事物的表達形式,將網絡語言的全民性展現了出來。“打工人”正是一個喜歡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吹捧自己是保安、打工人等身份的網名名為“抽象帶籃子”的網絡紅人所提出的。“打工人”一詞一經提出,就流行于新時代青年群體中,它的“全民性”便彰顯了出來。總而言之,“打工人”一詞涵蓋了新時代青年對自己廣義性工人身份的認知,是新時代青年提出的包括產業工人、知識型勞動者、個體勞動者等所有勞動者在內的工人群體的代表詞,是新時代青年在自身生產生活體驗中對新時代中國社會工人群體的科學概括。
三、“打工人”:新時代青年工人自覺的工人群體意識
“打工人”一詞的產生的過程是新時代青年對自身乃至新時代中國社會工人群體的科學認知的過程,本質上是新時代青年自身作為工人,其工人群體意識的自覺生成,為了追求幸福生活和個人發展而不斷發揮自身主體性的過程。
(一)關于盧卡奇工人“自覺的階級意識”的生成
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與市民國家同時存在。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隨著舊的統治階級的滅亡而消失的國家,后者是朝向共產主義階段而逐漸走向消亡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夠發達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私有制,存在包含著“物化”的經濟關系社會,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亦會使工人的意識達到它將成為自覺的程度。當前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列寧“灌輸論”的正確理論,對人民群眾、工人群體進行意識形態灌輸教育,但純粹的灌輸并不意味著無產階級意識的完全覺醒,灌輸的目的不是讓工人將理論直觀記憶下來,而是加快形成其群體意識的自覺。“‘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的結束恰恰意味著,人與人的具體關系,即物化開始把它的力量交還給人。這一過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標,無產階級關于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意識,即它的階級意識的作用也就越重要;階級意識也就必然越強烈地、越直接地決定著它的每一次行動。”[6]盧卡奇④的“自覺的階級意識”的生成中,“自覺”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將視角轉向中國新時代青年工人群體,他們經受過系統的無產階級理論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被“灌輸”的基礎,就更易于擁有工人群體意識的自覺。“無產階級意識的具備必須樹立無產階級立場,即意識到自己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主體—客體的同一,意識到自己肩上負有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以及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歷史地位。”[7]只有這樣的自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產階級才能肩負起發展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繼續消滅剝削與壓迫的重任,這正是無產階級通過歷史的中介作用,將階級意識與社會總體統一為“自身”的“自覺”的表現。新時代青年在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下,在信息時代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體會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追求美好生活而進行勞動奮斗的需要,而“打工人”的出現正是新時代青年代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工人群體總體的科學認知,網絡紅人“抽象帶藍子”所喊出的“打工都是人上人”也正是其對工人身份的積極認同,因此“打工人”一詞的出現是新時代工人群體意識自覺生成過程的重要確證。
(二)關于薩特“存在先于本質”
薩特⑤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存在先于本質”為基本命題,他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指出,“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現出來——然后才給自己下定義。”[8]3“人就是人,這不僅僅是說他是自己認為的那樣。而且也是他愿意成為的那樣。人除了自己認為的那樣以外,什么都不是。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則。”[8]3這就是薩特給“存在先于本質”做出的解釋,包含兩個方面:人的實際存在先于人的本質;人賦予了事物的本質。這兩個方面便是“存在先于本質”的合理性與參考性所在,依據薩特的觀點可得出:人先是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然后通過自己的自由選擇活動創造自己的本質。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的類本質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9],此種活動便是自由自覺的實踐(勞動),人之所以能同動物從根本上區別開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擁有與動物相區別的這一人的類本質,而人的存在和獲得本質的能力是同時產生的,人一開始就存在“非理性因素”,可以通過非理性的實踐獲得“理性因素”,然后再實現“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結合的再次實踐,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人的本質。“存在先于本質”的這一具體過程所具有的合理性不在于命題本身,在于薩特這一命題對人“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的主體性的強調,這種對個人存在主體性的重視是馬克思較為宏觀的語境中較為缺少的。薩特先是單純從個人的活動與選擇中去思考人的本質,再去看待“歷史中的他人”,看到了歷史條件下的個人,它對新時代中國的啟示在于,歷史條件下的個人到了像新時代中國這樣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需要在發展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繼續同剝削和壓迫作斗爭、為實現全人類解放的過程中,探索如何更好地減少自身的、個人的苦難,如何更好地實現個人的主體性價值,更好地增加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面臨新形勢下,為了中國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人的類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人自由自覺的勞動是為了自身全面的發展。新時代中國工人為了自身更加幸福的生活會不斷發揮自身的主體性,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只有在發揮主體性后能夠滿足自身主體性需求、獲得幸福感和獲得感,新時代中國工人才會更加努力發揮主體性,這是一個需要繼續不斷發展的良性循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所說“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10],人自由自覺地實踐、勞動正是為了幸福。“打工人”一詞的出現正是新時代青年對自身工人身份,對自身個體的主體性的肯定,是自身工人自覺意識覺醒的一部分。在義務教育的培養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確引導下,新時代青年敢于同“996”⑥等不法用工作斗爭,懂得為了自己的需求和美好生活而努力奮斗、努力“打工”,這本身是因為“打工”是有回報的,這也正是新時代青年愿意做“打工人”的原因。促進“打工”與回報的良性循環,有利于社會財富更加良好地被分配,有利于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三)新時代青年工人奮斗的主體性與個人幸福
在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條件下,在自己工人身份的生產生活體驗過程中,仍可能會產生“憑借自身努力奮斗獲得幸福,激勵自己奮進”以及“從事勞累、低收入的工作,從而抱怨與不滿”兩種感情。新時代青年對自身“打工人”身份的認同正是來源于自己奮斗得到的回報與幸福能夠勝過奮斗過程中的辛勞,所以我們在強調科學的奮斗精神的同時,必須注重勞動價值創造力的可持續性發展,即讓奮斗的工人能夠有回報,能夠滿足自己的主體性需要,能夠獲得幸福,這樣才能讓工人實現社會主義的再生產。
每一個工人作為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個人,在實現共產主義之前,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個人價值的實現與社會價值的實現還會存在矛盾,這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正是通過歷史中介的作用,將工人群體意識與社會總體統一為自身,即將個人的發展、工人群體的發展、社會的發展歷史地統一了起來。新時代青年創造的“打工人”一詞,將中國社會整個工人群體囊括了起來,“打工人”配合工人意識形態的教育,是工人群體意識的自覺生成。新時代中國,以新時代青年為主體的工人群體,在自覺的工人群體意識生成的基礎上,不斷為了幸福生活而奮斗,于是,工人發揮自身身份的主體性與工人個人幸福的實現之間客觀形成了矛盾,這是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衍生矛盾,這對矛盾關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主義建設,宏觀來說,關乎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要實現這對矛盾和諧地良性發展,就得解決這一矛盾,讓工人充分發揮奮斗主體性的作用,在此過程中擁有更多的幸福與獲得感,包括提高工人素質、維護工人權益、提高工人社會地位等各個方面,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解決這一矛盾與整個國家的經濟計劃與其他上層建筑領域的相應設計有關,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探討的重大課題。
結語
工人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體,要從廣義上去理解和重視,并予以充分的尊重。新時代青年結合改革開放以來工人的生產生活實踐,在自身的生產生活實踐過程中,超越了狹義的階層區分、分工區分,用“打工人”一詞科學概括了中國社會整個工人群體,這也意味著新時代中國工人群體意識的覺醒,表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工人為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與追求而發揮的主體性奮斗。因此,只有處理好新時代工人群體、新時代青年奮斗與幸福實現的矛盾,才能更好地發揮工人的作用,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
注 釋:
①“搬磚”:近年網絡用語,原指搬運磚塊,在網絡中,該詞引申為工作辛苦、重復機械、賺錢不多的工作。
②“寫字樓民工”:中產階層、白領進行自嘲的網絡用語,當代民工被狹義地定義為農民工、外來募工人員(外來工)、外地人,在城市中帶有很大的貶義,是城市被雇傭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體代表,于是中產階層、白領用該詞自嘲自身工作辛苦、回報低。
③“躺平”:近年網絡用語,指主體無論周遭環境怎樣變化,內心都毫無波瀾,對此不會有任何反應或者反抗,表示順從心理,以此為生活理念的群體即“躺平族”,面對各種壓力選擇“一躺了之”。
④盧卡奇:盧卡奇·格奧爾格,匈牙利著名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當代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和哲學家之一。
⑤薩特:讓-保羅·薩特,法國著名哲學家、文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會主義最積極的倡導者之一。
⑥“996”:指996工作制,具體是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時(或不到),總計工作10小時以上,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這一制度,反映了中國互聯網企業盛行的加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