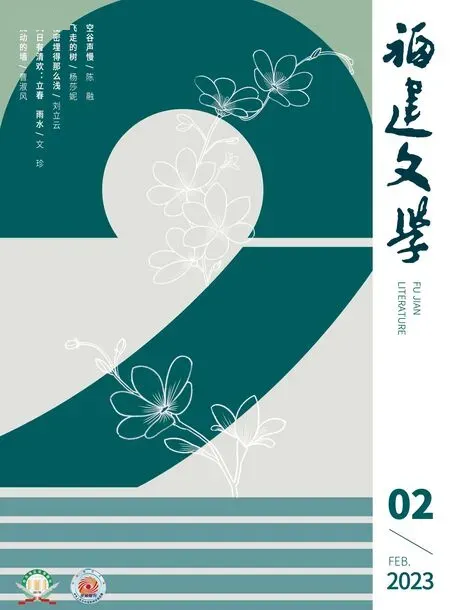山河與故人
——讀施曉宇歷史文化散文
龍 潛
1
施曉宇出版了《洞開心門》《都市鴿哨》《思索的蘆葦》《直立的行走》《大美不言壽山石》《閩江,母親的河》《秋水文章不染塵》《走陜北》等歷史文化和地域文化散文集。特別是散文集《施曉宇說史——一個人的另一面》《文人文話》和近年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解放軍文藝》《北京文學》《散文選刊》等刊出的作品,更是顯示了施曉宇對歷史文化的深刻洞察。
施曉宇用他的散文,講敘在社會現實的高歌猛進中,不應忘卻的歷史和傳統文化。他的散文無論是地域范疇、內容題材還是作家個人的文學觀念、審美理想和精神訴求,都在當下中國散文中表現出別樣的表述形態與價值系統。
施曉宇的散文在文學追求上是古典主義的。寧靜肅穆的古典主義文學是人類黑暗中溫暖的光亮。充滿悲憫情懷的作家所關注的是受苦受難的人們,他們在善與惡之間,在正義與非正義之間,表現出良知、見識、勇氣和高尚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崇高人格。他們對惡的詛咒,對一切被憐憫的人的深切同情,覆蓋和引導了人們心底潛在的美好渴望。
施曉宇的散文以非虛構方式,用從容的語言和客觀的理性態度,力圖再現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在這樣的敘述中,他的書寫穿梭于歷史和現實之間,始終站在客觀的立場去還原歷史,挖掘歷史背后的現實社會意義,遇見人被社會賦予的一切。在時光中,在中國社會的進步中,施曉宇相信歷史永恒。
現代化背景下,我們沒有靠近真正的現代,我們卻又似乎忘記了歷史,我們成為一種處于歷史與現代夾縫中的被異化的“過渡性”的人,對于現代的核心要義知之甚少。施曉宇的散文通過歷史文化和人物的書寫,讓歷史記憶和現實同時呈現,形成連接,創造了一個個具有張力的鏡像。他的散文串聯起大量的人和事,構建起別具一格的文本結構,用敘事來表達歷史中的各方姿態,從歷史的角度探求現代社會問題的根源。
施曉宇的散文將福建獨特的人文歷史納入自己的文學書寫之中。在現代性語境中,地域文化逐漸邊緣化和陷落。而對于施曉宇來說,福建不僅是地理空間、物理空間,還是心靈空間,他從中獲得了精神的引領。他的散文書寫,喚起人們對地域文化的關注,喚起人們思考這片土地與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喚起人們思考融合與沖突、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激進在發展與進步中的化解之道。
施曉宇的散文于敘述中始終有一種自我審視,這使得他的散文節奏舒緩,有著淡淡的憂傷。沈從文曾提到自我審視,大致說過這樣的話:離開自己生活來檢視自己生活,活人中很少那么做,因為這么做不是一個哲人便是一個傻子。施曉宇的散文是歷史的“個人經驗”的復活,具有沈從文說的“生活”之上“生命”的意義。如果說關于歷史的書寫是在溫習過去,那么施曉宇的散文已展現了強大的還原能力。他的書寫又不止于歷史,他念茲在茲的是文學在廣闊的時代中保存歷史的痕跡。
2
歷史是故事的發生地,它以自身的古老性和包容性鬼魅般吸引寫作者。施曉宇的《秋水文章不染塵》《走陜北》這兩部散文集,為我們展開了地域歷史的想象與建構。在民族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地理空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人們開始尋求地域文化認同與自身歸宿。其實,中國大地上的每一地域都承擔著這一重要的使命。一個地域的興衰命運反襯出百年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歷史趨勢,也折射出歷史與文化對于中華民族發展進程的價值。如同巴赫金所說的“道路”時空體,他說:“社會性隔閡在這里得到了克服。這里是事件起始之點和事件結束之處。”
施曉宇的散文中還展示了底層民眾的群像。這些文字向我們展現了生氣勃勃的人文風貌,是作者對故鄉和朋友的回望。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人們白日短行,施曉宇的散文對那些人的親切描寫,不僅表現出對小人物高尚精神的贊揚,還是自我的一種精神返鄉,即在生活中生活著。或許他們是平凡的人,但他們生活的困境其實是中國之困境,對他們生活迷惘的記敘其實是對中國的展望。
施曉宇是一個十分注重敘事技巧的作家,他的散文運用互文性結構,通過不同文本之間的聯系相互映襯、互為補充,增強了作品的層次感。這種橘瓣式結構,從多個視角對敘事空間展開觀察與敘述,打破了線性敘事的時間,使多個空間并置,從而在空間與場景的不斷變換中推進敘事進程。他散文中的“互文性”即讀者在閱讀完一個文本后,可以在其他文本中找到這一文本的補充或延續,使不同人物有自己開口說話的可能,自身形象與特點也因此更加飽滿。
時間是籠罩在空間緯度之上的一種強大的力量。歷史中那些往事和人物作為一種文學文本的表達,在被闡釋的同時也被想象。在當下與過去、保守與激進、傳統與現代的比較中,歷史的時間體驗得到強化。巴赫金在談到歌德作品中的時間問題時,認為歌德能在物體身上看到不同時間的存在及其背后所蘊藉的思想內涵。某種程度上,歷史的遺跡體現為時間的痕跡。歷史輝煌的過去以及因地理、政治等原因而逐漸衰落的現狀,提供給施曉宇的更像是一種時間性的遠距離想象,而非一種敘述元素那么簡單。《龍陽之癖》《謁司馬遷墓》《辜鴻銘祖地回望》等篇章證明了這一點。這些遺跡為時間所滲透,其意義超越了事物本身,在時間的流年中,展示了時間的綿延性。
時間是一種較為抽象的存在,而空間是一種較為具體的存在。從外在藝術結構形態來說,《訪蒲城三陵》《朱仙鎮里謁岳飛》《一代宗師宋慈》這些篇章大都以“地點·人物”的方式進行命名。按照陳平原的觀點,不同空間場景的并置、對比、組合,可以使文本獲得另外一種較為特殊的美感效果。這樣的布局其實隱藏著施曉宇對散文的整體構思以及對歷史的理解和想象。約瑟夫·弗蘭克指出普魯斯特、喬伊斯、艾略特的作品是用“同在性”取代了“順序性”,因而是“空間的”。顯然他所指的空間是抽象化的、符號化的空間,也即是文本的空間形式和空間結構。在施曉宇的散文中,其主要體現為時間的淡化和時間的凝固,從而賦予時間以精神內涵、文化內涵甚至是生命內涵。從施曉宇選取的意象看,不管是《屹立的馬尾》還是《杜陵四蘇》這類作品,其本身就體現出時間的空間化特征;書中的場景的描繪,即弗蘭克所謂的空間描寫,就像電影里面的定格畫面一樣,時間在這里被凝固、被定格、被停止,使事件表現為一種空間形態,這跟圖像敘事有了共通性。
施曉宇對歷史文化的寫作并不是烏托邦式的理想構建,而是試圖通過不同時空的拼接和并置,把歷史真實地展示出來。而這種異時性并置的書寫方式,有效地突出了知覺上的同時性。《秋風秋雨感業寺》《馬嵬坡與楊玉環》《他鄉遇故知》等作品因此成為充滿立體感的空間圖景。歷史的異質性、非理性、邊緣性和陌生感更多來自作家自身的體認。所謂歷史想象,離不開歷史的文學性感知、體驗和表達。古人就常常在想象中構建“天下”的概念。
施曉宇散文中的時間敘事是尋找歷史意義和文化內涵的重要手段,他善于用時間的穿越去強調一種歷史的時間體驗。歷史時間在施曉宇散文中并不只是作為背景而存在,也作為一種行文邏輯或者寫作策略。其中,時間的空間化以及多重空間的并置是施曉宇散文呈現空間形式的最主要手段,前者使時間被淡化,空間由此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意義;后者使其散文能夠容納更多的共識性場景,由此展露出對空間化效果的追求。
3
在中國散文發展歷程中,“真實”作為傳統散文的基石一直被不斷強調。然而,眾多散文作家嘗試在散文中加入想象的成分并因此獲得了成功,如余秋雨《道士塔》就將許多虛構的場景和情節引入文中,余光中《年輪》就在寫實與想象之間來回穿梭。施曉宇的《空海:中國取經》《屹立的馬尾》《杜陵四蘇》等作品,同樣也是由于涉及大量的想象成分才顯得豐滿。虛實結合一直是中國藝術的特點之一,文學藝術要求從虛與實的結合和統一中尋找藝術的美。很大程度上,文學對歷史的想象是對歷史空間的一種重塑,不僅能夠反映作家的情感與態度,也影響讀者對歷史的解讀。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想象”是文學的核心詞。近幾十年文學想象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種是從心理學角度來考察文學的想象問題,很大程度上將文學想象與形象思維等同起來,如金開誠的《文藝心理學論稿》和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第二種是從語言藝術的角度考察文學的想象,認為文學語言能夠實現“想象力的振奮”,倡導從文學話語中尋找文學的“表現鏈”,如童慶炳的《文學審美特征論》和楊守森的《藝術想象論》。
施曉宇散文的想象,本質上是自由性、超越性和創造性三者的統一。其自由性表現為施曉宇筆下的想象具有既包含某種在場的東西,又包含某種不在場的東西,是用有限的在場來表示無限的不在場;其超越性表現在施曉宇對于表象的想象既能夠突破自身,又能夠突破客觀現實以及時空限制,這是情感體驗和價值判斷的升華;其創造性表現為施曉宇散文既能創造出新的文學形象,又能把新形象綜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對歷史想象所具有的表現性、象征性和創造性的綜合呈現。特別要指出的是,雖然施曉宇散文對歷史的想象是基于歷史特有的地理空間、歷史變遷和文化形態,但作為一種文學創造活動,這具體又涉及到對歷史的感知、篩選、描述和意義賦予,表達的是對歷史的認識、回憶、期待,因而無法避免作家主觀色彩、審美情感和心靈啟悟的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