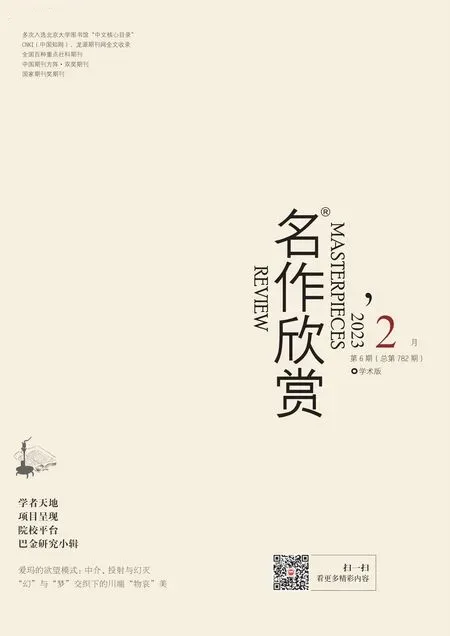對《春江花月夜》結構“斷層”現象的再思考
⊙李品一[吉林師范大學博達學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詩人張若虛的名作,聞一多先生曾對它做過極高的評價,說它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①。但是,這樣一篇杰作,卻被許多人質疑存在嚴重的結構缺陷,認為其“前16句與后20句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斷層’”。詩作的前半部分“借明月高懸之象追問宇宙之永恒,空靈博大”,而后半部分“借明月徘徊之景敘寫人間相思,細膩入微”,詩作前半部分寫宇宙人生的迥遠之思,后半部分寫世俗男女的人間之愛,這無論從情調還是意境上說都很難統一起來。②
筆者認為《春江花月夜》中并不存在明顯的結構“斷層”,人們對《春江花月夜》結構缺陷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闡釋者對詩作中“月下之思”一節的內涵進行了拔高性解讀。本文立足文本本身,以細讀的方式,解讀“月下之思”一節的內涵,理清詩作的意脈,并在此基礎上來論證詩作結構的合理性。
一、“斷層”產生的原因:闡釋者的誤讀
《春江花月夜》本是樂府舊題,是陳后主原創的宮體詩題目,書良辰美景、寫春情艷遇本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像隋煬帝的《春江花月夜兩首》正可作為代表: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漢水逢游女,湘川值二妃。
在《春江花月夜》詩題下表現美景愛情是傳統的寫法,張若虛的詩也依其舊例,他的詩被人們認為不同于古人寫法之處在于,在寫春江美景和游子思婦之情的兩部分內容之間,加入了“月下之思”這一節: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聞一多先生對這一節詩盛贊有加,認為這一節詩中表現了詩人“夐絕的宇宙意識”③,境界高遠,遠非以往的宮體詩所能比擬。李澤厚先生在對“月下之思”的哲學化闡釋方面邁出了更為長足的一步,他說這部分表現的是人少年時面對無窮宇宙,深切感受到的自己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認為這展現了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對人生、宇宙初覺醒的“自我意識”,表現了人對美麗世界、自身存在的珍視和對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無奈與感傷。④聞、李等大家的哲學化闡釋為人們對“月下之思”的理解框定了方向,時至今日,認為“月下之思”部分表現的是詩人對于“人生的哲理與宇宙的奧秘”的探索⑤已然成為一種共識。
筆者認為從詩作意脈的發展來看,“月下之思”部分其實是銜接春江美景與游子思婦之情的過渡性段落,在這一詩節中,詩人為了把自然之景與人間之情銜接起來,有意識地把人的活動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自然——宇宙”環境中來審視,但是詩人在這里要表現的并不是對人與宇宙關系的哲學性思考,而是對人與自然之間神秘情感聯系的復雜體驗。筆者認為忽視“月下之思”在全詩中的過渡作用,對“月下之思”部分進行過分的拔高性哲學解讀,導致文本意脈被人為割裂,是《春江花月夜》中結構“斷層”問題的實質。筆者將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細闡述。
二、對“月下之思”的細讀分析
在詩作中,普遍被人們認為最富哲學意味的是“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兩個問句,許多論者認為這兩句是詩人在發屈原式的“天問”,其性質與“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的疑問相似⑥,是對宇宙生成、人類本源問題的探索⑦,筆者的觀點與此相左,筆者認為這兩句疑問從行文脈絡上看,實乃因景而起,因情而生,詩人借此要表達是一種愉悅而又困惑的情感體驗。聯系上文來看,“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兩問是出現在“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的寫景句之后的,在這兩個寫景的句子中,我們能感受到詩人在面對美景時的心理狀態是很復雜的:有陶醉,江天無塵,脫俗的境界令人心曠神怡;有歡喜,皎月如輪,明亮圓滿令人內心愉悅;有孤獨,孤月高懸,煢煢孑立令人心中凄苦;有迷惑,一輪明月居然能同時喚起人內心兩種對立的情感,讓人捉摸不透。詩人感受到了景物對自己復雜審美體驗的喚起作用,但是,對為何會產生這樣一種情感體驗,詩人又想不清楚,所以“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兩句與其說是詩人在思考明月何時產生,人何時出現的“形而上”問題,還不如說他是在抒發一種感慨:面對著超塵脫俗的月下美景,我不禁思緒萬千,人與明月之間的這種詩意關系會是從何時開始的呢?人對明月的這種復雜體驗又會是怎樣產生的呢?
接下來詩人又寫道:“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目前人們普遍認為這兩句是詩人在用月的永恒來對比人生命的短暫,借此表達一種淡淡的哀愁。人們常常拿出類似的詩句來證明這一觀點,常被人們用來與《春江花月夜》類比的詩句有劉希夷《代悲白頭翁》中的“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以及李白《把酒問月》中的“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等。對此,筆者認為,其實張若虛的詩中所表達的與劉、李等詩人要表達的并非同一內涵,以劉、李詩句來證明張詩,本身就是對張詩內涵的遮蔽。
我們先來對比“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與“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這一組詩句。這些詩句看起來句式的確差不多,但實際二者強調的側重點是不同的,《春江花月夜》強調的是“望相似”,《代悲白頭翁》強調的則是“人不同”,《春江花月夜》說的是人雖然一代一代地在延續,每代的個體不斷在發生變化,但江月看起來只給人一種相似的印象,“江月年年望相似”有的版本也寫作“江月年年只相似”,這種相似的印象是指什么呢?從上文看,應該就是指那種由明月喚起的既讓人覺得圓滿美好又讓人感到孤獨寂寞的復雜體驗;從下文詩作對游子思婦之情的表現看,這種印象則是指那種天下有情人因望月而生的普遍的懷遠之情。而《代悲白頭翁》說的則是雖然季節輪回,年年春季鮮花盛放之景看起來都是相似的,但時光荏苒,每年賞花之人都已不同的現象。也就是說,《代悲白頭翁》想表達的是宇宙自然永恒,青春生命易逝的哲理,而《春江花月夜》要表達的則是個體雖不同,體驗卻相通的生命感慨。
我們再來對比“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與“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這一組。李白在《把酒問月》中寫的這幾句詩與張若虛的詩實在是太像了!他與張若虛一樣不但寫到了人與月的關系,而且也寫了古人今人望月時的共同感受,但是,兩詩似則似矣,詩中表達的情感內涵同樣各不相同: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云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里。
在《把酒問月》中,李白多次拿明月與人進行對比:“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寫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想上青天攬月難以做到,但月卻享有極大的自由,只要它想跟隨人就可以跟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寫與月相比,人的生命是短暫的,而與人相比,月的光輝卻接近于永恒。在這種對比中李白表達了對明月的艷羨之情,也同時表達了對自己人生有限、生命無力的惆悵之情。吳小如先生認為李白的這首詩應當是作于唐玄宗天寶三載(744)⑧,即詩人遭唐玄宗賜金放還的那一年。也就是說,李白是在遭遇了重大人生挫折的語境下,寫下了“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這四句詩,詩人從一個失意者的立場出發,想象古今之人觀看明月時的共同感受,感受中必然會帶有失意者個人的痛苦體驗。對比上文筆者對《春江花月夜》詩句的解讀,我們就會發現李白的詩句雖然在形式上看起來與張詩很像,但實際二者的情感內涵大相徑庭——李白要表達的是在永恒的宇宙面前,對自己的生命因缺少功業支撐而難以獲得不朽價值的感傷,而張若虛想表達的則是對人生代代不同而望月之情人相似現象的驚異。
“月下之思”的最后兩句是“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不知江月待何人”一句的表達讓人覺得不合理性之處在于江月沒有生命,怎么會“待人”?詩人明知江月不能待人,為何還要故作“不知”?其實,我們只要理清詩句之間的關系,詩人這樣寫的意圖并不難索解。“不知江月待何人”是承接上文“江月年年望相似”而來,這里的江月是個思念意象,它雖然不能“待人”,但與望月懷遠的“待人”情境有關,它是眾人普遍的思念之情的喚起者,也是人間普遍存在的等待之苦的見證者,江月總是會引起人的綿長的思念之情,月下總是會有數不盡的離別與等待的故事。經過這種邏輯還原之后,我們就會發現,其實,“不知江月待何人”一句要表達的是“我不知道在這一輪江月的見證下,人間正上演著多少關于等待的故事”。接下來詩人以“但見長江送流水”來結束本節,這里的“長江”是一個意象,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大江大河常作為永恒的時間、綿長的情感、無盡的生命之流的隱喻來使用,而“流水”在這里則是“長江”意象的派生物,表現的是“長江”的“流逝”的狀態。詩人用“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來給“月下之思”作結,表達含蓄,含義豐富:它讓人想到在時間的長河中,在那些我們并不確知的地方總是會有人在苦苦地等待團聚;它讓人想到在近乎永恒的時間長河中,人的思念之情也如江水般無窮無盡;它讓人想到人的光陰年華的流散消逝,人如流水般后浪推前浪代代更迭……那不盡的長江水,把人類族群的生命之流和情感之流融到了一起,使之都獲得了永恒的意味。
三、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春江花月夜》的“月下之思”部分與其說是在對人月關系進行玄遠的哲學思考,不如說是在以月為媒來表現詩人復雜的情感體驗。詩人通過“月下之思”對春江之景和游子思婦之情兩部分進行了過渡性銜接,實現了全詩意脈的貫通。
至于“月下之思”這段寫情的文字為什么容易被人們誤讀,易被當作哲理性語段來看待,筆者認為除了權威解讀的誤導外,詩作本身也確實存在著容易引人誤讀的因素,這就是這段文字表現了哲理詩中常見的二元對立的哲學范疇——異與同,變與恒,只不過詩人在處理這些對立的哲學范疇時采用的方法與哲理詩不同。比較一下下面這兩種表達——“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與“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代代皆不同”,會感覺到前者情趣重,后者理趣濃,這兩個句子在表達上差不多,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區別呢?我想這應該與前者表現的是對立范疇的和諧統一關系,而后者表現的是對立范疇的沖突對抗關系有關——和諧產生詩情,對立催生理趣,這兩種句子在表達上不易分辨,故而容易被誤讀。
①③聞一多:《聞一多全集3》,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版,第300頁,第299頁。
② 張蓮芳:《〈春江花月夜〉詩意“斷層”解讀》,《貴州文史叢刊》2006年第2期。
④ 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頁。
⑤ 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頁。
⑥ 張慶福:《唐詩美學探索》,華文出版社2000 年版,第68 頁。
⑦ 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北京大學中文系語文教育研究所:《語文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頁。
⑧ 吳小如:《說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