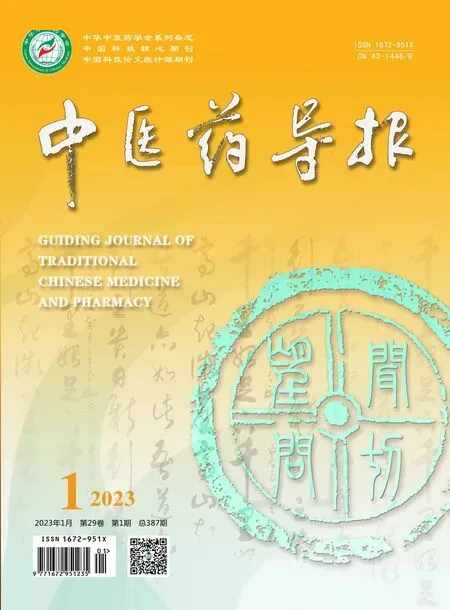王暴魁基于“陰火”理論辨治糖尿病腎臟病經驗*
孫超凡,王暴魁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北京 100078)
糖尿病腎臟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糖尿病最常見的慢性微血管并發癥之一,以腎小球基底膜增厚,系膜區細胞外基質沉積,腎小球硬化,伴或不伴腎小管-間質纖維化為病理特點[1]。其發病率逐年升高,目前已成為慢性腎臟病中進展至終末期腎衰竭的主要原因,臨床上主要表現為蛋白尿及漸進性腎功能損害等。糖尿病腎臟病在中醫古籍中并無明確記載,歷代醫家多根據臨床表現將其歸屬于“消渴”“水腫”“尿濁”等范疇[2]。中醫學認為,DKD病位在腎,由消渴病發展而來,臨床上多見火熱之證。故在病機認識上,“火邪”已得到多數醫家的普遍認可[3-5]。然火邪有實火、虛火之別,陽火、陰火之分,臨床中多數醫家往往忽略這一區別,偏向性認為DKD乃“實火”“陽火”所致,在治療中常應用大量清熱瀉火之品傷及脾胃、損耗正氣,反不利于疾病的治療和預后。“陰火”理論作為闡釋病機、診治疾病、遣方用藥的一種理論依據,在內科學中得到了廣泛應用。陰火的本質是在脾胃氣虛的基礎上繼發的虛火[6],以氣火不利、升降失調為要。從DKD與陰火的基本病機來看,兩者在發病基礎及起病特點等方面密切相關。
王暴魁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腎病科學術帶頭人,師從國醫大師張琪教授,繼承并發展張琪論治DKD的診治經驗,臨床經驗豐富,論治獨到。王暴魁教授認為陰火是導致DKD發生發展的基本要素,且貫穿疾病始終。早期陰火內生、耗氣傷陰,故見神疲乏力、氣短懶言、口干咽燥之癥;中期陰火鴟張,下擾腎絡,絡虛不固,故見蛋白尿等虛損之象;晚期陰火熏灼,痰瘀互結,致腎絡癥瘕而生,故見腎臟纖維化等病理改變。治療上多采用補脾益腎、調氣散火之法,寒溫并用以升陽散火,活血和血以消積伏瘀。筆者師從王暴魁教授,長期伺診左右,現將其論治DKD的經驗整理和總結如下,以饗同道。
1 陰火理論探析
1.1 陰火的基本特點“陰火”理論乃金元時期著名醫家李東垣所創,其在《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中曰:“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于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可見,陰火的發病基礎在于脾胃虧虛所致,由此衍生出心火、相火及氣機失調之火等,雖其部位不同、性質各異,然化源則一,統屬于“陰火”的范疇[7]。在致病特點上,陰火兼具“火熱”之性,在導致機體氣陰兩虛的基礎上,還可灼津為痰、煉血成瘀,造成痰瘀等病理產物蓄積,變證叢生。
1.2 陰火與陽火之分 火邪有陽火、陰火之別[8]。陽火是由六淫之邪、飲食積滯、火運太過等外在因素侵犯人體所引起火熱偏亢的一類病證,在治療上常采用清熱瀉火之法。陰火成因于七情內傷、勞倦過度等內在因素,是在脾胃虧虛、元氣虛衰等基礎上而繼發的虛火,法當補脾益氣、升陽散火。從陰陽辨證來看,陽火發于陽、現于陽,為陽中之陽;陰火源于脾胃虧虛所致故“發于陰”,兼具上沖之勢而“現于陽”,為陰中之陽;從表里辨證來看,陽火由外感而發,屬表;而陰火為內傷所致,屬里;從虛實而言,陽火常見煩躁譫妄、口渴汗出、小便赤澀、大便干結、苔黃脈數等一派實熱之象,當屬實證;而陰火則成因于脾胃虧虛,其本則虛。氣血乏源、五臟失養,則見心火、相火等,故陰火為本虛標實證。
2 陰火與DKD發病的聯系
王暴魁教授認為氣虛與虛火為陰火的基本要素。兩者不僅在病因病機及臨床表現等方面與DKD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亦是構成DKD炎癥反應的基礎。
2.1 氣虛為本 從病因病機來看,本病由消渴病發展而來,先天稟賦不足、后天飲食失養等均可傷及脾腎,致脾腎俱虛[9]。腎、脾乃先后天之本,生理上相互滋生,病理上相互影響。脾失健運致精血乏源、形體失養,故見神疲乏力、氣短懶言之癥;脾虛及腎,致腎氣虧虛、精關不固,故見蛋白尿等虛損之象。消渴病久,脾腎氣虛、氣化失司,水濕泛溢故見水腫等。如《圣濟總錄·消渴門》所言:“消渴病久,腎氣受傷,腎主水,腎氣虛衰,氣化失常,開闔不利,能為水腫。”此外,脾腎氣虛亦是陰火內生的基礎。脾失升清,致水谷精微等下流腎間,腎中相火被擾,離位上乘可生“陰火”[10]。DKD多見于中老年人,年老陰氣自半,腎中精氣匱乏,加之脾胃氣虛,難以下充,致腎中精氣更虧。腎為水火之宅,元氣與相火寄居于此。“火與元氣不兩立”,元氣虧虛致腎中相火妄動,發為陰火。《格致余論·相火論》言:“相火易起……臟腑功能失調,氣血津液枯竭,諸恙叢生,寧日無望矣,故曰元氣之賊”。
氣虛與DKD免疫炎癥微環境紊亂的發生密切相關[11]。研究[12-13]表明,DKD是一種慢性低度炎癥反應,具有低水平、持續性及非特異性等特點,表現為MCP-1、TNF-α、TGF-β、IL-1等炎癥因子水平升高且持續時間較長,與機體免疫系統[14-15]、線粒體能量代謝[16]、腸道菌群[17]、自噬[18]等密切相關。在體內高糖高脂等環境作用下,免疫功能下降、線粒體代謝紊亂、腸道菌群失衡、自噬過程減慢等都可被視為“氣虛”的表現。“脾者,主為衛”,衛氣依賴于脾氣的健運及充養得以發揮衛外御邪之功,與機體的免疫功能相似[19],因此免疫功能的下降多歸結于脾虛不充所致[20];氣作為機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與線粒體參與能量代謝、氧化還原等作用相似。因此,線粒體功能障礙亦可視為“氣虛”的具體體現[21];而腸道菌群分解代謝食物的過程與“脾主運化”功能相似,故腸道菌群紊亂與氣虛密切相關[22];此外,自噬是細胞通過溶酶體途徑降解受損或衰老蛋白質及細胞器,實現細胞更新的過程。在一定條件下,氣虛亦可致自噬過程減慢從而影響機體內的代謝[23]。
2.2 虛火為標 陰火內涵豐富、形式眾多,涉及心火、肝腎相火、郁火及氣機失調之火等,均與DKD密切相關。脾胃氣虛、生化乏源,陰血難以滋養心腎,君相火旺而內蘊成火;脾胃氣虛、升降失常,陽氣不得宣發,郁而化火;“火與元氣不兩立”,脾胃氣虛、元氣衰憊致壯火獨盛。從臨床表現來看,DKD患者雖呈現一派熱象,然多伴有氣短乏力、口干咽燥等氣陰兩虛之癥,其性為虛。王暴魁教授認為,從虛火而論,心其華在面、開竅于舌;DKD患者見心悸自汗、面色發紅、舌尖紅、脈細數等癥狀,與心火密切相關;肝腎位居下焦,精血同源、藏瀉互用,故機體見蛋白尿等虛損之象乃腎中相火妄動、精關被擾所致。此外本病多見頭暈耳鳴、面色蒼白等腎性高血壓、腎性貧血之癥,亦乃相火煎灼陰精,致精血虧虛難以上榮、清竅失養所致;陰火滯于中焦,致氣機升降失常,清濁相干、濁毒內蘊等,造成后期患者出現惡心嘔吐、皮膚瘙癢、尿少尿閉等癥狀。從臨床指標來看,DKD患者雖有炎癥因子水平升高,然具有慢性及低度等特點,且機體并未表現出明顯的紅腫熱痛,亦為虛火所致;從病理特征來看,腎小球血管擴張、血流量大、流速增快等病變不僅使腎小球內呈現“高血壓、高濾過、高灌注”等狀態,亦可造成腎血管內皮損傷,出現腎小球硬化、系膜細胞增生等“絡虛瘀損”的病理變化,亦乃虛火留于腎絡而成。
3 基于陰火理論辨析糖尿病腎臟病
3.1 寒溫并用,升陽散火 針對氣虛為本、虛火為標的基本病機,王暴魁教授在治療中多升陽健脾以治其本、甘寒瀉火以治其標,法尊東垣,常應用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加減治療。“惟當以辛甘溫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出自于《脾胃論》,該方由柴胡、黃芪、羌活、升麻、人參、黃芩、黃連、石膏等藥物組成[24]。其中黃芪、人參甘溫以補中益氣治其本;“惟瀉陰中之火,味薄風藥,升發以伸陽氣,則陰氣不病,陽氣生矣”,應用柴胡、羌活、升麻諸風藥升陽散火以升發氣機、恢復脾胃氣機升降之樞;此外,亦要注意燥熱為標的特性,佐以黃芩、黃連、石膏等甘寒瀉火除其標,防止辛溫太過而耗傷其陰。《脾胃論》載:“當先于陰分補其陽氣升騰,行其陽竅而走空竅,次加寒水之藥降其陰火,黃柏、黃連之類是也”。全方以陰火彌散為立義,一在病機基礎上,始終以補脾胃之氣為根本。腎中元氣不充,當以胃氣滋之而發揮固攝精微之功。二在病因病勢上,陰火彌散,當以甘寒瀉之。腎中相火旺盛,當用甘寒瀉火以截其灼津損絡之勢。三在氣機升降上,元氣不升而相火獨旺,當以升華脾陽而復其氣機。全方體現了甘溫補中、甘寒瀉火、升陽散火等論治陰火的思想。
3.2 活血和血,善用風藥 瘀血為糖尿病腎臟病后期進展至終末期腎衰竭的主要因素。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云:“初為氣結在經,久則血傷入絡”。糖尿病腎臟病發病日久,陰火灼津為痰、煉血成瘀,痰瘀膠著互結于腎絡,致腎絡癥瘕而生,造成病情加重。故在強調恢復氣機升降、散泄陰火的基礎上,王暴魁教授亦多重視瘀血為患,采用益氣活血、養陰活血、涼血活血等治法,隨證加減。其在臨床中善用桃仁、紅花、丹參等藥,既可活血和血以潤燥,又助輕清升散之品疏散陰火,即所謂“若陰中火旺,升騰于天,致六陽反不衰而上亢者,先去五臟之血絡,引而下行”。對于瘀血較重者,其應用水蛭、地龍、土鱉蟲等蟲類藥以增破血逐瘀、通達經絡之力,正如吳鞠通言“以食血之蟲,飛者走絡中氣分,走者走絡中血分,可謂無微不入,無堅不破”。此外,在注重瘀血為患的同時,其亦常應用穿山龍、青風藤、雞血藤等藤類風藥。此類藥物辛涼走竄,一方面可除腎中諸邪,具搜剔通絡之功;另一方面其性為涼,可泄越陰火,防火邪與他邪相煽。同時,藥理研究亦證實此類藥物具有抗炎、免疫調節、免疫抑制等作用[25-26],可降低蛋白尿。
4 驗案舉隅
4.1 病案1 患者,女,65歲,2021年10月20日初診。主訴:反復口干乏力10年,雙下肢浮腫3年。患者10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口干乏力,完善相關檢查后診斷為2型糖尿病,予二甲雙胍、瑞格列奈治療,未系統監測血糖。3年前出現雙下肢凹陷性水腫,尿常規示尿蛋白(+),外院診斷為“糖尿病腎臟病”,具體治療不詳,療效欠佳。刻下癥見:神疲懶言,倦怠乏力,口干舌燥,腰酸腰痛,大便偏干,小便泡沫量多,夜尿4~5次,雙下肢輕度浮腫。舌暗紅,苔薄黃,脈弦細。尿常規示:尿蛋白(2+),尿糖(3+);24h尿蛋白定量:2.05 g;血生化示,血肌酐:112.3μmol/L,尿素氮:7.5 mmol/L,尿酸:307.3 mmol/L;糖化血紅蛋白:7.5%。空腹血糖:6~7 mmol/L,餐后血糖:8~11 mmol/L。腎穿刺活檢符合DKD Ⅳ期。西醫診斷:2型糖尿病;糖尿病腎病Ⅳ期。中醫診斷:消渴;消渴病腎病。辨證:脾腎兩虛,陰火內盛。治法:補脾益腎,散泄陰火。方選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加減,處方:生黃芪30 g,黨參15 g,黃芩10 g,黃連15 g,葛根30 g,升麻6 g,茯苓20g,漢防己10g,女貞子20g,墨旱蓮20g,芡實15g,金櫻子15g,穿山龍20 g,青風藤15 g,桃仁10 g,丹參10 g,土鱉蟲10 g,石膏3 g。28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
2診:2021年11月18日,訴自覺體力改善,雙下肢水腫較前減輕,近日因搬重物導致腰酸腰痛等癥狀較為突出,納寐可,小便有泡沫,大便調。舌暗紅,苔薄黃,脈弦細。復查尿常規示:尿蛋白(2+),尿糖(2+);24 h尿蛋白定量:1.83 g。患者目前腰酸腰痛等癥狀突出,故予上方加牛膝20 g,蘇木15 g,伸筋草15 g。28劑,煎服法同前。
3診:2021年12月17日,訴諸癥悉減,仍有少許口干口渴等癥狀,飲水可解。舌暗紅,苔薄白,脈細。尿常規示:尿蛋白(+),尿糖(+);24 h尿蛋白定量:1.02 g;糖化血紅蛋白:6.9%。予2診方加天花粉15 g,枸杞子20 g。28劑,煎服法同前。
按語:本案患者為中老年女性,患2型糖尿病10年,診斷為DKD 3年。以口干乏力、水腫為主要癥狀,輔助檢查示尿蛋白、尿糖陽性,血肌酐、尿素氮指標升高等。患者消渴日久,脾腎俱虛、氣津兩傷,故見神疲乏力、口干舌燥之癥。脾腎虧虛又可致氣化失司、水濕內停,故見雙下肢水腫;“火與元氣不兩立”,氣虛化火、陰虛生熱,致陰火彌散于內,故見口干口渴、大便干結等,病癥相合、四診合參,辨證為脾腎俱虛、陰火內盛證,治以補脾益腎、散泄陰火。方中黃芪、黨參、升麻補脾益氣,升陽發散;女貞子、墨旱蓮滋陰益腎,固攝精微;陰火蒸騰于內、熏灼三焦,故以黃芩、黃連、葛根、石膏等以奏清上達下、逐熱瀉火之功;陰火久積、日久致痰瘀而生,使腎臟發生纖維化等病理改變,故應用桃仁、土鱉蟲等以活血和血,消積伏瘀;患者年逾六旬,陰氣自半、精血虧虛,腰酸腰痛及夜尿等癥狀較為突出,故加芡實、金櫻子、女貞子、墨旱蓮等滋陰益腎,固攝填精。同時,王暴魁教授常結合現代藥理學研究,針對機體所反應的癥狀,對癥治療,如防己、茯苓、穿山龍、青風藤等藥物具有改善水腫及蛋白尿的作用。2診、3診時患者諸癥悉減,考慮病機未變、方證相合,故守前方繼服,隨癥加減。如腰酸腰痛突出,加牛膝、蘇木、伸筋草以舒筋活絡,通經止痛;口干口渴明顯,加天花粉、枸杞子以滋陰瀉火,生津止渴。
4.2 病案2 患者,男,63歲,2020年9月21日初診。主訴:間斷口干乏力10余年,泡沫尿3年。患者10余年前出現口干乏力,于當地醫院就診查血糖升高(具體不詳),確診為2型糖尿病。平素注射胰島素諾和靈30R,早晚餐前各20 U/次,口服二甲雙胍(0.5 g/次,2次/d),未監測血糖。3年前發現小便有泡沫,查尿常規示尿蛋白(+),診斷為DKD,規律服用氯沙坦鉀片(0.5 g/次,3次/d),療效欠佳。刻下癥見:時有口干乏力,小便泡沫增多,量少色黃,自覺視物模糊、眼睛干澀,五心煩熱,納可眠差,大便1次/2~3 d。舌暗紅,苔薄黃,脈細數。輔助檢查示,尿微量白蛋白:421 mg/L,糖化血紅蛋白:7.2%,空腹血糖:7.6 mmol/L。眼底:雙眼視盤邊界清楚,視網膜靜脈輕度迂曲、擴張,視網膜表面可見散在片狀出血,黃斑中心凹反光存在。西醫診斷:2型糖尿病;糖尿病腎臟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雙眼)。中醫診斷:消渴;消渴病腎病;消渴目病。辨證:脾腎虧虛,陰火內盛。治法:補脾益腎,散泄陰火。方選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加減,處方:黃芪30 g,麩炒白術15 g,枸杞子15 g,生地黃15 g,女貞子20 g,墨旱蓮20 g,菟絲子15 g,三七粉6 g,蒲黃10 g,酸棗仁20 g,葛根20 g,黃連10 g,雞血藤15 g,羌活10 g,升麻10 g,防風10 g,柴胡10 g,牡丹皮10 g,赤芍10 g,黃柏10 g。28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
2診:2020年10月19日,訴視物仍有模糊,口干乏力、五心煩熱等癥狀有所好轉。舌暗紅,苔薄黃,脈細數。輔助檢查示,尿微量白蛋白:386 mg/L,糖化血紅蛋白:6.9%。予前方加青葙子15 g,密蒙花15 g。28劑,煎服法同前。
3診:2020年11月18日,訴諸癥悉減,近日因瑣事與他人爭吵致夜寐不安、入睡困難加重。舌暗紅,苔薄黃,脈細數。輔助檢查,尿微量白蛋白:321 mg/L,糖化血紅蛋白:6.5%。予2診方加合歡花15 g,首烏藤10 g。28劑,煎服法同前。
隨診至今,患者繼守3診方,隨癥加減。未有明顯不適,尿微量白蛋白持續小于300 mg/L,糖化血紅蛋白保持在正常水平。
按語:本案患者診斷為DKD 3年,中醫辨證為脾腎虧虛,陰火內盛證,故以補脾益腎、散泄陰火為主。陰火有心火、肝腎相火及氣機失調之火之分,故在辨治陰火的過程中,王暴魁教授根據患者癥狀及病位的偏向性不同,謹察病機,靈活加減用藥。患者病程日久,腎水虧虛,難以上承以制約心火,造成心火獨亢而發為陰火。陰火獨盛,耗氣傷陰,故可見口干乏力、五心煩熱之癥;心火獨亢、煎灼腎陰,致腎水虧虛,精關不固則見蛋白尿;心火上灼目絡,熱迫血行致脈絡爭張、破血逆行故使視網膜發生片狀出血等病理改變;心火獨盛、陽不入陰故見夜寐難安、入睡困難等心神不寧之癥。在治療上,以補脾益腎、散泄陰火,尤以清泄心火為主。方中黃芪、炒白術、女貞子、墨旱蓮、菟絲子健脾益腎,固攝精微;生地黃、牡丹皮、赤芍、黃柏滋陰瀉火,心腎并調,使君相二臟各安其位、各司其職;而患者出現視網膜出血等病變,乃熱迫血絡所致,故以三七、蒲黃、雞血藤涼血止血,通絡逐瘀。此外,王暴魁教授在散泄陰火的基礎上應用羌活、防風、升麻、柴胡等風藥加減,一方面升陽散火以助陰火發越;另一方面輕清走竄又可疏散瘀結以開通眼中玄府。患者在2診、3診時出現視物模糊及入睡困難等不適,故應用青葙子、密蒙花、合歡花、首烏藤等明目瀉火、養心安神,收獲良效。
5 結 語
糖尿病腎臟病是一種臨床常見病。中醫學認為火邪與本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故多施以清熱瀉火之法論治此病,但臨床療效欠佳。王暴魁以“陰火”理論為切入點,通過探討陰火與DKD二者在起病來源、證候要素及病機特點等方面之間的相關性,認為陰火導致了DKD的發生發展。這一思路摒棄了火邪中實火、陽火導致DKD發生的固有觀點,進一步擴大了“火邪致病”的病機內涵,彌補了“陰火”理論論治本病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