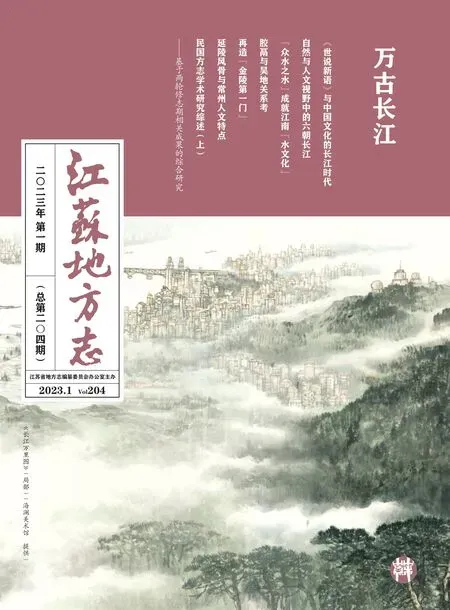胡福明主持首輪《江蘇省志》編纂散憶
◎張乃格
(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江蘇南京210004)
1988年9月6日,江蘇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江蘇省志》編纂方案,正式啟動省志編修工作。1990年4月17日,省政府決定,胡福明擔任《江蘇省志》總纂。在此期間,我于1989年上半年調入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1992年起先后任省志處副處長、處長,直到2008年初首輪省志編纂工作基本完成,近20年間始終在省地方志辦公室盛思明、汪文超、王建中等主任直接領導下,胡福明總纂主持、指導下工作,深切感受到一個哲人的風骨、學者的本色。
一、“編志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
江蘇歷史悠久,卻建省較晚,直到清康熙六年(1667)才從江南省分立出來,省志編修的歷史更短。康熙中期和雍正末乾隆初兩修省志,但編修的都是江南省(包括今江蘇省、安徽省、上海市)的通志,書名都題作《江南通志》,而不叫《江蘇通志》或《江蘇省志》。直到清末宣統期間,才著手江蘇通志的編纂。可惜不久辛亥革命爆發,繼而民國肇造,軍閥連年混戰,接下來又是日軍全面侵華,烽火連天,民生凋敝,時局維艱。江蘇省志編修幾起幾落,有人戲稱之為起步“大張旗鼓”,邁步“偃旗息鼓”。直到1945年日本敗亡,也只形成一大摞稿本,史稱《江蘇通志稿》,一稱《江蘇省通志稿》。可以說,江蘇省志的編修毫無經驗可以借鑒,1988年上馬的首輪《江蘇省志》是江蘇歷史上填補“空白”的創舉。當時參與編修工作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本單位、本系統、本行業的“活字典”和“筆桿子”,是編纂《江蘇省志》的中流砥柱。其中也不乏經歷過1949年后新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熏蒸,形成一定程度“左傾”思維的同志。譬如,有一部專業志第一章為《貨幣》,根據地方志橫排豎寫、類為一門的原則,通常可以劃分為實物貨幣、金屬幣、紙幣幾節,但編修該專業志的一位老同志強烈堅持,此章必須分設“反革命貨幣”“革命人民貨幣”等節。在今天看起來這是再簡單明白不過的事情,在當時卻爭論得不亦樂乎。加之地方志在體例結構、收錄標準、記述原則等方面有一些特殊要求,省志編纂究竟該從何處入手,一時難倒了一大堆“秀才”。另一個擺在大家面前的現實問題是,江蘇省志的編纂在全國起步相當晚,如何兼顧編纂進度與志書質量,矛盾也比較突出。
面對重重困難,胡福明總纂舉重若輕,始終強調兩條:一是解決辦法要在修志實踐中不斷摸索,一旦驗證有效,立即推廣落實。他主張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士做,各專業志編纂班子要認真學習地方志基本常識,充分尊重省方志辦專家們的意見。省方志辦專家也要認真學習相關專業知識、行業歷史,充分聽取各系統“行家里手”的意見。凡是在編纂實踐中經過充分溝通、反復商量,被修志專家、行業專家一致肯定的,一定要堅持下去,推廣開去。凡是修志專家、行業專家都否定的,要進一步研究,力爭早日取得共識。
二是強調找準地方志的“靈魂”,牢牢抓住編史修志的“牛鼻子”不松手。他多次提出,實事求是是地方志的靈魂,存真務實是編史修志工作的生命。在早期省志總纂座談會上,他就強調:“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充分保證志書的科學性,全面提高志書的學術質量和品位。”在《政府志》稿評審會上,他聯系隔代編史、當代修志的特點說:“當代人修自己的志有它的好處,就是熟悉情況。但也有它的特殊困難,就是怎樣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地寫成就、寫特點,也要實事求是地記述教訓。用兩分法寫志,志書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在首輪省志編纂總結座談會上,他聯系自己一二十年省志總纂的經驗,由衷地感嘆:“我有個看法,志是記,完整準確地老老實實記下來,不評價好壞,符合事實,就是志。編志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忠于事實。歷史上大史學家秉筆直書,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差不得,好不得;重不得,輕不得;多不得,少不得;亮不得,暗不得;大不得,小不得。編地方志是要有勇氣的,敢講真話實話,求真務實。當代修志,求真務實更難,實事求是更難。”并一再強調:“志的生命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當代修志更要注意求真務實,實事求是,講真話、實話,秉筆直書。”
針對不少專業志記“舊社會”國民黨的罪行和“新社會”共產黨的成就千言萬語,記國民黨的成就、共產黨的失誤惜墨如金,甚至“不著一字”,他強調:大家受黨教育多年,對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感情,對國民黨懷有刻骨的仇恨,因而我對志書揭露“舊社會”的黑暗、歌頌“新社會”的輝煌一點也不擔心。我所擔心的,是“舊社會”國民政權的成就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反映,“新社會”我們自己的失誤能不能得到實事求是的記載,而且記載比較到位。對志書記載改革開放后的成就、“文化大革命”前的失誤我一點也不擔心,擔心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就與改革開放后存在的問題能不能得到實事求是的反映,而且反映比較到位。史學界都知道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到抗日戰爭以前是民國的“黃金十年”。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現在已經幾十年了,但南京的城市布局與交通框架,基本上還是民國時期定下的。國民政府只有罪行沒有成就,“黃金十年”如何解釋?南京的城市規劃與布局如何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難道沒有失誤?沒有失誤,各方面都很好,那還干嘛要進行改革?既然要進行改革,那就說明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那樣的問題不少就是失誤。修志工作就是要把這些問題、失誤,如實地記載下來,以給后人留下教訓和警戒,否則就失去了修志的意義。
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國當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在首輪《江蘇省志》編纂中反復強調的實事求是、存真務實、秉筆直書的地方志編纂原則,可以說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理論在新方志編纂中的成功實踐。在他主持下,經過省直機關100多個廳局、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軍隊系統上萬修志工作者20年的不懈努力,首輪《江蘇省志》于2009年圓滿完成。全書分設92卷,成書118冊,總計7500余萬字,在江蘇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統地記載了兩千多年自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史。《財政志》榮獲全國地方志優秀成果一等獎,《方言志》《綜合經濟志》榮獲全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氣象事業志》《冶金工業志》《商檢志》《價格志》《電力工業志》《檔案志》《海涂開發志》獲得全省地方志系統成果優秀獎,《綜合經濟志》《軍事志》《社會科學志》獲得特別榮譽獎,《鄉鎮工業志》《衛生志》《土地管理志》獲得特等獎。
二、官書不能“闖紅燈”
胡福明曾經長期擔任江蘇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2018年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他既有哲人的深邃,又有大局意識、全局胸懷和政治擔當。在指導首輪省志編纂中,他常常站在全國乃至世界的高度,對一些看似“前衛”的觀點、“新鮮”的事物,另辟蹊徑,提出與眾不同的觀點,十分具有戰略前瞻性。當時有個市提出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的目標,媒體上宣傳得十分熱鬧。胡福明總纂卻說,國際化大都市不僅要有超群的政治、經濟、科技實力,而且要與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家發生較為密切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人口交流關系,有著國際化影響,否則名不副實。比如,全市人口中,外國人的比例能占到多少?有多少跨國公司的總部設在這個市?如果外國人的比例連1%都不到,全市連一個跨國公司的總部都沒有,大街上看到幾個外國人大家都覺得稀奇,還叫什么國際化大都市?況且,江蘇離上海那么近,如果上海成了國際化大都市,在江蘇再建設一兩個國際化大都市,布局上也不合理,國家不可能這么安排。宣傳部門根據市委的要求這樣宣傳未嘗不可,那是他們的職責。但志書就不能這樣記,因為這違背政治經濟學規律,要鬧國際笑話。
胡福明思維敏捷,善于獨立思考。省志編纂初期,大多數專業志都收集了數量眾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省委、省政府領導在江蘇各地視察的照片,有的還征集到不少領導人的題詞,準備放在志書卷首彩插的顯著位置,以為志書增光添彩。對此,他嚴肅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歷來主張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新編地方志不能走傳統史書“精英史”“帝王將相史”的老路。再說,省志的主修單位是省政府,省委書記、省長到自己的地盤上檢查工作、處理問題,這是他們的本分。自己的志書稱自己的領導正常履行職責為“視察”也不合適,這拉大了領導與人民的距離。在胡福明總纂的堅持下,首輪省志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所有專業志一律不收領導人的標準照;領導的工作照,只有當他和一線教師、工人、農民等一起出現時,才可以少量選收。直白點說,首輪省志領導人的照片入志,是“沾了人民的光”。有一部專業志打算收錄一位副國級領導的題詞,我們根據上述原則提出不同意見,這個廳的廳長親自打來電話,說是收錄這位領導的題詞是他們廳黨組集體研究形成的正式決議,不好改變。在征得省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汪文超同意后,我特地向胡福明總纂請示。他態度非常明確:告訴他們,就說我說的,不能破這個例,讓他們把題詞撤下來。事后他私下里跟我講,其實他和那位領導很熟,并對其高超的領導藝術十分欽佩。但具有高超領導藝術的政治家,不一定是藝術水平高超的書法家。當時我不太明白,后來調來那幅題詞的影印件一看,書法水平確實一般。
省志啟動階段,胡福明總纂每到一個單位,總是苦口婆心地跟這些單位的領導講,事業發展主要靠人才。編纂地方志的過程就是梳理事業發展脈絡、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可以更好地服務現實。你們要有意識地選擇有培養前途、有發展潛力的年輕人參加修志。等專業志編纂任務完成了,他們就成了行業專家,這對他們今后的發展、對單位事業的發展都有好處。當時省直機關有碩士學歷的人比較少見,他聽說省灘涂局把剛入職不久的研究生唐正東調到《灘涂開發志》編纂辦公室,并擔任副主編,非常高興,表揚省灘涂局領導有眼光。《灘涂開發志》出版后,唐正東果真成了系統的骨干,先后擔任省灘涂開發投資公司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公司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沿海開發集團公司黨委委員、董事、副總經理,省鹽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董事。曾任省農業農村廳廳長楊時云、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副廳長宋如亞,現任省黨史辦一級巡視員萬建清等,也都有過類似的省志編纂經歷。
對于志稿有可能涉及憲法、人權、保密等話題的內容,胡福明總纂有敏銳的政治嗅覺。他常說,敏感話題、泄密問題是一道“紅線”,無論如何也不能碰。省志有一部專業志,送審稿中詳細記載了全省兵工廠的地理位置、產品型號與重要年份的產量等內容。志稿評審時,胡福明指出,有些兵工廠的產品主要是半自動步槍、手榴彈、子彈等“大路貨”,這些東西早就人盡皆知,根本算不上秘密。有些軍工單位研制的雷達等尖端武器,對于臺灣情報部門來說也不是什么秘密,人家一清二楚。但法律有規定,紀律有要求,我們的志書必須妥善處理。你們國防科工辦要擔起責任,保密部門出具審查通過的報告,你們一把手主任簽字,才能送到我這里。另一部專業志送審稿中系統收錄了民國時期外國使領館的資料,包括這些使領館的地理位置、館舍布局、占地面積、建筑面積,甚至產權登記文獻等,資料十分翔實。胡福明總纂說,志書是官書,具有法律效力。書中的資料顯示,這是人家的館產。我們這樣寫,會不會產生負面效應?人家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資料當作證據,提起訴訟,追討館產?地方志應當實事求是沒錯,但也不能授人以柄,引火燒身,要把一切可能有隱患的“地雷”找出來,統統清除掉。
三、編史修志如同“做課題”
胡福明總纂原本是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骨子里就是個學者。他常講,省志專業志的編纂如同“做課題”,一部專業志就是一個單獨的課題。不要小看專業志編纂,全省這項事業的來龍去脈、興衰起伏是怎樣的,興衰起伏背后的深層次背景是什么,如何才能長盛不衰?把這些問題搞明白了,不但編了一本好志,完成了一個好課題,而且理清了事業發展的好思路。博古通今,古為今用,利國利民,造福子孫,功德無量,善莫大焉。
首輪省志各專業志大多由相關委辦廳局承編,其中有些專業志的主編由廳長領銜。這在修志早期,對于協調全廳內設處室之間的關系,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到后期統稿階段,其弊端也逐漸顯現。廳長掛主編,其他副廳長掛副主編,而真正負責志稿撰寫、全書統稿的同志只能“叨陪末座”,有的甚至連副主編、主編助理也輪不上,只能署個編輯。沒有主編名分,統稿名不正言不順,有時候正確的意見也不一定得到采納。而廳長、副廳長平時“日理萬機”,有的連開會的講話稿都要秘書準備好,哪有時間親自撰寫志稿、完成全書統稿?胡福明總纂認為廳長兼任主編的做法不太合適,稱之為“主編不沾邊”。他說,省志專業志的編修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設立專業志編纂委員會,主任由行政領導擔任,主要負責調配人手、落實經費、確立大計方針;一條腿是設立專業志主編,由行業專家擔任,主要負責篇目制定、資料搜集、志稿撰寫、字斟句酌。兩條腿不能并成一條腿,否則只能蹦跶,寸步難行。主編不是榮譽,是責任和擔當。我們常講,文責自負。聽說有部志書出版時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錯排成了“建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重大疏忽。如果行政領導掛了主編,就不僅要負領導責任,還要負直接責任,你干不干?1994年,省志第一部專業志《陶瓷工業志》正式出版,他在志書首發式講話中說:“領導主要抓修志工作中的大事、難事,具體業務要依靠修志人員。”又說:“修志工作專業性很強,要經過專門培訓,要在實踐過程中逐步熟悉業務,所以人員一旦確定下來,除個別特殊情況外,不能輕易變動,尤其是主編、副主編不能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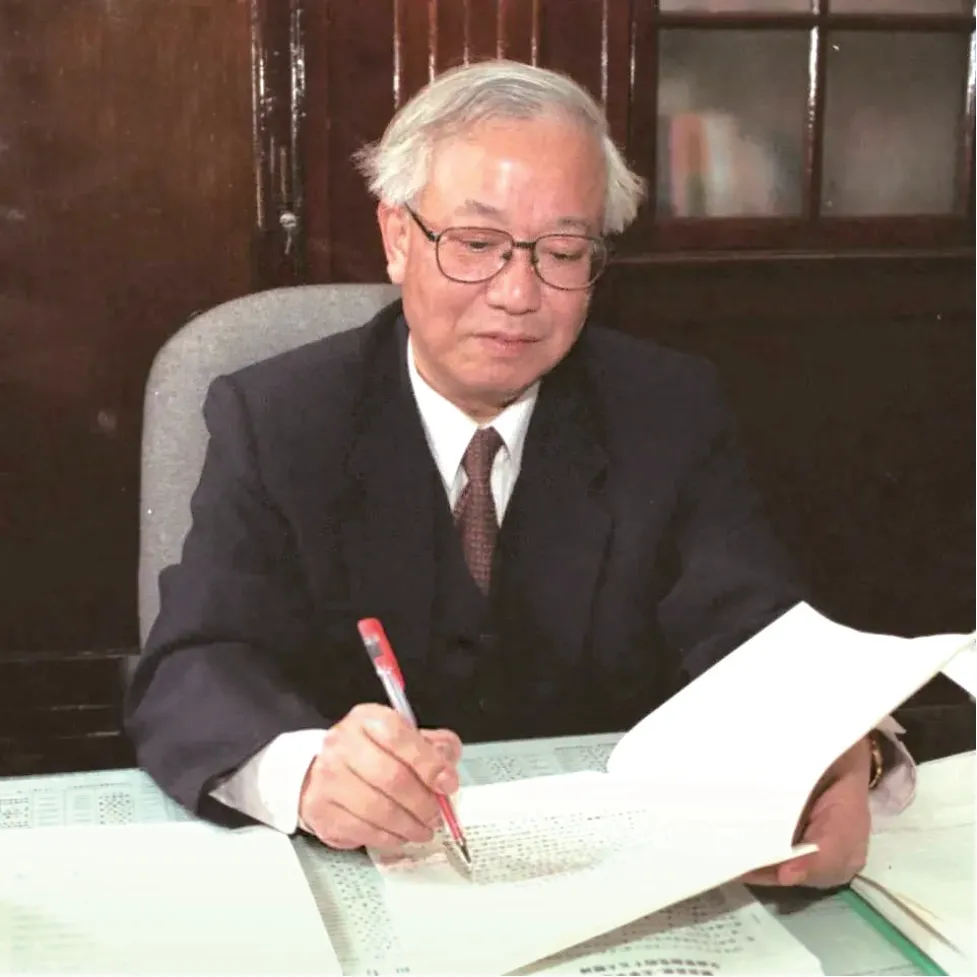
胡福明工作照
和一般廳局長比起來,胡福明總纂當然事情更多,工作更忙,時間更緊。但他在就任省志總纂后,只要能擠出時間,總是親臨相關專業志承編單位,或委托郁冠、吳镕、樊發源、姜其溫、蔡秋明、邱路、葉春生、熊人民、汪文超等副總纂,四處宣傳發動、“煽風點火”。從早期的工作協調會,到中期的志稿評審會,再到后期志書出版發行會,他都盡可能參加。而且他出席會議必定發表講話,但從來不要省方志辦提供講話稿,都是即席講話。他講話時慢條斯理,卻口若懸河,字字珠璣,無不切中志書記述的專業實際,具有極強的指導作用。由于省志有七八千萬字的規模,讓總纂一個人從頭到尾仔細審讀,不太現實。因此在多年的修志實踐中,我們逐漸形成一種頗為默契的工作模式:當一部志書進入最后終審環節,我們先向他匯報志稿的基本情況,包括該志編修過程、全書總體框架結構、記述的主要內容、志稿評審會上專家們的主要意見、后期修改情況、目前的質量評估,以及書中的重點和難點等。對于一些疑難問題,我們往往預設幾種建議方案,供他參考。聽了我們的匯報,他總是讓我們留下志稿,等有空時他要“翻一翻”。通常半個月左右,志稿的終審意見可以簽發出來。我們取回志稿,總能發現他不但簽有具體終審意見,而且大部分志稿確實“翻”了,不少稿子上留有他的批注,其中看得最多的是篇目、概述和重點章節。
胡福明總纂是我領導的領導,我是他部下的部下。但在他那里,卻常常把我當成學生看待,鼓勵我利用地方志海量的地情資料,做些學術研究。21世紀之初,《新華日報》等媒體持續開展“新世紀江蘇人新形象”的討論,一市一期,每期一版。討論的內容,實際上是全省及各地人的性格特征,諸如爭先領先率先精神、開拓創新意識、開闊豁達胸懷、團結協作氛圍、求真務實作風、民主法制觀念等。但人們的性格特征不但有區域化特征,還有模式化、群體性、傳承性、穩定性等特征。面對同樣一件事,同一地理單元往往人無分貴賤,地無分南北,時無分古今,人們的基本態度往往大體一致,短時間內一般不會受到政府號召、提倡的影響。顯而易見,新世紀江蘇人新形象討論中所涉及的新江蘇人、江蘇各地人的性格,并不是這些人固有的,而是各級黨委、政府賦予他們的,帶有鮮明的期許元素、美愿印記。為此,我萌生出著手江蘇民性研究的想法。胡福明總纂聽了后很高興,當即表示:“這個選題好!你好好做,做好了,我來給你寫序。”2003年,我的《江蘇民性研究》脫稿,后來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付印前,胡福明總纂讓我把全書清樣送過去,他花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通讀了書稿,并欣然作序。他在序中寫道:“作為特定地區的居民在世代生產、生活中長期形成的一種潛意識,民性是區域內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總和,因此較之區域文化研究中主要體現為區域進步動力的文化精神、文化傳統,民性更加具有普遍性。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目前在我國尚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基本上還處于空白。開展對于民性的研究,努力認識人們在長期實踐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優良品質、傳統和作風,以便于人們更加自覺地將這些品質、傳統、作風傳承下去,弘揚開來,同時將那些落后于時代,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惰性因素展示出來,以便于人們認識其本質,看清其危害,并最終摒棄它們,不斷提高國民的自身素質,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擺在區域文化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個迫切任務。”對這一選題的重要意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時還從民性研究史的角度,對書中有關崇尚文化的社會心理、清雅靈秀的審美情趣、沉穩務實的處事原則等江蘇民性的提煉,和資料搜集等基礎性工作等方面,作出高度評價。說來慚愧,我自認為學術水平并沒有達到胡福明總纂評價那樣的高度,胡福明總纂之所以這樣評價,實際上主要寄托了學術大師對于晚輩學生的深情期待。